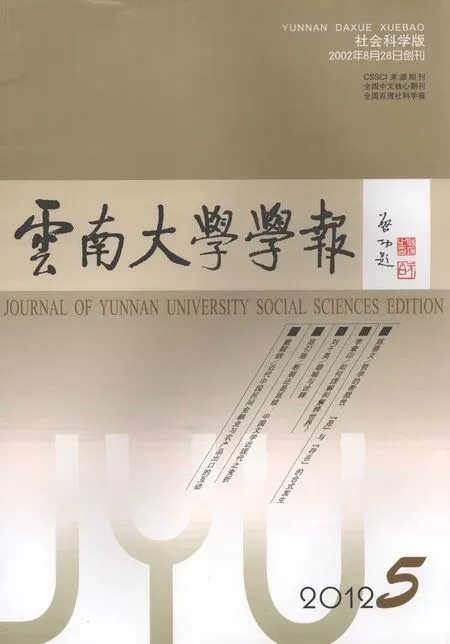乐府曲调的演化及其对乐府文学发展的影响*
王志清,杨基燕[.吉首大学,吉首 46000;.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北京 00048]
乐府曲调的演化及其对乐府文学发展的影响*
王志清1,杨基燕2
[1.吉首大学,吉首 416000;2.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北京 100048]
乐府曲调;徒歌;乐;变曲;乐府文学
乐府曲调在其流传过程中所产生的音乐演化和变异现象,大约有三种形态:徒歌演化为乐歌,本曲演化出变曲,旧曲演化为新声。利用歌曲的和、送声,成为曲调演化的主要音乐路径;此外,亦有“摘唱”和“新翻”等方式。曲调演化是音乐新旧递变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一定历史时期音乐文化活动的产物。曲调演化对乐府文学发展的影响体现在:提供了歌辞创作的曲调依据;产生出一批著名的同源性曲调,拓展了乐府文学的空间;实现了旧曲的新声化,促成旧曲体式的新变;丰富了乐府歌辞的风格。
乐府是我国古代重要的音乐类型之一,其兴盛期在汉魏六朝;至唐,燕乐崛起,乐府艺术所依托的清乐总体衰微,但部分曲调仍然传唱于宫廷和民间。乐府音乐的变迁大致经历了汉魏相和旧曲、南朝清商新声、唐世所传清乐等阶段,在乐府史的每一阶段以及跨阶段的音乐流传活动中,都存在着不同形态的曲调演化和变异现象。曲调演化既是音乐新旧递变的结果,也是制乐者进行的艺术改造活动。对曲调演化现象的揭示,可从微观层面增加描述乐府艺术嬗变之迹的清晰度。本文以曲调个案为基础,主要研究乐府曲调演化的形态、路径、动力和条件,以及曲调演化与乐府文学创作的关系,希望有益于乐府学的深入开展。
一、乐府曲调演化的形态和路径
乐府曲调演化的起点在哪里?笔者认为,应始于徒歌阶段。《尔雅·释乐》:“徒歌谓之谣。”[1](P2602)一般将无丝竹之类乐器伴奏的歌唱称为“谣”。《宋书·乐志》:“夫歌者,固乐之始也。……故圣人以五声和其性,以八音节其流,而谓之乐……”。[2](P548)“歌”即“徒歌”,是“乐”的源头;“歌”经过“五声”的规范、“八音”乐器的节制,曲调定型,即成为“乐”。
民间徒歌并非完全没有乐器伴奏。《宋书·乐志》在记叙晋宋时期兴起的吴声曲调后,有一句总结,“凡此诸曲,始皆徒歌,继而被之弦管”,[2](P550)显然,“徒歌”的特点只是不“被之弦管”,即没有管弦乐器的配合罢了。而在古代乐器史上较早出现的击节乐器,是可以配合“徒歌”的。民间歌唱中借助器物打节拍亦很普遍,如《淮南子》:“今夫穷鄙之社也,扣盆拊瓴,相和而歌,自以为乐也。”[3](P1236)《宋书·乐志》记载古时善歌者秦青“抚节悲歌”,一般理解为用手打着节拍唱歌。然而,汉代起于街陌讴谣的“相和歌”,其演唱形式为“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2](P603)这里的“节”显然是指一种乐器。“节”在“八音”中属于“革”,西晋傅玄有《节赋》。古乐器又有“节鼓”,《通典》卷一四四:“节鼓,状如博局,中开圆孔适容其鼓,击之以节乐也”。[4](P752)因此,不能排除秦青“抚节”悲歌或有“节”的伴奏。南朝清商新声中的“西曲”,流行于长江流域中部和汉水流域的广大地区,西曲《杨叛儿》:“七宝珠络鼓,教郎拍复拍”,《共戏乐》:“时泰民康人物盛,腰鼓铃柈各相竞”,歌词描写的应该是民间歌唱场景,其中出现的鼓、腰鼓、铃等属于击节乐器。
徒歌也已形成基本的声调。古时歌者韩娥善于“曼声长哭”,这种特殊的“歌哭”想必已形成旋律。南朝新声中的吴声曲调,如《阿子》《欢闻》《督护歌》等创调本事的记载中,皆曰“后人因其声”、“后人演其声”,这个“声”正是徒歌之声调,是演化为乐歌的音乐基础。击节乐器的伴奏以及简单的旋律声调,说明徒歌已具备初步的音乐规定性,是乐歌的初始形态,只是没有丝竹之类管弦乐器的节制,徒歌的声调并不定型。
“始皆徒歌,既而被之弦管”是乐府创调的一个基本方式。“被之弦管”从表面看是指配器,但通过配器,徒歌声调得以定型、规范,成为有章曲之歌。《乐府诗集》引《韩诗章句》曰:“有章曲曰歌,无章曲曰谣。”[5](P1165)“被之弦管”和声调的定型,也正是从徒歌到乐歌的演化。在这个音乐发展过程中,既保留了徒歌重要的音乐特点,也产生了一定的声调变异。
“和声”的广泛运用是民间徒歌的音乐特点。汉魏时代流行一种“但歌”,其演唱形式为“无弦节,作伎,一人唱,三人和”,[2](P603)“三人和”即是和声帮腔。汉灵帝中平年间,京都传唱《董逃歌》,“承乐世,董逃;游四郭,董逃;蒙天恩,董逃;带金紫,董逃;行谢恩,董逃;整车骑,董逃……”,这是徒歌的“逐句和声”。当汉世“街陌讴谣”发展为相和曲后,部分保留了“逐句和声”。如《乐府诗集》收录的魏文帝《上留田行》,从首句起,每一句歌辞后皆有“上留田”和声;谢灵运《日重光行》,则在每一句歌辞前有“日重光”和声。吴声、西曲的和、送声位置不同于相和歌,固定为前有“和”,后有“送”。南方徒歌如《阿子》《欢闻歌》在民间传唱时往往“歌毕辄呼”,这一音乐特点最终发展为吴声、西曲的曲式结构,今存吴声、西曲多数有和、送声。总之,乐府曲调中的“逐句和声”或固定位置的和、送声都源自徒歌。
由于古乐的失传,我们对徒歌到乐歌演化过程中发生的曲调变异,只能依靠歌辞体式的对比分析得来。《乐府诗集》“杂歌谣辞”收录江左以来的民间徒歌体式丰富,包括五言四句、五言二句以及三言七言相间的杂言体等,其中,以三言句式发端的歌辞颇为常见。三言句式节奏短促,可产生类似呼告和感叹的抒情效果。《乐府诗集》收录的吴声《团扇郎歌》,据本事记载,是晋中书令王珉嫂婢谢芳姿所制。芳姿即兴而唱的两首歌曲皆为三五五体式,其一:“团扇郎,辛苦互流连,是郎眼所见”,其二:“团扇郎,憔悴非昔容,羞与郎相见”。[5](P660)但这首徒歌经“被之管弦”发展为乐歌后,歌辞体式全部改变为整齐的五言四句,如其中一首:“青青林中竹,可作白团扇。动摇郎玉手,因风托方便”。包括《团扇郎》在内的吴声歌谣在发展为乐歌后,多样化的歌辞体式几乎整体消失,五言四句成为占绝对地位的基本体式,体式上的统一变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徒歌演化后的声调变异。
某些乐府曲调在其流传过程中,又从中演化出一支或数支新的曲调,即从本曲中演化出变曲。“变曲是指从旧有曲调中变化出来的新声,故古人往往以新声变曲连称”。[6](P57)汉武帝时代的宫廷音乐家李延年善为新声变曲,他利用张骞从西域带回的《摩诃兜勒》新制了横吹新声二十八解,所谓“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5](P309)南朝梁武帝精通音乐,《乐府诗集》引南陈音乐文献《古今乐录》:“梁天监十一年冬,武帝改西曲,制《江南上云乐》十四曲,……”[5](P726)李延年如何“因”胡曲造新声,没有文献可考,但梁武帝如何“改”西曲制《江南弄》,却有踪迹可寻。《古今乐录》记载《江南弄》组曲使用“三洲韵”。《三洲歌》是西曲曲调之一。梁武帝天监十一年,法云应梁武帝之命,将《三洲歌》原来的和声“啼将别共来”改为“三洲断江口,水从窈窕河傍流。欢将乐,共来长相思”,成了长短参差的杂言体式。“据许云和的研究,《江南弄》标明的“三洲韵”,实质是指声调上采用了法云所改西曲《三洲歌》的“和声”,所以,组曲歌辞才会形成为七言、三言结合之体式。[7](P441)故此,梁武帝借助“和声”以“改”西曲。
文献记载南朝吴声、西曲的创调中较多存在变曲方式,明确具有本曲、变曲关系的曲调包括:吴声《子夜歌》与其系列变曲,《懊恼歌》与《华山畿》,《石城乐》与《莫愁乐》,《三洲歌》与《采桑度》等。[6]《子夜歌》是南朝最著名的新声曲调之一,其“变曲”数量居新声之首。《乐府诗集》在《子夜歌》的题解中,征引唐吴兢《乐府解题》:“后人更为四时行乐之词,谓之《子夜四时歌》,又有《大子夜歌》《子夜警歌》《子夜变歌》,皆曲之变也”。[5](P641)本曲到变曲经由怎样的音乐路径?据《古今乐录》:“《子夜变歌》前作持子送,后作欢娱我送。《子夜警歌》无送声,仍作变,故呼为变头,谓六变之首也。”[5](P655)仔细分析这段话,似乎是讲“作变”与“送声”的关系。“作变”是一种特殊的音乐处理方式,多数“作变”是针对“送声”进行的。但并非绝对。没有“送声”仍可“作变”,只是终究属于特殊情况,故没有“送声”而仍“作变”的《子夜警歌》就被称为“变头”。从文献对《子夜歌》诸变曲“送声”的专门记载,以及“作变”与“送声”的关系,大致可判断,“变曲”之变与“送声”有一定关系。
再来看吴声曲调《懊侬歌》及其变曲《华山畿》。《乐府诗集》收录《懊侬歌》14曲,其中12曲五言四句,2曲例外。在例外的两曲中,其中一曲曰:“懊侬奈何许,夜闻家中论,不得侬与汝”,五言三句体式,歌辞中含有“懊恼”二字。由于吴声、西曲曲名往往包含在和、送声辞中,因此,这一曲很可能就是《懊侬歌》的送声。变曲《华山畿》今存25曲,其中23曲属于三句体歌辞,据此判断,变曲《华山畿》是由《懊侬歌》的送声演化而来的。
上述徒歌到乐歌、本曲到变曲的演化,大致发生在乐府史的同一阶段和同一音乐类型内部,对歌曲和、送声的利用,成为这两类曲调演化的主要音乐路径;如果跨越不同阶段和不同音乐类型,曲调演化的音乐路径更为多样。汉曲《王明君》本为琵琶曲,西晋石崇将之改变为舞曲,并造了新辞。据张永《元嘉技录》,宋文帝元嘉年间宫廷音乐中有《王明君》一曲。又据王僧虔《大明三年宴乐伎录》,宋孝武帝大明三年,《王明君》一曲“有閒弦及契注声,又有送声”。[5](P425)“送声”是南朝新声的曲式特点,显然,原本属于相和旧曲的《王明君》,在刘宋时代增添了“送声”,已经“新声化”了。又据刘宋谢庄《琴论》记载,《王明君》又有琴曲的形式,并且分为平调、清调、蜀调、吴调、胡笳等不同的音乐调式。今存晋乐所奏石崇《王明君》曲辞五言三十句,乐辞篇幅较长大,为典型的相和曲体式;至刘宋鲍照、梁施荣泰所作《王明君》就已缩短为五言四句。通过《王明君》晋辞和南朝辞体式上的较大差异,也能反映出曲调的“新声化”。
据《古今乐录》,“吴声十曲”曲目之一为《凤将雏》。应璩《百一诗》曰:“汉末桓帝时,郎有马子侯。自谓识音律,请客鸣笙竽。为作陌上桑,反言凤将雏。左右伪称善,亦复自摇头”,《凤将雏》本为汉曲。《古今乐录》又载,吴声中的“半折、六变、八解,汉世已来有之”。可见,南朝时,部分汉魏旧曲已进入南方的新声系统,经历了旧曲到新声的演化过程。这一演化经由了怎样的音乐路径?王运熙先生认为,吴声、西曲章法上多为四句,与汉魏相和曲有部分承递关系。这是因为以四句为一解,是汉魏相和曲的一般形态,相和曲的“一解”与吴声、西曲独立的“一首”在音乐上是相等的。[6](P34)这个结论确有事实依据。据《南齐书·乐志》的记载,南朝萧齐时代的宫廷杂舞曲多数采用摘唱中原旧曲的做法。如《拂舞曲·济济辞》摘唱晋曲六解中的最后一解,《拂舞曲·淮南王辞》摘唱晋曲六解中的第一、第五两解。“摘唱”缩短了乐章长度,使由若干“解”组织而成的旧曲长大篇幅靠近了新声的乐曲长度。上述材料虽集中于舞曲,但据此推论,“摘唱”可能是旧曲到新声曲调演化的音乐途径之一。
无论汉魏旧曲,还是南朝清商新声,至唐代,都已成前代遗声。尚在传唱的旧曲调可能经过“新翻”,焕发出新的艺术魅力。孟浩然《美人分香》:“舞学平阳态,歌翻子夜声”,又《崔明府宅夜观伎》:“长袖平阳曲,新声子夜歌”。白居易《折杨柳》:“六么水调家家唱,白雪梅花处处吹。古歌旧曲君休听,听取新翻杨柳枝”,刘禹锡《折杨柳》:“塞北梅花羌笛吹,淮南桂树小山词。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据此,《子夜歌》和《折杨柳》曲调在唐代都经过了“新翻”的艺术改造。一般的看法是,“新翻”是指为旧曲调配新歌词。任半塘先生指出,“翻”是指将前代遗声移宫换调。[8](P24)笔者同意任先生的看法。从唐诗有关“新翻”的内容来看,“新翻”是针对曲调进行的。如白居易《残酌晚餐》:“闲倾残酒后,暖拥小炉时。舞看新翻曲,歌听自作词”,“新翻曲”和“自作词”是相对而言的,自然是指乐曲;而且,既是“看”新翻曲,不言“听”,显然属于没有歌词的器乐曲。李绅《悲善才》“东头弟子曹善才,琵琶请进新翻曲”, 薛逢《听曹刚弹琵琶》“禁曲新翻下玉都,四弦掁触五音殊”,都能说明新翻的是“曲”,而非歌词。通过“新翻”旧曲,部分清乐遗声实现了在唐代的曲调演化。
上面讨论了乐府曲调的三种演化形态,它们各有不同的音乐起点,并且产生了不同的音乐结果。徒歌到乐歌,实现了歌曲音乐性质的转变和歌曲艺术的提升;本曲到变曲,产生了一支或一组同源曲调,扩大了乐府曲调的影响,丰富了数量;旧曲到新声,推进了曲调自身的更新,延续了旧曲的艺术生命力。
二、乐府曲调演化的动力和条件
乐府曲调演化的动力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音乐自身发展和新旧递变的内在要求,二是一定历史时期音乐文化环境的外部推动。
历代皆有新声,乐府曲调的演化即是音乐新旧递变的结果。郭茂倩《乐府诗集》解释历代新声不绝的原因:“盖不能制雅乐以相变,大抵多溺于郑、卫,由是新声炽而雅音废矣”,[5](P884)即认为新声的流行是由于统治者没有大力推行雅乐的后果。事实上,主观干预和行政手段并不能阻止新声的发展。据《汉书》记载,汉哀帝因“性不好音”,对流行俗乐极为不满,下诏裁撤乐府人员以抑制俗乐,但“百姓渐渍日久”,“豪富吏民湛沔自若”。[9](P1073-1074)音乐的推陈出新,势必需要从丰富的民间音乐中汲取新的养料,民间徒歌向乐歌的转化是历代新声发展的客观需求。
“音乐的发展是一条永不停滞的历史长河,它不会停顿在某个已经完成的体系之中,尽管这个体系中的一些作品具有尽善尽美的经典价值。社会经济及文化发展迅速的时代,尤易突破旧的音乐体系,产生新的音乐。”[10](P31)总体来看,融通开放的音乐文化环境表现出对流行俗乐和外来音乐较大程度的认同和接纳。新音乐元素作为乐府曲调演化可借助的素材,其移植和渗入加速了演化的进程。汉武帝时期的宫廷音乐文化建设即具备开放的特点,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汉武帝定郊祀之礼,采诗夜诵,其中有赵、代、秦、楚之讴,这使徒歌进入乐府,得以演化为乐歌;二是在胡文化流行的背景下,李延年利用《摩诃兜勒》制作了横吹新声二十八解,从胡乐中产生了本土化的变曲。
南朝梁武帝时期的宫廷音乐文化活动同样显示出开放性。尽管梁武帝鼓吹恢复古乐,并致力于萧梁宏大雅乐体系的建构,但他个人的音乐实践,却体现出对新声俗乐的偏好。梁武帝与沈约,以及宫廷乐人王金珠等组成宫廷俗乐制作班子,创作了数量颇丰的吴声新辞。《乐府诗集》收录的吴声、西曲歌辞除“晋宋齐辞”、“晋宋梁辞”等无主名乐歌外,几乎全部出自梁武帝和王金珠之手。但他并不满足于制作新歌辞,天监十一年,通过改造西曲,富于创造性的完成了新西曲《江南弄》《上云乐》组曲。两支组曲皆有“和声辞”,吸取了西曲的曲式结构;但经演化后的新西曲体式为错落精美之杂言体,又显示出对西曲声调的改造。除新西曲外,梁武帝还利用民间四时歌的形态,从传统舞曲《白纻曲》中演化出《四时白纻歌》。
新旧音乐之递变,开放的音乐文化环境,是乐府曲调演化的内因和外因,但在共同的内因、外因下,并非每一支曲调都能经历演化而成新曲。曲调自身的流行程度或受关注程度至关重要。一般而言,发生演化的曲调往往具备较大的艺术影响力,并引起了宫廷和上层社会的持续关注。比如《子夜歌》声曲动人,所谓“歌谣数百种,《子夜》最可怜”。[5](P654)据《南史》记载,在齐高帝的华林园宴集上,沈文季歌唱的即是《子夜歌》。这支在民间和上层社会备受青睐的曲调,其“变曲”数量居新声之首,也就很自然了。另一支吴声曲调《懊侬歌》历史悠久。现存最早的歌辞是西晋石崇为其伎妾绿珠所作的“丝布涩难缝”一曲,后来刘宋少帝又制作《懊侬》新歌三十六曲。梁天监十一年,梁武帝将《懊侬歌》更名为《相思曲》。西晋至萧梁,《懊侬歌》艺术上的更新、长久的音乐魅力最终孕育了变曲《华山畿》。
乐府曲调的演化既是音乐自身的嬗变过程,同时也是制乐者完成的音乐艺术改造和提升的活动。在不同的演化形态中,拥有专业乐人的宫廷乐府以及大量蓄伎的贵族豪富都发挥了直接的作用。据《南史》载,梁武帝曾经赐给徐勉吴声、西曲女伎各一部,说明萧梁宫廷内的新声演唱已有专业分工。新西曲《江南弄》《上云乐》的产生,有赖于宫廷新声的专业化和高度艺术化。
南朝蓄伎的贵族中,萧梁时期的羊侃甚为突出。据《梁书·羊侃传》:“羊侃甚豪侈,善音律,姬妾列侍,穷极奢侈。有舞人张静婉,容色绝世,腰围一尺六寸,时人咸推能掌上舞。侃尝自造采莲、棹歌两曲,甚有新致,乐府谓之《张静婉采莲曲》。”[11](P561)《采莲》《采菱》本为南朝民间歌谣。南朝新声《神弦歌·采莲童曲》其一“泛舟采菱叶,过摘芙蓉花。扣楫命童侣,齐声采莲歌”,这是江南日常采摘莲叶劳动中齐唱采莲歌的情景,透露出欢娱的气氛;其二“东湖扶菰童,西湖采菱芰。不持歌作乐,为持解愁思”,采莲歌不仅增欢娱,还可解愁思,更可注意者,民间还出现了演唱《采莲》的职业艺人“采莲伎”。《采莲歌》进入上层社会后,艺术上日益精美。羊侃的新《采莲》舞曲甚至引起了乐府的关注,并以舞人姓名命曲。梁武帝改西曲所制《江南弄》七曲之三即为《采莲曲》,其和声辞曰:“采莲渚,窈窕舞佳人”。至此,民间《采莲》经过羊侃和梁武帝的新造,完成了曲调的演化和舞容的新创,成为宫廷名曲。从《采莲》曲的演化来看,高级的制作条件和制乐者的音乐修养,是决定乐府曲调经演化后所能达到的艺术程度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乐府曲调演化对乐府文学发展的影响
乐府是辞、乐、舞结合的综合艺术形态,乐、辞关系中,乐具有决定地位,因此,曲调的演化对乐府歌辞的创作是有影响的,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1.提升了乐府音乐艺术,奠定了乐府文学创作的音乐基础。
徒歌到乐歌的演化,由于器乐伴奏的完善和曲调的规范、定型,不仅丰富了乐府音乐表现的手段和声情,更重要的是,使具有较大自由度的徒歌声调发展为有调可循的章曲。曲调的定型为乐府歌辞的创作提供了声调依据,从而可以通过“依调而作”的方式,创作数量更多的乐府新辞,形成“一调多辞”的音乐文学现象。《乐府诗集》以调系辞的编排方式,直观地反映出曲调在辞、乐关系中的决定地位以及乐府文学“依调而作”的丰富成果。
2.衍生了新的乐府曲调,拓展了乐府文学的创作空间。
本曲到变曲的演化,最终形成了一组同源性的曲调,不仅为歌辞创作提供了新的曲调依据,扩展了乐府文学的创作空间,而且,扩大了曲调在上层社会的影响和知名度,造就了乐府史上的一批著名曲调,留下了数量颇多的系列歌辞,繁荣了乐府文学创作局面。
3.实现了音乐自身的持续发展,促成了乐府旧曲体式的新变。
无论汉魏旧曲经“摘唱”实现新声化,还是清乐遗声经“新翻”产生出新声曲,都属于不同时代的旧曲向新声的演化。乐府史的每一阶段都存在一种主流新声,主流音乐之外的旧曲虽整体处于衰落状态,却并非短暂间销声匿迹。其间,有些曲调逐渐失传,有些曲调则通过调式的变化、乐章长度的缩减等多种艺术改造方式实现了自身的演化,延续了艺术生命力,融入到当世新声的音乐格局中。不同时代的旧曲向新声的转化促成了旧曲体式的新变。汉魏相和旧曲在南朝总体性的“新声化”,使旧曲体式转变为短小的五言四句新声体式;而南朝遗声入唐后,体式也呈多样化,比如《子夜四时歌》在唐代就有五言四句体、五言六句体、五言八句体等。
4.丰富了乐府歌辞的文学风格,渗透了宫廷文学的旨趣。
如前所述,乐府曲调演化的发生地,多是在宫廷乐府以及蓄养大批歌妓的豪富之家,这势必会将宫廷和贵族的音乐审美旨趣融入新的曲调中,造成曲调风格的精美、奢华,同时也要求歌辞风格的富丽。萧梁宫廷乐人王金珠所作吴声《上声歌》曰:“名歌非下里,含笑作《上声》”,《上声》起于徒歌,进入宫廷演化为乐歌后,即不再是所谓下里巴人之曲了。显然,宫廷音乐制作有其自觉的艺术方向。乐府史上歌辞风格的转变,从根本上说是音乐变迁与曲调演化带来的结果。
[1][晋]郭璞注,[宋]邢昺疏.尔雅注疏[M].[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C].北京:中华书局,1980.
[2][梁]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汉]刘安撰,高诱注.淮南子[M].二十二子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4][唐]杜佑.通典[D].北京:中华书局,1984.
[5][宋]郭茂倩.乐府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6]王运熙.乐府诗述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7]许云和.梁武帝《江南弄》七曲研究[J].武汉大学学报,2010(4).
[8]任半塘.唐声诗下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9][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 [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0]钱志熙.汉魏乐府的音乐与诗[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0.
[11][唐]姚思廉.梁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责任编辑/袁亚军
I207.226
A
1671-7511(2012)05-0077-05
2011-10-20
王志清,女,吉首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杨基燕,女,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文化传播学院教师。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齐梁乐府诗音乐与文学关系研究”(项目号:09CZW02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