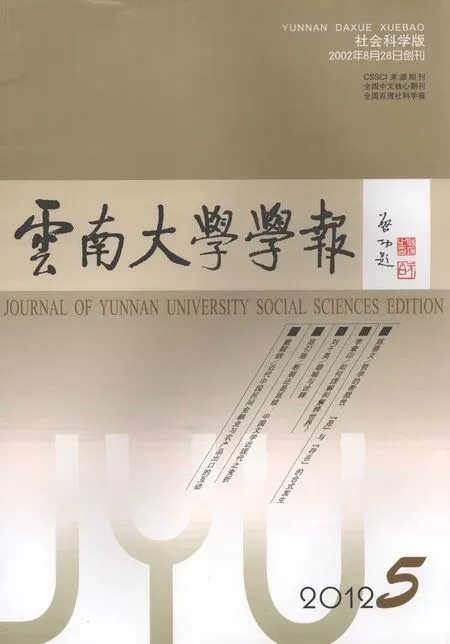哲学的希腊性:“是”与“存在”的合式发生
陈春文[兰州大学,兰州 730000]
哲学的希腊性:“是”与“存在”的合式发生
陈春文
[兰州大学,兰州 730000]
哲学;希腊性;亚里士多德;是;存在;合式;翻译
“存在”与“是”不是简单的择一而译的问题,而是哲学思想的双螺旋:一个是在原因中的求证,从中演绎出一整套的时空参照体系;一个是在原理中的求证,在不矛盾律的基础上,不断延伸真理的知识维度。无论是在原因中求证还是在原理中求证,是西方哲学的固有理路,是西方哲学追求真理的固有品格,忽视这一点,我们就不可能完整地理解西方哲学,不可能理解以西方哲学为基础的西方文明,不可能理解西方文明全球化深而且广的影响。
一
“关于”哲学,我们知道得甚多; 同时,我们对此却又思之甚少。“关于”哲学,它的问题我们可以无穷列举,但对什么是“关于”,“关于”的学术脉络是什么,它的判断尺度是什么,我们却思之甚少。问题的频繁转换,意见的层出不穷,论争的此起彼伏,都显现在“关于”哲学的层面,这种“哲学”越繁荣,真正的哲学之思也就越加赤贫。我们不仅在哲学的赤贫时代思索哲学,而且我们规定和阐释时代的思想本身就是赤贫的。这种赤贫不仅无意回归到思自行追问的肃穆与虔诚,而且还受到其内在价值观的鼓励。哲学的分科化如此,不断在哲学前面加定语如此,用人类学的知识搜索时代哲学的真理求证是如此,用时间的历史分期置换对时间本身的思考是如此,再用如此得来的时间观念替代时间的显示和时间的创造亦复如此。经过一系列的置换和转换,我们已经无力回归到哲学自身的追问中来。罗列问题,增加问题,用一个问题取代另一个问题,这是在做“关于”哲学的事;探讨问题成为问题的条件,澄清思想成为可能的种种条件,在追问中使哲学的语汇沉入到哲学的基本面上来,这是在做哲学着的事,亦即海德格尔所讲的直面思的事情。
西方哲学是个大题目。海德格尔倾其一生,就做了一件事:重新解释西方哲学。尽管海德格尔基于自己的思想判断认为哲学终结了,但他对西方哲学的再解释却激发了哲学思想的无限生机。你可以基于自己的哲学观点不同意他的哲学终结说,但你不能回避什么是哲学的提问,你不能放弃反思自己哲学立场的权利,你不能不承认海德格尔的思想活动使思物变得活跃起来,甚至使我们有可能把整个哲学作为一个问题回溯到思物的追问中。国内哲学界经过20多年翻译和研究海德格尔思想的积累,已经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哲学视野和在思想的基本面追问的能力,并在一定范围内形成了严格的思想的概念和严肃的哲学见识。这些积淀不仅为中西思想之比较奠定了新的参照系,活跃了中国哲学界的神经,而且加深了对西方哲学及以西方哲学为基础的整个西方文明的再认识,并且对加深理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西方文明的全球化进程产生了不可替代的影响。但是,从哲学本身而言,海德格尔对中国哲学界的根本作用还是在于促使我们向哲学运思的基本面回归,后现代问题,“是”与“存在”的界定问题,分析哲学与存在哲学的关系问题,科学与哲学的关系问题,后哲学问题,语言问题,技术座架语言中的伦理问题,无一不彰显着海德格尔思想在当今中国学术界的文本价值。海德格尔之前,我们是在不同的哲学家那里找问题;海德格尔之后,我们把哲学本身当成了问题,从而才有了对西方哲学的再解释问题,出现了源自于西方哲学内的深层次的思想解放,这种思想自身的解放被不同层次、不同立场、不同学术背景的人所索取,不仅影响面宽,范围广阔,而且话语衍生力极强,具有极强的传感差异的能力,远远超出了一般“主义”的影响。这种思想的解放力量和差异力量,只有在思想赖以滋生的文本发生转换时才有可能,且是同一思想路径自身的文本转换,而非在外力挤压下的文本裂变。如中国的新文化运动,虽然是一场巨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但它不是中国思想自身的文本转换,而是在外力作用下启蒙的结果,它所产生的结果是传统的断裂,但并没有成就新的思想文本,依旧是颠簸流转,恍惚不定,极易被浅层的变故所左右,无法形成思想自身的轨迹。这说明此种思想解放没有文本价值,无法完成思想自身的超越,自然也不会积淀为人类理性恒常的哲学语言和精神财富。
二
国内哲学界在近些年对西方哲学的研究中有了新的进展,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不断地向西方哲学的缘起地追问,对哲学的希腊性的体会持续加深;另一个是不断有人跟进“是”与“存在”的翻译问题。这两件事都是哲学的大事。能否意识到哲学的希腊性,事关什么是哲学的问题,事关区分真哲学和伪哲学的问题,它是确定是否进入哲学之思的标准,按希腊人的观点,这是区分真理和意见的地方。本文不专门讨论这个问题。是与存在的翻译问题既是大问题,也是真问题,所谓真问题就是严格地在哲学中追问,问到的是哲学的真问题,严格的哲学问题。它既是汉语翻译中遇到的真问题,也是西方哲学自身中固有的真问题,它既事关汉语言思想的特点,又牵涉对整个西方哲学的理解问题,绝非字面之争、文化之争、分析哲学与存在哲学之争的问题。
对于中国哲学界来说,是与存在的问题首先是个中国问题,是中国近代翻译界转译西方哲学时遇到的问题,我们的前辈学者选择了“存在”译法。存在与不存在本不是中国思想、中国语言和中国文化的问题,我们自生的问题是有与无,但有不等于存在,无不等于非存在。存在以及它的对称物非存在之译,并没有把西方哲学的理路接合到中国思想的言说方式中,它仍然是个陌生的结构和体系。但中国近代翻译界选择“存在”译法也自有其理。首译哲学时,我们的先辈并不知哲学为何物,我们移释西学的套路是先取器物,再循器物之技术,再循技术之科学,再循科学之哲学……。这个套路决定了我们翻译中的近代取向。无论科学还是哲学、艺术的翻译,都立足于近代欧洲的尺度,尤其是近代自然科学的尺度。翻译中救国图存的急功近利取向,以及对异在物的思想功力之不足,决定了我们对西方哲学做出“存在”倾向的翻译,做出以近代性为视域的翻译。
什么是近代欧洲或者哲学的近代性?你可以说哲学在经历了漫长的漂泊远航之后又靠岸登陆了(黑格尔),你更可以说希腊的逻各斯(原本的理性)被近代的知性(可理解性)所置换,你也可以说哲学在终结自己前的向着行星语言的筹划(海德格尔)……然无论怎样界定,近代是以自然科学为标志的命名方式,是沉思的哲学向研究的科学的转移过程。沉思的思想变成科学的认识,思想的逻各斯渊源变成认识的因果链条。只有纳入到因果链条并经过认识者确知的认识才能被确认为知识。认识者自我确知便成为近代之为近代的信条,确知(Bewu tsein,以往通译为“意识”,这个词的本意是确知,即bewissen在时态上的完成,但也可引申为确知是对sein的确知)。这才有了认知者(主体)和认知径路(sein)的关系,并在认知径路和认知对象之间衍生出一系列的知识论体系。汉语在翻译sein时,出于汉语言文化基因的缘故,出于改良国家的功利取向,后来又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不断强化对sein的“存在”解,并把近代欧洲Sein和Bewu tsein在知识论上的对应关系改造为存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完全淹没了西方哲学求证真理的本性,使其不知不觉中被改造成适合中国人口味的辩证法(Dialektik本是希腊人的种属差异的递进法,求真知的方法,与中国人的辩证法风马牛不相及)。由于德国哲学在近现代欧洲哲学中的特殊地位,以及德国哲学与近代中国的特殊关系,德文sein的汉语翻译对于中国哲学界理解西方哲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除去汉语言自身的原因,就翻译而言,从sein中单取“存在”解,严重地误导了中国人对西方哲学的深层探讨,并从根本上阻碍了我们对整个希腊渊源的西方文明的理解和在科学与哲学上严肃地求证真理的步伐。
三
但在概略地交代过这些背景之后,我们是不是就一定逢sein便译作“是”呢?本文就“存在”和“是”在汉语中的语义担当存而不论。前面说过,译作“是”还是译作“存在”,不单纯是汉语的问题,它也是西方哲学中固有的问题,正因为如此,我以为,“是”译说是中国学人理解西方哲学的一个进步。但如果说sein的“是”和“存在”解是西方哲学文本中固有的问题,我们就应该检讨“是”的是其所是和“存在”的是其所是,而不是视之为简单的替代关系。以德文的sein为例,只要从语言学的系动词结构出发,或者从逻辑出发,它就不可能有“存在”解,如作为系动词的sein的一系列衍生语态“ich bin Lehrer”,“du bist Lehrer”或者“S ist P”,“存在”解根本不通,但一经涉及实存或状态判断,如“Gott ist”(神在),或者“ich bin auf dem Lande”(我在乡下),“是”译就没有依据,且不通。Sein的问题既不单纯是语言学问题,也不单纯是逻辑学问题,更不是流俗意义上的哲学问题,它是语言学之所以成为语言学、逻辑学之所以成为逻辑学、哲学之所以为哲学的问题,它是一个先行问题。在德文中有个神秘的虚拟结构,“es gibt”,它能融合两个情态动词“haben”和“sein”的语义,只要在没有具体主词的情况下,只要在需要虚拟主词的情况下,它就会及时地出现。“es gibt”的“es”在汉语中可以译作“大我”,也可以译作“虚拟主语”,也可译作“无始之始”、“无源之源”,“es gibt”有“它在”,“它是”,“它给”,“它被”,“它生成”,“它决定”,“它有”等诸多汉译解,我列举的这些也不是它的全部,它既可以做主动解,也可以做被动解。但汉语既没有虚拟结构,也没有被动态的身世,根本就难以企及西语(西方哲学)的虚拟价值和被动态的极端重要性。单纯从语言学上取“是”解和“存在”解根本就无法触及sein的晦暗之处。归根到底,sein不是某个具体的问题,而是使问题成为问题的问题,它潜存于哲学的基本规定中,哲学之为哲学,西方哲学之为西方哲学,与sein的晦涩的结构有关。
“es gibt”的虚拟性、被动态、多功能的结构,并不是现代西方语言的现代发明,它是各种现代西方语言继承下来的一份古老的遗产。这种语言本身就是哲学,它是由哲学而来的语言,自然也在这种语言的如此言说中蕴含了种种哲学的问题。不管是语言学问题、逻辑学问题、科学问题、哲学问题、神学问题,最终都是希腊性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基本上对汉语言的思想经验和传统来说是陌生的、难以理解的,我们局限在汉语言中所做的种种努力总是猜测大于求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才出现了各种基于猜测的玄论。两种无法重合的言说方式,一种是哲学的,一种是非哲学的。用没有经过深究的非哲学的语言去解读哲学的语言,得出诸种不清晰的玄奥的所谓哲学解释,自然就不足为怪了。
隐藏在“是”与“存在”之分歧背后的,是哲学的希腊性问题,也就是说,哲学在缘起上是希腊的、希腊语的、希腊的逻各斯的,是被动态的、虚拟式的。不仅哲学在缘起上是希腊的,我们至今言说哲学的唯一可能性仍然是希腊的,只要我们在严格的意义上言说哲学。哲学的基本局面以及由基本局面规定了的问题只能从哲学的希腊性缘起上说起。“是”与“存在”的问题也不例外。很多人不同意海德格尔的哲学终结说,自然也不会理解海德格尔提出的思的任务。人们为什么不同意他的哲学终结说?因为他们理解的哲学仍是世界观意义上的哲学,仍是无规定的“智慧”字面意义上的哲学,仍是价值需求和生命体验意义上的哲学,既没有规定,也没有划界,根本没有意识到通过一系列证明规则把“智慧”转化为求证知识的真理语言是哲学的自性规定。如果你同意海德格尔的哲学终结说,当然是在真正的哲学尺度上同意,也就是说,只要你契合了海德格尔的哲学终结说,你也就运思了海德格尔的哲学追问,那你自然也就有了哲学发生的概念、哲学的希腊缘起概念。有了哲学的希腊缘起概念,就自然会追问哲学的发生与非哲学的发生的种种可能性、哲学前与哲学后的种种运思的可能性,以及哲学对于欧洲内在历史尺度的天命性质。有了这样的概念,就不会把西方人领有的哲学天命与国人领有的非哲学的天道守常的天命混为一体。
沉入到哲学的希腊性中去,这是保证哲学追问严格性的唯一途径;返回到哲学由之而来的路径上,并递归到它的缘起处,也同样是理解“是”与“存在”关系中关键信息的原始密码。希腊性是我们理解哲学的起点,但哲学却不是希腊性的起点。海德格尔谈哲学的终结,它终结在哲学的希腊性上,但希腊性并没有因哲学的终结而终结。希腊性大于哲学,它有可能哲学地发生,也有可能非哲学地发生。但事实上是哲学地发生了,并因此我们从西方获得了一个哲学的世界,这个世界从发生到终结便是黑格尔意义上的一部展开的哲学史。在这部哲学史中隐藏着一个由“是”和“存在”构成的双螺旋结构。这个双螺旋结构决定了西方哲学到底要吐露怎样的思想信息。只要我们体会到哲学的希腊性,体会到哲学在希腊性上的历史的发生,我们就有可能摸索到理解“是”和“存在”双螺旋结构的线索。这个线索就是Metaphysik。
四
Meta-physika,我们通译为形而上学。但这种翻译实际上是张冠李戴,此译完全模糊了中西学术的差异,看上去和听起来都似是而非。中文理解形而上学的参照物是道器之分,实际上是有形无形之分,有形无形之分界并无“原理”的依据,实际上是不能原分的(Urteil,逻辑上译为判断)。而Meta-physika则完全不同。亚里士多德的Physika是求索运动之因的,不仅依范畴列出构成运动的因,而且还探寻因的原因,而这些原因是和原分相关的。与原分相关的追问运动实体的过程以及探讨运动与实体相分离的过程被称为Meta-physika。这个意思本来很单纯:physika,就是物理,探索运动因的物理;Metaphysika,就是物理之后,探索运动实体以及运动与实体如何分离的后物理。这是一个非常清晰的物理—后物理结构,这个结构的哲学性非常显著,具有鲜明的希腊哲学进而西方哲学的特点——一个运动化的世界图像。这个运动化的世界图像虽然已有将近三千年的展开史,虽然现代科学已经极大地丰富了这个世界图像,但它的基本规定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读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感觉与读一位近现代西方哲学家的著作在理路上丝毫没有过时的印象,因为它们依然是运动的世界图像,依然是同一的哲学,依然是同一个世界。这个物理—后物理结构在现代世界中很容易被简单地解读为科学与哲学的关系,这种解读是建立在科学与哲学已经分开的基础上的。但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科学与哲学是不分的,都是哲学,他只作出了第一、第二哲学的区分。亚里士多德之后的西方人就在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理解哲学,哲学就是指被物理—后物理地阐释出来的世界。在他们眼里,不可能有什么其他的哲学。
哲学就是后物理,这在西方不会有什么争议,但哲学不仅仅是后物理,从亚里士多德意义上说,哲学是整个Physik——Metaphysik结构,而物理是这个结构中最基本的东西。这也是为什么西方哲学在缘起处就显得非常科学的缘故。“是”与“存在”的分际就蕴含在这个物理—后物理的结构中。一方面是规定运动的物理的世界图像(科学——第二哲学),一方面是探索运动与运动实体相分离的哲学(第一哲学)。物理层面的问题是“存在”问题,后物理层面的问题是“是”的问题。无论“是”说还是“存在”说,都不能完整地澄清希腊哲学,自然也就无法完全理解西方哲学内在演绎的理路。“是”的问题看上去是单纯的逻辑问题,实际上它是个逻各斯的问题;“存在”问题看上去是个似是而非的“本体论”(存在学)问题,而实际上它是弗西斯(physis)的问题。逻辑中的“是”渊源于逻各斯,但它却不再逻各斯地言说;物理中的“存在”渊源于弗西斯,但它却不是弗西斯,而是带着一系列范畴的规定,已经是有模有样的科学语言了,是物理了。逻各斯不是哲学语言,但逻辑已经是哲学语言;弗西斯不是哲学语言,但物理已经是哲学语言。“是”与“存在”的问题就出现在从“前哲学”语言到哲学语言的转移中,它是与哲学同步出现的,正因为如此,我们说“是”与“存在”的合式才是真正的哲学基本问题,单一的“存在”或“是”的追问方式都不是哲学的真实发生。它是与希腊哲学相伴生的,但并不是希腊哲学产生前希腊思想中天生的。希腊天生的思想世界是密托思(Mythos,通译神话)。密托思是希腊人的本然世界,而哲学是对密托思进行翻译的结果,这就是说,“是”与“存在”的合式问题是在把密托思翻译成哲学语言时出现的,是把密托思语言翻译成人语文本的哲学语言的结果。希腊的密托思(所谓神话)并不是一般人类学意义上的神话,不是在外延和内含上扩展人本主义的人格神。希腊世界原本就是属神的、受神托付的、在泛神的让予中的,人以及其他都是神的折射和投影,人的来历和归属都在神的显示和让予中,人接受神的传达和派遣,接受神派来的信使和中介,“回忆”(柏拉图)神的托付和交待,“回忆”信使对密托思的转达和翻译,这才演绎出逻各斯的一系列(哲学地看)十分复杂的含义。Physik(物理——存在)只是从运动的规定中抽取了密托思中弗西斯的一部分可人为规定的东西、可哲学化的东西;Metaphysik(后物理)只是从密托思的逻各斯中抽取了一部分可哲学化的所谓逻辑的规定。但“是”与“存在”的合式(Metaphysik)是哲学,不是密托思,不是希腊人的原世界,而是经过哲学翻译的世界。
海德格尔说哲学终结了,他说这句话时蕴含了哲学的发生。我认为,哲学发生于翻译,对密托思的翻译。“是”与“存在”的合式就是应此一翻译的需要而生成的。单纯“是”的结构译不出密托思,单纯“存在”的结构也译不出密托思。而它们的合式则在相互规定中保证了它的整体翻译结构趋近于密托思。“从根本上说,哲学产生于一种广阔的文本翻译,也即从神语文本(密托思文本)向人语文本(哲学文本)的翻译。正是在这种大跨度的翻译中,无论密托思还是逻各斯都失去了自己的渊始本义,不仅密托思变成宗教,而且逻各斯也转变为逻辑。”[1](P51)我的这个结论是从海德格尔那里引申过来的。不仅密托思变成宗教、逻各斯变成逻辑是在神语文本向人语文本翻译时发生的,而且“是”与“存在”的分际与合式也是在这种翻译中发生的。我们一经承认“是”与“存在”的问题,我们就承认了人语文本,承认了哲学,就在以哲学的姿态研究问题,按照“是”和“存在”的合式规定哲学地解释、科学地演绎密托思文本,亚里士多德是这个文本翻译过程中的奠基性人物。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科学家和哲学家在寻觅科学和哲学的历史路径时,都不约而同地要回到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中去。从“是”和“存在”的合式文本来说,亚里士多德是哲学思维的开端,并因此他也剪断了希腊人神胎的脐带。从此,希腊人开始尝试用自己的两条腿——物理和后物理——走路。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物理就是处于列举状态的存在,用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就是有多少个Kategoria(直观)就有多少种存在;亚里士多德用Physika(物理)研究列举状态的存在,列举状态的存在不受种属递进的约束,每一个存在的种都能回归自己的‘单纯’。亚里士多德把处在列举状态的存在之后的自动分离存在的在场性列在物理之后,也就是后物理,后物理讨论什么是什么。这里出现了用‘是’规定弗西斯的需要。在哲学文本中,作为合式出现的弗西斯实际上是‘是’与‘存在’的合式。”[1](P56)有多少种直观,就有多少种存在;直观的可以列举,在直观中列举的可以生灭;存在问题有生灭问题。这是亚里士多德的规定。但“是”不能列举,它是类的规定。列举要在范畴中列举,范畴之所以是范畴,在于它是规定者。亚里士多德把规定者(是)摆在第一哲学的位置上,而把受“是”规定的可列举的存在摆在第二哲学的位置上。很显然,在哲学意义上,我们可以问上帝存在不存在,但使这个问题获得哲学正当性的前提是:什么是上帝?只要我们哲学地追问,这就是真正且恒常的哲学问题。
亚里士多德并不是从密托思文本向哲学文本转移的始作俑者,但他是集大成者。实际上,在亚里士多德之前,巴门尼德和赫拉克利特就已经开始了对密托思文本进行准哲学的翻译。只是他们各取一路,巴门尼德用“是”的路向来翻译,赫拉克利特用“存在”的路向来翻译,由此产生了影响整个哲学史的动静之争。作为巴门尼德的“是”,是圆满、恒静、永恒,是牢固真理的永恒核心;作为赫拉克利特的“存在”,则恒变无居,永恒变易,并无常驻之真理。这是一场对密托思文本的解释权之争,并非哲学意义上的真理论证。从非哲学的语言看,说既动又静、既变化又守恒是可以的,但在哲学文本中,这种既A又B的论断是不允许的,要澄清和规定在什么条件下是A,在什么条件下是B。亚里士多德逐层规定和澄清了哲学作为哲学的整个文本递进过程,完全是胸有成竹的现代哲学家的派头。
五
是与存在的分际终究是希腊思想内在的分际,是哲学内的问题。是与存在有分际,是与存在的出现也有分际。是与存在的分际点在于规定运动(是)和规定中的运动(存在)。是与存在出现的分际在于哲学对密托思的翻译,仅有“是”不足以转释密托思世界,单纯的“存在”也不足以翻译出密托思。哲学对密托思的解释采用了“是”与“存在”的合式,求是与直观存在的合式。在原因中求证就是存在问题,在原理中求证就是是的问题。在原因中求证引发出动力学的科学观,并逐步引发出近代科学的世界图像;在原理中求证,分延出了系统的逻辑学,这个逻辑学不仅是语言的,而且是几何学的,单从语言中解释“是”的构造是不够的,还要探究使几何公理、定理、定义构成整个求证体系的求是点。只有这样,“是”的阐释才有可能与“存在”等深等幅。
在原因中求证,这不单纯是知识的问题(知识固然是力量,但不仅仅是力量),而是要在产生力量的科学中理解到它的哲学性;在原理中求证,这不单纯是逻辑学的问题(逻辑固然是真值意义上的真理,但它是语言学的真理,并非真理的整个证明体系),这里蕴含了数理与物理(变量与参量)的深刻关系。柏拉图要求学习哲学的人要有几何学素养是有其思想深度的。西方哲学进而整个哲学的肃穆与尊严也体现在这种几何学的严格性上。只有能够在原因与原理两种求证路径上自由穿越的人才称得上是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家和科学家。
在密托思时代,希腊人安居在弗西斯(physis)中,那里并不存在一个哲学问题,也不存在由哲学演绎而来的其他问题。在巴门尼德和赫拉克利特时代,他们各自从弗西斯中分离出“是”和“存在”的路径,并各自企图用一个路径遮蔽另一个路径,但都是以半人半神的格言方式探究弗西斯,具有明显的从神语向人语翻译迁移的迹象。到了亚里士多德时代,已经从神语向人语的迁移中孕育了足够的正在形成中的哲学语言,希腊人学会哲学地翻译弗西斯,主要是亚里士多德用Physika语言翻译Physis,并相应地出现了Metaphysika的言说方式和思想方式。我始终强调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位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家,这不仅因为他把“是”的问题与“存在”的问题合式地提出,而且也因为他把Physika放在前置地位。亚里士多德揭示的基本哲学语言是Physika的,这是中心话语,其他的思想话语并没有自足的称谓,所以他的学生才把支持Physika这种主导的哲学语言之外的文献统称为Meta-physika。Physika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那里就不具有基础地位,他们的“哲学”语言自然也不是对密托思中弗西斯的整体翻译,因此也很难说是“是”与“存在”合式意义上的哲学家。是亚里士多德从根本上完成了从神语世界向人语世界的翻译,并由此产生了哲学语言中的语言学、诗学、逻辑学、解释学、分类学、物理学、动植物学等广阔的科学概念(虽然这里的“科学”与近代实证科学的品格不尽相同)。西方科学和西方哲学一再回到亚里士多德那里寻求科学分际的界定语言并非偶然,这是一再重温把神语世界翻译成人语世界的翻译规则(逻各斯),不了解这些规则,就无法支撑和扩大科学语言的通约性,就会从根本上造成思想的混乱。亚里士多德是一位广义的翻译大师,就像他是精确的分类大师一样,不论翻译也好,分类也好,都是在铸造西方哲学化语言的基本语汇,没有这些基本语汇,哲学寸步难行。这些基本语汇实际上是在语言中划界,给密托思中的弗西斯语言向Physika语言的翻译划界,划界的依据是逻各斯,在逻各斯语言转为逻辑语言时,这种翻译必须遵守不矛盾律,不矛盾律是逻辑语言不背离逻各斯语言的最后屏障,也是哲学语言不背离密托思语言的最后屏障。逻辑并非是语言游戏,它负载着哲学从密托思中蜕变出来时众多的言说困局和思想困局。物理也不是简单的近代意义上的物理学,而是希腊人从密托思的领受者变成了规定者,从弗西斯的层层呈现变成了Physika的层层规定。亚里士多德思想体系的出现意味着神语世界向人语世界过渡的完成,意味着哲学由爱智慧转向了物理—后物理这种求证真理的思想纲领。
密托思言说时,它逻各斯地说;哲学言说时,它逻辑地说。密托思说什么?说弗西斯;哲学说什么?说Physika。什么是哲学?哲学就是逻辑地言说Physika,说哲学是物理—后物理就是这个意思。最后,我想引述海德格尔的一段话作为结语:“密托思是规定人的一切本质并攸关人的根基的律令,此一律令让思敞开在显示中,敞开在出场中。逻各斯言说的(与密托思)是同一个东西,并非如传统哲学史所认为的那样,因为密托思与逻各斯对立起来,才使哲学脱颖而出。相反,恰恰是希腊早期思想家(巴门尼德,残篇第8)在同一个语义上使用密托思和逻各斯;只是到了无论密托思还是逻各斯都不能固守其渊始本义时,密托思和逻各斯才开始分开,并对立起来。这件事在柏拉图那里就发生了。密托思惨遭逻各斯破坏这种看法,是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中的近代理性主义从柏拉图的根基中继承过来的一种偏见。同样,宗教从来都没有被逻各斯破坏过,事实总是并只是:神自行隐退了。”[2](P7)海德格尔这段话几乎揭示了哲学、西方哲学的所有隐晦之处,隐含了哲学基本面中一切有待去思的东西,如果我们真正哲学地思想过的话,哲学就不再是我们的界限,而是纵身到思的使命中去的契机。
[1]陈春文.论海德格尔的思想坐标[A].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第五辑[C].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2]M.Heidegger.Was heisst Denken[M].
■责任编辑/袁亚军
B502
A
1671-7511(2012)05-0003-06
2011-08-24
陈春文,男,兰州大学哲学与社会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