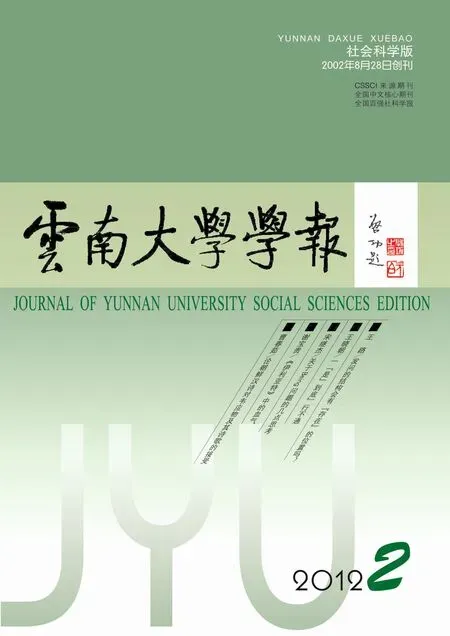“谁能够告诉我我是什么人?”
——悲剧《李尔王》中人物与读者的距离变化
谭君强
[云南大学,昆明 650091]
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之一的《李尔王》,①本文所依据的版本是William Shakespeare, The Tragedy of King Lear. New York: Airmont Publishing Company, Inc. 1966. 参考的译本是朱生豪译,方平校的莎士比亚:《李尔王》;载《莎士比亚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被誉为“任何语言中最伟大的戏剧之一”,[1]﹙Px﹚在20世纪,其甚至“逐渐取代了《哈姆雷特》的地位,被普遍认为是莎士比亚最伟大的悲剧”。[2]英国学者奈茨(L. C. Knights)认为,《李尔王》这一作品,具有最伟大的艺术作品的三个特征:“这一作品具有永恒性和普遍性;它在作者内心发展历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标志着它所代表的文明在意识领域发生变化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时刻。”[3]﹙P283﹚即使是只具有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这样的作品都会吸引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去进行阐释,以探究其深奥的意义,吸取其源源不断的养料。
我们知道,悲剧中的同名主人公不列颠国王李尔,是一个性格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的人物。一开始他是一个自信、甚至刚愎自用的君王,自信到认为将国土分给三个女儿,自己只需保留一百名骑士,人们仍然会像过去那样崇奉他,尊他为国王;刚愎自用到当小女儿考狄利亚在接受他从“王国中划分出来的三分之一沃壤”时,因未像她的两个姐姐一样言过其实,而是说出了实话:“我爱您只是按照我的名分,一分不多,一分不少”,“要是我有一天出嫁了,那接受我的忠诚的誓约的丈夫,将得到我的一半的爱、我的一半的关心和责任”。[4]﹙P152﹚却由此引起李尔王的震怒,把将给考狄利亚的国土分给了大女儿和二女儿。但是,接受了他全部国土和财富的两个女儿,迅即与自己的父亲反目,在大女儿对他的顶撞中,李尔在狂怒中说道:
这儿有谁认识我吗?这不是李尔。是李尔在走路吗?在说话吗?他的眼睛呢?他的知觉迷乱了吗?他的神志麻木了吗?嘿!他醒着吗?没有的事。谁能够告诉我我是什么人?(Who is it that can tell me who I am?)[4]﹙P178﹚
此时的李尔甚至对自己的言语行为产生了怀疑,对自己究竟是什么人产生了怀疑。英国著名莎剧演员、剧作家格兰威尔-巴克(H. Granville-Barker)认为:“登场人物的感情当时有什么意义,人物本身也可能都搞不清楚。”[5]﹙P157﹚然而,登场人物可能都不明白的事情,对于读者或欣赏者可能就是另外一回事。不论是先前作为一个国王的李尔,还是此刻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李尔,以及此后流落荒野、在暴风雨中心系其过去从未关心过的民众的李尔,读者应该可以从他自己所展示出来的言语行动中感知、认识与接受李尔——尽管在这一过程中,读者或欣赏者自身的情感伴随着悲剧的进程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换句话说,对李尔来说,最“能够告诉我我是什么人?”的,是读者,是欣赏者。
读者与作品的关联,是不言而喻的。任何一部艺术作品,绝非一个独立自足的完整系统。相反,它是与读者和欣赏者及其阅读与欣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德国接受美学的代表人物依瑟尔指出,文学作品中存在着两极,即艺术家一极和审美的一极。“艺术家一极涉及作者创造的本文,审美的一极则指由读者所完成的实现。”根据这种两级性,人们可以推断,文学作品不可能与文本或文本的实现完全一致,而是事实上必定处于这两极之间。文本只不过在它被实现时才具有生命,而且这种实现决不独立于读者的个人气质。文本“与读者的结合才产生文学作品,这种结合虽不可能精确地确定,但必定始终是实质性的”。[6]﹙P350﹚也就是说,一部文学作品既不等同于文本,也不等同于文本的具体化。因为文本只有在具体化中才获得生命,而具体化的文本也必然带有读者的个人气质。当读者和作品发生关系即阅读时,文本才能成为文学作品。离开读者的参与,离开读者的阅读活动,一部文学作品不过是堆印着的铅字,就像一部不经音乐家演奏的乐谱一样。
就小说、戏剧这类叙事虚构作品而言,读者的这种参与活动从某种角度来说,可以被视为与文本的一种对话。美国学者布斯明确指出:“在任何阅读经验中都存在着作者,叙述者,其他角色与读者之间的一种隐含对话。四者中的每一个在涉及到其他任何一个时,都在价值的、道德的、认知的、审美的,甚至是身体的轴线上,可以从同一到完全对立而变化不一。”[7]﹙P90~91﹚这种变化将导致距离,尤其是读者与叙述者及其他角色距离的产生。而在文学作品阅读或欣赏的过程中,这种距离会呈现出一种动态变化的过程。这种变化又涉及到作者、叙述者、角色与读者的信念与规范的问题。在价值、道德、理智、审美等诸方面,作者、叙述者、角色与读者之间的信念与规范之间往往有很大的距离,当然也可能存在一致的情况,或逐渐缩小这一距离乃至变得同一。而在作品中,作者透过其叙述者运用不同的距离控制,往往可以达到不同的效果。布斯列举了几种产生不同效果的距离变化的情况:叙述者在小说开始时远离读者,结束时接近读者;开头接近读者,结束时则远离读者;开头远离读者,尔后接近,但失去价值,结束时又远离读者;开始时接近读者,然后离开,但逐渐领悟,重又接近;开始时背离读者,以后离得更远(许多现代“悲剧”几乎没有什么悲剧性,原因就在于主人公在开始时就离我们如此之远,以至于我们对他毫不放在心上,而在结束时甚至离我们更远);开始时接近读者,结束时更为接近……而“从作者的眼光看来,他的作品的成功阅读将他的隐含作者的基本思想规范与假定的读者的规范之间的距离减少到零”。[7]﹙P92﹚也就是说,随着阅读或欣赏过程的展开,作者透过其作品中隐含作者所展示出的信念与规范,与读者之间的信念与规范逐渐趋于一致,读者或欣赏者在不知不觉中最终接受了隐含作者所显示的信念与规范。
在上述诸种叙述者、人物、读者与作者的距离控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叙述者开头远离读者而结尾接近读者这一距离变化中所达到的惊人成就。在这种情况下所出现的种种变化、以及对于读者所引起的反应都是相当大的。读者与文本的接触,就“使作品处于运动之中,正是这个过程最终产生了在他自身内唤醒种种反应的结果。”这样一来,就使读者的创造活动处于高潮之中。而对读者来说,“当阅读是积极的、有创造性的时候,它仅仅是一种愉快。”[6]﹙P350~351﹚这从另一方面解释了这种距离变化引人注目的原因。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戏剧中所出现的人物,在我看来,应可看作一个参与故事的人物叙述者。因而,小说这类叙事虚构作品中透过叙述者所发生的距离变化的情况,在戏剧中应是同样适用的。可以说,莎士比亚的《李尔王》中所展现出来的人物与读者之间的距离变化,正是上述这种理想的距离变化,它不仅使作品具有惊人的艺术感染力,也使其所刻画的人物具有尤为深刻的意义。那么,在《李尔王》中,人物叙述者是如何将自己的思想规范传达给读者,读者与人物叙述者的距离又是如何逐步缩小,读者的思想规范是如何通过叙述者的讲述与活动从而与隐含作者的基本思想规范趋于一致的呢?
《李尔王》的第一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这里,李尔作为一个刚愎自用的君王以一种带有戏剧性的夸张方式表现了出来。李尔王因为自己年纪老了,决心摆脱一切世务的牵萦,把责任交给年轻力壮之人。他准备把他的国土划分成三部分,分给三个女儿。然而,他先要听听孩子们对他表现的孝心:“孩子们,在我还没有把我的政权、领土和国事的重任全部放弃以前,告诉我,你们中间哪一个人最爱我?我要看看谁最有孝心、最有贤德,我就给她最大的恩惠。”[4]﹙P151﹚大女儿高纳里尔和二女儿里根均在父亲面前说出了一通冠冕堂皇的漂亮话:
高纳里尔 父亲,我对您的爱,不是言语所能表达的;我爱您胜过自己的眼睛、整个的空间和广大的自由;超越一切可以估价的贵重稀有的事物;不亚于赋有淑德、健康、美貌和荣誉的生命;不曾有一个儿女这样爱过她的父亲,也不曾有一个父亲这样被他的儿女所爱;这一种爱可以使唇舌无能为力,辩才失去效用;我爱您是不可以数量计算的。
里根 我跟姐姐具有同样的品质,您凭着她就可以判断我。在我的真心之中,我觉得她刚才所说的话,正是我爱您的实际的情况,可是她还不能充分说明我的心理:我厌弃一切凡是敏锐的知觉所能感受到的快乐,只有爱您才是我的无上的幸福。[4]﹙P151﹚
这些让李尔听来十分受用的漂亮话,使他决定立即划分给她们各自三分之一的国土。而深信自己的“爱心比我的口才更富有”[4]﹙P152﹚的小女儿考狄利亚,一如前文所述,说了实话。这样,她不仅被李尔斥之为“没有良心”,而且李尔发誓从现在起,永远和她断绝一切父女之情和血缘亲属的关系,把考狄利亚“当做一个路人看待”。[4]﹙P153﹚李尔以这样的言语行动,在读者面前立刻树立起一个刚愎自用、任性、强人所爱的形象。人人都渴望爱,父亲渴望儿女的孝心。然而,即便是父女之间的爱,也应是出自内心,而非口是心非。“爱只能发自内心,不可强求而得,不过强求别人相爱,也是相当普通的事”。[3]﹙P291﹚李尔所做的,正是这样的事,而当他强求而不可得时,他的表现是令人憎恶的。而且,当他的忠臣肯特大胆规劝他时,也被他严词拒绝:“你要是想活命,赶快闭住你的嘴。”[4]﹙P154﹚肯特仍不顾一切地继续规劝他,李尔却命令他在第六天“必须离开我的国境”,而此后十天内,如果“我们的国土上再发现了你的踪迹,那时候就要把你当场处死”。[4]﹙P155﹚按布斯所说,叙述者可能与读者自身的规范产生或多或少的距离,比如身体与情感上的,或道德与情感上的。[7]﹙P91﹚李尔以其言行,显示出自己的昏聩,这么一个面目可憎的人物,自然而然地一开始便在理智、道德、价值判断以至于情感等诸多方面远离了读者,而读者自然也与人物叙述者的思想规范保持着非常大的距离。
剧情的发展,使读者与人物叙述者的距离逐渐发生着变化。李尔的两个女儿各自在接受了一半的国土之后,对父亲的态度迅速发生了改变:高纳里尔将李尔的一百人的卫队裁撤为五十人,对李尔训斥有加;里根和她的丈夫康华尔公爵命令用足枷枷起了李尔派去的使者、大臣肯特,并对李尔说:“您该明白您是一个衰弱的老人,一切只好将就点儿。”[4]﹙P201~202﹚正是剧情的这些发展,人物之间相互关系的转变,以及他们在面对其他人物时态度的变化,逐渐缩小着读者与人物叙述者的距离,使读者的感情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从痛恨李尔转而逐渐对他产生了同情,对李尔转向神的倾诉也给予了理解:“神啊,你们看见我在这儿,一个可怜的老头子,被忧伤和老迈折磨得好苦!”[4]﹙P204﹚而对李尔因饱受自己女儿们的虐待而产生的复仇心也不会感到吃惊:“不,你们这两个不孝的妖妇,我要向你们复仇,我要做出一些使全世界惊怖的事情来,虽然我现在还不知道我要怎么做。”[4]﹙P204﹚第二幕末尾李尔的这一宣示,已经让读者感受到将会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而接下来大臣葛罗斯特在对他儿子的话中,进一步证明了即将到来的事情:“出人意料之外的事情快要发生了”,[4]﹙P212﹚原因在于国王受到了凌辱,“总有人会来替他报复的”。[4]﹙P212﹚
一如伊瑟尔所言,阅读活动可以被描绘成一种透视、前意象、回忆的万花筒。每个句子都包含有对下一句的“预观”,形成一种对即将到来的事物的取景器;而这也改变了“预观”,同样也成了已读过的东西的“取景器”。[6]﹙P354﹚读者将前后关联的种种事件逐渐连接起来,先前的事件既可以预示后来的事件,而后来出现的事件也可以改变对先前事件的“预观”。这在不同人物的身上会出现不同的情况。对于李尔的两个女儿来说,是沿着虚伪——无情——丑恶的方向发展;而对李尔来说,则是沿着昏聩——刚愎自用——醒悟——复仇的方向发展。在剧中人物的这一发展过程中,读者也逐渐对各个人物所展现的性格有了较为明确的认识,在这一认识过程中,也就使读者与人物的距离发生着变化。
受到自己女儿的凌辱而要进行报复,自然是无可指责的,而在对李尔两个女儿的丑恶表现看得一清二楚的读者来说,从对李尔的憎恶逐渐转为同情与理解也是十分正常的。李尔的一步步的变化,逐渐改变着读者在李尔一开始的行动之后对他的“预观”。在李尔的复仇出现之前,人们看到,流落荒野的李尔展现出他饱经磨难之后所出现的新的思想与情感。在倾泻不止的暴风雨中,李尔却不听大臣肯特之劝让其进茅屋中去,他在暴风雨中呼喊道:
衣不蔽体的不幸的人们,无论你们在什么地方,都得忍受着这样无情的暴风雨的袭击,你们的头上没有片瓦遮身,你们的腹中饥肠雷动,你们的衣服千疮百孔,怎么抵挡得了这样的气候呢?啊!我一向太没有想到这种事情了。安享荣华的人们啊,睁开你们的眼睛来,到外面来体味一下穷人所忍受的苦,分一些你们享用不了的福泽给他们,让上天知道你们不是全无心肝的人吧![4]﹙P213~214﹚
这里,可以说,是作品的一个转折,读者的思想规范与人物叙述者的思想规范之间的距离猛一拉近,不仅是对作为人物叙述者的李尔产生了同情与理解,而且与李尔在思想上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在价值判断的天平上,读者不由得大大地转向了李尔。被自己两个不孝而残暴的女儿逼得癫狂的李尔,此后在语无伦次的癫狂中却说出了许多充满真知灼见的话。在看到被挖去双眼的大臣葛罗斯特时说道:“一个人就是没有眼睛,也可以看见这世界的丑恶。”[4]﹙P247~248﹚当高高在上为王的时候,他看不到他所统治的世界的丑陋。而当他沦落到底层,与受苦受难的普通民众为伍时,当他自己也饱经磨难时,他看到了,并说出了真话。
李尔遭遇的灾难和不幸是如此深重,在悲剧中,“李尔的不幸是莎士比亚所有戏剧中最可怕的,甚至可能是全世界文学中最可怕的。”[8]﹙P107﹚情况何以会如此呢?这不能不与其时代关联起来。当《李尔王》于1605年在伦敦的环球剧院首次上演时,[1]﹙Px﹚正是英国处于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期。这时的英国,已经显示出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那种把一切人伦关系都淹没在利己主义冰水之中的特征。含情脉脉的封建人伦关系已经崩溃,赤裸裸的金钱与利害关系充斥着朝野。李尔的大臣葛罗斯特在第一幕就说出了这样的话:“亲爱的人互相疏远,朋友变为陌路,兄弟化为仇雠;城市里有暴动,国家发生内乱,宫廷之内潜藏着逆谋;父不父,子不子,纲常伦纪完全破灭。”[4]﹙P164﹚悲剧所描绘的就是一幅人与人之间天然关系全部破裂的图画。作为一个国王,李尔所拥有的是权势、地位与财富,这自然是他的两个女儿与臣下所孜孜以求的,因而,他们可以在他拥有这一切时对他卑躬屈节,说尽好话。而当他的手中不再握有这一切时,他在这些曾对他卑躬屈节的人们面前就出现了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在读者的眼里也逐一显现出来。失去权力之后,“他仅仅成了一个老人,然后,是一个在他那样的年纪未受到尊敬的老人,接着,是一个处于疯狂中、带傻乎乎的孩子气的老人,到戏剧的结尾,则是一个处于绝望中的人。”[1]﹙Pxii﹚从李尔的变化中,人们可以发现时代所刻下的深刻的印记。
李尔的刚愎自用是从对小女儿考狄利亚的态度开始的,也是以对考狄利亚态度的彻底转变而告终的。在第一幕,当他的大女儿和二女儿对他反目之后,他意识到敢于向他说真话的小女儿考狄利亚是正确的,但还是认为考狄利亚仍有小小的错误:“考狄利亚不过犯了一点小小的错误,怎么在我的眼睛里却会变得这样丑恶!”[4]﹙P177﹚而当考狄利亚看到两个不义的姐姐虐待自己的父亲,就兴兵前来讨伐她们而被捉住,被缢死时,李尔的悲痛达到了极点。他抚着考狄利亚的尸身,说出了这样一段话之后悲愤地死去:“我的可怜的傻瓜给他们缢死了!不,不,没有命了!为什么一条狗、一匹马、一只耗子,都有它们的生命,你却没有一丝呼吸?你是永不回来了,永不,永不,永不,永不,永不!”[4]﹙P272~273﹚这段话“是莎士比亚笔下最痛苦的一节”,[9]﹙P240﹚从中可见李尔王哀痛之深,也足见李尔从开始时对考狄利亚显示的刚愎自用已完全转为对她的深厚的爱与痛惜。连同他此前所显示出的对普通民众的爱,以及对这一丑恶世界的认识一起,李尔完成了他性格的彻底转变。
读者的阅读活动,是一种参与文本创造的活动。读者通过逐渐融入作品,参与这种创造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完全有可能改变其原有的认识,从而对人物、事件作出新的阐释,得出新的结论。我们可以从19世纪的一位批评家阅读夏洛蒂·勃朗特《简·爱》的反应中看到这种变化:“我们用了一个冬日之夜来读《简·爱》,对我们曾经听到过的对此书的过分赞誉有点愠怒,坚定地下决心要像克劳克(Croker)一样持批评态度。但是,随着我们的阅读,我们既忘了赞扬也忘了批评。我们与简同甘共苦,融为一体,最后大约在早晨四点与罗切斯特先生结婚了。”[6]﹙P364﹚在《李尔王》中,也可以看到与此相类似的反应过程,当然,这一过程与阅读《简·爱》所产生的变化原因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读者与文本中的人物之间所出现的距离变化的状况是不一样的。
李尔在性格上的巨大转变势必促使读者发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李尔的性格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促使李尔性格转变的原因何在?同时,在观察这个人物的时候,读者自身的思想情感也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一如俄国批评家杜勃罗留波夫所说:“在观察他的时候,我们起初感觉到对这个昏狂暴君的痛恨;但是,随着剧情的发展,我们却越来越会把他作为一个普通的人而加以谅解;到了最后,我们就已经不是对他而是为了他、为了整个世界——对于那种甚至能够把像李尔这样的人也引到昏狂的地步的野蛮而非人的社会状态,充满着愤怒和激烈的仇恨。”[10]﹙P131~132﹚联系悲剧出现的时代,联系英国十六七世纪的状况,人们不难理解李尔的遭遇,也不难理解李尔历经磨难后所出现的思想变化。而在这一巨大的变化中,人们也可以理解隐含作者在作品中所展现出来的价值意义与道德规范。在悲剧中,正是从一开始时,人物叙述者在价值、道德、理智、情感、思想等诸方面远离读者,到最终与读者几乎在所有这些方面都融为一体,作品中隐含作者所展示出的信念与规范,与读者之间的信念与规范逐渐趋于一致,读者在不知不觉中最终接受了隐含作者所显示的信念与规范。这样一来,作品既使读者真正认识了李尔,与他的思想情感发生了强烈的共鸣,也完成了这一令人难忘的形象的塑造;不仅使这一人物取得了一种极好的效果,也赋予整个作品以深远的意义。
[1]H. K. Girling. Introduction to King Lear[A]. In William Shakespeare, The Tragedy of King Lear[M]. New York: Airmont Publishing Company, Inc. 1966.
[2]李毅. 二十世纪西方《李尔王》研究述评[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1996,(4).
[3][英]奈茨. 李尔王[A]. 殷宝书译.杨周翰. 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下)[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4][英]莎士比亚.李尔王[M].朱生豪译.方平校. 莎士比亚全集(第九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5][英]格兰威尔-巴克. 论《李尔王》[A].殷宝书译. 杨周翰. 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下)[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6][德]伊瑟尔.阅读过程:一个现象学的论述[A].朱立元译. 朱立元,李钧.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下卷)[C].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7]Wayne Booth. Distance and Point of View: An Essay in Classification[A].In Essentials of the Theory of Fiction(Third Edition)[M].Eds., Michael J. Hoffman and Patrick D. Mupph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5.
[8][美]阿兰·布鲁姆,哈瑞·雅法. 莎士比亚的政治[M].潘望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9][美]格林布兰特.俗世威尔——莎士比亚新传[M].辜正坤,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10][苏]阿尼克斯特.英国文学史纲[M].戴镏龄,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