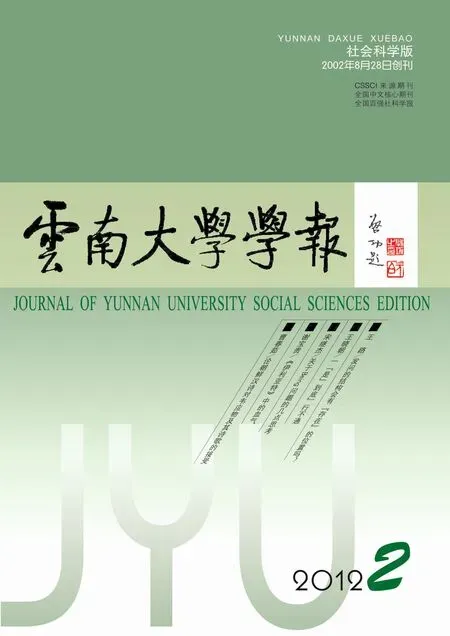方龄贵先生:我的父亲与导师
方 铁 口述;张昌山,姚铁军 撰文
[云南大学,昆明 650091]
一、人生经历
我父亲的祖籍是在河北滦县回头庄。我们祖上大概在清朝后期跟着“跑关东”来到今天的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县老达房方家岗子。后来,曾祖父逃荒到吉林省德惠县,祖父又辗转流落到郭尔罗斯前旗,就是今天的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祖母是郭尔罗斯前旗蒙古族人。1918年5月21日,父亲出生在前郭县吉拉吐乡锡伯屯村。此后,又随祖父迁往扶余县。
父亲8岁时进入吉林省扶余县第一区第四初级小学读书,后升入县立第一高等小学。“九·一八”事变后便失学在家劳动。1933年在吉林省前郭旗西北屯私塾读书。1934年在吉林省扶余县初级中学读书。1935年初入关到北平,先在知行补习学校学习,后考入北平东北中山中学高中部读书,并随校迁往南京板桥镇。抗日战争爆发,学校迁往湖南湘乡县永丰镇。1938年,父亲高中毕业,在长沙报考了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这个时候岳阳失守,长沙危急,父亲等不及发榜便和另外五位同学一起徒步从长沙走到重庆,历时四十六天。途经沅陵,从报纸上得知自己被录取在西南联大。到了重庆,路费又成了问题,父亲就只得向老师和同学借。当时有一个青年会,可以帮助沦陷区的同学,也资助了父亲一些路费。在1938年底,父亲终于到达昆明。等他去西南联大报到时,才知道已经是规定时限的最后日子,再迟一天就要编入下一个年级。这年父亲20岁,从此便和西南联大,特别是和云南、昆明结下了不解之缘。1942年秋,父亲从联大历史系毕业,接着考入北京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史学部,师从蒙元史大家姚从吾、邵循正两位教授,专攻蒙古史、元史。1946年5月,由姚从吾先生主持,聘请雷海宗、徐炳昶、毛子水、向达、唐兰、吴晗几位先生组成答辩委员会,通过了毕业论文《元朝建都及时巡制度考》的答辩,父亲获得硕士学位。
父亲是研究生毕业前结婚的。我母亲是云南大姚人。昆明当时有一个作家叫刘澍德,是我父亲的东北老乡,他在母亲的家乡大姚中学教过书,是刘先生介绍我父亲和母亲认识的。父亲在20世纪80年代撰写了长文《忆刘澍德》,纪念这位故人,但主要是说刘先生的为人与学识。父母亲于1945年结婚。抗战胜利后又面临一个去留云南的问题。父亲已在昆明结婚了,母亲又是云南人,在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北返时,父亲选择留在昆明。父亲研究生毕业,由恩师姚从吾先生介绍给云南大学历史系主任徐家瑞,就在云南大学历史系做讲师。父亲在云南大学做专任教师只有一年多点的时间,但我们家从此就与云南大学结缘。后来父亲还在云南大学兼课,研究生论文答辩也常常请父亲作评委,当然各种学术交往就更多了。我母亲是云南大学生物系毕业的,我也是云南大学毕业的,我姐姐方慧师从云南大学江应樑教授攻读博士研究生,后来我和方慧姐姐都在云南大学工作。父亲在云南大学工作期间,他的老师、昆明师范学院历史系主任蔡维藩先生再三托人跟父亲讲,希望我父亲回到师院。所以父亲在云南大学教书的同时,还在昆明师院兼课,代姜亮夫先生讲中国通史。1947年,父亲就转入昆明师院,先后任历史系副教授、教授兼系主任,主要讲授元史学、蒙古史、辽金元史、中国史学史、史学概论、中国通史等课程。父亲后来还担任过师院图书馆馆长。1987年退休。虽然退休但他并没有休息,仍为云南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生上课,讲蒙元史;继续进行学术研究,笔耕不辍。父亲还是《春城晚报》的“铁杆”作者,常用辛代等笔名发表文章。父亲的文笔非常优美,记得他去内蒙古包头市参加学术会议,到成吉思汗陵参观,父亲作了详细的笔记,回来后写成《包头寻访记》,刊登在《春城晚报》。2007年8月,云南师范大学与中国元史研究会、中国蒙古史学会在昆明举办了“中国蒙元史学术研讨会暨方龄贵教授九十华诞庆祝会”,父亲的道德文章受到了大家的肯定与敬仰。2011年10月22日,父亲安详地离我们而去,享年94岁。父亲在遗嘱说:“书不能流散,要永远保存下去”。父亲走时还惦记着自己的书,书是他的生命。今天,父亲手书的“书不出室”字条仍贴在书架上。
关于父亲的民族成分,父亲依惯例一直从祖父填报的是汉族。解放后,大家知道了父亲的民族出身,认为父亲是蒙古族,这让父亲很受触动。我的祖母是蒙古族,父亲身上流淌着蒙古族的血脉,而且平生有许多蒙古族亲友,朝夕相处,往来频繁。成人后又在名师指导下以研治蒙元史安身立命,和蒙古族有着深厚的民族感情和血肉联系。父亲申请民族成分从母,由汉族改为蒙古族,并递交了必要的证明材料和申请书,经有关部门审核批准,把民族成分改为了蒙古族。我的民族成分现在也是蒙古族,我的孩子也是蒙古族。父亲对蒙古族感情很深,对民族盛事非常热心。2003年,父亲接受邀请,饱含深情地撰写了《蒙古人进入云南七百五十周年纪念》碑文。2006年,在云南召开中国蒙古史学术研讨会时,父亲撰写的碑文由内蒙古大学副校长胡格吉勒图教授译成蒙古文,蒙汉双语同时刻在云南通海县兴蒙乡的纪念碑上。云南不少地方的蒙古族同胞甚至将这篇纪念碑文用于祭奠祖先。
在父亲的生命历程中,书占据着特殊重要的地位。前面说过,父亲曾兼任过学校图书馆馆长,“文革”中有人贴父亲的“大字报”,说父亲是宣传“封、资、修”,说父亲当了馆长还花了三千块钱买一部书。其实是三千块钱买了一部四部丛刊,有几千本,非常珍贵。父亲还买外文书,这又被说是宣传资本主义。而买俄文的书,被说是宣传修正主义。后来一落实,都不成立。当时父亲买的这些书,现在都成了学校图书馆的镇馆之宝了。父亲为人很低调,记得“文革”曾有一段时间买不到煤,他说,买不到煤了,看来只有烧书了。低调的父亲有时也会幽上一默,虽然是一种深刻痛苦的幽默。书是他的生命,怎么舍得烧掉!
二、师承与学术交往
父亲走上蒙元史的研究之路,是与姚从吾先生和邵循正先生的指引分不开的。按照西南联大的规定,历史系的学生除必修中国通史、西洋通史、中国近代史外,还要选修两门断代史,父亲却选了四门:宋史、辽金元史、元史、明清史。其中父亲最感兴趣的是辽金元史和元史。辽金元史是姚从吾先生讲授,辽金元都兴起于东北,辽金元史很大部分讲的是东北史,是父亲家乡的历史。邵循正先生主讲元史,由于父亲身上流着蒙古族的血脉,与生俱来,因而对此内容倍感亲切。学校要求学生毕业前要交一篇毕业论文,导师由自己聘请。父亲请邵先生为指导教师,并商定论文题目为《元代边徼诸王叛乱考》。这是父亲有关蒙元史的第一篇习作,但却由此引发了父亲研究蒙元史、走治学道路的决心。1942年父亲在历史系本科毕业后,考取了北京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史学部的研究生,姚从吾、邵循正两位先生同为父亲的导师,姚、邵两师均是蒙元史大家,父亲很崇敬他们。在艰苦岁月中,两位先生对父亲倍加呵护,悉心栽培,父亲一辈子都铭记两位恩师的谆谆教诲。
(一)师从姚从吾先生
姚先生名士鳌,字占卿,别号从吾,河南襄城人,1894年10月7日生。早年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国学部毕业后赴德国留学13年,师从汉学家佛朗克教授及蒙古史专家海涅士教授,治匈奴史、蒙古史。他曾在柏林大学任讲师,后应北京大学之聘,任史学系教授,主讲蒙古史、匈奴史,名声大振。姚从吾先生教父亲习读汉文史料,不但把案头常用的四部备要本《元史》赠予父亲,要父亲认真点读,还把叶刻本《元朝秘史》、《蒙兀儿史记》长期借父亲学习,指导父亲正确进行史料的搜集、整理、辨伪及运用。先生要求父亲凡有述作,必须尽量用原始材料,万不得已引用转手史料时,必须注明出处,切忌直接称引。先生还规定父亲每星期三下午向他汇报读书心得,呈交读书笔记和对《元史》的圈点,父亲若有失误,先生立即检出指正。元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特殊的朝代,一般认为大都是元朝唯一的政治统治中心,但先生认为并非如此。他把考证的重任交给了父亲。父亲虽有些惶惶然,但还是通过搜检《元史》及大量的有关史料,在10万多字的《元朝建都及时巡制度考》论文中明确提出,元朝实行大都和上都两都并立的制度,大都便于对内地的统治,上都着重对蒙古故地的照管,可以说有点二元帝国的意思。硕士论文答辩时,父亲简明而清晰地阐释了论文《元朝建都及时巡制度考》的观点。当论文获得全票通过时,最为高兴的是父亲的导师姚从吾先生,先生激动地说:这是元史研究的一大突破,是对元史研究的一大贡献。先生对父亲在生活上也十分关心。抗战期间,物价飞涨,研究生的津贴根本不够用,先生知道父亲举目无亲,除了同意父亲在中学兼课外,还设法让父亲在他所主持的中日战争史料征集委员会帮助翻译一点日文资料,取得一些报酬。另外还在联大的师范学院文史地专修科为父亲谋了一个半时教员的位置,通过讲课,让父亲进行教学实践,同时也增加了父亲的收入。父亲结婚时,先生欣然担当主婚人。后来先生去了台湾,晚年集中力量研究辽金元史及蒙古史,在《蒙古秘史》的研究上用力最多,成就卓著。解放之前先生还来信让我父亲给他买书,后来就没有联系了。先生1970年4月15日逝世于台北,享年七十有六。其门人故旧在先生逝后编辑出版了《姚从吾先生全集》,共有七卷。
(二)师从邵循正先生
邵先生字心恒,福建福州人,1909年11月21日生。先生毕业于清华大学政治系,后考入清华研究院,改攻中国近代史、蒙古史。后来留学法国,师从东方学大师伯希和治蒙古史及波斯文,成绩优异。先生后来又往德国柏林大学深造蒙古史一年多。回国后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北京大学讲授中国近代史、元史、蒙古史、波斯文。先生精通波斯、蒙古、突厥、满、英、日、法、德、俄等多种语言,特别是精于语言对音之学,这也深深影响着父亲在多语言治蒙元史方面用力甚多。父亲本科时听先生讲元史,毕业论文又受先生指导。父亲读研究生时,先生开设了蒙古史研究、西方学者对中国史地之研究两门课。当时听讲的除父亲以外,还有一位清华的研究生,后来这位同学中途辍学,只剩下父亲一个人。在蒙古史研究课上,邵先生主要是讲《元朝秘史》、《至元译语》、《华夷译语》,还教父亲波斯文,并亲手用印蓝纸复写作为教材发给我父亲。先生充分掌握中外蒙元史料,并以渊博的语言学和蒙古学知识,循循善诱,把父亲带入了一个研究蒙元史的学术世界。《元朝秘史》总译虽出自蒙古文原作,但错讹、疏漏之处仍为数不少,先生根据标音蒙古文并参照中外史料逐条补译,文笔之古朴与旧译相仿佛,父亲在先生的补译中吸收着最新营养。《至元译语》是研究元史的必备之书,向达教授有一部手抄本,先生亲自为我父亲相借,师之恩情,父亲终身未忘。遗憾的是,父亲1946年进行论文答辩时,先生已赴英国讲学,未能在场与学生同享成功的喜悦。那一年年末先生才回国,先在清华大学,后调北京大学,父亲则居云南以至终老,师生从此彩云南北。直到1961年,父亲回东北老家探亲,路经都门,始获到北京大学探望老师。师生一别16年,相见之下,恍如隔世。先生对我父亲的来访,喜出望外,异常激动。交谈中,父亲说起当年先生关于《元朝秘史》总译的增补工作,并问先生此稿的完成情况。先生感叹说稿已完成,但在流徙中遗失,正拟校订《秘史》以成定本,便有调父亲入京协助校订《元朝秘史》之议。父亲为有机会继续从先生问学而庆幸,自然从命。先生当即将小林高四郎的《元朝秘史之研究》一书交给了我父亲,要父亲译出为校订《秘史》之用。父亲竭三年之力,将小林书译毕,寄呈先生审正。后来先生通过中华书局和北京大学几度商调父亲到其历史系工作,后因多种原因调动未成,书虽译了出来,事情却搁下了。先生1973年辞世,享年六十有四,未曾想1961年北京一晤竟成师生永诀。父亲每每思之,犹有余憾,然而始终记得要做先生门下一名及格的学生。1982年,元史研究会主编的《元史论丛》创刊,父亲即刻把自己保存多年的先生论文手稿整理出来,寄往《元史论丛》第一辑发表,以告慰先师在天之灵。
(三)与沈从文先生的往来
东北发生战事,父亲远离家乡求学。漫漫求学路,父亲把对家乡和父母的思念,把在炮火中颠沛流离的学习生活写成文章,寄给上海的《申报》和香港的《大公报》,同时也可换取一些稿费以备零用。父亲说他第一篇文章的稿费是三毛钱。父亲上中学时一位老师曾给父亲介绍了沈从文先生的《边城》,后来父亲写文章受沈先生的影响很大。父亲也曾对我说过,1938年他高中毕业报考西南联大历史系,主要是想读清华大学历史系,因为父亲崇拜的作家端木蕻良、孙毓棠都是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的,以为清华历史系是作家的摇篮。父亲赴重庆路过沅陵时,曾经去找《边城》里的女主人公翠翠。父亲在联大的头两年参加了一个叫做“南荒社”的文艺社团,并且是南荒社的中坚力量。萧乾曾在《大公报》担任副刊编辑,虽未和父亲谋过面,但编发过父亲的文章。他和沈先生是至交。当时沈先生在联大教书,住在昆明青云街靛花巷。父亲由萧乾介绍,拜识了沈先生,从此趋访无虚日,凡有所习作,径送请沈先生过目斧正。有时稿子回到父亲手中,发现原稿经沈先生批改,不但加工润色,甚至对个别的笔误都细心予以纠正,连标点符号也不放过。父亲说:沈先生不但为我修改文章,还经常把一些中外文学名著借给我阅读,其中有一本是陈彬和选注的《元朝秘史》。由此我知道《元朝秘史》是一部非常重要的蒙古文典籍,是研究蒙古历史、文学、语言和社会制度必不可少的历史文献。沈先生借书给我时,要我注意此书文字是多么古朴自然,富有生命活力,希望我在书中古朴清新的情节和文字中获取文学创作的营养。父亲深为书中蒙古草原的磅礴气势和粗犷风情所吸引。父亲曾说过因为我的祖母是蒙古族人,因而对之倍感亲切。未曾想此书竟开启了父亲研究蒙元史的学术之路。沈先生的栽培给了我父亲意外的重大收获。父亲移文就史,但治史而不忘修词为文。父亲重师生情谊,一生都很感激沈先生。1988年沈先生去世,父亲十分悲痛,撰文《哭沈从文先生》,此情可追。
(四)与白寿彝、何兆武、汪曾祺方国瑜、李埏诸先生的往来
1975年,父亲应白寿彝先生之约,入京参加编写《中国通史纲要》。是年底,有一天早晨起来,父亲突然晕倒,因身体原因父亲只能从北京回到了昆明。但是父亲还是完成了《中国通史纲要》中很多人物的编写工作。1976年初,我陪同父亲到北京看望白先生,那时先生已是满头白发,他为人和蔼可亲,给了我很多鼓励。这部书198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还被译为英、法、德、俄、日、西班牙、阿拉伯等语种,行销海内外。
父亲说:“何兆武、汪曾祺都是我的老朋友。何兆武每次到昆明来,都到我这儿来叙旧聊天。汪曾祺和我都是沈从文先生门下的师兄弟,我搞文艺的时候跟汪曾祺来往比较多,后来他搞文,我搞史,虽不是同行了,但却是至交。”
父亲与方国瑜先生过从甚密,对方先生非常尊重。父亲曾领着我去看望方先生。方先生逝世10周年时,父亲亲自撰文《方国瑜先生对元代云南史地研究的贡献》,高度评价方先生功业流布人间,足以不朽。
父亲和李埏先生是当年西南联大留在昆明的同学。父亲说:李埏跟我联系比较多。我们都是北京大学研究所的研究生,也是云南大学的同事。不仅父辈有同学同事之谊,我与李先生的长公子李伯重也是情同手足。
三、学术研究
父亲是大家公认的蒙元史学家、中国历史文献学家,重史料与考证,懂得英、日、法、德、俄及波斯、蒙古、突厥、八思巴等多种语言,特别是善于以多语言治蒙元史,一生著述甚多。据不完全统计,在《历史研究》、《民族研究》、《史学史研究》、《社会科学战线》等国内刊物上发表过学术论文70余篇,出版了《元朝秘史通检》、《大理五华楼新出元碑选录并考释》、《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通制条格校注》、《古典戏曲外来语考释词典》、《元史丛考》专著6部,还有译著多种。父亲的学问与贡献受到了国家、社会和学界的高度评价和赞扬,被誉为中国蒙古史和元史研究的泰斗,先后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云南省人民政府社科优秀成果荣誉奖、国家新闻出版署优秀辞书奖、教育部中国高校社科优秀成果奖、云南教育功勋奖和云南省有突出贡献的哲学社会科学老专家、云南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等多项殊荣。父亲的学问可谓博大精深,我的研究与了解还不深广,故而仅就父亲的六部专著作些介绍。
(一)《元朝秘史通检》
该书五易其稿,父亲耗时多年,1986年由中华书局影印出版。《元朝秘史》又名《蒙古秘史》,13世纪成书,是研究蒙古历史、社会、文学、语言最重要的古典文献,明初由蒙文译为汉文,为蒙元史学者必治之书。为着便于寻检,往往都要自己动手,编制一个有关人名、地名、种姓名的索引,这是一件很必要而又很烦琐的工作,做起来既耗时又费事,是很不容易做好的。20世纪初,国学大师王国维就看出问题所在,曾致力于《元秘史山川地名索引》的著述,但因沉湖而成未竟之作;日本学者箭内亘曾著《元秘史地名索引》和《元秘史部族名索引》,但均未见公开发行。父亲初从沈从文先生处得陈彬和选注的《元朝秘史》,后著《通检》,系以《四部丛刊》三编本《元朝秘史》、叶氏观古堂《元朝秘史》和俄藏本《元朝秘史》为蓝本逐条对校,于每个条目所在收专名之下,注明所见卷、页、节次,用拉丁字转写对音,并立“对校”一栏据叶氏观古堂刻本、俄本逐条勘对,别其异同,正其讹误,又立“附见”一栏,将《圣武亲征录》和《元史》所见的相关异名,收录互见。此书既出,可免同行学人自编索引之劳,成为了国内外学者不可多得的必备工具书。多年过去了,《元朝秘史通检》已难在坊间一见。2006年,我姐姐方慧到北京开会,一个外地学者在旧书摊淘到一本《元朝秘史通检》,他向方慧炫耀说这是花2000元淘到的一本好书,这本书现在已是千金难求了。父亲说这本书出版时才12.5元。
(二)《大理五华楼新出元碑选录并考释》
从1253年忽必烈率大军进入云南到1381年梁王把匝剌瓦尔密投湖自杀,蒙古族对云南的有效统治长达128年,这期间的碑刻、铭文遍布云南各地。1972年,云南大理城拆除明初修建的五华楼,发现了一批垫做石脚的元碑。时值十年动乱,对“四旧”破坏之不遑,县文化馆所收不过有限的几通,多数被用来砌筑县体育馆篮球场的看台。1977年,昆明师范学院副院长、著名云南地方史专家王云教授回乡探亲, 参观大理县文化馆,发现数条元碑, 得知从五华楼所出, 还有一些砌入球场看台, 遂去踏勘, 惊喜地发现有大量宋元碑刻。回昆明后, 王云先生向云南省文化局领导作了汇报。省文化局拨出专款,昆明师院派出父亲与王云、潘鐇、杨德华诸先生于1979年到大理, 与县文化馆的人士一起清理,进行抢救性拆除,获得宋代石碑3通、元代石碑66通,并有纪年为宣光九年的北元碑一通,远比《新纂云南通志》金石考所收录的要多。碑文不仅对蒙元史研究有极高的价值,而且为研究南诏史、大理国史以及白族史、彝族史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材料。父亲以其扎实的元史功底对这些石碑碑文加以注释,以《大理五华楼新发现宋元石碑刻选录》为题,于1980年提交给南京中国元史研究会,此后,父亲开始对宋、元碑刻进行系统研究,先后写出十几篇论文,并与王云先生合著《大理五华楼新出元碑选录并考释》,于2000年在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分上下两编,上编《选录》部分,由父亲与王云合作,下编《考释》所收论文为父亲独撰。
(三)《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
元朝是蒙古族建立的王朝,统治时间近百年。入明以后,蒙古族在各方面仍有较大的影响。元明戏曲中有一些蒙古语词是很自然的,对这些语词的解释,历来是一个难题,相关专著寥寥。父亲为了搜寻元代社会经济史料,曾遍检元明戏曲书,发现其中有不少源于蒙古语的词语。父亲早在学生时代就熟读《元史》和《元朝秘史》等基本史料,并且将搜寻范围扩大到各种元人文集、笔记杂著和通俗小说,从中汲取旁证材料。在语言资料方面,父亲利用各种蒙古语辞书和蒙古语族、突厥语族及满——通古斯语族的语言调查材料,还旁及波斯、普什图、阿拉伯、梵、印地、俄、芬兰、匈牙利等多种语言。父亲这本书是先以油印本提交1981年在乌鲁木齐召开的蒙古史学会年会。并曾请元曲大家吴晓铃先生指正。书内收蒙古语87事,后吴先生赴美国讲学,讲到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时,曾出示此油印本,引起在场的美国元曲大家韩南(P.D.Hanan)教授和加拿大元曲大家施文林(Wayne Schlekh)教授的极大关注,要求允许复制。1991年由汉语大词典出版社正式出版,内容增订为蒙古语114事,如将各种异写包括在内,实得203事,书末附有“引用和参考书目”,共收汉、蒙古文和日文、俄文、西文文献近400种。为便于读者检索,还附了“词目索引”。最后是英文提要。本书出版前后受到很多学者的高度重视和赞扬。季羡林先生的评价是“不同凡响,可喜可贺”。 吴晓铃先生誉之为“必传”之作。杨志玖先生认为“精雕细刻”、“叹观止矣”。
(四)《古典戏曲外来语考释词典》
此书为《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的姊妹篇。《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出版后,父亲从中外有关文献及个人钻研中又有新得,同时收到许多学者和读者的来信,认为蒙古语不仅在元明戏曲中有,明清小说及清代戏曲中也存在。父亲从而对旧作进行了大量的修订增补,他在《金瓶梅词话》、《醒世姻缘传》及400多种清代戏曲中搜检出近百条蒙古语,本着“元明补充、清代全录”的原则,把清代戏曲中的蒙古语也收了进去,所收蒙古语系目已近200条,并有部分来自波斯语、阿拉伯语的词语及来自满洲语的借词。书名因更为《古典戏曲外来语考释词典》,并由汉语大词典出版社、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发行。澳大利亚罗依果教授(Prof.I.de Rachewiltz)说自己几乎每日用到此书,当是对之极大的肯定。
(五)《通制条格校注》
《通制条格》是元朝主要政书《大元通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历来与《元典章》相提并论,里面有很多跟元朝典章制度、法律、社会经济有关的史料,原30卷,现存22卷,是研究蒙元史和中国法制史的重要典籍。国务院古籍出版规划小组把《通制条格》列入《古籍整理出版规划》,要求编著一部《通制条格校注》,这项艰巨的任务落到了父亲肩上。校注《通制条格》容不得一丝懈怠,父亲费时10年,摘抄卡片近万张,寻检有关史料,旁搜元绍,对文本认真细致地作了校点,就书中有关人名、地名、名物制度兼及书中偶见蒙古语和其他外来语等一一作了注释考订,数易其稿,终于使《通制条格校注》于2001年交由中华书局出版。罗依果教授来信说在收到该校注之前,他用日本人著作,此后可不借用日本人所作了。
(六)《元史论丛》
该书2004年由民族出版社出版。书中收录父亲20篇有关元史的文章和一篇译稿——小林高四郎的《元朝秘史·引论》,副标题是《元朝秘史研究小史》,此外还有几篇关于《通制条格》的文章,比如《通制条格人名考异》,《通制条格释词五例》,《通制条格札记》,《通制条格中有关云南史料举证》,《读〈黑城出土文书〉》,《为“不怕那甚么”进一步解》,《通制条格行文体例初探》等。这本书可算作《通制条格校注》的补编本。全书收入了父亲不同时期的一些重要论文,基本勾勒出了他一生研究元史的基本轮廓。
父亲一生著书立说,完成了这六部著作。这些书也就奠定了他在蒙元史研究中的地位。父亲的史学著作严谨而又多有文采。这严谨归功于姚从吾和邵循正两位老师,这文采得益于沈从文大师的影响。父亲认为,治蒙元史,基本功要扎实,要熟练掌握《元史》等基本史料;眼界要宽,纵向了解《宋史》、《辽史》、《金史》、《明史》等,横向还要懂得世界史;要善于利用参考书和工具书,手头离不开常见的清代著作;治学要严谨,引用必须注明出处,遵守学术道德。遗憾的是,父亲退休较早,没有直接招收过研究生,学问和精神的直接传承多少留下了些遗憾。好在学界尤其是一些后学还感受到了他的价值并给予了关注,我想,有价值的学术及其精神,一定会得到继承并发扬光大的。
四、对后辈的关心和教育
父亲是学者,一生从事蒙元史研究。父亲更是教育家,教过小学、中学和大学,教过本科生、硕士生,指点过博士生,育人无数,桃李满天下,很多学生成了各行各业的骨干和领军人物。父亲20岁到了云南,就再也没有离开过这片红土地,为云南教育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其人其文入选了《云南学术大师文库》,父亲还被授予云南教育功勋奖,其为最年长者。父亲曾自许“教书不但是我的职业,也是我的乐趣,所谓‘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我觉得我的生活很充实、很满足、很幸福、很自豪,可以说,我并没有虚度年华。我常讲,人如果有第二次生命,我将毫不迟疑地仍然选择教书这个行当,不离开三尺讲坛。”学生们都说我父亲课讲得非常好,口齿清楚,逻辑性强,娓娓道来,从从容容,临下课开始总结,总结完了下课的钟声就响起来了。父亲从教60多年,言传身教,教书育人,“愿为红烛甘做人梯”是他的人生写照。
解放前,父亲在昆明师范学院教过一个学生,他每逢中秋节、春节都来家里看望我父亲,父亲都留他在家吃饭。后来父亲知道他家穷,每到过节都请他到我家吃饭,多年如一日。父亲是一辈子爱护学生。
2004年的一天,云南师范大学杨德华教授带着他的三届元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和跟班进修元史的杨剑利向父亲请教如何学习蒙元史。父亲面对年轻的治元学者,由惊讶转为欣慰。他惊奇的是9人都是元史专业。当他逐一落实各位学生的姓名后,脸上露出欣喜微笑。他说:元史难学,蒙古人名、地名难记,一定要下决心、下苦功才能学好。相信通过努力,云南有望成为中国南方蒙元史研究的中心之一。杨德华教授是父亲十分器重的学生,他所在的元史专业的硕士点在云南省是唯一的。可惜的是杨德华教授英年早逝。
父亲对子女注重言传身教。我们可以说是在父亲的书堆里长大的。父亲有藏书6000余册,大部分都是线装书。小时候有的是时间读书,读了中外名著再读各类专著,前后也不知道读过多少书。父亲还给我们订《民间文学》等杂志,从图书馆为我们借书看。即使在“文革”期间,父亲对我们也管得很严,是要求我们在家里好好读书。父亲每次和来访的有关专家学者交谈时,都让我陪同在侧,我也有机会耳濡父亲的学问,目染大师们的风采。父亲一生问学,可当我们兄弟姐妹都在上山下乡时,父亲曾痛心的感叹:我教了一辈子书,子女却不能上大学!受父母书香沐浴,加之国家政策转好,后来我们都考上大学。我姐姐方慧是云南解放后培养的第一个女博士,现在是云南大学中国少数民族法制史的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先后获全国优秀教师、全国师风师德标兵等称号。我先在瑞丽当了3年知青,又在楚雄当了7年工人,后来父亲鼓励我,还帮我油印复习资料,我考上了云南大学历史系,并且留在了云南大学工作,当了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像父亲一样我也爱读书爱买书,我现在的藏书有两万多册。我和父亲同为《中国历史大词典》的撰稿人,在2005年10月云南省优秀社科成果表彰会上,我们父子的作品都获奖了。父亲和我们在家谈得最多的还是读的书、做的学问。父亲经常指导我们的学术和学问,亦曾亲自给我们指点并修改论文,改得非常专业、非常仔细。后来年事高了,父亲还是经常看我们写的文章。我们有书出版了,送给父亲,父亲放在书桌前,常常拿起来看一看,感觉很欣慰。也许是这浓郁的学术熏陶和严格要求,我们家两代人共有八位是正、副教授,其中两位还是博士研究生导师,很多人说我们家是文化世家、学术世家。内蒙古电视台制作的电视剧《蔚蓝的天空》,就实地拍摄了我们家的情况作为素材。父亲对我们的成长影响深远。
我们的父亲,我们的导师,虽已离世,但他的学问与精神永在。坐在父亲20世纪70年代设计的卡片桌前,回想父亲给我们的教诲,我们是幸福的。父亲还是穿一件深蓝色的中山装,目光炯炯,神采奕奕,满是慈祥。道德文章,日月同辉,父亲永远活在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