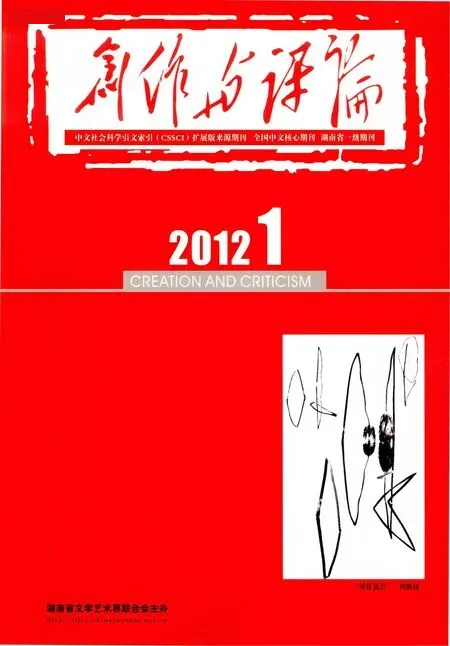去波恩(短篇小说)
■ 徐则臣
进站之前,我和小周窝在他的二手商务车里说话。暖气开着,天有点儿冷,小周建议先别进站,进去了也是瞎挨冻。我知道他是想和我再多说一会话,能和一个中国人在异国他乡如此深入和漫长地聊天,对他来说机会并不多,虽然他兼职导游,接的团绝大多数都是中国人。小周说,要是去中国像去瑞士、法国、意大利、比利时那样方便就好了,开车几小时就到。要是。要是。从前天开始到现在,我至少听他说了五十个“要是”。要是在天津就好了。要是回趟家像串门那么方便,他觉得待在这里也不错。要是在国内,他就开一个旅行社,专门接待德国人。要是小魏去国内找工作,回去后他们就要孩子。要是。要是。
“要是——你烦了?”他发现我两眼发直,显然在走神。
“哪里,你说。”我指着车站顶上的巨大的球,相对于古典的欧洲式建筑它有点现代了。不过我还是说,“很漂亮。”的确很漂亮。单看都很漂亮。
法兰克福是个好地方,作为城市不大不小。刚来的第二天,我就抽时间从东到西走了一遍。风景不错,在繁忙里你还是能看到从容和优雅,是个过日子的好地方。在这里你可以什么都不缺。小魏是小周的女朋友,二十七岁,在法兰克福大学念社会学博士学位。拿不下博士不结婚。小周跟我一样大,硕士毕业前认识了小师妹,等她念完本科,再等她念完硕士,现在要等她念完博士才能结婚。这个从大连来的小个子女孩让小周欲罢不能,他是真喜欢她,可是从天津来的压力也很大。母亲说,你爸翻过年就七十,想抱孙子都想出了白内障,现在连个婚都没影。小周安慰二老,快了。他爸说,我看玄,人家拿了博士以后,还要当博士后呢?要是当完了博士后又说这辈子不想结婚呢?要是结了婚不打算要孩子呢?他爸的“要是”也很多,弄得他很烦。小周只好叹气,走一步看一步吧。
昨天晚上我安慰他:“没问题,小魏不像丁克那种人。”
当时我坐在沙发上,看着小魏倒过茶后去厨房的背影,对坐在沙发另一头的小周说。
小魏的背影不喧嚣,也绝不僵硬,腰身的过渡跟动作一样果断柔和,可以想见不久的将来作为贤妻良母的亲和力。但她在留居德国这一点上认死理,除了大连和法兰克福,这辈子她不打算待在第三个地方。小周不能理解,我也不能理解。虽然法兰克福的确是个好地方,德国的发展空间比较大,医疗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很完善,但是小魏不像咬牙切齿的人。她给我们沏的是铁观音,小周只喝这一种。小周解释,只有铁观音才能让他喝出中国茶的味儿来。小魏一笑,露出左边的一颗小虎牙,说:
“别听他的,偏见。人老了就这样。”
小周自嘲:“别打击一片,我和徐先生可是一样大。”
“那人家看着可比你年轻。”
小魏把假话说得自然家常,小虎牙又露出来。我天生老相,就算是用老周的白内障双眼来看,我也不会比小周显得年轻。反正小魏不像咬牙切齿的人,但她的确是咬牙切齿要留在这地方。
我来这里参加一年一度的书展,有个新书见面会。活动结束,朋友们都走了,我想在周边看看,就一个人留了下来。等着两天后去波恩大学做个朗诵,我的小说翻译,波恩大学的赫尔曼教授会在车站接我。我不懂德语,他就把我托付给了旅行社,导游小周。
小周带我看了歌德故居、罗马广场、保尔大教堂、老歌剧院、修道院和博物馆、美术馆等,讲解极为敬业。他的方式是夹叙夹议,叙是叙这些景点,议的却是他自己、德国的华人状况以及国内的事情,其中充满了他的“要是”。他在北京念的本科,很多地方和事件是我们共同的记忆,说起来显得相当投机。其实我的兴趣不大,和一个久疏国情的人聊天,总有迷离恍惚和隔靴搔痒之感。而且,小周的故国情深体现得比较单薄,你让他说出个回去的一二三,他也语焉不详。他就是觉得回去了心里才踏实,情绪化得仿佛只是一种抽象的焦虑。我时刻担心他会举起拳头上下耸动,高喊:我要回去,我要回去。当然这也正常,就跟想家一样,你要把它赋上个微言大义反倒像假的了。本能最真实,也容易唠叨。他翻来覆去地跟我说过去,说想回去,说“要是”。他简直是亢奋地说着汉语普通话,某一刻舌头跑在了大脑前面,我就听到了舌头下坠的天津话。
昨天中午去古代雕塑品博物馆,经过入住的酒店时,小周突然停车,跟我说,要不退房吧。退了房我住哪儿?他拍拍胸口,住他家。条件差了点儿,他说,但你可以再听见一个人说中国话。我差点就拒绝了。有他这么一个人说中国话已经够唠叨了,我可不想再添一个。转念一想,也许他想再挣一份房钱?我正犹豫,小周重新发动了车,说:“我就是想在一起多说一会儿话。”他以为我跟他一样,想多听一个人跟自己说母语。我按了一下他搭在方向盘上的手,停下。我下车收拾了行李,退了房,拎着箱子搬到了他家。
他和小魏租的房子,类似于我们的筒子楼,小两居。楼外面爬山虎一直蔓到了顶。家里的摆设不复杂,倒是各种家具上放满了女孩子喜欢的小玩具,单看风格和造型,我猜是从中国来的,随便在电视机旁拎起一个米老鼠,果然屁股后头的商标上印着“M ade in China”。墙纸、桌布、沙发套和床单、被罩都以金黄和浅绿为主色调,既温馨又清爽。和一般的德国家庭比,这只能是年轻的创业者之家;但和留学生的临时小家比,这个家更让人心安。这从小周的状态就能看出来,进了门他几乎是把自己摊在了沙发上,四肢放松地散开,跟着长舒了一口气。
我说:“小周,你还是乖乖地跟小魏待在这里吧。”
“为什么?”
“你离不开这个沙发。”
小周笑了,说:“她不在家,我就跑到沙发上睡。舒服。”
我也笑笑,他明白我的意思。
昨天晚上我们俩聊到凌晨三点半,吃水果喝啤酒。小魏在旁边偶尔插一嘴,更多的时候在开啤酒和削水果。插上的几句话都是一针见血,是个社会学博士的水平,但她看小周的眼神却是一个小师妹该有的小鸟依人。我开玩笑说,小魏这么伶牙俐齿,小周岂不要受欺负?小魏说,才不,他得意着呢,他知道他是我的主心骨。小周说,哪有啊,我在跟魏博士一起追求进步。好了,不听他们文雅的调情了,我想知道他们在法兰克福生活的真实感受,以及对国内的看法。包括小魏知道的留学生的状况。对话的方式像在访谈。凌晨一点半,小魏先去睡了,明天有课。凌晨三点半,我也不行了,想问的都问完了,只剩下一连串的哈欠。小周还是精神矍铄,为了不耽误我明天的行程,他才不舍地进了卧室。最后一句话是:今天说得真爽,快把自己说空了。
说空也是一种享受。作为一个写作者,从语言的意义上,我能理解小周此刻的心情。这剩下来的几个小时,他可能睡得酣畅,当然也可能失眠。我睡在那张舒服的沙发上,躺下来看见窗外风经过树梢,枝叶摆动幅度越来越大。迅速入睡对我不成问题。
火车开动前五分钟我们进站。小周把我送上车安顿好,脚刚落到站台上,车门在他身后关上。德国火车从来都像瑞士钟表一样守时。他在车门外对我挥手,亲热地叫我徐哥,下次来法兰克福一定要找他和小魏。尽管小周有无数个“要是”,他显然清楚还是得待在法兰克福,当然前提是,我再来能找到“他和小魏”。我也挥手,兄弟,好好过。火车开始离站。
车里有点儿冷,谁也没料到一夜大风气温就陡然掉下来。幸好我买了一件呢子大衣,此刻派上了用场。跑了好几家商场,最后买到的还是件黑色的。德国男人好像不穿别的颜色,满商场一抹黑。我把自己裹紧,这是个二等车厢的小包厢,面对面共六个座,我一人坐一边,对面是个看书的老太太和一个吃泡泡糖的小姑娘。小姑娘戴着耳机摇晃着两只脚,隔五秒钟噗地吐出一个大泡泡,啪的又炸掉,十四五岁的样子,涂了靛蓝色眼影,她的泡泡遮住大半张脸时让我感觉更冷了。她的泡泡炸掉时,老太太就从眼镜上方对我笑一下。这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一脸松弛的皱纹,像从黑森林童话里走出来的善良的老奶奶。她在看一本英文小说,脚边是一根原木拐杖。我用英语和她打了招呼,她的英式发音十分优雅。她将在波恩前一站下车,她说,我们三个人一个包厢,这会是一个愉快的旅程。
涂眼影的小姑娘摘下耳机,用摇滚乐的节奏向我们点头,说:“要吃泡泡糖吗?”
我和老太太对她微笑说谢谢。
这时候车行已经二十分钟,检票员刚刚查过票,从门外进来一个穿橙色薄毛衣的女孩,对着票坐到我旁边。“你是——”她犹疑半天,突然歪着头问,“中国人?”让我惊奇的是,这个长着一张欧洲脸的女孩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儿化音很重。没等我回答,她又接着说,“我是瑞士人,住在法兰克福。”
“哦,”我说,“你的普通话说得比我好。”
“我外婆住在北京的一个小四合院里,离恭王府不远。”
“那咱们算半个老乡。”
“刚才有中国人经过这里吗?年轻的,小伙子,瘦高个儿。”
她的思路之跳跃我有点儿跟不上。想了想,好像没看见,大部分时间我都盯着窗外。“找人?”
“没有事情。”她笑笑,脸小,鼻子高,嘴巴大,一口好牙。“我外婆是中国人。”
德国老太太又从眼镜上面看我们,眨巴两下眼,用英语说:“你们说话很好听。”
女孩用汉语说:“您听得懂汉语吗?”
老太太很茫然,显然不懂,鼻子眉毛往一块儿皱:“W hat?”
女孩改用英文回答她:“我说,您的精神头儿真好。”
老太太很高兴,接着看书。涂眼影的小姑娘继续摇头晃脑地听音乐,那节奏已经不太像摇滚了。
“你外公是瑞士人?”我问。
“日本人。”她说,“中国跟日本打仗的时候,我外公就在北京,做建筑设计,就是画图纸的。他的汉语说得比我还好,人家都以为他是中国人,要不你们那个‘文化大革命’早把他打死了。你说我爸妈?我妈当然是中国人,二十一岁嫁给我爸。我爸是德国人,后来移居瑞士,所以我就是瑞士人了。老爸学的也是建筑,我外公的学生。”
“呵呵,他骗了你妈吧?”
“没有骗,是我妈先喜欢我爸的。”
我的中国式幽默对她没用,他们家祖传的语言天赋也帮不上忙。和她的相貌一样,这个女孩严格地继承了德国人的较真,“是我妈先喜欢上我爸的”。
好吧。“常回中国吗?”
“嗯。”她的声音低沉下来。门外走过一个人,她扭头看了一眼。和我说话的这段时间里,她至少扭头三次,也就是说,门外至少经过三个人。这个包厢在这节车厢尽头,紧挨着洗手间。突然,隐约有人在叫,还是多声部,隔很多个车厢传过来。然后火车轮子吱嘎嘎响,紧急刹车停了下来。
周围一片旷野,火车在坡上,青草缓慢地向下长,整齐得如修剪过一般,直到河边。波光潋滟的这条漫长的水就是莱茵河?我没问旁边的女孩,她半个身子都偏向了包厢的门。河对岸的山坡在上升,直到最高处,一座古老的城堡缺了半面墙。十来户人家悠闲地散布在山坡上,和城堡一样醒目的是教堂,白墙黑顶,精瘦挺拔,十字架高高指向天空。一个乘务员经过包厢门口,被她叫住了。他们叽哩哇啦的德语我听不懂,就看见那大肚子的乘务员指手画脚地说话,前腿弓后腿蹬,时刻准备往前冲。说了几句果然就往前冲了。
我问女孩,都说的啥,她就一句话匆忙打发了我:“有人跳车了!”说到第五个字人已经到了门外,咚咚的脚步声跑远了。我走出包厢,过道里回响着杂乱的脚步声。老太太也拄着拐杖跟出来,用英语嘀咕:“为什么不想想还有我们老头老太太!”
我问:“您说什么?”
老太太示意我打开车窗。“年纪轻轻跳什么车!”
“乘务员说,死的是个男的!”涂眼影的小姑娘也出来了,耳机挂在脖子上。“我同学的哥哥也是跳火车死的。”我把窗户打开,一股冷风灌进来,小姑娘缩着脖子躲到一边,被老太太推进了包厢。老太太的话听不懂,大意应该是小孩子不能看。因为小姑娘撇撇嘴不屑地回了一句,我觉得可能是:谁稀罕看死人!
火车的前半截身子正在拐弯,有个平缓的弧度,伸出头正好可以看见事发地点。车的这一边没有河流,草都很少,断断续续有一些大石头,不知道是天生就在铁轨边还是摆列在这里另有用途。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一个人从车窗里跳出来,迎头撞到石头上,想不死很困难。一堆人围在那里,我看见那个混血的女孩踮着脚,抱着脑袋想从人群外往里钻。难道是她要找的人?如果真是这样,死的就是那个我没看见的、年轻的瘦高个儿中国小伙子。我向那节车厢跑去。
半道上遇到混血女孩,捂着嘴边走边流眼泪。我说:“他?”
她摇摇头,说:“我看不下去。”为了能继续说下去,她重新捂上嘴再松开,“脑浆都流在了石头上。”
死掉的小伙子非常年轻,德国人,穿着咖啡色帽衫,石头划破了他的脸,死的时候眼睛睁大了,看见了岩石、冷风和灰暗的天空。
那女孩说:“我冷。”
我要把大衣脱下来给她穿,她不要,天的确冷。她让我披着大衣,她用大衣的一半裹住自己,一手抱着我的腰,我们用一种古怪的姿势走回了包厢。
她叫阿格妮丝,汉语名字李安雅,后者是她只读过五年书的外婆取的。她喜欢别人叫她安雅。安雅生长在外婆的四合院里直到八岁,父母回瑞士才把她带走。如果不是一张洋毛子脸,她站在中国小学三年级的课堂上回答问题,没人会发现她不是中国人。
“我的成绩很好,语文、算术都考一百分。”说到这里她总算心情好了一点。“你不相信?”
相信。可我想知道的不是这个,所以我说:“刚刚那个人——”这么说是因为现在火车又重新开动了。他显然不是他。但是那个中国的“他”是谁呢?她嘴角刚聚集起来的一点笑意又熄灭了,让我觉得自己的好奇心有点儿残忍。“对不起,我就是随便问问。”
“没有事情,”安雅用这别扭的四个字表示她并不介意,“就算你不想听我也打算跟你说的。”
“嗯?”
“我难过得快憋死了。”
我隔着一只大衣袖子倚在车窗上,安雅抓着另外一只袖子在大衣里靠着我。为了避免这个造型让对面的一老一少起疑心,刚进包厢我就此地无银地对她们解释:这位小姐冷。
安雅一开口我就知道,即使我一声不吭,她也不会放过我,她有如此蓬勃的倾诉欲望。她必须说出来,就像小周逮着我不撒手一样,她终于找到了一个貌似可靠的从中国来的、说汉语的听众。甚至问题都和小周类似:爱情,两个人,何去何从的未来。那个她担心以身殉情的小伙子叫高歌,南京人,我的江苏老乡。世界真是小。
他们很小的时候就认识,高歌的姨妈和安雅外婆邻居。每年寒暑假高歌都到姨妈家来,除了到处逛,大部分时间他们都在外婆的四合院里玩。后来安雅去了瑞士,回北京的次数依然很多,继续见面。再后来,高歌去了德国留学,他们见面更多了,有了爱情。他学的是汽车制造,汽车制造业是德国最大的工业部门,传统的四大支柱产业之一,广阔天地,大有可为。毕业了高歌也舍不得走。但是安雅想走,这个在欧洲待了快二十年洋姑娘偏偏想去北京生活。这么多年她只喜欢北京,她觉得真正像家的地方。她像涂眼影的小姑娘这么大时,就清晰地知道了什么能让她安妥,在四合院里一坐她能坐一夜,啥也不干就两眼望天。我想不出北京空气污染成那样的天有什么好看的,不过那会儿空气要比现在好一点。八十多岁的外婆身体很好,安雅用下巴指指对面的德国老太太,比她还硬朗。外婆立了遗嘱,小四合院归外孙女,谁也别打算抢。
“你的专业是?”
“古典建筑,祖传的。”
“那北京的确是个好地方。”
“北京的老建筑都快拆光了,新楼房盖得又高又土,难看死了。我才不会因为学建筑才回北京呢。我为了生活。”
生活,一个宏大的词。
“就是你们说的过日子。实实在在地每一天都开心地过。不是,那个词叫什么?对,讨生活。我不讨生活。过好日子不需要那么多钱。”
这话要是被劳苦人民听见了,肯定一堆板砖伺候过来。但我理解这个经过欧洲中产或者小康生活之后,被培养出来的朴素的生活见解。有时候的确不需要穷凶极恶地捞钱也能过上好日子。更要紧的是心境。当然这也让人不舒服,她还有个瑞士爹娘呢,还有个四合院可以继承。在北京城里,有一个四合院意味着什么,很多人比我更清楚。
跑题了。说说你那男朋友吧。
“他让我待在这里,不去北京。要死要活地不允许。我们吵了一年多。”
“坚决不妥协?”
“不妥协。他对我好,可是我去北京不影响我对他好啊。我们可以结婚,可以生孩子,我们都年轻,可以两边跑,八个小时我就飞过来了。他不答应,威胁我要自杀。”
应该不是特例吧,生活在德国的瑞士人安雅不能接受这个威胁,但她担心,刚刚跳车的小伙子把她吓坏了。为什么不能满世界跑呢?她不理解,我现在喜欢北京,我就可以去;哪天不喜欢了,回来呗。他非要让我给一个更正大的理由,哪有那么多像山一样大的理由?你觉得这里可以发挥自己,好,你待在这里;我觉得北京好,就去那里。世界这么大,就是为了让我们到处跑的。我们都得听自己的,你说是不是?
我说是。她和小周的情况似乎不完全一样。小周、小魏和高歌,你能看出他们就是个中国人,在外面待了多久都是;这个安雅,哪怕她在四合院里终老,也是个混了好几次血的。大家都听自己的,方式不一样。
“那个啥,我那小老乡,真自杀过?”
“吃过安眠药,开车时还想撞过树。我也知道,他是舍不得我离开。他说他离了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可我这也不算离开啊。对吧?”
我也不知道对不对。
上车前他们又吵了架,安雅用了个成语:天翻地覆。原因是高歌见到了她买的车票,担心她是要去机场,这趟车的确经过法兰克福机场。安雅不过想见见朋友,说说话散心,这几天吵架吵得她要崩溃。为了避开高歌,出门发现天冷都没回去加衣服,直接来了车站。
“我换了好几个车厢才到这里,”安雅说,“在路上我好像看见他在跟着我。”
可能她多虑了,我没看见一个高个子中国小伙子站在门外过。现在让她放心的是,起码高歌没出事。这就好。她早就不哭了,开始跟我讲他们在北京和法兰克福的生活。她在讲述这些生活时,我恍惚觉得她就是小周,两个重叠在一起。也许大家的生活不过如此,大同小异,也可能是我困了。
也该困了。昨天晚上三点半睡,早上七点半起,像我这样每天必须八小时的人,这一夜只睡了一半。在车里和小周聊天时还好,有早餐的两杯咖啡顶着,小魏现磨的咖啡味道醇正。小周不住嘴地说,隔三差五征求我的意见,该怎么办。可惜卑之无甚高论,清官难断家务事,我只能说,听自己的,再为对方考虑一下,然后顺其自然。我自己都知道,这其实是屁话,等于没说。但我能说的只有这些。在一个陌生的国度,对一种陌生的生活,现在我只能是一双耳朵。对安雅,作为耳朵我也勉为其难,困意像浓雾弥漫全身,我的脑袋开始对着窗玻璃乱点。
“困了?”安雅中断她的倾诉。
“有点。对不起。”
“没有事情,”她说,“我也困了,昨晚几乎一宿没睡。”她停下来,往我身上靠了靠,闭上眼。“睡吧。”
对面的老太太和涂眼影的小姑娘早就睡着了。睡着了的老太太一手拿书,一手拿着拐杖。小姑娘在梦里还跟着音乐缓慢地晃动脑袋。对她们来说,我们俩就是两个哇啦哇啦不知疲倦地制造低分贝噪音的人。
火车的猛然停顿惊醒了我。睁开眼,包厢里就我一个人,右边的大衣空荡荡地耷拉下来。不知道她们什么时候下的车。已近傍晚的天色提醒我,波恩肯定到了。我拎着行李下车,在站台上抽了一根烟,还没看见赫尔曼教授。两天前他告诉我,如果他没能及时出现在站台上,就给他打电话。我顺着出站通道往外走,穿过车站大厅时看见投币公用电话,开始拨赫尔曼教授的手机。
“在哪儿呢?”他问。
“车站啊。”
“我一直在站台上,怎么没看见你?改火车票了?”
“没改,就你说的那趟车。”
“奇怪。”赫尔曼教授有点纳闷。我听见电话里他的夫人,从中国江西来的美女杨女士说:“问问徐先生,他周围都有什么?”赫尔曼教授说:“你看看四围,有什么标志性的东西。”
我抱着电话往四周看,所有的车站都差不多。然后透过窗户看见了黑魆魆的教堂,庄严雄伟地矗立在车站门口。我说:“教堂。赫尔曼教授,一座高大的教堂,全身都是黑的。”
“My God!”赫尔曼教授说,“你坐过了站,到科隆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