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如何变成“天才作者”
○姜文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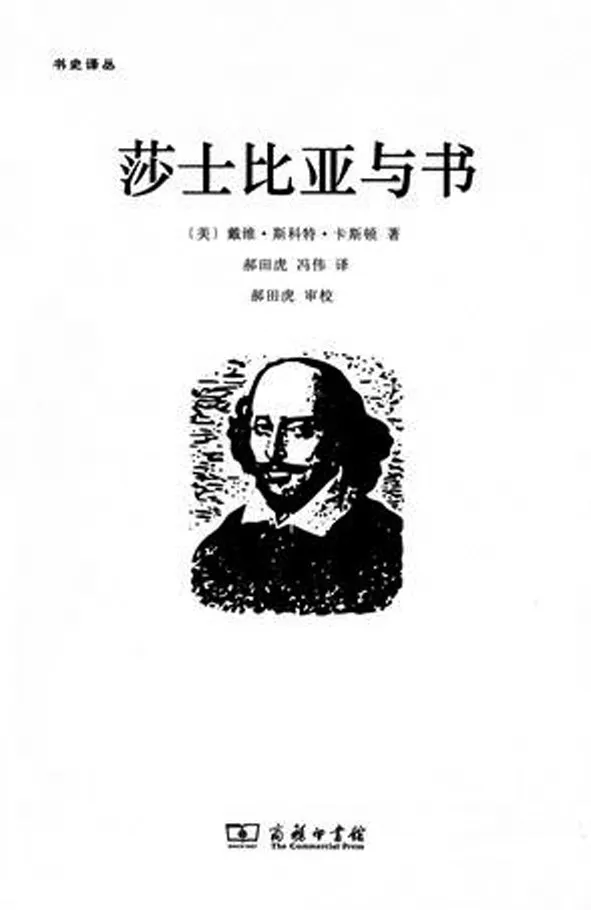
《莎士比亚与书》,(美)戴维斯·斯科特·卡斯顿著,郝田虎、冯伟译,郝田虎校,商务印书馆2012年5月版,35.00元。
一提起莎士比亚,人们就自然而然地想到他是戏剧家、文学家,还会联系到他写的十四行诗歌。根据文学史家黄承元(Alexander C.Y.Huang)所著《中国的莎士比亚们》(Chinese Shakespeares,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的研究,莎士比亚在中国的介绍从1839年就开始了:当时由林则徐主持翻译的《四洲志》里顺便提及了莎翁的名字。莎翁作品的中文翻译也已经是蔚为大观了。文学爱好者们对于各个译本和英文原本的比较和鉴别更是突出了莎士比亚这个英国十六七世纪文学创作者的天才和神秘。
莎士比亚的作品是如何通过印刷媒介流传到现今的?这个过程里面发生了什么?这些问题便是刚刚有中文译本的《莎士比亚与书》试图回答的。该书作者是研究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的戴维·斯科特·卡斯顿教授。他是世界著名的阿登版莎士比亚(the Arden Shakespeare)的联合主编,曾在伦敦大学、达特茅斯学院、哥伦比亚大学教书,目前是耶鲁大学的乔治·M·博德曼英文讲座教授,出版了多本关于文艺复兴和莎士比亚的书,比如《理论之后的莎士比亚》、《莎士比亚与时间的形体》。他在关于莎士比亚的问题上无疑是最具权威的学者之一。
两位译者是研究英国早期近代文学的中青年学者,在学术翻译方面颇有经验,译笔流畅通顺,十分可读。尤其在翻译涉及印刷文化的专有名词方面,他们处理得当,可见是花了不少功夫。对于比较复杂而容易引起混淆的名称或者词汇,他们还将英文附在后面,方便了读者去查询。
莎士比亚与以莎士比亚为作者的书
卡斯顿采取的研究方法是历史版本考据。这一点,只要看一下这本书的主要目录就知道了:“从剧场到印刷厂;或曰,留下好印象/印数”、“从4开本到对开本;或曰,尺寸之类的重要”、“从当代到经典;或曰文本修复”。他的主要观点是:莎士比亚成为我们今天所知的全球文学天才,并不是莎翁自己努力的结果,尽管莎士比亚自己的杰出才华是不可否认的。然而,在这个过程里面,印刷商和出版商的种种活动对于莎翁作品传播的物质形式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从而使其成为可能的阅读,这些也需要在衡量作品的意义和价值的过程里面得到承认。在这一点上,正如莎翁剧作第一对开本(the First Folio)的编者约翰·赫明(John Heminge)和亨利·康德尔(Henry Condell)所宣称的,莎士比亚四散的“肢体”是在印刷厂收集修复,从而被重新组合成全集的。
对于卡斯顿来说,莎士比亚并不认为自己是文学戏剧家,也不认为自己是专为读者写作的人。我们所知的莎士比亚现存的手迹仅限于六七个签名、两个单词和《托马斯·莫尔爵士》中的147行。后世所热爱的那个超越时空的艺术家似乎还没有诞生,这种情况至少一直到了17世纪后半期,而莎士比亚的地位完全确立,也要到18世纪50年代。莎士比亚不像他的同时代人本·琼森,似乎满足于仅仅为剧院写作。莎翁作品的第一次出版是以对开本的形式,那已经是他死了7年之后的事了。他的两个朋友约翰·赫明和亨利·康德尔,以及一起共事的演员,第一次收集出版了他的作品。这个集子被设计为作者莎士比亚的剧作全集,是将莎士比亚确立为单一和独特的文学作者的开始。而事实上,这个开本里印刷出版的各剧本是由作者稿本、抄本、经评注的4开本和舞台演出本组成的,而莎士比亚也确实是在剧院经济内部从事合作生产的剧作家。
实际上,赫明和康德尔也并不是不清楚莎士比亚最初的原本在剧场里是被如何修正的。但是,他们却在对开本的标题页上将威廉·莎士比亚作为唯一的作者提出来,故意宣称剧本“确实是根据它们最初的原本印刷的”,而且,从未提起表演剧团,虽然这两位毕生都在剧院快乐地工作,也是从那里知道莎士比亚的剧作的。卡斯顿告诉我们说,也许他们如此声称的目的是要标榜与先前廉价的4开本(quarto)不同。后来,牛津大学的图书馆饱蠹楼(the Bodleian,中文名为钱锺书译)1624年初收藏了这一部莎士比亚对开本,这几乎是这家重要图书馆第一次收藏后来我们归之为文学之一种的戏剧。卡斯顿认为这体现了“早期现代书业的商业欲望”是如何有意地将历史上的莎士比亚“重构为”“作者”。有意思的是,卡斯顿在他发表于别处的一篇文章《英国文学的创造 》(“TheInventionofEnglish Literature”,收入论文集《改变的动力:纪念伊丽莎白·爱森斯坦文集》[Agents ofChange:EssaysinHonorof Elizabeth L.Eisenstein],马萨诸塞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里,将这个时期饱蠹楼的这种收藏行为视为英国文学经典化历史性的开始。也许,我们可以推测说,卡斯顿写这本《莎士比亚与书》并不仅仅是要讨论这个单独例子,而是借此向我们展示文学的物质性和媒介性与其自身历史形成的关系。
在此书关键的一章里,卡斯顿仍然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考证不同版本的莎士比亚戏剧集,以及同时代的编者和印刷商如何宣称他们是“修复”了莎翁的作品。1632年的第二对开本在第一对开本的基础上所做的编辑工作,大多是为了在拼写和语法上符合17世纪30年代早期的语言环境,而由此也确立和稳固了第一对开本赋予莎士比亚戏剧的文学地位。对于卡斯顿来讲,“莎士比亚的剧作”能够流传下来,也恰恰是由于这些剧作本身的开放性和可塑性。即使宣称对莎士比亚的作品崇敬几乎达到顶礼膜拜地步的刘易斯·西奥博尔德(Lewis Theobald),也在编辑《理查二世》(Richard II)时只保留了莎士比亚原作的1/4左右,而且重新分配了其中的一些台词。至于1725年出版的由18世纪名诗人蒲柏(Alexander Pope)编辑的那个版本,则是由蒲柏比较1623年第一对开本之前各个印刷版本之后的结果。这个版本意义重大,既标志着历史文献考证方法的开始,也是后来编辑们敌视剧场的开始。而这个版本一直可以不断地修订,也是因为印刷商雅各布·汤森(Jacob Tonson)家族只有一直延用这个本子才能连续持有版权。
卡斯顿为我们梳理了莎士比亚各个版本在历史上是如何产生的,有些什么样的人参与进来,他们对于莎士比亚的经典化做了哪些事情,以及他们与当时印刷文化的关系。作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专家,他总是娓娓道来。在他的叙述下,各个版本之间的故事互相连接,妙趣横生,对细节的把握也很精确到位。他的观点很明确:“莎士比亚”是一本无法最终确定的书,我们现在所知所读的莎士比亚是这一历史过程的结果,也是这个仍然在延展的过程的一个环节。文本本身并不是权威的、不变的,作者的身份也与文本流传的历史紧密相连。而这一历史过程,在我们今天的印刷和数字媒体并存的环境里,具有开放性。这似乎是卡斯顿教授所暗示给我们的,也是他这本书结尾一章“从抄本到电脑;或曰,思想的在场”的意义。
作者身份的建构与文本的开放性
这本2001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的著作,其实是缘自卡斯顿1999年在伦敦大学学院所做的诺思克利夫勋爵系列讲座。这个讲演的另一个版本发表在2002年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本题为《早期近代英格兰的书籍和读者:物质研究》(BooksandReadersinEarlyModernEngland:Material Studies)的集子里。在这篇文章里,卡斯顿的论证仅限于16世纪末、17世纪初。他指出,莎士比亚本人作为剧院的股东,根本不在意剧本能否出版,当时出版剧本并不能为作者带来多少收入;剧本也并非某个单一作者的作品,更多是剧团各个成员合作的产物,当时剧本还不太属于高雅的文化作品,多是属于娱乐业一时之作。这本《莎士比亚与书》里,卡斯顿在他之前的论文基础上,又增加了相当多的内容,更清楚地勾勒出莎士比亚文本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经典化、不同的莎翁版本之间的关系,以及近代印刷文化是如何成就了莎士比亚的天才作者身份。卡斯顿也更有意识地从书籍和媒体的历史角度来梳理莎士比亚的文本化。
理论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和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分别在《什么是作者》(What Is an Author?)及《作者之死》(The Death of the Author)的文章里面,都提出作者身份和天才概念是一个从早期近代以来逐步建立起来的个体概念。历史学家伊丽莎白·爱森斯坦(Elizabeth Eisenstein)和阿德里安·约翰斯(Adrian Johns)也分别在他们的著作中告诉我们,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印刷文化以及与其有关的一系列的文化活动(比如阅读)都是从早期近代开始的,是一个历史的建构过程。近代意义上的文学概念和实践的产生更是与这一过程脱不了干系。我们若是想当然地认为作为文艺复兴时期英格兰文学天才的莎士比亚从一开始便是如此,那便是犯了历史知识的时代误植(historical anachronism)的错误。
如今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多媒体时代里面,一系列的电子阅览器如iPad正在改变我们的阅读习惯,更不用说无处不在的网络使得文本更具开放性。有些批评家已经在预言传统意义上的印刷文化和书的终结了,文学的死亡也大概可以归入这个大的媒体环境的转换之中。所谓早期近代的印刷文化已经让位于后现代社会的多媒体并置。
也许并不是这样的。在《早期近代英格兰的书籍和读者》这本集子中有另外一篇文章《书与卷:巡览圣经》(Books and Scrolls:Navigating the Bible),作者是宾夕法尼亚大学英文系的教授彼得·斯塔列布拉斯(Peter Stallybrass)。 斯塔列布拉斯教授以早期新教徒对当时印刷的《圣经》的阅读为例,论证说近代书籍从“卷”到“书”的历史正是书签出现和被使用的历史,也就是说原先的连续性的阅读(continuous reading)由于有了印刷出来的书,可以转换为非连续性的阅读(discontinuous reading)。读者可以随时翻至《圣经》某个书卷,并做出相应的标记。我们通常认为,18世纪的小说是印刷文化的典型现象,而小说的阅读是围绕着情节和人物的,一定是从第一页读到最后一页的连续行为。而对斯塔列布拉斯来说,小说阅读其实是书籍史里面的一种非常规的现象,因为直到18世纪中期印刷文化中发行数量最大的还是宗教性质的读物,包括《圣经》。
总而言之,人们通常以为数字媒体使得我们的阅读行为从持续性的变为断裂性的,也就是说我们想从任何地方开始阅读都可以,也通常以为这使得它对于先前的印刷媒体来说是一次完全的转变。可事实也许正好相反,数字媒体带来的断裂性阅读也许正是从早期近代开始的印刷媒体的一种延续,而如今无所不在的数字媒体倒正好为我们观察历史上的印刷文化提供了一个平台。若是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卡斯顿的这本《莎士比亚与书》出版得正合时宜:无论时代如何,莎翁都在那里。但,已经不是原来的莎翁。尤其是这书的最后一章更是详细介绍了作者如何利用数字媒体进行莎士比亚的教学和阅读。
文学的流传与书籍历史的关系最近几十年一直是学术界的热点,中国研究方面如哈佛大学田晓菲2007年由中华书局出的《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英文本TaoYuanming&Manuscript Culture:The Record of a Dusty Table由华盛顿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便是其中一例。卡斯顿的这本书以莎士比亚为例,在讨论早期近代的书、作者、印刷、书业、版权、阅读及其与社会的关系方面,所给我们的教益是很有价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