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后重提吴伯箫
○子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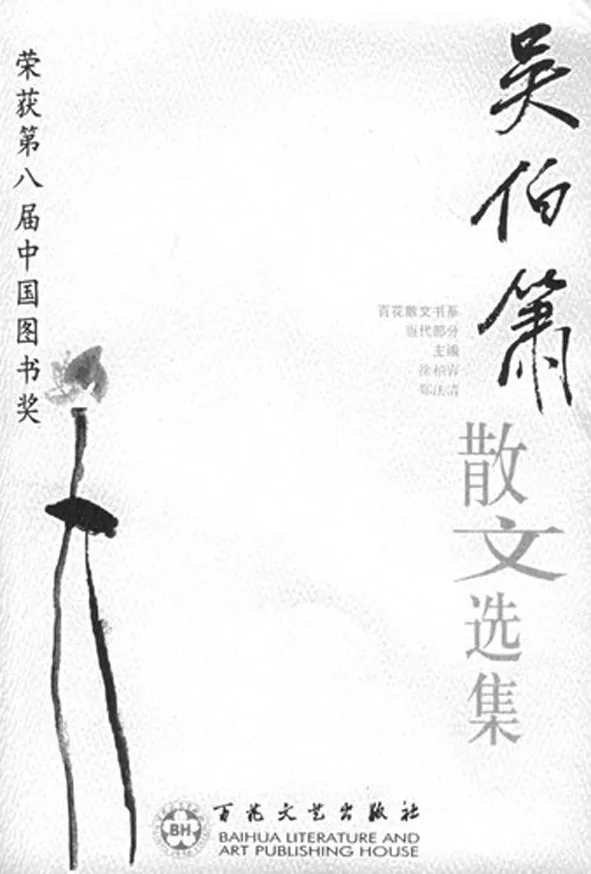
《吴伯箫散文选集》,吴伯萧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9月版
我开始关注作为散文作家的吴伯箫,是1982年上半年。那时我刚从师范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吴伯箫故乡一个县级重点中学初为语文教师不久,由讲授高中语文课本中的吴氏散文《猎户》和作为吴氏小同乡这两件事而产生“读其书想见其为人”的冲动,即去莱芜城郊吴家花园村寻访在一个小饭店做事的吴伯箫三弟吴熙振老人。在听说吴伯箫患癌症住院的情况后,我给他写了一封信,盼望着会出现收到回信的奇迹。不成想这个奇迹终于没有出现,老人家于当年8月初离世,享年76岁。
历史当然无法假设,不过根据后来我接触到的有关文献,我仍然有一些固执的念头。第一,如果吴能够活到90年代,随着社会形势进一步开放和文化的进步,吴的自述性文字会增多,一些讳莫如深的历史纠结也许会逐步解开;第二,吴的思想和散文写作会有比较大的突破,也许他会对自己写作“分水岭”“从《北极星》开始”的说法有新的思考。
可惜突如其来的癌症夺去了他对历史和生命给予重新打量、沉思的机会,留下了遗憾。这遗憾就是吴伯箫历史形象的塑造没有得以完成,或者说由于生命的中断,一些他本来可以做完、至少可以做得更好的工作没来得及去做。此后,人们在评说他时,所依据的也只能局限于他已经做出的,而那些可能做出的就永远不能算数了。
这就是时间的残酷性。也许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一个人真正能够完成他自己。设想一下,郭沫若活到一百岁,会不会重新有“觉今是而昨非”之叹惜呢?
吴伯箫一去三十年,他故乡的老屋和生前的住所犹在,却因为与他的关联变得载浮载沉起来,折射出社会变迁的些许形影。
他离世十年时,两卷本的《吴伯箫文集》在历经辗转后终于由他生前担任副社长的人民教育出版社硬面精装出版了1340套,慰藉中见寒酸;在青岛海滨,一个新开辟的文化名人园林里塑起了吴伯箫的坐像,事先我受托向青岛市宣传部门提供了我所有的吴伯箫照片资料,事后则撰写了一万字的《吴伯箫传略》收入《青岛历史文化名人传略》一书;在东北,由他一个早期学生编辑的“纪念文集”却只能由大家集资“内部出版”。他离世二十年时,我受他故乡莱芜一中的委托到北京寻访吴氏亲友、查阅文献,筹备一个以他名字命名的“文学馆”。在京期间,吴伯箫次子吴光玮兄长为我复印了刚刚出版的《记忆》杂志,里面刊载了一篇有关他在延安“抢救运动”中被迫做“坦白明星”的文章,多多少少揭示了吴伯箫生涯中或许是最大的一个精神创痛,但文章作者对吴伯箫蒙冤与受辱的解释却似乎有失厚道,语近刻薄。我曾经就此事和此文请教当年在延安的一位著名诗人,他来信表示:“1943年抢救运动,是共产国际大特务康生领导的。吴伯箫是个老实人,做个坦白分子并不奇怪!奇怪的是文章的作者到今天还这样低水平!林贤治主编的《记忆》登用此文,必定当作历史悲剧公之于世,对吴伯箫毫无损害。”
除此之外,也陆续看到一些关于他故乡老宅的消息。他故乡的报纸曾在90年代初有过“吴伯箫故居修葺一新”的报道,而没过几年却又看到不少吴氏故居如何破败、无人过问的报道和感叹。比如2000年5月27日《人民日报》“大地周刊”之“编读往来”栏目中,就有一则《吴伯箫故居存亡未卜》的读者来信。凡此种种,似乎表明吴伯箫仍然在一定范围内受到一些人的关注。但是,随着人教版语文课本选目的变化,随着人们生活的日益物质化和丰富多彩,吴氏散文渐渐淡出中学生和普通读者的视线,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有些无名读者带着怀旧情绪提到吴的作品,也已经多是记忆中的课本范文了,他那些好不容易收入文集的早期佳作竟没有引发足够的重视和反响。
现在,我从所存的吴氏档案中抽出这套《吴伯箫文集》,一些记忆和想法重被勾起。当年“文集”出版后,就由编者之一吴光玮寄赠给我,我随即撰文《完整的吴伯箫》刊于《博览群书》杂志给以介绍,认为:“至此,一尊完整的吴伯箫塑像算是宣告完工。”其实这里所谓“完整”仅仅是从作品搜集的角度而言,尚不足以表达吴伯箫最终的文学形象和人格形象。一方面,出于种种原因,属于吴伯箫撰写的文字,无论是文学性的还是言论、教学性的,无论是创作还是译文,也都还有个别篇什遗落了;另一方面,正如前面所言,吴伯箫还想写并且有可能写出的文字也永远不可能收录进去了。
2002年暑期,我在北大图书馆所存延安时代的《解放日报》上,找到了他那篇自谓“暴露了小资产阶级思想感情的《山桃花》”,实际篇名应为《谷里的桃花》,不过借他所爱的女性表达对美德的称颂,虽说文字绮靡跳荡了一些,但以“小资”视之怕只能见出“思想改造”给作者带来的心理阴影了。这一篇就没能收入“文集”。在我看来,连同作者早期的“街头夜”一辑,被视为“京派”散文支流的《羽书》和战时在前线、后方写下的或纪实或沉思的十数篇作品,才是吴氏散文的精华。《羽书》集里的文字,仿佛只有香港的学者司马长风给过它们不一般的评价,而且是在吴伯箫“靠边站”的时代。
到了现在,从互联网上的资料看到,有论者借批评魏书生的语文教学模式开始指责吴伯箫1961年的散文《记一辆纺车》为“粉饰太平之作”了,真可以感觉到世事沧桑的变迁。不过感慨之余,也还有困惑:1959-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固然更近于政治灾害,但对如吴伯箫这样抱着真诚的“共产主义理想”、老实到“迂”、对执政党的政治承诺毫不怀疑的共产党员作家而言,面对现实困难而以革命时代的“大生产”为精神动力、激励人们“与困难作斗争”,就算是“粉饰太平”了吗?他的真实动机里面包含着回避矛盾、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的因素吗?他究竟属于“迂”还是“伪”?需要指责的究竟是吴伯箫这样天真的理想主义者还是别的什么人?
我以为,这是三十年后想到吴伯箫这位散文作家时需要认真思考的一些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