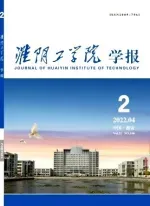论延光四年佛像的史学意义
张同标
( 华东师范大学艺术研究所,上海 200062)
0 引言
根据现有的文献记载和考古文物,我们倾向于这样的看法:佛教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而佛教造像的传入有可能要晚些。三峡出土的“延光四年”(公元125年)摇钱树佛像(见图1),有明确纪年可考,是目前所知的国内最早的佛教造像。由此来看,佛教造像在中国产生,与“两汉之际”佛教初传中国,并不同步。佛像初传中国,可能比佛像义理传入要晚百年左右。这尊古佛至少有两个重大意义:一是,可以缩小古印度贵霜王朝迦腻色伽即位年代的争论范围,对探究佛教造像在古印度的起源有重大意义;二是,可以证明中国古籍记载的早期佛教造像虽有夸饰之词却是有事实依据为基础的。
1 延光四年佛像的发现与型制
为保护三峡水库淹没地区的地下文物,2001年10月到2002年1月进行了紧急的考古发掘。重庆市博物馆与宝鸡市考古发掘队,在重庆市丰都县槽房沟墓地的后汉时期的9号墓中,发现了带有纪年题记的摇钱树佛像。槽房沟汉墓位于重庆丰都县镇江镇观石滩村东北约700米,在长江北岸的一座小山的底部,现在已淹没在水下。从墓中发现的这尊佛像,现藏于重庆博物馆,在近年来报道的中国早期佛像之中,当属极其重要的发现,为中国早期佛像的年代、造像类型和宗教义理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据目前仅有的简单的报道:从槽房沟9号墓中,发现的随葬品有舞俑、侍俑、武装俑等各种人物俑,又有塘槽、井户、家屋、乐器等陶制模型,以及摇钱树、钱币和生活用品,凡51件。①
摇钱树台座为灰泥陶质,底大顶小,呈覆斗状,下边长 14.4cm,上边长 6.4cm,通高 7.2cm。上绘黑色纹饰,底部涂橘红色,顶部中部插孔直径1.8cm,孔深3.2cm。摇钱树原先应当是插立于孔中的。台座的斜侧面有“延光四年五月十日作”的铭文一行九字(图1右)。同墓出土的陶质台座,在最初的报告中,没有明确说明台座与佛像钱树是一个整体,但这种规模不大的单室墓,基本上属一人之墓或夫妻合葬墓,墓主本人的日常用品之外的随葬品是成套的,因而可以断言,台座与佛像是属于同一座摇钱树。覆斗型台座是比较普遍的型制,出现较早。在云南昭通市曹家老包的后汉中期砖室墓中发现的这种覆斗型石制钱树台座,侧面刻有“建初九年戊子造”的铭文,建初是东汉章帝的年号,九年为公元84年,属于东汉中期,比槽房沟的年代早。两者除了年代与材质的差异之外,其型制基本相同,符合早期摇钱树座的特征。
摇钱树为青铜铸造,现仅存树干的一部分。佛像在考古简报中已有详细的叙述:佛像的下半,已经损坏不存,残存部分高约5cm,火焰状发饰,高肉髻,通肩衣,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握衣角。佛像铸造在树干上,树干的残存部分长约12cm,佛像在树干残存部分的底端。摇钱树流行于汉代的西南地区,是当时独特的一种随葬品,最初出现于东汉前期,盛行于汉代中期,持续到三国时代。在摇钱树的台座、树干、装饰题材方面的研究,已初步构成了一个编年体系,表现了一定的变化和发展的规律,但这件作品的摇钱树残损过甚,无法从其型制自身进行年代判断。
罗二虎对其进行了更加详细的研究,依据墓室型、陶马陶俑,对墓葬的年代进行了讨论。②他的结论是:“综合以上的分析,能够确认从槽房沟墓中出土的钱树制作于公元125年。摇钱树的年代,与墓的形式、构造、随葬品的年代一致,该墓的年代是东汉中期的末尾,具体地说,是公元125年稍晚一些。”
该造像睁眼高鼻,高肉髻有竖向纹路,右手施无畏印,衣纹呈凸棱状,腹部以下残损。与同类摇钱树佛像相比较,总体造型相似,尤其是施无畏印的手势和高肉髻这些无可辩驳的佛教特征,表明这是一尊典型的早期佛教造像。惟衣饰略有不同,佛像身著交领衣,而不是通肩或右袒的袈裟。摇钱树台座“延光四年(公元125年)五月十日作”铭文,为佛像断代提供了准确的依据,是目前国内出土的明确佛像之中的第一尊古佛像。
2 关于迦腻色伽即位年代的争议
关于古印度佛教造像的起源和编年,与迦腻色伽即位年代密切相关。现在的考古文物已证明,在迦腻色伽初期已有佛像。秣菟罗制作的立佛,已被运送至鹿野苑、舍卫城、憍赏弥等地,造像的铭文分别为迦腻色伽二年和三年,造型相似,说明在秣菟罗的佛像制造业已经具备了一定规模。在犍陀罗发现的迦腻色伽金币也铸造佛陀立像。这些情况说明,迦腻色伽在位期间迎来了第一个佛教造像的高峰期,而不是初创期。——只有在佛教造像的高峰期,佛像才有可能传入中国,并且在四川普遍出现在摇钱树上。制造于公元125年的四川摇钱树,说明了古印度佛像高峰期的相对年代。考虑到中印之间的迢迢万里的艰难路途,加上宗教信仰的接受程度等因素,又考虑到中国早期佛像几乎与佛教教义无关,应该是古印度造像而不是在佛教教义影响下出现的中国制造的佛像。据此,我们推测,古印度的佛像高峰期应该在公元一世纪中后期。如果考虑到50年左右的时间差,那么,所谓“公元一世纪中后期”,可以把印度佛教的第一个兴盛期具体到公元80年前后。
由此联想到许多学者的关于迦腻色伽与佛像起源的讨论。关于他即位年代有公元78年说、公元128年说、公元144年说,中国学术界比较通行的是公元144年说。在此毋庸详细讨论各种学说所依据的证据,事实上,这些证据极为繁琐,而且由于缺少明确的纪年依据,他们往往依赖各种文献记载和考古实物之间的“证据链条”加以推测。尚未知道有中国学者参与“证据链条”的详细讨论,我们也没有能力进行这样的讨论。
不过,至少可以肯定“公元144年说”的可能性很小。——如果迦腻色伽即位于公元144年,那么,公元二世纪中期前后形成的第一个造像高峰,无论如何也难以解释延光四年佛像以及在此期间或稍后形成的大批量的摇钱树佛像。——“公元144年说”显然与中国造像所推定的早期佛像编年框架无法协调。同样的道理,“公元128年说”也无法得到满意的解释。因而我们更倾向于“公元78年说”。
也确实,有不少学者更加倾向于“公元78年说”:克雷文(Roy C.Craven)在《印度艺术简史》(1976)中指出,“公元78年是引人注目的年代,因为看来既符合贵霜王朝的年代,又标志着重要的塞迦(shaka)纪年的元年,而且与佛教经典的第四次结集巧合”③。Partha Mitter在《印度美术》一书中注明迦腻色伽的在位时间是“c.78~101ce”④。印度的史学家也相信“迦腻色伽是在公元一世纪时执政,并开创了自公元78年开始的塞种纪元。迦腻色伽的纪元可能逐渐就被称为塞种纪元,因为这个称呼被西印度的塞种王公们使用了一个很长的时期”⑤。其实,早在1960年,在英国伦敦曾为此召开了专门的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后来发表了26篇论文,没有人使用“公元144年说”,仅有一人采用“公元128年”说,其他诸家均采用“公元78年说”⑥。我们无意进一步追踪他们的讨论,但是,可以确信的是,这个年代,得到了中国考古文物的强烈支持。
迦腻色伽即位于公元78年这个结论,直接引起古印度佛像产生时期的讨论。就秣菟罗的佛像造像而言,早在1927年,库马拉斯瓦米(Ananda K.Coomaraswamy)就已经推测“早期作品的年代可推溯至迦腻色伽初年以前,那时佛像就开始制作了”,也明确指出佛像产生的时期是“公元一世纪中叶或初叶”。即使铸造于迦腻色伽金币上的有希腊字母铭文明确标示的那件佛像,也同样只能说明了佛像产生于迦腻色伽以前。岂有铸造用于商贸流通的金币而使用不为人所知的佛像的道理?所以,结合中国发现的公元125年摇钱树佛像分析,我们也同样赞成库马拉斯瓦米的观点,认为“佛像是在西元一世纪中叶前后,至少同一世纪的末叶以前制作的”。这里,我们应该满怀敬意地提到荷兰的德黎芙女士的论断,她的著作《斯基泰时期》在1949年已经出版,直到2002年才有了完整的中文译本,她首先依据铭文研究的成果,强调了迦腻色伽即位于公元78年的意见,指出:“公元一世纪的前半已经进入了秣菟罗时代了,那个时代已经习惯于把佛陀的形象以人的姿态表现了。”⑦在古印度造像中,缺少非常明确的纪年基准,即使造像中有王名与年数,也因为印度历史的模糊、纪元的起始年份的含混不清而丧失力度,因而对印度古佛像的编年基准,可以说均无法忽视中国纪年造像那样斩钉截铁的份量。前列两位学者能够分别在八十年前和六十年前作出这样的判断,确属难能可贵。
3 文献记载中的汉代佛像基本可信
考察佛教造像传入中国的主要根据,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即史料与实物。但是,由于时代久远,加之各种人为或不可预测的因素,可以利用的考古实物毕竟有限;在史料方面,多为后人追记,有的则为僧人杜撰,以讹传讹的现象不绝史书。尽管如此,这些文献记载还是为我们研究早期中国的佛像艺术,提供了参考依据,仍值得在学术研究中进行分析取舍。
就文献记载,佛像传入中国于东汉明帝时期(公元58年~公元75年)即已开始。《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二引南齐王琰《冥祥记》云:
汉明帝梦见神人,垂二丈,身黄金色,项佩日光。以问群臣,或对曰:“西方有神,其号曰佛,形如陛下所梦,得无是乎?”于是发使天竺,写致经像,表之中夏。自天子王侯咸敬事之,闻人死精神不灭,莫不惧然自失。初,使者蔡愔将西域沙门迦叶摩腾等,赍优填王画释迦倚像,帝重之,如梦所见也。乃遣画工图之数本,于南宫清凉台及高阳门显节寿陵上供养。又于白马寺壁,画千乘万骑绕塔三匝之像(T52,No.2106,p.413,c2 -11)。
这则记载,千余年来的佛教文献中常见引用,但是这则史料显然是僧侣们探寻佛教渊源而不断回溯和层层积累的结果,带有明显的虚构和想象⑧。因为在袁宏《后汉记》、范晔《后汉书》中,只提到汉明帝遣使求法,既不见使者名字,也不见有带携佛经和优填王释迦倚像之事。至于优填王造像,当出自《增一阿含经》,就《增一阿含经》的这个说法,当是在盛行佛像崇拜后才形成的,不完全可信。关于《冥祥记》的这一记载,以前都认为是完全不可信的。但现在的考古发现证明,明帝(公元58年~公元75年)之后五十年(公元125年),在三峡已出现了佛像,具备了佛教造像的基本特征。《冥祥记》的这段记载,纵然有虚饰的成分,其中提到的“项佩日光”、“显节寿陵上供养”云云,确是早期佛像形象特征和依附于丧葬的特点,这已经在阮荣春教授的“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中得以证明。而且,以前所认为的,公元一世纪期间古印度的贵霜时期尚没有产生佛像,现在由“延光四年”佛像的出土,这一说法已经没有必要再予以坚持,至少在公元一世纪中后期,印度已经形成了佛像偶像崇拜。而且,这段时期也未必是佛像诞生的最初期。
“明帝感梦”之事固然未必可信,但佛教于此前后已传入中土当属事实。《后汉书》卷四十二《楚王英传》⑨记载,刘英“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汉明帝于永平八年(公元65年)说:“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这里提到的“伊蒲塞”,多译为“优婆塞”,即在家亲近奉事三宝和受持五戒的男居士;“桑门”即“沙门”,即出家修道的僧人。“尚浮屠之仁祠”与“与神为誓”对举,可能说明这位死于公元71年的楚王刘英,在斋戒祭祀时,可能已经设有供奉对象了。“楚王英始信其术,中国因此颇有奉其道者”,毕竟这时的佛教信仰还并不普及,也没有引起知识精英阶层的足够重视。
此后六七十年间,东汉桓帝(公元147年~公元167年在位)在皇宫中“设华盖以祠浮图、老子”。颜师古注解说“浮图,今佛也”,可能指的是佛像。桓帝还是与那位刘英一样,把浮图与黄老并祀。浮图与黄老均主张清静无为,按襄楷的说法,“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尚生恶杀,省欲去奢”(《郝氏后汉书》卷八十三下),均能赐福祐人,故而他们并不刻意区别何为浮图,何为黄老,体现了佛教初传中国混迹于神仙方术的基本特点。中国学术界曾认为东汉桓灵年间(公元147年~公元189年)已有不少佛教造像或具有佛教特征的造像,现在看来并非不可能。
见诸《三国志·吴志·刘繇传》有关笮融的史料之中,还明确记载兴建佛寺、佛像和社会一般民众信仰的情况。笮融本人信仰佛教,他为了宣传佛教,曾“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彩”,且把“设像”与课读佛经结合起来。从“布席于路,经数十里,民人来观及就食者且万人”分析,这是一个盛大的浴佛法会,其中一定也包含有行像仪式。不过,笮融所造铜人就文献记载和邳州发现的举右手铜人造像(见图2)⑩分析,佛像的特征尚较模糊。既然作为浴佛用,当用裸形诞生佛,即裸形童子立像;而且既以黄金涂身,又何须衣以锦彩。不过这种浴佛或行像,对中国人来说,是件新鲜事,“来观及就食者且万人”,首先是好奇心的驱使,其次是为了就食。虽然他们对深奥的教义并不会产生多大兴趣,但毕竟看到了“佛像”,这无疑在他们的心目中又树起了一尊宗教信仰方面的具像。
三国时代,在南方,弘扬佛教取得很大成效的康僧会,其世居天竺,父亲因商贾移于交趾。他于吴赤乌十年(公元247年)来到建业(今南京),营立茅茨,设像行道,由是“江左大法遂兴”。曹不兴、卫协等亦在这“大法遂兴”的时代风潮下不断涌现出来。至此,可以说,中国佛教艺术迎来了它的第一个盛期。
在北方,汉魏时期的佛教信仰,并未像南方那样植根民间流布广泛,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统治者的限制,《高僧传》卷九《佛图澄》:“往汉明感梦,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汉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汉制,亦循前轨。”当时佛经的输入和翻译也多出自天竺、月氏、安息、康居等国来华僧人,汉地沙门极为少见。记载中最早的汉地出家者是严佛调,所著《沙弥十慧章句》为第一部汉僧佛教著作。
曹魏时期,政府虽一再颁布政令禁绝祠祀。据《魏书·释老志》:“魏明帝曾欲坏宫西佛图(佛塔)。外国沙门乃金盘盛水,置于殿前,以佛舍利投之于水,乃有五色光起,于是帝叹曰:自非灵异,安得尔乎?遂徙于道东,为作周阁百间。佛图故处,凿为蒙汜池,种芙蓉于中。”若按前引《高僧传》所言,险为明帝所坏的宫西佛图,当为西域胡为所立。
西晋初期,汉人出家仍受到禁止,由于佛教已深入民间,禁令实际未能奏效,据载西晋已有僧尼二千七百余人。此间佛教在中国北方得到迅速发展,佛教发展最为活跃的地方是位于丝绸之路上的几个城市,据载有敦煌、酒泉、长安、洛阳等。大乘佛教在这期间趋于盛行,并出现用汉文写的注疏著作。在涌现的诸多汉文译经僧人中,以世居敦煌的月氏人竺法护成就最为卓著,终其一身译经149部,梁僧祐在《出三藏记集·竺法护传》中赞誉说:“经法所以广流中华者,护之力也”。
有关西晋北方的佛教艺术,以洛阳为例,《魏书·释老志》云:“晋世洛中佛图有四十二所矣。”据《法苑珠林》卷一百二十载,西晋有佛寺180所,据以可知,洛中之外,佛寺也并非希罕之物,其中或许有佛像存在,只是北方汉至西晋的佛教遗物今多已不存。
就以上史料而言,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佛教及其造像在中国发展的最初阶段的情形。应该说,佛教造像在中国的兴起主要在笮融和康僧会之际的汉末至三国期间。现在,基于文献分析所得出的结论,已经可以通过延光四年佛像加以证实。

图1 重庆三峡出土延光四年(公元125)摇钱树佛像左,佛像特写;中,佛像与钱树残片;右,摇钱树座题字特写。

图2 邳州青铜造像
注释:
①2002年3月22日,陕西宝鸡市考古队的龙宏斌和辛怡华,在《中国文物报》发表了简略的报告,同年7月又发表了比较详细的报告,发表了相关照片:《陕西宝鸡考古队完成三峡文物发掘任务》,中国文物报,2002年3月22日第2版;《重庆丰都槽房沟发现有明确纪年的东汉墓葬》,中国文物报,2002年7月5日第1版。又,何志国《丰都东汉纪年墓出土佛像的重要意义》,《中国文物报》2002年5月3日第7版。
②罗二虎《重慶で新発見の紀年銭樹の仏像について》(重庆新发现的纪年钱树佛像),龍谷大学,《佛教文化研究所紀要》43,2004年,pp.62 -71。
③罗伊·C·克雷文(Roy C.Craven)《印度艺术简史》(A Concise of Indian Art),王镛、方广羊、陈聿东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2月。按,原著撰于1976年。
④Partha Mitter《印度美术》(牛津艺术史丛书),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
⑤辛哈班纳吉《印度通史》,张若达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3年,第176页。
⑥这一情况,来自杉本卓洲的论文。杉本卓洲《マトゥラにおける仏像崇拝の展開》(その1、その2、その3),金沢大学文学部論集.行動科学.哲学篇 17,1997年;18,1998年;19,1999年。
⑦德黎英《斯基泰时期》,许建英、贾建飞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按,该书第一章《纪元》(第1-70页)专门讨论年代问题,认为迦腻色伽即位于公元78年(第50页)。又按,据马歇尔《塔克西拉》汉译本第54页:西方学者一般把中亚的游牧民族笼统地称为斯基泰人(Scythians),印度人称他们为塞人(Saka),中国人则称他们为塞人或塞王。他们主要来自三大部族,即Massagetai、Sacaraucae、Sahae。
⑧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之第一篇《佛教之初输入》,湖南湘潭:湘潭大学出版社,2011年。
⑨《后汉书》卷四十二《楚王英传》,中华书局新校本第5册第1428页。
⑩邳州市燕子埠乡尤村发现,墓室上门额缪宇墓志铭表明墓主为东汉桓帝元嘉元年(151)彭城相行长史事、吕守长缪宇。该墓所出鎏金铜造像。通高7厘米,重560克,造像呈曲膝跪坐状,右手拇指分开,四指并拢向上举过耳,掌心向前,示无畏,长袖垂于腕下,左手轻轻放在右膝上。
此像跽坐,衣饰有花纹,头发盘结由发簪固定,均与佛像有别,故而可说是受佛教影响,却难以说成是佛像。而且,举右手也不完全是佛像特有的做法。巴尔胡特窣堵波的龙王礼佛就有举右手施无畏印的外道形象。
[1]罗伊·C·克雷文(RoyC.Craven).印度艺术简史(A Concise of Indian Art)[M].王镛,方广羊,陈聿东,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2]辛哈班纳吉.印度通史[M].张若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3.
[3]德黎英.斯基泰时期[M].许建英,贾建飞,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
[4]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M].湘潭:湘潭大学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