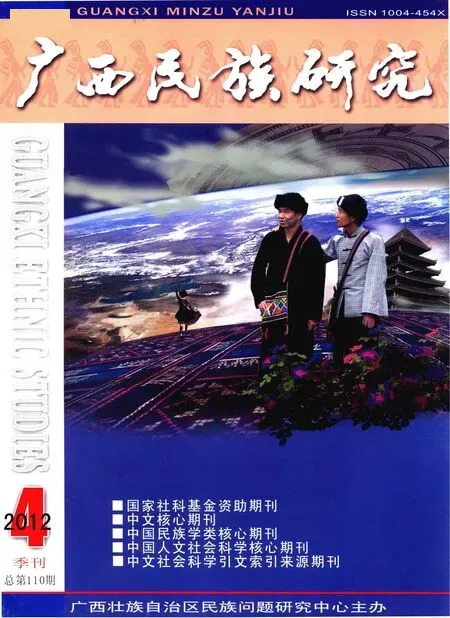当前湘西苗族社会的“文化网络”治理机制研究*:以湘西花垣县BL村为例
崔 榕
一、导言
杜赞奇认为中国传统社会像一张“权力的文化网络”,即人们生活在由各种组织、规范、礼仪、信仰等因素所构成的文化网络之中。这是一个天衣无缝的网络。它可以严格约束人们的言行,有效控制着乡村的社会秩序。[1](P3;P10)杜氏提出的“权力的文化网络”成为中国学者研究乡村社会治理的一种重要模式。
作为中国农村的组成部分,湘西苗族地区传统社会中同样也存在着一张权力的“文化网络”,它由民间精英、社会规约、民间仪式、民间信仰等多种文化因素组成,在历史上这些因素相互协调、配合,共同发挥规范、控制苗族社区的功能。但是,随着国家现代化和乡村法治建设的推进,湘西苗族地区治理中的“文化网络”已发生了很大的变迁。
那么,在当前湘西苗族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这一“文化网络”具有哪些治理特征和运行规律?它变迁中苗族社会治理提供了哪些强大保障?弄清这些问题,是当前民族地区充分发挥“文化网络”的治理功能,构建民族社会的治理机制,维护民族地区团结、稳定与和谐发展的重要前提。为此,笔者选取湘西花垣县BL苗族村寨作为田野调查地点,重点对当前湘西苗族社会传统“文化网络”所生成的治理机制进行了研究。
二、当前湘西苗族村寨“文化网络”治理机制主要构成及其功能体现
(一)民间精英:乡村秩序的维护者
民间精英是乡村社会治理中不可或缺的主体,他们在乡村政治社会结构中,掌握着一定的话语权和符号权利,能够调动更多的社会资源,获得更多的权威性价值分配。在BL村,民间精英类型既包括传统精英类型,如苗族头人、宗族族长和文化能人,也包括现代化建设和新的发展机遇造就的乡村新型精英类型——农村实用人才。这些民间精英主要以以下方式参与村寨治理
1.解决乡民纠纷,调节人际关系
笔者对近两年BL村民间精英参与调解村民矛盾纠纷事件情况进行了大致统计,具体情况如下:

次数事 件参与处理成功率 (%)总数 参与成功次数邻里不和15 13 86.67%婆媳不合14 10 71.43%夫妻不合11 8 72.73%山林、田地划界问题53 42 79.25%13 11 84.62合计
可见,他们对于村里纠纷能够进行有效地参与和处理,调解的总成功率接近80%。目前,在BL村调解纠纷事件中,民间精英参与方式呈现出以下新的特点:
第一,国家正式权力与民间精英非正式权力形成力量互补。改革开放以前,民间精英受到国家政权机关的排挤与抵制,一般情况下极少正式参与村内事务的管理。而在改革开放以后,为了更好地维护基层和谐的发展环境,国家除了采取现代法治外,开始主动尝试通过协调或妥协的方式,充分借用湘西苗族社会中的民间精英,处理乡村社会的人际关系,来维护乡村的公序良俗。由于“正式行政权力”选择与村里的民间精英合作,实现了权力与文化的有机结合,使得权力在实施过程中,不仅具有很强的正当性和权威性,而且也变得更加符合情理,让村民们易于接受与信服。因此,他们在维护乡村秩序、传达国家意志等工作上往往“比那些不为村民接受、单单由上级指派的体制精英来得更容易,也更有效率”[2]。正因为如此,在当前国家基层政权的调整中,BL村的民间精英的身份和地位得到了重新认识,其所发挥的治理功能也日渐凸现。村民们反映,现在村干部经常会邀请村里的“头人”处理问题,“只要‘头人’出面,90%的问题都能解决。”
第二,新型精英开始充当村民矛盾的调解者。以往,“族长”、“寨主”等传统精英深谙村落权力运作的游戏规则,是民间权威和村落非正式权力中心。因此,在调解村民矛盾冲突方面,主要由他们来出面解决。但目前,新型精英——农村实用人才也开始参与其中。村民们反映,现在村里发生纠纷,他们除了向村镇干部和德高望重的长老们反映情况外,还会和村里“土专家”、“田秀才”等实用人才商议处理办法。农村实用人才的参与,往往会促使这些事件得到及时有效地解决。
对于农村实用人才在调解矛盾中所发挥的作用,笔者从村民以及村镇干部对农村实用人才的评价中得到了证实,他们普遍认可农村实用人才的处理方式。例如,村民WDF反映:
他们是我们寨子里的“香饽饽”,哪家要是有什么矛盾,他们出来很管用,我们都听他们的,哪家有“骂娘”扯皮的,只要他们出面解决,问题百分百都能解决,没有一个敢倔的。
村干部WBS也承认:
农村实用人才的确在解决村里纠纷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们有时要解决村里的难题时,还专门请他们出马帮忙解决,办事效果很明显。
农村实用人才这一突出作用,也得到了政府部门的肯定,认为他们是“农村和谐使者”,由他们协助党委、政府向群众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调解社会矛盾,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农村实用人才之所以可以发挥这样的作用,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这些在现代性背景下崛起的新型精英,是农村生产力因素中最先进、最活跃的组成部分。其身分特征与传统型精英有明显不同:若传统型精英是以名望、地位、特定文化中的位置乃至明确的自我意识为前提;而新崛起的现代型精英则因为市场经济中的成功而在乡村具有广泛的影响力。[3]他们既能实现个人致富,又能改变村里的穷困面貌,这种杰出才能和独特魅力,让村民们佩服、信任。二是在经济利益关系上,农村实用人才与村民们之间具有现代科层式的关系。农村实用人才建立农产品基地,实行产业化、规模化经营,大多数村民都成了其雇员,在这种经济体制下,村民们理应服从农村实用人才的管理。三是与传统精英一样,农村实用人才不仅熟悉村里的村规民约、乡俗礼节等文化规范,而且对村里每家每户的情况,甚至对每一个人的性格,他们都相当了解。正因为如此,当村里发生矛盾、冲突时,他们会根据实际情况,游刃有余地采取相应的处理办法。
2.组织村寨文化活动,传承苗族传统文化
文化是村民的情感归依和心灵家园,也是村寨产生凝聚力的重要资源。文化精英在宣传、传承村寨文化的同时,也增强了村民之间的情感认同。在BL村,影响力较强的文化精英共有5名,年龄均在60岁以上。他们对苗族传统文化充满感情,在村寨历史、文化的讲述以及对习俗规则的解释方面具有很强的话语权。
“村庄本身具有一种正面的评价机制,即具有制造生活意义的能力。”[4](P247)近年来,随着国家民族文化保护政策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实施,BL村对于民族文化活动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参与苗族文化活动也随之成为村民们重要的生活内容,这为村寨的文化精英提供了施展才能的机会。如WHS(66岁)告诉笔者,他现在的生活一直处于“忙碌的状态”,“本寨和外面寨子组织活动要请我,旅游景区文化设计要请我,苗族椎牛仪式要请我,不懂的地方都要请教我。”从他的谈话中很容易察觉出其内心的欢悦与满足,这种生活状态让自己的价值与意义在村寨中得到了极大的体现,其出任“乡村领袖”的主要动机仍然“是出于提高社会地位、威望、荣耀并向大众负责的考虑,而不是为了追求物质利益。”[5](P4)
以前BL村由于没人“牵头”,村寨的文化活动开展较少,村民的生活平淡。面对外来多元文化的“入侵”,村寨生产地方性价值能力较弱。但是,近年来,在村寨“文化能人”的努力下,村寨的文化活动逐渐开展起来,村寨组建了苗鼓队、舞狮队、舞龙队等文艺团体,这些文艺团体构建和巩固了村寨新的生活意义。除了经常外出参加表演外,BL村还多次主办湘西苗族传统节日“赶秋”活动。在为村寨赢得荣誉的同时,也给村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自豪感和充实感,拉近了村民之间的距离,促进了村民的团结与合作,且村民的文化主体意识也得到了重新唤醒,使传承与发展民族文化成为村民重要的生活价值取向,有效避免了市场经济中的个人主义与消费主义对他们生活全方位的占据。
3.带动发展经济,促进村寨的现代性转型
经济繁荣是新农村建设的目标之一,也是当前国家倡导的乡村治理的主要内容。在BL村,新型精英不仅在调解村民矛盾冲突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还担当着带领广大村民脱贫致富,促进村寨经济发展的重任。
第一,新型精英促进村寨生产方式的改变。BL村以前的经济结构较为单一,主要是种植水稻、玉米等传统农产品,人们的思想观念保守,生活水平较低,在现代化发展中处于劣势。近年来,该村的新型精英通过引进新技术、新产品,实行规模化经营,使得该村农业生产结构发生了很大改变,出现专业化、规模化的发展趋向。不仅如此,该村新型精英在个人获得较好经济效益的同时,还招募和吸纳了85名村民,增加了他们的经济收入,有力地促进了村民生活质量的改善和提高。
第二,新型精英促进了村民知识水平和思想观念的改变。科技实践与创新精神是新型精英的独特品质。BL村的新型精英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一方面,他们敢于将自己的田地作为最新科技的“试验田”,在广大农户面前起到示范带头作用;另一方面,他们敢于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大胆对农业科技进行改进或创新,为农村增产增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为村民提供了一个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农业的活生生的样式,极大地触动了村民的思想观念。在调查中,村民LXT(47岁)为笔者谈到了他在技术或思想上的“收获”:
以前搞农业只晓得勤扒苦做,没有想过种田还要现代技术。他们 (农村实用人才)头脑灵活,有知识,经常教我们如何种植新品种,如何管理。以前我们种地主要是为了自给自足,没想过可以靠农产品赚钱。但是,他们见识广,路子多,搞规模化生产,做‘订单式农业’,发家致富了。他们让我们开了眼界。
目前,在这些新型精英的资助和鼓励下,已有12名村民已开始“单干”,尝试发展自己的产业。
第三,新型精英推动了新农村公共服务设施建设。BL村的农村实用人才发家致富后开始回报社会,不仅扶持广大百姓兴业,而且还积极投入村寨里的公益事业,对村容村貌进行改造,努力为村民们营建一个整洁舒适的生活环境。例如,2008年村寨整修道路,有6名新型精英出资,每人捐款3万元,共计18万元。2009年,村寨进行水渠配套工程建设,吴天龙带头发动群众捐资10万余元,义务投工600余工日,完成了村寨水渠工程,可以实现600余亩稻田旱涝保收。在新型精英的支持与参与下,BL村的村容村貌有了很大的改善。
(二)还傩愿:乡村秩序的文化表达
在BL村,还傩愿是一项十分隆重的仪式活动。该仪式可以增强社会道德规范的权威,巩固民族成员对文化边界的持守,能有效维护乡村社会秩序的稳定。
第一,还傩愿是BL村村民广泛参与的仪式活动,在村民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近年来,BL村的村民在秋收之后就会开始筹办还傩愿仪式。一些村民表现积极,经常会带头出资选购道具行头、推荐演员、编排节目等。仪式举行时,村寨里的男女老少欢聚一堂,对仪式中的人物扮相、台词和故事情节等津津乐道。在谈到傩戏时,村民WSG(42岁)兴奋地说:
还傩愿在我们寨子里是一件极为隆重的事情,我们都很喜欢。每次只要是举行这样的活动,我们都会主动捐款。其中,傩戏表演最好看,看的人都很多,每次戏场子都被会人围得满满的,他们的表演也很精彩,经常逗得我们哈哈大笑。
在还傩愿仪式当中,村民们的投入、捐助、观看和谈论等,有助于形成以聚合、团结为价值取向的社会环境,而这种的社会环境对个人的行动也起到了约束作用。这种约束是微观的个体行为秩序形成的基础,宏观社会环境正是通过其对个体行动所施加的一定的约事,确保了整个宏观社会过程的有序运行。[6](P316-326)在关注村寨公共事务氛围之下,村民之间的感情得到了交流,和谐团结的人际关系得到了不断加强和巩固。
第二,还傩愿仪式是村寨争取、维护村寨良好荣誉的机遇。为了让外来的客人对村寨留下好印象,BL村每一次还傩愿的举行都显得十分慎重。村干部和村里精英努力动员村民打扫场院,组织排演节目,村民们也主动配合村寨活动安排,以和善的态度来接待客人。有村民反映:
还傩愿时,我们都会帮着搬运演出器材、出工修路、招待客人等等,主要是为了寨子的这个活动能够举办得更加出色,让客人对我们寨子留下好的印象。我们要尽力给寨子争光,而不能给寨子丢丑。
因此,还傩愿仪式的举行,有利于加强地方性规范,让村民们更为注意自己的言行,共同维护村寨的尊严和名声,从而也强化了村民的村寨认同感和归属感。
第三,BL村苗族村民在还傩愿仪式中象征性地引入“国家”,以在乡村治理中寻求国家的“在场”。
首先,神坛的布置加进了国家的符号。在仪式中引入“国家”,是湘西苗族的传统习俗。例如民国时期,湘西苗族的神坛对联中就有这样的内容:“黄金殿上巍巍主,白玉阶前荡荡臣”、“洒扫礼门迎圣驾,展开仪路接君王” 等。其中“主”、“圣驾”、“君王”作为国家权力的象征,已被苗族民间引入仪式中。如今,BL村还傩愿仪式仍然沿袭着这样的传统,在对联中有这样的词句:“国基铸定千秋固,泰斗昭辉万代宁,民拥宪法行善道,安居乐业谢皇恩”。如果说此前还只是以“君王”等象征符号隐约地表达对国家的尊崇,现在则直接将国家请进了仪式中,实现了国家力量对苗族社会的延伸,从其对联中可以看出BL村村民希望在乡村秩序中得到国家权威的有力保障。
其次,仪式中各路神仙的出场是对国家治理功能的模拟与表达。在还傩愿仪式中,各路神仙,如探子、先锋、开山、和尚等都会登台亮相,通过独白与演唱,来介绍自己的特殊能耐。
人类学学者认为,傩戏中的神是帝国官僚的化身;鬼是人们不喜欢的危险的陌生人的超自然的代表。神、鬼表达的是农民对他们的社会世界的阶级划分。[8](P147-148)同样,BL村傩戏中的众神也可视为是对国家或国家官员的投影。岁月虽已变迁,但BL村苗民在傩戏中仍然上演着驱魔赶鬼的故事,这些故事或符号与以文字记载的国家意识形态关系极为密切,表达出人们对国家的持久依赖,希望能够借助于国家威力,来完成为村寨禳病祛鬼、增添福祉的心愿。
再次,还傩愿仪式是对国家机构运作的模拟与象征性的操演。芮马丁曾指出:“中国社会中的仪式,……反映了政治对宗教仪式的深刻影响,同时反应了民间对政治交流模式的创造。”[9](P149)同样,BL村傩戏中的各位神仙与国家机构也应存有象征比拟关系,这些角色的分工实际上是对国家机构的运作的模拟,是国家形象在民间文化场域中的特殊表现。BL村以通俗易懂的戏剧形式将国家“拉到”人们的生活当中,“实现”了国家对苗族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进行管理的愿望。
(三)民间信仰:村民的生存策略和逻辑
民间信仰是湘西苗族解除生活忧患的一种重要策略,当地民间有“三十六神,七十二鬼”之说。虽然在1949年后,特别是在20世纪60-70年代受到过强烈冲击和严厉批判,但是湘西苗族一直以来以各种方式坚守着这一份传统,从未真正放弃过。
在BL村,客老司SSD较为详细地介绍了他目前常做的36堂法事①法事名称遵照讲述者的发音记录,笔者按法事的治理功能进行了大致分类。统计结果如下:
1.有关人际关系处理的法事:“土排”;“比考”;“岩鱼”;“岩堂”;“却勾柔”。
2.有关生产事务的法事:“烧田坎纸”;“攻牛游”;“谢土”。
3.有关病情处理的法事: “了鬼洞”; “神经愿”;做“五鬼”、“了鬼端”; “扒高度”; “广头”;“鬼悟”;“五给忙角”;“五给咔从”;比露”;“露道”。
4.有关村寨事务处理的法事:还傩愿;“保东斋”;“倒火场”;“喜斗洞”;求雨。
5.有关家庭事务处理的法事:“洗屋”;“殇亡鬼”;“求子愿”;“吃斋的傩愿”;求财;“修得悔”;“架路边桥”;“架天桥”;“接龙”;“架桥”;“全空”;“做天狗”;“隔殇亡鬼”。
可见,神灵信仰与他们的生活紧密相联,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或需要,他们都有向神灵祈望帮助的心理定势。尽管BL村的民间信仰是一种非科学的世界观,但是,它的客观作用不可低估,它为村民提供了一种公认的价值取向和生活规则,使人的行为有底线和有畏惧。
目前,在我国的许多乡村社会里,在市场经济的猛烈冲击下,人们被商业戾气所袭扰、裹挟,乡村社区共有的信仰正被摒弃。然而,没有信仰约束的乡村社会是危险可怕的,“一旦村庄社会中的人们不再受到内心力量和外力道德力量的约束,则任何不可理喻甚至丧尽天良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10](P232)而在BL村的情况却恰好相反。独特的民间信仰为村民生活提供了多样的公共服务,不仅调节了人际关系,加强了地方社会网络的力量,避免了村寨社会道德的失守,而且也关照到了政府所难以触及的地方,成为政府管理的有益补充。因此,BL村村民对村寨信仰传统的恪守和执着,在当前乡村社会价值多元化背景下更显难能可贵。
(四)习惯规约:乡村秩序维持的界线
习惯规约是湘西苗族社会中维护社会稳定,进行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之一。这些规约有成文的,也有不成文的约定俗成的规矩,但不管哪种形式,都起到了整饬民风、预防失范的功能。目前,BL村村民生活中主要还保留着以下习惯规约:
1.合款
合款是湘西苗族以地缘关系为基础建立的一种组织形式。湘西苗族聚居区,曾长期保留“合款”组织,并具有强大的凝聚力。1949年以后,由于村级行政机构与法规制度逐渐建立与完善,合款组织的部分功能被基层政府组织所取代,其存在的必要性大大减少。
在BL村,村民们在目前日常生活当中,有时也动用“合款”形式:一是在秋收时,他们会制订款约,以维护秋收秩序;二是与邻界村寨发生山林、田地纠纷时,村寨里的老人会出面组织“合款”,以求在与对方交涉时更具优势。
除了上述情形以外,村民们更多地是将“合款”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对外讲述,且在有意识地“放大”其组织功能。村民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当前社会转型时期,他们仍存有忧患意识,他们希望通过突出“合款”这一民族文化资源,来形成威慑力,防范村寨利益受到外界侵害。
2.乡规民约
乡规民约是湘西苗族村寨传统的治理方式。民国期间,国家政权虽试图在湘西苗族地区推行国家司法管理,但在实践上,它却未能成功废除地方治理的传统规则,建立起“正统”的执法和监察渠道。因此,乡规民约仍然是巩固湘西苗族地区治理秩序有效手段。如1919年,凤凰县都良由苗寨为了维护水井卫生,就立下护井石碑[11](P278-279),1949年以后,国家为了实现对民族地区的有效管理,并没有强行取消民族地区合理的传统规约。因此,至今湘西苗寨还延续着制订乡规民约的习俗。
目前,BL村常常借用乡规民约来维持村寨的生活、生产秩序。乡规民约规定:村里出现偷盗、破坏生产及作风不良等行为,要求肇事者杀1头猪、罚交100斤米、100斤酒,用以安排全体村民一顿饭食。吃完之后,召开村民大会,要求肇事者向全体村民作检讨,并安排两场电影。
村干部是BL村乡规民约的主要制定者和执行者,他们在协调国家法规与乡规民约的关系上显得十分谨慎:一方面注重与国家权力积极配合,尽量促使村寨乡俗传统成为国家法规的有效补充;另一方面在解决纠纷方式上,讲究规约优先原则,国家权威是备用资源和最后底线。
虽然,乡规民约在内容上越来越受国家法律的影响,但是相对于国家法律,乡规民约具有特定的治理原则及管辖范围,其处理事情的方式更符合村寨习俗,结果容易让人接受。因此,在近两年BL村的纠纷事件处理中,乡规民约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权威性得到了大多数村民的认可与尊重。
3.饮血息讼
湘西苗族敬畏鬼神,深信神灵在人间的超凡力量和咒语的灵验,当遇到是非曲直难以分辨或是被冤枉无法自白的情况下,苗民通常求助于鬼神来裁定。其中,最常见的形式就是去天王庙或土地庙“唱血酒”赌咒。如清严如熤在《苗防备览·风俗上》中就记载有:
遇冤忿不能白,必造诸天王庙,设誓刺猫血滴酒中,饮以盟心,谓之“吃血”。……其入庙,则膝行股栗,莫敢仰视。理屈者,逡巡不敢饮,悔罪而罢。
民国时,此种决断是非的方式仍很盛行,“苗民两造争端,是非莫辨遇冤不能自白,即至天王庙吃血设盟,无论大小讼案,当可立决。”[12](P480)
1949年以后,国家全面主导着社会转型和民间社会生活的样式,湘西各地的天王庙、土地庙作为“封建残余”而被摧毁,人们遇到民事、刑事纠纷,一般也会寻求政府力量解决,“喝血酒”的情况明显减少。但是,国家权力并未完全消除村寨的传统规则,“喝血酒”在BL村还是以隐形的方式存在。不过,为了躲避国家的阻拦和惩罚,村民们一般会选择在晚上进行该仪式,程序也更为简略:在见证人面前,双方“赌咒,喝血酒,摔碗”,然后立即散开。
1978年以后,为了恢复民间社会的活力,国家权力开始有意识进行回收,政治环境也日益宽松。在这种情况下,BL村又重建了“天王庙”和土地庙,“喝血酒”又一次成为村民们常用的解决纠纷方式。有村民反映:
我们寨子一直有“喝血酒”的习惯,最近的一次发生在2006年。有两家发生了矛盾,他们就到天王庙去“喝血酒”摔碗赌咒。之后,他们就不吵架了,都等着“赌咒”显灵。
可见,在当前法治社会建设进程中,BL村的村民们还在运用“喝血酒”的方式来处理日常纠纷,虽然赌咒后果难以查验,但它实现了村民们对“无讼”传统的尊重和乡村礼治秩序的维护。
三、思考与启示
第一,湘西苗族“文化网络”机制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一直延续其旺盛的生命力。自从中国被卷入现代化的历史宿命之后,国家政权就曾试图斩断乡村社会中的“文化网络”,对乡村实行直接管制。然而,“20世纪国家政权抛开、甚至毁坏文化网络以深入乡村社会的企图注定是要遭到失败的。”[13](P4)这一结论在民国国家政权向湘西苗族乡村渗透、扩张的实践中得到了证实。1949年至1978年期间,国家的权力虽然深入到了社会底层,取得的管理效果也十分突出,但是对乡村的治理方式却过于严厉与僵硬,乡村社会又缺失了活力与个性。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主体的多元化和利益的分化,湘西苗族社会矛盾也逐渐增加。为了促进民间社会健康和谐的发展,国家政府开始调整治理方式,在运用自身的能量时,也开始征用民间社会中传统的治理资源,其中最具效力的治理资源之一就是乡村中“权力的文化网络”。于是,当前湘西苗族地区传统的文化网络治理机制又重新焕发了生机,其社会控制功能得到了充分发挥。
第二,在国家推进现代法治建设过程中,湘西苗族社会对其传统的治理方式进行了灵活、有效地调适,实现了苗族社会治理模式的再建构。湘西苗族一方面主动顺随和接纳国家的意愿与倡导,让“国家在场”,使社会主义法治成为其实现乡村治理的主要手段;另一方面,他们也并不丢弃自己的文化传统,仍然延续着其“文化网络”治理机制,并且发挥了独特效力。湘西苗族“文化网络”的铺陈,不仅实现了国家公共权力运行与地方性利益的动态平衡,避免了当前社会急剧变革和多元文化价值对湘西苗寨地方性规范和村民本体性价值的冲击,有效地保护了苗族村寨的内聚性,而且也为苗族传统文化构建了一个传承和发展的完整“场域”。
第三,民族地区传统“文化网络”的延续,对于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社会主义法治的要义自然是国家法主导对乡村社会秩序的塑造,但是“法治秩序的建立不能单靠制定若干法律条文和设立法庭,重要的还得看人民怎样去应用这些设备。”[14](P58)也就是说,它需要与乡村社会礼治秩序的契合和互动。同时,田野调查也显示,国家法并非容纳不了民族社会中的“小传统”。民族社会中传统的“文化网络”机制,是重要的社会管理资源,若能正确认识和理性利用,完全可以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有力补充和有益资源,而并非一定是社会主义法治进程的障碍。因此,国家需要创新社会管理方式,可以从民族社会获得合法性,与民间力量一道来整合社会;两者保持良性的沟通与合作,互动相补,更有利于民族社会的稳定和和谐。
[1][5][13][美]杜赞奇著,王福明译.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2]仝志辉,贺雪峰.村庄权力结构的三层分析:兼论选举后村级权力的合法性[J].中国社会科学,2002(1).
[3]贺雪峰.村庄精英与社区记忆:理解村庄性质的二维框架[J].社会科学辑刊,2000(4).
[4][10]贺雪峰.村治模式:若干案例研究[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
[6]Alexander,Action and Its Environments[M].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8.
[7][12]石启贵.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R].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8][9]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11]湘西州民委.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志从书:民族志[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
[14]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