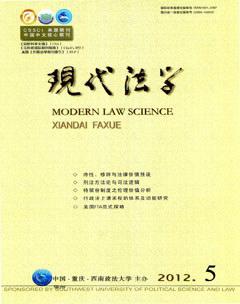行政法上请求权的体系及功能研究


摘要:行政法上的请求权源自于公权利,请求权作为公权利的一种类型,其权能覆盖整个公权利。行政法上的请求权可以分为原权型请求权和救济型请求权。原权型请求权包括给付请求权、行政合同上请求权、公法上无因管理请求权、公法上不当得利请求权、无瑕疵裁量请求权和行政程序参加请求权,救济型请求权包括防御请求权、损害填补请求权和确认请求权。各种请求权之间存在着逻辑关系,从而形成了对公民的严密保护。请求权将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联结起来,对于确定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判决类型以及行政法规范的体系化具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请求权;公权利;原权型请求权;救济型请求权;保护规范理论
中图分类号:DF31 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001-2397.2012.05.09
所谓请求权(Anspruch)是指“谁得向谁,依据何种法律规范,有所主张”[1]。请求权原本是对民事权利的一种分类。这种分类与另一种对民事权利的分类——人身权和财产权并列。只不过前者是按照权利发挥作用的方式 与请求权并列的概念是支配权、形成权、抗辩权。(参见:张俊浩泵穹ㄑг理[M]北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70保 ,后者是按照权利所保护的利益形式确定。关于权利和利益的关系,笔者认为权利本质上是一种利益,但(1)权利是利益在法律上的类型化,还存在法律上规定但没有纳入某种权利的利益,以及法律没有规定但事实上对当事人有利的利益;(2)权利代表着一种正当化的利益,还存在不具有正当性但对当事人有利的利益。 当然,请求权概念的出现主要是为了界定权利遭受侵害而产生诉讼之前的实体形态;同时,通过请求权的实体形式,权利人的抽象权利演化为具体当事人、具有具体内容的权利形态[2]。也就是说,通过请求权的概念装置,使得当事人的权利得以实现,所以请求权被称为权利作用的枢纽。[1]64
请求权在民法上已成为构建整个民法体系的基石,但在行政法上却长期处于被忽视的状态,这其中主要的原因在于传统行政法学一直受德国学者Otto Mayer所开创的行为形式理论的影响(即以行政行为的研究作为行政法学的中心),而以权利义务为中心的法律关系理论在传统行政法学上一直备受冷落 参见:赖恒盈毙姓法律关系论之研究——行政法学方法论评析[M]碧ū保涸照出版公司,2003;张锟盛毙姓法学另一种典范之期待:法律关系理论[J]痹碌┓ㄑг又荆2005,(121) ;但是,这种冷落并不代表请求权概念在行政法上毫无立足之地。由于在行政法上,行政机关负有两种义务:一种是针对公共利益的义务,一种是针对相对人请求权的义务;而只有行政机关违反针对相对人请求权的义务,相对人才能提起行政诉讼寻求救济如果行政机关违反针对公共利益的义务,只能通过公益诉讼的方式救济,而我国现阶段并不允许行政公益诉讼的存在。 ,所以,请求权是否存在,首先涉及到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问题。其次,由于法院要针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来做判决,面对不同的请求权意味着法院将采用不同的判决类型来应对之,所以请求权还涉及到法院的判决类型的问题。 与大陆法系的诉讼类型不同,我国采用了判决类型的概念。判决类型与诉讼类型的区别在于:(1)不同的诉讼类型适用不同的诉讼要件,而判决类型适用统一的诉讼要件;(2)诉讼类型由原告选定,如果选择错误,如本来应用撤销之诉而用课予义务之诉,将导致败诉的后果,而判决类型由法院决定;(3)由于诉讼类型是原告选定,所以法院一般不能随意更改诉讼类型,相应地法院只能严格在原告的诉讼请求范围内裁判;而判决类型由法院选择,可能导致法院超出原告诉讼请求裁判的情况,如原告请求撤销具体行政行为,但法院发现该行为已经不可撤销,改用确认违法判决。再次,作为请求权基础的法规范本身可以通过请求权的确定得以体系化,而这一点对于尚未法典化的行政法规范尤其重要。
一、行政法上请求权理论的发展请求权在民法上是对民事权利的一种分类,在行政法则是对公权利的一种分类。按照公权利的作用,可以分为支配权(赋予权利主体得自由对标的物拥有支配并得排除干预的权利,如自由权)、请求权、形成权(是指人民得藉由该权利的行使,使人民与国家间的法律关系发生“创造、变更或消灭”的作用,如行政合同缔结权、终止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参见:李惠宗敝鞴酃权利、法律上利益与反射利益之区别[G]//台湾地区“行政法学会”毙姓法争议问题研究(上)碧ū保何迥贤际槌霭婀司,2000:161-162保┕权利中之所以没有抗辩权,只因为抗辩权理应由请求权的义务主体来行使,而公权利的义务主体是行政机关,行政机关无法成为公权利的权利主体。 讲到请求权,不能不先从公权利谈起。
(一)何谓公权利?
一般认为,公权利的研究始于德国学者Gerber,他于1852年出版的《公权论》(über塮fentliche Rechte)一书中指出:其之所以研究公权,是“欲发现相对于私法的公法独特性的法学原理”[3];但给出公权完整定义的是另一位德国学者Bühler。他认为,公权是指人民基于法律行为或以保障其个人利益为目的而制定的强行性法规,得援引该法规向国家为某种请求或为某种行为的法律上地位[3]20。故公权并非是受保护的个人利益本身,也不等于发动法院救济的诉讼权能,其本质乃是公法上的法地位。个人因法规的赋予而取得此一法地位,并依法规的规定而产生各种请求权。由此,Bühler将公权的三要素界定为:法规范的强行性、私益的保护性、对国家的请求权的赋予性[3] 36-38。其后,Bachof又对Bühler的理论进行了发展,从而形成了具有通说地位的公权理论:(1)公权利必须是基于实定法而产生,这可以被看做是公权的请求权基础。Bühler认为该实定法规范必须具有强制性,只有这样才能赋予行政机关义务;而Bachof认为即使赋予行政机关裁量权的规范,也能够产生公权,因为裁量并非意味着行政机关可以自由,而必须是合义务的裁量,这就为后来的无瑕疵裁量请求权的出现奠定了基础。(2)作为公权产生基础的实定法规范不仅要赋予行政机关义务,而且要以保护个人的利益为目的。因为公法规范一般以保护公共利益为主要目的,对此人民并无要求行政机关履行规范义务的一般法律执行请求权,更不存在相应的诉讼途径(大众诉讼)[4]。此时,个人即使从中获益,仅属“反射性利益”,并非公权利。这就是后来用以区分公权利与反射性利益的保护规范理论。所谓保护规范理论(或称保护目的理论)是指经由法律的解释,对公权力主体课以义务,其目的在于或至少同时在于承认及保护特定个人的利益,使其得为自己而予以实现时,即存在人民的公权利。(参见:陈敏毙姓法总论[M]北本:神州图书出版公司,2003保 Bachof对此的贡献在于,他认为对法规范保护目的的解释,并非探究立法者的主观意思,更重要的是对利益的客观评价,且并非探究制定法律当时的利益评价,而是探究现在的利益评价;所以,Bachof将保护规范理论从主观目的解释带入了客观目的解释。(3)如果法律上被保护的利益被赋予起诉可能性(诉权),即意味着将该利益提升为主观权利。法规范所能赋予权利主体的法律上之力,无有较于得循法院的诉讼途径以实现利益的法律上之力更为强大者[1]43。
现代法学王锴:行政法上请求权的体系及功能研究二战后,公权理论又有了新的发展。首先是厘清了基本权利与公权的关系。早期由于德国缺乏违宪审查制度,所以,基本权利并不被视为主观公权利,而仅是一种规定国家权力界限的客观法而已。但是,1949年的基本法规定基本权利直接约束公权力,又明定任何人的权利若受公权力侵害,均可提起诉讼。并且鉴于宪法中的基本权利效力高于法律,传统通过法律解释来获得公权利的做法自然不如从基本权利中直接推导出公权利更具确定性和安定性。其次是关于第三人公权利的问题。过去行政法上的请求权仅针对具体行政行为的直接相对人,而不及于利害关系人(第三人);但是,如果发生具体行政行为对相对人有利而对第三人不利的情形,由于相对人缺乏诉讼的动机,如果不赋予第三人请求权,则违反正义。故德国联邦行政法院认为,土地所有人就其建筑申请案,未对第三人的原告利益作必要斟酌或顾及,以致发给该土地所有权人的建筑许可客观上违法,则依其情形,此一斟酌或顾及义务的违背,将同时侵害第三人原告的权利,第三人得据以请求法律上的救济,即请求撤销土地所有权人的建筑许可。BVerwGE 93,8(88). 再次,事实上利益说的兴起对公权理论的冲击。传统的公权理论认为,必须是法律上规定的某种权利,乃至法律上规定的某种利益方有解释为公权利的可能。而事实上利益说认为只要事实上对当事人有利,即使法律对此没有规定,也有公权利的存在;但是,如果将公权利等同于事实上的利益,那么保护规范说将彻底失去意义,所以,当前各国均不采纳事实上利益说。事实上利益说提出了值得反思的问题,即如何解释现有的立法,从而使某种值得保护的利益成为公权利。对此,日本2004年新《行政事件诉讼法》规定法院在对处分或裁决的相对方以外的人判断是否具有法律上的利益时,不仅应当根据该处分或裁决所依据的法令上的明文规定,还应当考虑该法令的宗旨、目的以及在该处分时应当被考虑的利益的内容、性质。在考虑该法令的宗旨和目的时,有与该法令共同目的的相关法令时,也应当参照该宗旨和目的比如在新泻机场案件的判决中,法院认为,定期航空运输事业许可所依据的法律是《航空法》,但在解释时,与《航空法》目的共同的《关于公共用机场周边的飞机噪音障害防止等法》、《特定机场周边飞机噪音对策特别措施法》的宗旨、目的也必须考虑,从而因飞机噪音受到明显妨碍者对于撤销航线的许可行为具有法律上利益。(参见:江利红比毡拘姓诉讼法[M]北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237-238保 ;在考虑该利益的内容和性质时,在该处分或裁决违反作为其根据的法令的情况下,应当酌量被侵害利益的内容、性质以及被侵害的形态、程度。比如在原子炉设置许可案件的判决中,法院认为,《核能原料物质、核能燃料物质与原子炉规制法》所保护的利益除了作为一般利益的公众的生命、身体安全与环境利益之外,还包括因事故等直接受到重大损害的范围内的住民的生命、身体安全等个别利益,所以,因事故等直接受到重大损害的范围内的住民对于原子炉设置许可行为具有法律上利益。
(二)公权利的内容
关于公权利的内容,最早Gerber认为仅包含选举权。其后,Georg Jellinek在1892年出版的《主观公权利体系》(System der subjektiven 塮fentliche Rechten)一书中对公权利的内容进行了系统性的研究。根据Jellinek的观点,公权主要分为三种:自由权、受益权和参政权。自由权旨在请求国家权力的不行使或排除国家权力对个人自由的违法侵害;受益权又分为权利保护请求权(请求国家保护私权和公法上的请求权)、利益满足请求权(请求行政活动以满足自己的利益,如请求交付公文书、高等教育机关的入学许可等)、利益斟酌请求权(相当于请愿权,即请求国家对于属于国家机关权限的事项给予处理);参政权旨在请求国家承认公民能为国家活动的权利[3]44-47。与Gerber不同的是,Jellinek认为参政权不限于选举权,还包括君主及摄政的权利、任共和国元首及法官的权利、被选举权、由国家公务所产生的请求权、公法上国体之代表者与管理的请求权,以及选举诉讼制度确立时赋予各选举人请求登记于选举人名册或检查不正当投票等权能暨各选举人利益的保护等[3]47。
在当代学者的论述中,杨建顺教授认为公权可以分为参政权、受益权和自由权三大类。参政权包括选举权、被选举权、条例的制定、改废请求权、事务监督请求权、议会解散请求权、议员、首长及其他官员的解职请求权、对违法支出等的监查请求权以及纳税者诉讼权等;受益权包括宪法上的受益权(如生存权、受教育权、劳动权等)、要求特定行政行为的权利(如接受许可和认可的权利、请求特许的权利、请求行政上登记的权利、请求生活保护决定的权利、请求养老保险金裁定的权利等)、作为具体请求权的公权(如行政上的损失补偿请求权、议员的岁费请求权、公务员的工资请求权以及经过行政上的裁定而具体发生的养老保险金请求权等)、行政上的不服申诉权、行政案件诉讼提起权;自由权是指私人的自由不受行政主体的违法侵害的权利。除此之外,公权还包括行政程序参加权、排除违法行政请求权、行政介入请求权、无瑕疵裁量请求权[5]。
(三)请求权与公权利的关系
从表面来看,请求权是公权利的一种类型,但其实,请求权与公权利之间具有更复杂的关系。(1)公权利都是实体权利,但请求权兼具实体和程序双重性质。请求权原本是德国学者Windscheid从罗马法上的诉的概念中转化过来的,Windscheid引用了《学说汇纂》中的一段话:“诉不过是指通过审判要求获得自己应得之物的权利”,但是,Windscheid却剥离了罗马法上的诉所内含的诉权或可诉请性的因素,提出了纯粹的实体法上的请求权概念:请求权是法律上有权提出的请求,也即请求的权利,某人向他人要求一些东西的权利[6]。在Windscheid之后,Larenz又重新恢复了请求权中的程序法意义,“这个概念(请求权——笔者注)不仅表明一种客观上(实体法)上的权利,而且也表明一个特定人针对他人的特定请求权可以通过诉讼来主张和执行,它首先说明一种实体法地位,同时也表明了程序上的功能。”[7]由此可见,请求权兼具实体法上的权利和程序法上的诉权的内涵。这也就揭示了为什么德国法上要以起诉可能性作为检验主观公权利是否存在的标准,乃至为什么要区分主观公权利与反射性利益。保护规范理论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排除那些与具体行政行为无直接关系的人起诉,即防止民众诉讼的出现,因此保护规范理论在行政诉讼中是作为原告适格的判断标准出现的。 (2)请求权的权能可以涵盖所有的公权利。虽然公权利中,除了请求权外还有支配权和形成权,但支配权和形成权中仍存在请求权的可能。比如支配权主要是自由权,但公民的自由权被行政机关侵犯后,公民将产生侵害行为排除请求权,即请求行政机关撤销违法干预行为。对此,民法上通常将请求权分为独立的请求权和依附的请求权也有学者称之为原权型请求权和救济型请求权。(参见:张俊浩泵穹ㄑг理[M]北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71保 ,前者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也就是公权利中原有的请求权的意思,比如无因管理请求权、不当得利请求权等;后者是当公权利中的支配权、形成权受到侵犯后,作为对它们的救济而存在的请求权,比如侵害行为排除请求权等。
综上所述,行政法上的请求权是公民为了贯彻其公权利,而向行政机关提出的作为或者不作为的要求。这些要求既可以直接向行政机关提出,也可以通过法院向行政机关提出;因此,请求权是联系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的纽带。
二、行政法上的请求权的类型王泽鉴教授将民法上的请求权分为六种类型:契约上给付请求权、返还请求权、损害赔偿请求权、补偿及求偿请求权、支出费用偿还请求权、不作为请求权[1]68。那么,行政法上到底存在哪些请求权类型?笔者认为,行政法上的请求权也可以分为原权型请求权和救济型请求权两种。前者包括:给付请求权、因行政合同产生的请求权、公法上无因管理请求权、公法上不当得利请求权、无瑕疵裁量请求权、行政程序参加请求权等等原权型请求权是不断发展的,比如无瑕疵裁量请求权、行政程序参加请求权都是近年来新兴的请求权种类,再比如在德国最近还出现了行政立法请求权。(参见:程明修鼻肭笮姓机关订定法规命令之行政诉讼[G]//行政诉讼制度相关论文丛编:第4辑碧ū保骸八痉ㄔ骸保2005:141-159 ;后者包括:防御请求权、损害填补请求权、确认请求权。
(一)原权型请求权
1备付请求权
可以说,给付请求权是最原始意义上的请求权。根据给付内容的不同,可以分为作为请求权和一般给付请求权。
(1)作为请求权
作为请求权是请求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权利,在行政诉讼上对应课予义务之诉。课予义务之诉在我国行政诉讼法上被称为履行判决。但从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4条第3项的规定来看,被告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的,判决其在一定期限内履行。该条中的“履行职责”是一种笼统的表述,并未明确指向要求被告做出具体行政行为,故笔者认为我国的履行判决是广义的给付请求权的体现,即包括了作为请求权和一般给付请求权。其实,我国行政诉讼法上与课予义务之诉相近的是责令重做判决,但责令重做判决在我国并非独立的判决类型,而是作为撤销判决的附带性判决。 到底课予行政机关什么样的义务呢?从德国的实务来看,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课予行政机关做出特定的具体行政行为的义务,一种是课予行政机关做出具体行政行为(或者答复)的义务。两者的区别在于,对于前者,具体行政行为的种类法院已经给了明确的指示,对于后者,法院只是要求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至于作何种具体行政行为,由行政机关自己决定。至于法院做何种判决,视案情的可裁判程度而定,亦即主要看行政机关此时是否还有裁量权。如果行政机关尚有裁量权,则法院只能课予行政机关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义务;如果行政机关没有裁量权,比如裁量权收缩为零或者原告请求行政机关做出羁束行为的,法院则课予行政机关做出特定的具体行政行为的义务。这种作为请求权在我国的表现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9条第1、4款:被告对依法应当公开的政府信息拒绝或者部分拒绝公开的,人民法院应当撤销或者部分撤销被诉不予公开决定,并判决被告在一定期限内公开。尚需被告调查、裁量的,判决其在一定期限内重新答复。被告依法应当更正而不更正与原告相关的政府信息记录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被告在一定期限内更正;尚需被告调查、裁量的,判决其在一定期限内重新答复。当然,关于政府信息公开行为是否属于具体行政行为,在学理上尚有争论。在此,笔者接受我国学界和实务界的通说,认为该行为属于具体行政行为。
(2)一般给付请求权
一般给付请求权是请求行政机关给予除具体行政行为之外的其他给付的权利,包括请求金钱给付、请求为事实行为(例如原告请求提供关于其认为应付损害赔偿责任的公务员的姓名和住址、请求缔结公法契约等等)[8]。根据给付的理论基础的不同,一般给付请求权又可分为两种:第一,原始的给付请求权(Originare Leistungsanspruche),是指直接由基本权利导出的对国家的财物给付或生活照顾的请求权。[9]当然,这种原始的给付请求权只在最低限度或最基本程度内得到承认。第二,分享权(Teilhaberechte),是指国家已有一个先行的行为,却拒绝他人的一个特定给付,此时他人即可要求相同的给付。比如我国《行政许可法》第5条第3款规定,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申请人有依法取得行政许可的平等权利,行政机关不得歧视。因此,分享权是间接从平等原则导出的,并非直接源自于宪法上的基本权利,故也称之为派生的给付请求权。
2毙姓合同上的请求权
虽然行政合同并非立法用语,但我国法律中已经存在若干行政合同则是不争的事实。关于行政合同的分析,参见:王锴惫法释义学与比较方法[M]北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163-189 最典型的如(1)公用事业特许经营协议。《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第8条第5项规定:当地建设部门应当与获得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权的企业签订公用事业特许经营协议。(2)环境自愿协议。《清洁生产促进法》第29条:企业在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的基础上,可以自愿与有管辖权的经济贸易行政主管部门和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签订进一步节约资源、削减污染物排放量的协议。(3)行政强制执行协议。《行政强制法》第42条,实施行政强制执行,行政机关可以在不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况下,与当事人达成执行协议。(4)拆迁补偿协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25条规定,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就补偿方式、补偿金额和支付期限、用于产权调换房屋的地点和面积、搬迁费、临时安置费或者周转用房、停产停业损失、搬迁期限、过渡方式和过渡期限等事项,订立补偿协议。民法上,合同请求权包括履行请求权(包括重新履行、修理和重作等)、返还给付请求权、减少价金请求权、违约损害赔偿请求权[2]。行政合同上的请求权可以比照处理。比如《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第29条规定:主管部门或者获得特许经营权的企业违反协议的,由过错方承担违约责任,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3惫法上无因管理请求权
无因管理本是民法上的制度,是指某人(管理人)未经委托或者没有其他根据为另一个人(业主)提供管理。在管理行为符合业主的客观的或者推测的意思,或者履行以公共利益为目的的义务时,无因管理就具有合法性。在这种情况下,管理人享有补偿其支出的请求权[10]。公法上的无因管理请求权主要是公民在未经委托的情况下为行政机关从事公权力行为的情形,此时公民享有请求行政机关补偿其支出的权利。比如《人民警察法》第34条第2款规定,公民和组织因协助人民警察执行职务,造成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抚恤或者补偿。《消防法》第49条第2款规定,单位专职消防队、志愿消防队参加扑救外单位火灾所损耗的燃料、灭火剂和器材、装备等,由火灾发生地的人民政府给予补偿。
4惫法上不当得利请求权
公法上的不当得利请求权,亦称为公法上返还请求权(Zffentlich-rechtlicher Erstattungsanspruch),是指在公法范畴内,欠缺法律上原因而发生财产变动,致一方受益,他方受损,受损害一方得请求返还所受利益的情形[11]。公法上的不当得利请求权主要针对公民对行政机关不法的财产征收征用行为的返还请求,最典型的如我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51条,该条规定纳税人超过应纳税额缴纳的税款,税务机关发现后应当立即退还;纳税人自结算缴纳税款之日起三年内发现的,可以向税务机关要求退还多缴的税款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税务机关及时查实后应当立即退还;涉及从国库中退库的,依照法律、行政法规有关国库管理的规定退还。再比如《突发事件应对法》第12条规定,有关人民政府及其部门为应对突发事件,可以征用单位和个人的财产;被征用的财产在使用完毕或者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结束后,应当及时返还。从我国《国家赔偿法》第32条第2款来看,似乎是把返还财产作为国家赔偿的一种方式。这显然是混淆了不当得利请求权和损害赔偿请求权。首先,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范围远远大于损害赔偿请求权,因为作为不当得利请求权的构成要件之一的“欠缺法律上原因”包括自始无法律上原因或者虽有法律上原因,但于财产变动后法律上原因已不存在两种情形,而损害赔偿请求权仅针对自始无法律上原因的情形。其次,不当得利请求权的功能是返还财产, 返还的范围还包括财产所产生的孳息,比如我国《国家赔偿法》第36条第7项规定,返还执行的罚款或者罚金、追缴或者没收的金钱,解除冻结的存款或者汇款的,应当支付银行同期存款利息。 而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功能是在无法返还财产的情况下的金钱填补。
5蔽掼Υ貌昧壳肭笕
行政机关在大部分的行政领域中,皆有行政裁量的空间,但当某种特定职务的执行变成是行政机关的法律义务时,行政机关的裁量空间就会受到限缩。而行政机关的职务变成义务的前提是:(1)行政机关应做成无裁量瑕疵的决定;(2)在裁量限缩的情况下,行政机关必须采取唯一的无瑕疵的决定。符合这两个要件,公民对行政机关就享有公法上的请求权。参见:李惠宗敝鞴酃权利、法律上利益与反射利益之区别[G]//台湾地区“行政法学会”毙姓法争议问题研究(上)碧ū保何迥贤际槌霭婀司,2000:157
(1)裁量瑕疵
1960年公布的德国《行政法院法》将裁量瑕疵予以成文化。该法第114条规定,行政机关经授权依其裁量而为时,法院仍得审查行政行为与拒绝及不作为的行政行为,是否因裁量行为超越法定范围,或因与授权目的不符的方法行使裁量权而违法。从条文中可以看出两种裁量瑕疵类型,一个是逾越法定界限,另一个是以与授权目的不相符的方法行使。这一规定仍然非常抽象,对学说上的裁量体系并未做进一步的详细规定,有待学说和法院的判决予以补充。随后,1976年的《行政程序法》颁布,该法第40条规定,行政机关被授权依其裁量做成决定时,其裁量权的行使应符合授权的目的,并应遵守法律规定的裁量范围。这一规定与前述《行政法院法》的规定相呼应,前者明确规定法院有权审查裁量瑕疵,后者明确规定行政机关有无瑕疵裁量的义务。
但是,到底什么才算是无瑕疵裁量?毛雷尔将裁量瑕疵分为四种:(1)裁量逾越。行政机关没有选择裁量规范规定的法律后果,比如根据收费条例规定对具体行政事件可以收取20-50马克的规费,而行政机关决定收取60马克。(2)裁量怠慢。行政机关不行使法定裁量权,即构成裁量怠慢。(3)裁量滥用。行政机关根本没有遵守裁量规范的目的,比如未有法律例外规定,考虑个人或者政党政治的因素,采取警察措施不是为了排除危险,而是为了照顾。(4)违反基本权利和一般行政法原则。适用于所有行政活动的基本权利和一般行政法原则,特别是必要性和比例性原则,是对裁量的客观限制,行使裁量权时必须遵守,否则将构成裁量瑕疵[10]130-131。毛雷尔的理论特点是其似乎意识到将一般法律原则的违反划归裁量逾越或滥用的困难,故自成一类说明。沃尔夫、巴霍夫和施托贝尔将裁量瑕疵分为三种:(1)裁量逾越。是指行政机关超越法定的裁量权界限,即在具体案件中选择了法律没有规定的法律后果。(2)裁量懈怠。即行政机关不适用应当适用的“可以式规范”。(3)裁量滥用。是指行政机关有意不遵守法定的内在活动界限。也就是说,构成滥用裁量权的行政措施本身具有适法性,但就本案事实而言,根据客观的利益权衡和法定目的,裁量权的行使不得违反宪法原则或者其他法律原则,例如自由权、平等、比例性和价值决定等原则。沃尔夫、巴霍夫、施托贝尔的第三种分类类似于毛雷尔的第四种分类[4]367-370。
笔者认为,理解裁量瑕疵,一方面要与行政合法性原则相区分,另一方面也要与行政合理性原则区分。首先,裁量瑕疵不属于行政违法,因为合法性原则构成行政行为的外部界限,而裁量权的行使是基于立法者的授权,亦即裁量必然是在授权范围内进行,如果超越授权范围,则属于违法。因此,笔者认同德国学者G塼z的观点G塼z指出,裁量逾越构成违法的场合,与单纯的违法无异,应非真正的裁量行为,也非真正的裁量瑕疵。(参见:叶俊荣甭鄄昧胯Υ眉捌渌咚仙系奈侍猓跩]毕苷时代,1987,13(2)保 ,认为裁量逾越不属于裁量瑕疵,而属于行政违法。其次,裁量瑕疵属于合法但不合理的问题,所以裁量瑕疵与行政合理性原则存在交叉。裁量瑕疵只不过是行政合理性原则下的一些具体原则在裁量权行使上的具体表现。基于此,笔者首先将裁量瑕疵分为裁量滥用和裁量错误。前者是指基于不合目的或不合事理的动机,后者是指未就相关事实为充分的考虑与衡量。对于前者有不当联结禁止原则、妥当性原则的适用,对于后者有平等原则、必要性原则、均衡性原则的适用。也可以用主观不法和客观不法来分别指代裁量滥用和裁量错误。再次,笔者认为,裁量瑕疵除了包括裁量滥用和裁量错误之外,还应包括裁量怠慢。裁量怠慢看上去似乎与行政违法中的不作为类似,但其实有本质的区别。行政不作为属于行政机关违反应予作为的义务,故系违法;而裁量怠慢中,行政机关对于是否裁量本来就享有裁量权(决定裁量),也就是说,即使行政机关不裁量,比如每次都按最低幅度来处罚相对人,也不违法。所以,裁量怠慢本质上仅为不合理。与裁量滥用和裁量错误两种作为的不合理相比,裁量怠慢属于不作为的不合理。
(2)裁量权收缩
裁量权收缩是指在一定的事实状态下,如果应防止的危险性增大,发生的可能性越高时,行政机关裁量的幅度即应收缩,甚至收缩为零。行政机关在此情形下便只有作为的义务,倘若仍不作为,即应受违法的评价。此时,国民享有请求行政机关发动规制权限的行政介入请求权。[3]267裁量权收缩的构成要件包括哪些?在日本行政法学界有三要件说、四要件说、五要件说。有关日本学者各种学说观点,可参见:王和雄甭坌姓不作为之权利保护[M]碧ū保喝民书局,1994:280-294 通说的五要件认为,首先应考虑被害法益的对象性,亦即被侵害法益的重大性程度。其次为具体危险的紧迫性,又分为危险性的程度和紧迫性的程度两个问题来讨论。再次为危险发生的预见可能性。第四为损害结果的回避可能性。第五为规制权限发动的期待可能性。期待可能性也称为补充性要件,即被害者个人并无自力回避危险以防止损害发生的有效手段,即非依赖行政机关行使规制权限则不能防止损害结果发生。反之,如果单凭私人的努力即能回避危险,即不应请求并期待行政权限的发动[12]。
日本学界有关裁量权收缩论的构成要件理论虽然精细,但也不无可议之处。最大的问题在于,通说的五要件之间存在相互交叉的现象。比如作为第二个要件的“具体危险的紧迫性”与第三个要件的“危险发生的预见可能性”以及第四个要件的“损害结果的回避可能性”,这从学者的论述就可以看出,比如阿布泰隆教授在论述“具体危险的紧迫性”时就提出“行政机关容易得知该危险的要件,应修正为行政机关如果行使权限加以调查即能得知该危险为已足”,相同的论述在“危险发生的预见可能性”时又再次出现[12]327,329。而在“损害结果的回避可能性”的要件中,由于对传统的“行政机关行使其权限即容易能防止结果的发生”中的“容易”进行了缓和,认为只要发生有具体危险的预见,且有行使权限的根据规定时,即应采取回避结果的一切对策或手段[12]331。可见,这三个要件现在的逻辑关系是,只要客观上存在具体危险的紧迫性(以盖然性为标准),行政机关就具有了危险发生的预见可能性,而行政机关只要预见到了危险的发生;就有了采取一定措施的回避可能性。这三点最终都归结于危险发生的紧迫性要件上。由此,可看出日本的裁量权收缩论仍存在缺陷,为此,笔者将裁量权收缩的要件总结为:(1)所涉法益的重要性。首先,是生命权所保障的生命法益,所以,行政裁量如果涉及人民生命存亡的事项时,行政机关的裁量权即产生收缩的效果;其次,是人民的身体和健康利益,行政裁量所涉事项如果属于上述者,也构成裁量收缩的效果;再次,是涉及人民身体自由。除此之外,基于宪法优位的原则,有关基本权利所保护的法益也构成裁量收缩的要素,例如婚姻和家庭、财产权的保障等[13]。(2)危害法益的强度和严重性。在德国,危害法益的强度和严重性主要是1960年的“带锯判决”所确立的特别强度标准,即“在存有特别强度的干扰和危害时,行政机关对于不采取行动的决定,于一定情况下,甚至可以显示为具有裁量瑕疵。从而,在实务上,法律上所赋予的裁量自由产生收缩。因而仅存有唯一无瑕疵的决定。” BVerfGE 11,95ff钡是,对此有学者提出,在个别情况下,也可能发生不具严重程度的危险状态,但行政机关仍无其他斟酌的余地,从而只有采取防范的措施,才不致构成裁量瑕疵。比如某人将汽车违规停靠在他人车库的出入口或者某一家庭因穷困而无居住处所,向地方主管机关寻求协助[13]127-128。(3)裁量收缩的解除。第一,事实不能。即使裁量收缩的要件具备,但如果行政机关所必须采取的措施于事实上或法律上不可能的,法院即不得作成判令行政机关为特定行为的判决。第二,期待可能性。当人民可以自己处理特定的危险或干扰的状态,特别是其可以透过民事救济途径解决问题的,行政机关即无必须采取行动的义务,否则将使行政机关陷入民事争议的纠葛之中。 李建良教授在裁量收缩的解除中将“期待可能性”与“补充性”并列(参见:李建良甭坌姓裁量的缩减[G]//当代公法新论——翁岳生教授七秩诞辰祝寿论文集(中)碧ū保涸照出版有限公司,2002:134-138保└据日本学者的阐述,补充性如果作为独立要件,行政不作为的责任将很难成立。所以将此一要件合并到期待可能性要件之中。笔者对此表示赞同,补充性只是判断期待可能性是否存在的一个标准而已,故与期待可能性不是并列关系,而是后者吸收前者。
我国行政法上有关无瑕疵裁量请求权的实例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许可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1条,据此人民法院审理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案件,认为原告请求准予许可的理由成立,且被告没有裁量余地的,可以在判决理由写明,并判决撤销不予许可决定,责令被告重新作出决定;但是,该条的问题在于,如果“被告没有裁量余地”,即裁量权收缩为零时,法院到底是责令被告重新决定还是责令被告准予许可?无瑕疵裁量请求权原则上并无要求行政机关作出特定行为的效力,而只能要求其无瑕疵地作出裁量决定。只有在行政机关的裁量权收缩至零时,才能请求作出特定的决定[14]。由此可见,该条如果规定“责令被告准许许可”,可能更符合无瑕疵裁量请求权的要旨。
6毙姓程序参加请求权
行政程序参加请求权是随着行政程序法的出现而出现的,是要求参与行政机关意志形成的权利,主要包括听证请求权、阅览卷宗请求权和保密请求权。参见:陈英淙,黄惠婷狈ㄖ喂之警察理念与权限[M]碧ū保涸照出版公司,2007 我国虽无专门的行政程序法,但《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等诸多法中大多为行政程序的规定。行政程序参加权请求中最重要的就是听证请求权。行政听证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正式的听证(formal hearing),即行政机关在作成处分时,依法律规定应给与听证的机会,使当事人得以提出证据和反证、对质、诘问证人,然后基于听证笔录作成处分的程序。这种正式的听证也被称为审判型的听证(trial-type hearing)、准司法性的听证(quasi-judicial hearing)、基于证据的听证(evidentiary hearing)或者对造型的听证(adversary hearing)。另一种是非正式的听证(informal hearing),是指行政机关作成处分时,只需给予当事人口头或书面陈述意见的机会,以供机关参考,无需基于记录作成处分。这种听证也被称为辨明型的听证(argument-type hearing)、准立法性的听证(quasi-legislative hearing)或者陈述的听证(speech-making hearing)[15]。正式听证与非正式听证的区别在于:(1)正式听证中,各当事人都有机会知悉和答辩对方所提出的证据与辩论,非正式听证则只是陈述意见并不提出证据;(2)正式听证用于解决事实的争执问题,非正式听证则用以解决非事实方面的法律和政策的争执问题以及裁量问题;(3)正式听证手续慎重,经常采用法庭的审讯方式,花费时间较多,而非正式听证程序简易,常用聊天的对话方式;(4)正式听证多由专门的行政法官(administrative law judges)主持,而非正式听证不必由行政法官进行,普通行政官员也可主持,以求简便可行[15]165。在我国,这种正式听证和非正式听证的区分也有体现,非正式的听证在我国的立法中多被称为陈述、申辩,比如《行政处罚法》第32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行政机关应当采纳。正式的听证比如《行政处罚法》第42条第1款,该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行政许可法》第47条,行政许可直接涉及申请人与他人之间重大利益关系的,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许可决定前,应当告知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
(二)救济型请求权
正如毛雷尔教授所说,主观公权利的实践意义在于司法救济[10]153。因此,救济型请求权并非不如原权型请求权重要,同时,救济型请求权往往通过行政诉讼中诉之利益的方式予以体现。诉之利益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诉之利益包括:(1)请求的内容是否适合成为审判的对象,即所谓诉讼对象或对象适格的问题;(2)当事人对于该请求是否有正当的利益,即所谓原告适格的问题;(3)依据具体的状况,判断有无请求法院审判的具体实益,即所谓权利保护必要的问题。其中,原告适格又称为主观的诉之利益,权利保护必要又称为客观的诉之利益或狭义的诉之利益。本文所讲的诉之利益是指原告适格,即主观的诉之利益。
1狈烙请求权
防御请求权源自主观公权利中的支配权,亦即宪法中的自由权。根据防御的时机的不同,可以分为不作为请求权和排除请求权。不作为请求权旨在要求行政机关消极不为发动妨害其权利的行为,带有预防的作用,而排除请求权是行政机关积极地除去已经做出的违法干涉行为的现实结果,用以回复至未受侵害前的权利圆满状态。
(1)不作为请求权
不作为请求权(Zffentliche Unterlassungsanspruch)是指请求行政机关不作一定的行为,在行政诉讼中表现为请求不作为的一般给付之诉,又称为消极的给付诉讼。不作为之诉依据行为的时间可以分为两种[8]132:一种是一般不作为之诉,是指行政机关已为原告认为违法的干预行为,原告起诉请求于将来不再为此种干预行为。从德国的实务来看,一般的不作为之诉包括请求不再为提供资讯的行为、请求停止由公权行政行为或与公权行政行为有关而生的环境污染等[8]133-134。另一种是预防性不作为之诉,是指行政机关尚未为任何的干预行为,但原告欲对将来第一次面临威胁的行政干预,自始即予以防止,因此诉请法院判命相关行政机关不为该项干预行为。我国的预防性不作为之诉主要体现为政府信息公开中的反公开诉讼,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1条规定,被告公开政府信息涉及原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且不存在公共利益等法定事由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确认公开政府信息的行为违法,并可以责令被告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造成损害的,根据原告请求依法判决被告承担赔偿责任。政府信息尚未公开的,应当判决行政机关不得公开。
(2)排除请求权(Beseitigungsanspruch)
第一,侵害行为排除请求权
侵害行为排除请求权是当事人请求行政机关除去违法的侵害行为的权利,在行政诉讼上对应撤销之诉。侵害行为排除请求权首次出现在德国联邦宪法法院1981年的湿采石判决中。该案中,法院认为,对于一个违法的征收行为,当事人应当首先致力于行政法院请求撤销该侵害行为,他不能不循此途径,反而请求补偿。也就是说,对于是否防御违法的征收或直接请求补偿当事人并无选择权。倘若当事人使该侵害行为已具有不可撤销性时,则应驳回其补偿的请求。BVerfGE 58, 300ff. 这一判决被认为是确认了第一次权利保护优先原则,即侵害行为排除请求权(第一次权利保护)优先于损害填补请求权(第二次权利保护)适用。
第二,结果除去请求权
结果除去请求权(Zffentlich瞨echtlicher Folgenbeseitigungsanspruch)类似于民法上的恢复原状请求权之所以说“类似于民法上的恢复原状请求权”,是因为民法上的恢复原状请求权要求恢复到若无违法行为发生现在应当所处的状态,而结果除去请求权仅仅是恢复到违法行为发生之前的原来状态;也就是说,结果除去请求权是恢复到当事人没有损失,但不包括可得利益。 ,是指对于公权力行政行为所造成、且仍持续存在的不法结果,受害人民可请求行政机关排除此一不法事实状态的行政法上实体权利[16]。比如建筑许可证已被撤销,但依据该许可证已经修建的建筑即需要通过结果除去请求权被拆除。结果除去请求权一般是作为对侵害行为排除请求权的补充,即侵害行为排除请求权是对侵害行为的法律状态(即法律效力)的除去,而结果除去请求权是对侵害行为造成的事实状态(该事实状态并非一定存在)的除去。结果除去请求权在我国法上的体现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9条第2项: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规定判决撤销违法的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将会给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失的,人民法院在判决撤销的同时,可以分别采取以下方式处理:……(二)责令被诉行政机关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这里的“责令行政机关采取补救措施”就有结果除去的意思。但是,从我国《国家赔偿法》第32条第2款来看,立法者似乎将恢复原状作为国家赔偿的一种方式,但是,这显然混淆了结果除去请求权与赔偿请求权。结果除去请求权与赔偿请求权的区别在于,首先,结果除去请求权重在结果的违法,而不论行为本身的违法与否。比如根据合法的建筑许可证建成的建筑物,事后因故建筑许可证需要撤回,那么,虽然建筑许可证本身合法,但如果在撤回后拒不拆除该建筑物的话,即构成违法,该建筑物仍有结果除去的必要。其次,赔偿请求权是在无法恢复原状的情况下给予的金钱填补,也就是说,结果除去请求权原则上不采取金钱填补的方式。由于德国的国家赔偿诉讼是由普通法院采用民事诉讼的程序审理,故要求金钱填补的不仅仅是直接损失,还包括可得利益。而结果除去请求权是作为行政法上的救济途径,故只能恢复到过去的原状;但是,如果恢复原状事实上不可能、法律上不允许或者欠缺期待可能性而无法付诸实现时,那么就要恢复到跟原状同等价值的状态,此时,也可以采用金钱填补的方法来达到跟原状同等价值。这被称为结果补偿请求权,用来取代无法实现的结果除去请求权。(参见:刘淑范惫法上结果除去请求权之基本理论[J]闭大法学评论,(72)保┑是,结果补偿请求权对于采取二元法院体制的德国固可适用,但对于采用一元法院体制而且国家赔偿也仅赔偿直接损失的我国,实无借鉴的必要,否则将造成结果除去请求权与损害赔偿请求权之间的混淆。
2彼鸷μ畈骨肭笕
损害填补请求权是指行政机关的行为已经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情况下,当事人要求行政机关填补该损失的权利。从本质上说,损害填补请求权亦属于一般给付请求权的一种。但是,作为最后一道救济,损害填补请求权具有独立存在的意义。根据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行为的合法与否,损害填补请求权可以分为赔偿请求权和补偿请求权。以行为的合法、违法来区分赔偿与补偿是否仍有意义,在学理上存在争论。(参见:王锴贝优獬ビ氩钩サ慕缦蘅次夜《国家赔偿法》的修改方向[J]焙幽险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4)保
(1)赔偿请求权
我国的赔偿请求权以《宪法》第41条第3款为指导,包括公法赔偿请求权和私法赔偿请求权。前者针对的是行政机关的职权行为(《国家赔偿法》第2条第1款),后者针对的是行政机关的职务行为(《民法通则》第121条)。那么,这种职权行为与职务行为有何区别?应当讲,职权行为强调的不仅是“与职务相关”,而且关键是“行使公权力”的行为,而职务行为仅指 “与职务相关,但非行使公权力”的行为。按照台湾学者的说法,也就是所谓的公权力行政与私经济行政的区别[17]。当然,本文基于公权利的立场,主要讲公法赔偿请求权。公法上赔偿请求权的构成要件包括:第一,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第二,职权行为,包括统治高权行为(运用命令、强制等手段干预人民自由权利的行为)和单纯高权行为(不运用命令、强制手段,而是以提供给付、服务、救济、保护等方法来实现行政目的的行为,诸如行政契约、营造物的设置或管理、社会福利行政、社会保险、劳动行政、建筑区与技术规制、道路指标或公园绿地的设置等等)[18];第三,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亦即从保护规范理论出发,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违反旨在保护特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益的法律规定的职务义务;第四,有损害后果。
(2)补偿请求权
我国的补偿请求权首先根据理论基础的不同,分为特别牺牲补偿请求权和衡平补偿请求权。特别牺牲补偿请求权认为国家对人民财产权的干预,无论其形态是否为财产权的剥夺,抑或财产权利用的限制,财产权人的牺牲程度,如与他人所受限制相比,显失公平且无期待可能性者,即构成征收征用,国家应予补偿[18]1728。特别牺牲理论的提出,将征收征用补偿的原因系于平等原则,亦即为大家而牺牲者,其损失应由大家分担而补偿之[19]。衡平补偿请求权是指国家对于某些不属于特别牺牲的损失,基于社会国原则或者社会连带的思想,也可以主动给予补偿,从而实现社会正义。比如我国的生态效益补偿和资源补偿。其次,特别牺牲补偿请求权又根据补偿的损失不同,再分为针对财产损失的补偿请求权和针对非财产损失的补偿请求权(或称为公益牺牲补偿请求权)。公益牺牲补偿请求权(Aufopferungsanspruch)专门针对人民非财产性损失(包括生命、健康、身体、自由)的情形[20],比如儿童强制接种疫苗造成儿童长期健康的损害。再次,针对财产损失的补偿请求权根据造成财产损失的行为形态分为征收征用的补偿请求权、财产权限制的补偿请求权、具有征收效果的补偿请求权。应予补偿的财产权限制与应予补偿的征收征用的区别在于是否构成对财产权的剥夺应予补偿的财产权限制在我国包括:(1)财产权使用或收益的妨碍造成的补偿,比如《风景名胜区条例》第11条第3款规定,因设立风景名胜区对风景名胜区内的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和房屋等财产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给予补偿。(2)行政强制措施造成的补偿。比如《动物防疫法》第66条:对在动物疫病预防和控制、扑灭过程中强制扑杀的动物、销毁的动物产品和相关物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给予补偿。(3)信赖保护补偿。比如《行政许可法》第8条第2款规定,行政许可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修改或者废止,或者准予行政许可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变更或者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由此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财产损失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补偿。 ,具有征收效果的侵害补偿(enteignender Eingriff)是指人民的财产权因合法行政行为的附随效果而受有损失者,如该附随效果具有特别的持续影响,逾越公益牺牲的界限,国家应给予补偿[18]1731-1732。一般来说,这种附随效果多系出于“偶发”或“不可预见”,但是受害人的损失又特别严重,故有必要由国家予以填补。这种具有征收效果的侵害在我国法上也存在,比如《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第15条第2款规定,人民警察依法使用警械、武器,造成无辜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由该人民警察所属机关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有关规定给予补偿。
3笔欠翊嬖谌啡锨肭笕ǎ
诚如前述,救济型请求权是对公权利中原本非属请求权的权利进行救济而产生,正如防御请求权是针对支配权,对于形成权则通过确认之诉予以救济参见:李惠宗敝鞴酃权利、法律上利益与反射利益之区别[G]//台湾地区“行政法学会”毙姓法争议问题研究(上)碧ū保何迥贤际槌霭婀司,2000:162 确认之诉根据确认的内容,可以分为三种:确认法律关系存在与否的诉讼(一般确认之诉)、确认具体行政行为无效的诉讼、确认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诉讼。从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7条来看,我国并无一般确认之诉,但存在确认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有效、违法、无效的诉讼。至于确认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有效的诉讼,可以说是我国的“特色”。(参见:甘文毙姓诉讼法司法解释之评论——理由、观点与问题[M]北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161-162保┤啡暇咛逍姓行为违法的诉讼在德国也被称为续行确认诉讼,因为它是在原来的撤销诉讼或给付诉讼无法继续进行的情况下产生。我国也有类似规定,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7条第2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作出确认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或者无效的判决:(一)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但判决责令其履行法定职责已无实际意义的;(二)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 ,那么,是否存在与此相对应的确认请求权呢?
德国《行政法院法》第43条第1款规定,原告有即受确认的正当利益者,得起诉请求确认法律关系存在或不存在,或请求确认行政处分无效。该法第113条第1款规定,行政处分前已撤销,或因其他原因已经消灭者,法院得依申请以判决确认行政处分违法,但以原告就此有正当利益为限。所谓法律表象是指,由于无效的具体行政行为是严重且明显的违法,当事人有权拒绝,而行政机关往往坚持该行为的合法性和效力,甚至凭借其公权力的后盾对当事人进行强制执行,所以即使具体行政行为无效,仍会造成具有某种法律效力的表象。 该确认诉讼中的正当利益往往被称为确认利益。那么,能否从该确认利益中发展出一种确认请求权呢?德国多数学者对此持肯定的态度,理由有三:(1)基于诉讼权保障的意旨。《德国基本法》第19条第4款第1句规定,任何人的权利若受公权力侵害的,得向法院请求救济。此规定即决定了所谓法律救济途径(透过法院救济)是以个人权利受侵害为前提。(2)基于诉讼经济的考量。根据德国《行政法院法》第42条第2款和第113条第1、5款的规定,原告的权利是否遭受侵害,一方面是以“权利有受侵害的可能”的态样出现,作为原告适格问题,仅决定法院针对原告起诉能否进入本案裁判,另一方面则以权利确实遭受侵害的态样出现,作为诉讼有无理由的问题,决定本案裁判本身的内容。可见,原告个人权利的要求在这两个层次中至关重要,如果放弃了权利的概念,则确认诉讼只是一种利害关系人诉讼,法院的判决也将形同一张“有关法律关系是否存在?”“具体行政行为是否无效?”“已消灭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违法?”等法律问题的鉴定书而已。(3)基于行政诉讼制度的体系解释。即使“权利受到侵害”要件只明文规定在撤销诉讼、课予义务诉讼等诉讼中,也不能排除确认诉讼应包含相同的要素的可能。就确认已消灭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诉讼而言,由于这种诉讼是对撤销诉讼、课予义务诉讼的续行在德国,如果行政机关事先已经确认了具体行政行为无效或者违法,当事人将丧失确认利益。 ,则在提起这两种诉讼之初,就必须满足“权利受侵害”的要件。再就确认具体行政行为无效的诉讼而言,原告诉请确认的对象虽然是一个自始不发生效力的具体行政行为,但原告的权利仍可能受到具体行政行为所生法律表象的侵害这种程序性请求权是指行政程序性请求权,与诉讼程序无关。 ,其处境无异于撤销诉讼中的原告。即使就一般确认诉讼而言,如果将法律关系理解为原告和被告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则法律关系的确认必然会与原告的个人权利有关,由此就能导出确认诉讼与个人权利相关的要求。换言之,原告诉请法院确认的对象其实就是原告公法上权利的状态,而当有关此权利状态的争议确实能够透过一般确认诉讼加以解决时,原告不但具有确认利益,并且该诉讼也与原告的个人权利有关[21]。德国联邦行政法院也在1981年的Mülheim-K塺lich核电厂判决中指出,依行政法院法第43条第1款的规定,要合法提起一般确认诉讼,仅要求原告具有自身即受确认判决的正当利益,此正当利益虽其范围较法律关系更广,但这并不表示,完全不会因为该具体行政行为而权利受到损害的人也能提起确认该具体行政行为无效的诉讼,而是该被诉请确认无效具体行政行为至少应会涉及原告的法律地位始可[22]。由此可见,确认诉讼的提起是因为该确认会影响原告的法律地位,亦即该确认对原告具有利益,并且这种确认利益值得法律保护,由此才产生了确认诉讼的必要,也由此衍生出了公民的确认请求权。
所以,确认请求权是旨在保护当事人确认利益的请求权,亦即当确认有助于改善当事人在法律上、经济上或理念上的地位时,当事人有权请求行政机关予以确认。在行政机关不予确认或者确认结果非当事人所期望的情况下,当事人可向法院提起确认之诉。关于各种学说的介绍,参见:程明修惫法上结果除去请求权在国家责任体系中的地位[G]//胡建淼惫家赔偿的理论与实务焙贾荩赫憬大学出版社,2008 当然,这种确认利益到底是什么?在确认具体行政行为无效的诉讼中,确认利益就是无效的具体行政行为会给当事人带来“事实上的负担效果”,因此当事人有必要通过确认来除去该项负担。在确认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诉讼中,确认利益包括:(1)如果不确认违法,将重复发生危险。即当行政机关有重复做成与已消灭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相同的具体行政行为之虞时,原告的确认利益就会存在。例如警察机关禁止某甲于特定日期举行政治性集会,在禁止期间内该特定日期已过,但某甲表明其将来仍有意再举办类似的活动时,遂诉请确认禁止的合法性。(2)原告就确认有回复名誉的利益时,确认利益也获得承认。亦即,当侵益行为对原告名誉、人格的事实上影响,在该具体行政行为消灭后仍然继续存在的,即有确认的必要。例如主管机关拒绝给予军人忠诚记录的理由是基于该名军人的某种行为者,该名军人因而公开受到同僚的贬低,并且这些理由也被第三人相信。(3)基于确认判决的先例拘束力,为普通法院的损害赔偿或其他补偿程序预作准备。依德国联邦行政法院的见解,具体行政行为于撤销诉讼中消灭的,原告为向普通法院提起损害赔偿或其他补偿程序预作准备,即承认其对于行政法院就该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性的确认有正当利益,但原告必须确实地主张其将要提起民事诉讼。如果损害赔偿、损失补偿之诉明显毫无胜诉希望的,则不构成确认利益[21]128-156。在一般确认诉讼中,原告的确认利益在于被诉请确认的法律关系能够期待在判决中澄清该法律关系中的具体争议。比如公务员希望使他的妻子获得充分保障,因此希望诉请澄清一个有争议的法律问题:他死后,他的妻子有无受国家照顾的请求权?具体来说,确认未来法律关系的确认利益应以法律关系真实发生的可能性来判断。确认过去法律关系的确认利益应以当该法律关系是否虽已经完成但现在仍然持续发生作用来判断,特别是权利持续受到侵害、有重复发生的危险、持续的歧视性效果,或根据法律问题的厘清对于原告将来拟采取的行动是否重要来判断。确认现在法律关系的确认利益在于该法律关系是具体的且有争议的。所谓“有争议”是指一个法律关系的存在或不存在,或者法律关系的内容有不明确的情形,如果法律状态的不明确是因为当事人有不同的见解,而且原告也想要确认其将来行为的方向,或者原告有理由担心主管机关将对其权利造成危害时,确认利益特别要被承认。所谓“具体的”是指经过各种实际发生的事实或当事人的行为,引发各种有关权利义务的歧见;换言之,法院不能只是被委请确认一些想象中的抽象法律问题或事实[21]160-168。
三、行政法上请求权之间的逻辑关系经过上面的分析,笔者构建出了一个行政法上的请求权体系。但是,请求权在行使时必须依照一定的顺序行使,这就构成了请求权之间的逻辑关系。
(一)原权型请求权之间的逻辑关系
王泽鉴教授把民法上原权型请求权行使的顺序安排为:契约上请求权、无权代理等类似契约关系上请求权、无因管理上请求权、物权关系上请求权、不当得利请求权[1]72。这样安排的考虑为:尽量避免于检讨某特定请求权基础时,受到前提问题的影响。对此,笔者认为,行政法上的请求权也存在类似问题。首先,原权型请求权先于救济型请求权被检视。其次,原权型请求权中,程序性请求权优先于实体性请求权参见:赖恒盈毙姓法律关系论之研究——行政法学方法论评析[M]碧ū保涸照出版公司,2003:104-105 ,因为没有正当程序的保障,将很难产生正确的结果。所以,无瑕疵裁量请求权、行政程序参加请求权应优先被检视。再次,实体性请求权中,给付请求权和行政合同上请求权应当被同时检视。只不过前者是法定的给付,后者是约定的给付。如同民法般,行政合同上请求权优于公法上无因管理请求权且优于公法上不当得利请求权。
(二)救济型请求权之间的逻辑关系
救济型请求权之间,防御请求权和损害填补请求权之间的顺序关系在德国被称为第一次权利保护和第二次权利保护。虽然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1981年的湿采石判决中确立了第一次权利保护优先原则,但是关于第一次权利保护和第二次权利保护的内容到底为何,学说上并未取得一致。关于维持判决是否有存在的必要,参见:莫于川毙姓诉讼制度改革中的焦点问题——目标、方案和理由[J]敝厍煊实缪г貉Пǎ2006,(2) 笔者认为,可以从救济型请求权的功能——保护当事人权利的角度来思考。对于一个将对公民权利造成侵害的行为,公民首先可以发动不作为请求权,要求行政机关不作出该侵害行为,作为第一层的保护。如果侵害行为已经做出,公民可以接着提出侵害行为排除请求权,要求行政机关撤销该侵害行为,作为第二层的保护。如果侵害行为排除后,还有残余的侵害后果的,公民可以发动结果除去请求权,要求行政机关除去该侵害结果,即恢复到权利未被侵犯前的状态,此为第三层的保护。如果侵害结果无法被除去,即已经产生了不可回复的损失,此时公民可以发动损害填补请求权,要求行政机关用金钱弥补损失,作为第四层的保护。
现在的问题在于,确认请求权在救济型请求权中的地位何在?笔者认为,这要从确认诉讼在行政诉讼中的定位谈起。德国《行政法院法》第43条第2款规定,原告的权利依撤销诉讼或给付诉讼能够实现或本来能够实现者,不得提起确认诉讼。此规定于请求确认行政处分(即我国的具体行政行为——笔者注)无效时,不适用之。这被称为确认诉讼的补充性或者备位性。由于确认诉讼缺乏撤销诉讼的形成作用(即除去违法行为的效力)和给付诉讼的执行作用(即对不履行给付义务的行政机关进行强制执行),因此,基于诉讼经济的考虑,为避免原告选择效力较弱的诉讼救济途径,且为防止在确认诉讼之后仍须再提起其他更有效的诉讼类型造成司法资源浪费,所以,立法者明定确认诉讼的备位性,促使争议的解决尽量集中在一种最为直接有效的诉讼类型[23]。虽然德国《行政法院法》只是规定了一般确认诉讼的备位性,但其实对于确认具体行政行为无效的诉讼和确认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诉讼也适用。确认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诉讼天然具有备位性,因为它是在具体行政行为已经消灭或者已经不需要给付的情况下提起。确认具体行政行为无效的诉讼虽然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但是具体行政行为究竟是无效(严重且明显违法)还是可撤销(一般违法),在诉讼争议之初,当事人往往很难区别。因此在诉讼实务上,往往允许当事人先提起撤销诉讼,待审查中发现其实为无效时,允许当事人转换或变更为确认无效诉讼[24]。可见,确认请求权是作为侵害行为排除请求权的补充而出现,即当事人无法主张侵害行为排除请求权时,可以主张确认请求权。
由此可以整理出行政法上的请求权体系及逻辑关系:
四、结论——请求权在行政法上所能发挥作用之展望诚如前述,请求权在行政法上的作用有三:
(一)请求权是否存在涉及到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问题。对此,保护规范理论发挥着关键作用。但是,由于传统的保护规范理论比较繁琐,所以近来出现了缓和的迹象。对于具体行政行为的直接相对人,一般都肯认其享有请求权。因此,保护规范理论的重心就转移到对具体行政行为的第三人(利害关系人)是否享有请求权的分析上。在我国,变更判决是对撤销并责令重做判决的“变种”,即撤销并责令重做是责令行政机关重做具体行政行为,而变更判决是法院替行政机关重做具体行政行为,由于法院并非行政机关,替行政机关作具体行政行为容易造成司法权和行政权界限的模糊,故变更判决的作出应非常谨慎,只有在行政处罚显失公正,即行政处罚机关的裁量权收缩为零时才有可能。所以,变更判决可以看作是对公民的无瑕疵裁量请求权的一种救济。 2000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条规定了相邻权人、公平竞争权人、行政处罚的受害人等利害关系人享有原告资格,但是他们为什么享有原告资格?这必须用保护规范理论来进行验证。比如对于行政处罚的受害人为什么对于行政处罚享有原告资格,根据《行政处罚法》第7条第1款,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违法受到行政处罚,其违法行为对他人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由此可见,行政处罚不仅具有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还具有保护受害人获得民事赔偿的目的。
(二)请求权的不同类型涉及法院采用何种判决类型,由此可以优化行政诉讼的判决类型。我国行政诉讼的判决类型主要有六种:维持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判决、撤销判决、变更判决、确认判决、履行判决,但还有很多未被类型化的判决类型,比如撤销并责令重做判决、撤销并责令采取补救措施判决、确认违法并责令赔偿判决、补偿判决等等;同时还缺乏一些应当有的判决类型,比如不作为判决、确认法律关系存在与否的判决、一般给付判决等等。而这些问题的解决,请求权概念发挥着关键的作用。换言之,如果承认当事人的某种请求权,那么,诉讼上必然出现与之对应的判决类型。其中,原权型请求权都针对给付判决(根据要求给付的内容是否属于具体行政行为分为课予义务判决和一般给付判决),救济型请求权中的不作为请求权也针对给付判决(与原权型请求权针对积极的给付判决不同,不作为请求权对应的是给付判决中的消极的给付判决),结果除去请求权和损害填补请求权都针对给付判决中的一般给付判决,侵害行为排除请求权针对撤销判决,确认请求权针对确认判决。由此可以形成如下的请求权与行政诉讼判决类型的对应结构:
(三)通过请求权基础的分析来体系化行政法的法规范。请求权之所以成为民法的基石,就在于通过分析请求权基础可以将整个民法的法规范予以整理。整个民法典的规范就是由请求权基础规范、辅助规范和请求权对立规范构成[2]。涉及到规定如何产生和取得请求权的规定为请求权基础规范或请求权规范。请求权规范规定了主张该请求权的前提,只有在满足该前提的条件下,请求权人才能够令义务人为履行(包括作为和不作为),在发生争议情况下,才能够通过国家权力通过强制执行获得满足。请求权规范由事实和法律后果构成。辅助规范细化了请求权规范的事实构成以及法律后果。辅助规范亦同样可划分为事实构成和法律后果,但辅助规范常常并未规定法律后果,其仅仅涉及到技术性的规定,如定义、期间的长短或法律行为的具体形式。对立规范阻止、消灭或阻却请求权,对立规范构成抗辩的基础。以《行政处罚法》为例,该法第31条(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和第32条(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行政机关应当采纳)构成请求权基础规范,即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享有行政程序参加请求权。第41条前半句(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不依照本法第31条、第32条的规定向当事人告知给予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或者拒绝听取当事人的陈述、申辩,行政处罚决定不能成立)是辅助规范,规定了行政机关侵犯行政程序参加请求权的法律效果,即行政处罚不成立。第41条后半句(当事人放弃陈述或者申辩权利的除外)是请求权对立规范,即行政机关可以通过该条来阻碍当事人的行政程序参加请求权的法律效果发生。ML
参考文献:
[1] 王泽鉴.法律思维与民法实例——请求权基础理论体系[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68.
[2] 朱岩.论请求权[J].判解研究,2003, (6).
[3] 王和雄甭坌姓不作为之权利保护[M].台北:三民书局,1994:25.
[4] 汉斯·J·沃尔夫,奥托·巴霍夫,罗尔夫·施托贝尔毙姓法:第1卷[M].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2:505.
[5] 杨建顺比毡拘姓法通论[M].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 1998:191-206.
[6] 金可可甭畚碌律骋恋碌那肭笕ǜ拍睿跩]北冉戏ㄑ芯浚2005,(3).
[7] 卡尔·拉伦茨钡鹿民法通论(上册)[M]. 王晓晔,等,译北本:法律出版社,2003:322.
[8] 吴绮云钡鹿行政给付诉讼之研究[M]. 台北:“司法院”,1995: 128-130.
[9] 庄国荣蔽鞯轮基本权理论与基本权的功能[J].宪政时代,15,(3).
[10] 毛雷尔毙姓法学总论[M]备呒椅,译.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747.
[11] 林锡尧惫法上不当得利法理试探[G]//翁岳生教授七秩诞辰祝寿论文集——当代公法新论(下).台北:元照出版公司,2002:268.
[12] 刘宗德毙姓法基本原理[M]. 台北:学林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8:334.
[13] 李建良甭坌姓裁量的缩减[G]//当代公法新论——翁岳生教授七秩诞辰祝寿论文集(中).台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2:123-124.
[14] 王贵松甭畚掼Υ貌昧壳肭笕ǎ跩]毖习与探索,2010,(5).
[15] 罗传贤泵拦行政程序法论[M]. 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1985: 164-165.
[16] 林三钦惫法上“结果除去请求权”之研究[G]//翁岳生教授七秩诞辰祝寿论文集——当代公法新论(下)碧ū:元照出版公司,2002:239.
[17] 董保城,湛中乐惫家责任法——兼论大陆地区行政补偿与行政赔偿[M].台北:元照出版公司,2005:2-3.
[18] 翁岳生毙姓法(下)[M].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 1641-1642.
[19] 郑玉波狈ㄑ瑁ǘ)[M]. 台北:三民书局,1984: 25.
[20] 叶百修毙姓上损失补偿之意义[G]//翁岳生教授七秩诞辰祝寿论文集——当代公法新论(下)碧ū保涸照出版公司,2002: 298-299.
[21] 张尧钧毙姓诉讼上确认利益之研究[D]敝姓大学法律学研究所,2009:86-88.
[22] 叶百修,吴绮云钡氯招姓确认诉讼之研究[M]. 台北: “司法院”, 1991:24.
[23] 刘淑范甭廴啡纤咚现备位功能:行政诉讼法第六条第三项之意涵与本质[J].人文及社会科学集刊,2003,15(1):59-112.
[24] 林三钦薄靶姓争讼制度”与“信赖保护原则”之课题[M].台北: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7:35-39.
Framework and Function of Claims in Administrative Law
WANG Kai
(Law School of Beiha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1, China)
Abstract:Claims in administrative law are derived from public right, which, since falling within the scope of public right, can exercise a function covering the whole public right realm. Claims in administrative law are made up of original claim and remedial claim. The former includes payment claim, administrative contract claim, claim arising out of voluntary service, unjustified enrichment claim, claim for flawless discretion and claim for participating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while latter includes defense claim, indemnity claim and claim for declaration. All claims correlate logically with each other rendering seamless protection to citizens. Moreover, claims combine administrative law with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which is of great importance as to ascertaining the proper plaintiff, deciding typology of judgment and establishing administrative norms.
Key Words:claim; public right; original claim; remedial claim; theory of protective nor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