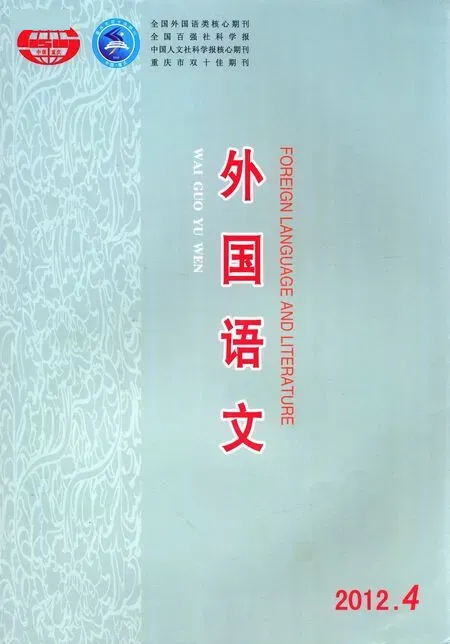“来”的语用化刍议
侯国金
(四川外语学院 外国语文研究中心,重庆 400031)
1.“来”的来龙去脉
“来”和“去”,英语的come/go,都是表示由远及近或向相反方向移动的最典型的运动动词——“动词中最纯、最典型的词”,“所有动词中最具有动词特征的词”(Miller&Johnson-Laird,1976:527——转引自文旭,2007),如例(1)、例(2)。这种用法是很普遍的,可称为无标记用法。几个汉语词典差不多都说“来”是“从别的地方到说话人所在的地方,跟‘去’相对”,而“去”则是“从说话所在的地方到别的地方(跟‘来’相对)”。其实偏离和例外是很常见的,均算有标记用法[参见侯国金(2005a,b)对语用标记的讨论]。下面重点说“来”,一是因为篇幅有限,二是因为认识了“来”对认识“去”以及英语等欧洲语言的对应词都能发挥作用。
(1)(某上海人邀请重庆朋友)到上海来。
(2)(语境同上)下个月我去你们重庆。
“来”的有标记用法主要有哪些呢?我们可以把“来”的上述由远及近的移动看成两类。一是真实空间的由远及近的移动,如上面的例子;二是虚拟或心理空间的由远及近,如例(3)、(4)——表示抽象化的友情。例(5)的“来”略带真实的方位移动,有时可换为“去”(表相反的方位移动),可以说就是一个助词,因为删除它或改放“带”字之后都不怎么影响大意。例(6)的“起来”表实义时是“站起来”或“起床”之义,表虚义时为某事物进入或接近某动作或状态。这个“起来”也是助词。例(7)“来”(常与“着”连用),完全虚化为助词,“用在句尾,表示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相当于‘来着’”(李行健等,2004:777)。另外,例(2)也可以改说(2')——这是心理上的由远及近,即把对方的家或居住地当作近(主/东道主),而把自己这里当作远(客/客人)。
(3)(大人鼓励小孩跳进游泳池来游泳)来来来。
(4)我们之间没多少来往。
(5)说着出去一会儿,果然带了个后生来:……(《红楼梦》第7回)
(6)东边房门口坐的珍伯母也放声大哭起来,……(胡适《九年的家乡教育》)
(7)(贾母忙哄他道:)你这妹妹原有玉来着……(《红楼梦》第3回)
(2')下个月我来你们重庆。
通过对大量语例的考察,我们发现,从真实空间的移动到非真实空间的移动,“来”的用法从无标记到弱标记,再到弱中标记、中(等)标记、中强标记,最后到强标记和极强标记,其实经历的是一个逐渐语用化的过程。侯国金(2008:20-21)提出“语用化”,指的是“一些话语在使用中逐渐形成表达与字面义不同或相距甚远的意义[不一定是含义,可称为‘羡余意义’(residuemeaning)]的现象”。往往铺垫以“含义化”(implicationalization)即语辞表达字面意义以外的东西之倾向或过程,表现为隐喻化、语法化等特点。本文的“语用化”是涵盖(微观)含义化、虚化、语法化、隐喻化、边缘化、非理据化等的认知语用过程①如“来!”[类似于例(12)]——含义化:“靠近我!”语用化:“吃点!/喝点!/我教你。”再如“你又来了!”[同例(15)]——含义化:“你又要做或做了一件坏事。”语用化:“别这样!/不要做那件事!”(同上:21 页)。有标记的“来”都不同程度地象似(iconic)于无标记的“来”(有关象似性参见Haiman,2005;王寅,2003)。请看下表:

空间虚实 U/M 对立 标记等级 语例 基本用法与意义真实空间由远及近无标记用法 例1)听者朝说者方向进行物理移动真实和虚拟空间的由远及近兼而有之虚拟空间由远及近有标记用法弱标记 例(3) 几乎同例(1):主要用于鼓励、劝诱弱中标记 例(4) 几乎同例(1):谁来谁往已不要紧,“来往”已成表关系的成语中标记 例(5) 真实和心理空间的由远及近兼而有之,几乎虚化为助词中强标记 例(6) 几乎同上,“起来”几乎虚化为助词,表示接近或进入某动作/状态强标记 例(7) 完全虚化为助词,表示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极强标记 例(2') 与真实空间的用法相反,以对方为中心的心理空间的又远及近
文旭(2007)文中通过Talmy(1985)的“运动事件框架”构建了所谓“运动事件描写框架”,并以此探讨了“来/去”的语用意义及其指示条件。文旭的“典型语用意义和非典型语用意义”大约与我们讨论的无标记和有标记用法相当。他所介绍的“来/去”的一些“指示条件”②文旭说,“来”的上述用法的指示条件为:说话人说话时在目标;图形到达目标的时候,说话人在目标;说话人说话时,听话人在目标;图形到达目标的时候,听话人在目标;目标是听话人的家、工作单位或家乡等(他说的“图形”指人,“目标”指动作者的目的地)。是有参考价值的。由于他运用的是这一框架,也由于他的视角不同于笔者,他在文章里好像是就(“来/去”的)词而论词,而很少考虑语句的各个组成部分及其相互关系,更没考虑大于句子本身的语境以及非言语语境(因素)。左双菊(2011)分析了“来/去”的语义泛化过程及其诱因。她认为“来”经历了“发生、来到”义阶段和“做某个动作”义(代替意义更具体的动词)阶段。他说“去”经历了“去1-4”阶段。她说泛化的内在动力是隐喻和转喻机制,其外动力则是经济原则。笔者基本赞同,并认为:1)短语和语句语境是考察“来(/去)”的重要切入点;2)不同的“来”构式其“来”的语用化的内在和外在驱动力还有其他机制和原则。因此,下文谈谈“来”的短语结构与功能,如它前面或/和后面常有什么词,是单用还是叠用,是不是连动式,它们都表达什么样的意义和功能,受制于什么认知语用原则,等等。
2.从无标记中“来”,到弱、中标记中“去”
2.1 真实空间的由远及近的移动
这是无标记用法,作动词,表示方位的移动,可称为“来1”(关于“来1-3”,参见 §3.8)。结构是:“来”(省略方位词);“到+方位词(+来)”;“来到 +方位词”;“来 +方位词”。假如在“来”前面可加“快”、“到+方位词”、“乘火车/汽车”,后面可加“了、过”,这个“来”就是无标记的。当然,满足某一个条件未必就是无标记的,例如,满足两个条件却为弱中标记(用法)的就有“回(到复旦)来(了)”等。除了例(1)外,再如:
(8)每个上面长出两瓣嫩叶,笑迷迷的好像是说:“我们又来了!”(胡适《乐观》——原文的诗体即三行改为散文体即一行了)
(9)甲午(1894)中日战争开始,台湾也在备战的区域,恰好介如四叔来台湾,……(胡适《九年的家乡教育》)
一般是来者在“来”之前,但有时是来者在“来”之后。如:
(10)这样一个家庭里忽然来了一个17岁的后母,……(同上引)
(11)他母亲也凑到他跟前来了。(路遥《人生》)
2.2“来”的单用或叠用
这是弱标记用法,语用含糊地[比较左双菊(2011)的“泛化”]起到鼓动、号召、鼓励、劝诱的作用。结构是:“来;来来;来来来;来+吧;来吧+来吧”。除例(3)外,再看例(12)。这其实是“假指令句”(pseudo-directive)(侯国金、张妲,2002;侯国金,2008:422)。
(12)来!快把他斫倒了,把树根亦掘去。(胡适诗歌《乐观》,原文为三行,这里改为一行;“他”指大树)
2.3“来”与近义词连用
这是弱中标记用法,结构是“来往、往来;来回、回来;来去;来临;来归、归来;到来、来到;进来”。“来”与连用的近义词调换次序,有的意义不变,如“来往、往来”,有的稍有变化,如“来归、归来;到来、来到”,还有的意义有很大差别,甚至行不通,如“来回、回来;来去;来临;进来”。此时的“来”不是真切的“来”,有些许隐喻性——受制于隐喻机制和生动原则。
2.4 代动词用法
这是中标记用法,受制于转喻机制和Zipf(1949)提出的“最省力原则”。结构是“来+数词+量词(+名词)”——代动词(pro-verb),相当于一个动词,由于其多义性,几乎是万能动词。如:
(13)你不来点(酒)?
(14)少来!(=不要这样!)
(15)你又来了?/少来这套!(=不要这样嘛!)
(16)慢慢来,别着急!(路遥《人生》)
(17)但就是要娶,也应该按乡俗来嘛,……(同上)
(18)可是哪来得这东西呢?漂白粉只有县城才能搞到。(同上)
(19)还是我来吧。(搬东西,处理问题等)
这种用法表现出言者的随便语气或写作者的口语文体。这样用的“来”多半可以换成其他更加精确的字词,如例(13)可以换为“要/喝”,例(14)可换为“做/说/嘲笑”等,其他还有“等、工作、操作、执行、仿照、遵守、弄、买、运”等。左双菊(2007)发现,“来、去”带宾用法频率很高,区别在于“来”作为“万能动词”具有非凡的带宾能力,其宾语成分呈现多样性因此其“语义类型复杂”。按照她的个案研究,“来”字带宾语的优先序列是处所宾语66.3%,施事宾语16.8%,受事宾语12.7%,其他有结果宾语、目的宾语和方式宾语。“去”只是带宾能力有限的“弱及物性动词”,其宾语只能是体词性的且语义类型也多为处所宾语①按照其个案调查,处所宾语占92.%,施事宾语占6.3%,致使宾语占1.3%。。
3.从中、强标记中“来”,到极强标记中“去”
3.1 真实或虚拟空间移动的补语“来”
表示真实空间移动的是中标记用法。像助词,作补语,结构是“请/叫/带/邀/聘+人名 +来;请/叫 +来 +人名”。如例(5)以及下例:
(20)我母亲几次邀了本家长辈来╋,给他定下每月用费的数目。(胡适《九年的家乡教育》
常常起补语作用的“来”是“起来、出来、下来”。如:
(21)我从不知道她醒来坐了多久了。(同上)
(22)她说到伤心处,往往掉下泪来。(同上)
(23)一天门外也没逛,斗大的字不识一升,倒学起文明来了!(路遥《人生》)
(24)痴情的姑娘为了让心爱的男人喜欢,任何勇气都能鼓起来。(同上)
(25)要往祠堂里哭太爷去,那里承望到如今生下这些畜生来!……(《红楼梦》第7回)
表示虚拟空间的移动的结果或语效则为中强标记用法,也作补语,受制于隐喻机制和生动原则。典型的结构是“动词+(起)来”。其他有:“过来、想来、飞来、上来、起来、看来、下来”②全文的“来”词语组合许多来自刘兴策等(2003:276-277)或李行健等(2004:777-778),一并鸣谢。等。例(6)的“大哭起来”的“起来”是“大哭”的补语,再细分起来,“来”是“起”的补语。有时,“起来”表示“起床/站起来”的意思。
(26)于是,三个掏粪的人就在车站的停车场上打了起来……(路遥《人生》)
(27)他觉得他既然已经成了国家干部,就要好好工作,搞出成绩来。(同上)
像“冲出来/去一个大汉、拿来/去一本词典”类构式,有人称这里的“来、去”为“趋向补语”。只是宾语有时在“来、去”前,有时在“来、去”之后。这样一来,就还有“冲出一个大汉来/去、拿一本词典来/去”。至于两者有何差别以及“来、去”有何差别,这跟“来、去”后的宾语是施事宾语(如“一个小孩”)还是受事宾语(如“一篮苹果”)有关,跟其间的动词是位移动词(如“走、送、拿、滚”)还是非位移动词(如“炒、切、包、割”)有关。(王丽彩,2005;刘慧,2011)。
3.2 心理空间的由远及近的移动
这是中强标记用法,受制于隐喻机制和生动原则(犹如人的来临)。如:
(28)爱情?来得这么突然?(路遥《人生》)
(29)德顺老汉在前面又抿了一口酒,醉意便来了……(同上)
(30)他想起刚才老刘那声喊叫,灵感立刻来了。(同上)
3.3“来 +NP”构式
这是中强标记用法,“来”作名词的定语,受制于转喻机制、模糊机制和最省力原则。如“来宾、来客、来人、来稿、来函、来鸿、来件、来书、来信、来意、来文、来照、来历、来路、来潮、来年、来生、来日、来世、来势、来源、来头、来火”等。比如“来稿”可能是“寄来、送来、拿来、捎来、发来、传来的稿子”中的一项,言者只说“来稿”就是模糊地以泛指的“来”代替具体的“来”法,达到省力的目的。看例句:
(31)我们之间没多少来往。
“来+NP”构式若为动宾结构,就是把“来”作为“万能动词”来用了,如“来劲、来菜、来神”等,如例32),此时“来”隐喻化或泛化程度极高。
(32)最近打牌手气好,很来菜。(是“来钱”的委婉语)
3.4 表示“去”的“来”
这是极强标记用法,“来”非“来”,“来”即“去”,即表示真实空间由近及远。这是转喻机制和反讽原则使然。除了例(2')以外,还有:
(33)我就来。(其实是“我就去”)
(34)你不来也行。我到你这里来!(路遥《人生》)
3.5 作为话语标记的“来”③ 陕北神木话里的“来、去”可充当话题标记(邢向东,2011)。
这是强标记用法。结构是“数字+来;数字+名词+来;这样/那样/如此+一来”等。最典型是“一来……二来……”,表示列举。还有“时间短语+(以)来”,如“一个星期(以)来”。这个“来”是“概数助词”,搭配的量词“个”等是不能或缺的(张谊生,2001)。注意“来人、来个人、十来个人”的区别,只有“十来个人”的“来”才是“概数助词”。注意,此时的“来”语用化(泛化、隐喻化、虚化、功能化)程度极高。
(35)我到上海去,一来是办点事,二来是看看朋友。(李行健等,2004:777)
(36)一来送妹待选,二来望亲,三来亲自入部销算旧账,再计新支。(《红楼梦》第4回)
(37)30多年来,我不曾重见这部书,……(胡适《九年的家乡教育》)
其他还有“说来、算来、如此说来、这样看来、细细想来、说起来”等。如:
(38)子兴道:“正是,说来也话长。”(《红楼梦》第2回)
(39)说起什么来都头头是道……(路遥《人生》)
(40)且说荣府中,合算起来,从上至下,也有三百馀口人……(《红楼梦》第6回)
3.6 表示曾经发生过的事情的“来(着/了)”
这是强标记用法,一般结构为“VP+来(着)”,受制于隐喻机制、最省力原则和生动原则。“来着/了”一般用于陈述句或疑问句(偶尔用于惊叹句)的句末。除例7)外还有:
(41)你昨天干什么来(着)?(李行健等,2004:777;“着”为笔者加,下同)
(42)这话我什么时候说来(着)?(同上)
(43)贾母忙哄他道:“你这妹妹原有玉来着……”(《红楼梦》第3回)
(44)贾母便命:“去见你娘来。”(同上)
例(44)的这一用法相当于法语、英语的将来完成时,意思是叫听者到远处或近处见“你娘”。比较例44'),这是叫听者跟着说者一起去见远处的“娘”。
(44')……“来(,)见你娘去。”
干红梅(2004)认为,“来着”“与句子表达的时制、动态无必然联系,与句子强调动作或强调宾语无必然联系”。它是“语气助词”,陈述句中表示陈述语气,功能上相当于“了、啦、的”等,疑问句中自然表示疑问语气,相当于“吗、呢”等。赵志清(2010)利用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语料库调查发现,“来着”这一虚词(介于语气助词和动态/时制助词之间)的语法意义是:1)表示过去,主要用于陈述句;2)表示“一时忘记而寻求提醒”,主要用于疑问句。他的数据表明,“来着”多半用于陈述句句末,句中有时可带“了、过”。陈前瑞(2005)则认为,“来着”小句由表过去(尤其是最近的过去)到不表过去,反映了语言使用者的主观性的高低(此乃主观化的结果)。具体说来,“来着”小句的现时相关性主要是:A.涉及因果,如下例;B.前后或正反对比,如例(46);C.引出下文的话语,如例(47);D.以反问指责,如例(48);E.想不起来或提醒例(41),(42);F.报道新信息,如例(49)。它们的呈现阶段和排序如下,A、B>C、D>E、F,象似于主观性的高低。如:
(45)瞧你又在练功呀!你何苦来着?
(46)甲:你当时是抱着什么动机参加义和团的?
乙:我本意没想参加义和团,想到绿营当兵来着。(改自陈前瑞,2005)
(47)我正这么想来着?(《读者》合订本,摘自赵志清,2010)
(48)你早干什么来着?晚啦![同例(46)]
(49)杨妈告诉金枝,老爷子审金秀来着,把金枝的事全问出来了。(同上)
3.7“来”的习语(化)表达式
这是强标记用法。词语的字数越多,标记性越强,词语越新颖,标记性越强。这也说明,在一些陈词滥调式的双字习语(如A组的“由来、从来、本来”里),“来”的由来或来历已经语用化,其往昔理据基本消失殆尽,至少我们使用时不必联想到它们最初的理据说(如“由来”的意思是“由什么而产生”)。
1)双字结构:“来向,由来,本来,从来,迩来(=近来),古来,后来,胡来,将来,近来,历来,年来,日来,生来,素来,外来,未来,向来,夜来,以来,由来,原来,自来,看来”①参见张爱玲(2007)对“看来”(即“在/从……看来”)的主观化的讨论。等。
2)三字结构:“来不得,来不及,来得及,来复枪,来复线,来回倒,来路货,舶来品,过来人,数来宝,外来词,自来水,吃不来,吃得来,到头来,反转来,合不来,合得来,何苦来,划不来,说不来,说得来,下不来”等。
3)四字结构:“来而不往,来回来去,来回摇摆,来龙去脉,来路不明,来去匆匆,来去无踪,来日方长,来势汹汹,来者不拒,来者居上,来者可追,来之不易,来之能站,来踪去迹,后来居上,嗟来之食,眉来眼去,逆来顺受,先来后到,迎来送往,空穴来风,心血来潮,纷至沓来,蜂拥而来,古往今来,继往开来,接踵而来,卷土重来,苦尽甘来,礼尚往来,否极泰来,死去活来,突如其来,信手拈来,有生以来”等。
4)六字以上结构:“老死不相往来;来无影,去无踪;来者不善,善者不来;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等。
3.8“来”的连动式
“来”的连动式有弱、中、强标记各种用法,比较复杂。最简单的结构为“来 + VP”。“来”(以及“去”)“在具体义动作动词之前时是位移动词,在短时性动作动词之前时是助动词;在动词短语或介词短语与动词短语之间时是连词:在‘到+处所宾语’与动词之间时是趋向动词”(唐秀伟,2010)。当“来”表示真实空间的移动时是无标记用法,当它表示心理空间的移动,即由一个动作/状态发展到另一动作/状态时,就是强标记用法,受制于隐喻/转喻机制和最省力原则。
(50)本县太爷的差人来传人问话!(《红楼梦》第1回)
(51)我们开个party来欢送学姐们如何?
(52)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红楼梦》第4回)
53)刘姥姥道:“也没甚的说,不过来瞧瞧姑太太、姑奶奶,也是亲戚们的情分。”(同上,第6回)
(54)叫几个妥当人来抬去。(同上)
(55)你到底能不能全方位多层次地来应和这个?(张全生,2011)
朱德熙(1982:166)说这种“来”没有实在的意思,仅用于连接。刘月华等(2001:703)说它是表达某种意愿,起到缓和语气的连接。刘丹青(2002)认为这个“来”是“纯联系项介词”,前面若有介词“用”就联合构成“框式介词”。多数人认为这个“来”后面的动词是目的。张全生(2011)基本赞同但认为以往研究存在的缺点在于:1)捆绑式研究“来、去”好像它们没有什么差别——实际上存在很大差别;2)没有给“来+动词”类构式以“分布上的分类”。他认为该构式可以细分为“施事+来+动词”分构式以及“介宾结构/述宾结构/其他状语成分+来+动词”分构式。姑且仿效辛承姬(1998)而称无标记即表示空间位移的“来”叫做“来1”(见§2.1),而把“施事+来+VP”(分)构式中语义更加泛化的“来”叫做“来2”,再把构式2即用在介宾结构和VP之间的“来”叫做“来3”(准结构助词),那么,“来2”表示(动词的)动作施动者(第一、第二人称代词)的“主动意志”,语法上不是必需的;施动和“来”一般不插入其他成分,而且倾向于两个小句的对比;至于“来3”,辛承姬认为它代表着“语义泛化的极端”(通过下文的分析可以看到这还不算极端)。董晓琨(2006)和张全生(2011)则认为,“来2、来3”是焦点标记词(focus marker),分别标识“来”前成分为“对比焦点”和“常规焦点”。在例(50)中,“来”标识了前面“差人”为对比焦点,在例(55)中,“来”前面的“全方位多层次地”为常规焦点。至于标记的焦点为什么是“来”前成分而非“来”后成分?张全生(2011)说,1)“来”后的VP是常规焦点;2)焦点结构出现变化时,“来”前成分就是新结构的常规焦点或对比焦点,3)需要借助标记词“来”。
多数人①如李明(2004)、王国栓(2005)、梁银峰(2007)等。同意,从古(南宋以后)汉语开始,“来+VP”或“来+EVENT”这种“基本句法环境”促使“来”发生语法化。张全生(2011)指出,包含“来+VP”构式来源于上古汉语(母)构式“VP1+(NP1)+来 + VP2+(NP2)”(姑且称“构式1”),后者提供了“来”“发生语法化的格式”,由于“VP1”和“NP1”语义类别逐渐嬗变,尤其好似“VP1”逐渐扩大了选择范围,VP2前的“来”日趋语法化。他说,该母构式的两个VP和“来”属于一维时间,由于时间对空间的隐喻性能,VP1或者表致使义或者表支配义,完成VP2一定是VP1的目的。这个“来”也算目的标记。张全生说,在中古汉语中,VP1增添了表处置意义的动词“持”和“把”。由于VP1的处置义增强了,“NP1由受VP1支配可以理解为受VP2支配、进而变为受VP2支配,VP1则由处置义动词语法化为处置介词”,构式1就衍生出构式2“PP+(NP1)+来 + VP+(NP2)”。如他的例子:
(56)今日亲家初走到,就把话儿来诉告。(《快嘴李翠莲记》)
那么,焦点标记词“来”是如何语用化而形成的呢?根据张全生,构式1的语义重心是“VP2+(NP2)”部分,体现了“已知信息—新信息”的分布原则。“来”是目的标记,标明其后的“VP2+(NP2)”为焦点成分。不过,从构式1到构式2,结构信息的分布有些许变化。张全生说,在构式2中,修饰性成分“PP+(NP1)”成为语义重心(常规焦点)(参见端木三(2007)的“信息-重音原则”)。张全生补充说,“来”的这一用法后来日趋常用,出现的语境也日益增多,“PP+(NP1)”部分会泛化为各种真正或非真正意义的状语成分。②张全生(2011)后面讨论了NP1为“我/你”时的一些不同情况,这里就不赘述了。
张全生的分析很到位,具有朴素的语用学思想。笔者认为,连动式中的“来”是否标识前面或后面为信息焦点是一个认知语用问题,更准确地说,是一个关联问题。若说两个VP都为焦点,一是没必要,二是会给“来”和全句带来超负荷新信息。号称的新信息多了也就不新了。根据关联原则的精神,在一定上下文语境和情景语境中,构式1通常是以“来”后部分为焦点。注意例外也是有的(属于有标记)。至于构式2,“来”前后两个部分都有可能成为焦点。当语句的(预设的)主位意义(thematic meaning)是(问)如何/怎样“来+VP+(NP2)”的,构式2的“VP1+(NP1)”就关联地成为焦点了。比较而言,假如(预设的)主位意义是(问)“PP+(NP1)”是什么目的、用途、用意等时,焦点就关联地落在“VP+(NP2)”之上。其次,任何语言都有连动式,只是连动的“连动词”或标记词不同罢了。英语用to(and的一种用法也算),法语用 d e,日语用て(念 t e,表示连动、中顿、目的等)。汉语本有“而、以”。“而”是并列关系,相当于英语的and或but,所连不完全是连动式。“以”是“以便”之略,表示“目的”,没有连动式的丰富而模糊的构式意义/效果。听来更加悦耳和间接的“来(以及一定的‘去’)”正好挑起了连动词的大梁。另外,有趣的是,汉语和英语、法语、日语等语言的“来、去”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既有的用法又有语法化的用法,其机理大同小异。
以上的“来”传达的真实空间移动少之又少,而下面的“来”,从例(57)到(59),虚拟性和隐喻性逐渐增强。有时一句话可以有几个这样的“来”,如例(60):
(57)明楼起来敬酒。(路遥《人生》,无标记用法)
(58)因那日买了个丫头,不想系拐子拐来卖的。(《红楼梦》第4回)
(59)后来大嫂二嫂都生了儿子了,她们生气时便打骂孩子来出气,……(胡适《九年的家乡教育》)
(60)他拼了老命(来)挣钱来养活妻子儿女。
4.“来”的语用化概述
胡适的《九年的家乡教育》这篇散文共有9,321个字,共有64个“来”。表示真实空间的由远及近的移动只有20个,占31.25%。多半是用于习语的“来”,如“后来、向来、起来、这十天半个月来”。其中“后来”就有12次。路遥的小说《人生》共有109,695个字。“来”用了904次。初步统计表明,90%以上是非真实空间的移动,如“越来越……,换来的钱,走来走去,说来说去,躺下来,掉下来,看来”等。当然,还有一些介于真实和虚拟空间移动之间的,如“过来、飞来、传来、到来、冒出来”等,不过这些是§2.8所说的补语用法(属于中强标记)。古典长篇小说《红楼梦》共有846,648个字,“来”字用了11,121次。由于语篇长,“来”字多,我们没有做具体细致的考察。除了“后来,原来,想来,历来,站起来,这样一来”等弱、中、强标记用法外,有很多无标记用法和弱标记用法,表示的几乎是真实空间的由远及近的移动。
“来”的语用化主要是遵守Grice(1975)的“合作原则”和Zipf(1949)的“最省力原则”的产物。交际者使用言语符号表达的意思必须是自己信以为真的(符合质准则),提供的信息量不大不小(遵守量准则),但同时要简洁、省力[遵守方式准则(以及最省力原则)],组织话语的方式和信息(质)本身还得切题,与语境相关联[符合关系准则(以及Sperber&Wilson(2001)的关联原则)]。表示真实空间由远及近移动的“来”是遵守所有原则的无标记式。“来”的其他的用法则或多或少地偏离或违背了上述原则。
以下再以上面的分析为对象来进行语用化分析小结,都以符合关联原则为前提,都有认知语用机制作为某种语用化过程的内力,都以某种语用原则为其外力。
1)§2.1的情况是最常见的,这里就不赘述了。
2)“来”叠用(见§2.2)是偏离合作原则的方式准则,以求急切、紧迫的敦促或催促等语效。其内力为隐喻机制,其外力是最省力原则(以另类方式图经济,比较一下更具体语义的变体)。
3)“来”与近义词连用(见§2.3),尤其是可以调换位置的情况,偏离合作原则的量准则,以求到双音节语效。此时的“来”不是真切的“来”,有些许隐喻性——受制于隐喻机制和生动原则。
4)“来”的代动词用法(见§2.4)偏离方式准则,受制于转喻机制和最省力原则,以求含糊与省力的语效。
5)表示真实空间移动、作补语的中标记用法(如“请+人名+来”,见§3.1),对合作原则的方式准则则有些许偏离,相当于“我请他,他才来的”,还有表示虚拟空间的移动的结果或语效,作补语的中强标记用法[如“大哭+(起)来”],这是对质准则有所偏离,相当于“从没哭到哭再到大哭的状态转移”,所求均为省力简洁的语效。该用法受制于隐喻机制和生动原则。
6)心理空间由远及近的移动(中强标记用法,见§3.2)偏离质准则,受制于隐喻机制、生动原则和最省力原则,表达“像人由远及近一样地到达”之意,所求为省力与生动之语效。例如,夫妇之间闺房里说的“(我要)来了”所说的“来(者)”不是真实的“我”,而是心理感受的“我”,这里指高潮。
7)“来+NP”(中强标记用法,见 §3.3)有时是真实空间的移动,相当于“到来的/刚到来的/即将到来的/已经到来的”,如“来宾,来潮,来稿”的“来”;有时表示虚拟空间的移动,标记性更强,相当于“像人或物一样到来”,如“来势,来头,来劲”。该结构有时可以改为“NP+来”,但有差别。受制于转喻机制、模糊机制和最省力原则。在例(61a)中,“我”为无标记话题,语用功能是好像“我”能操纵“月经”的来去。另外,该结构中“月经”不能委婉化为“(小)妹妹/表妹/表叔/姨妈”。在例(61b)里,“我”和“月经”为有标记话题,因为后者为从属话题,语用功能为“我”对它没辙。该结构的“月经”能够像上面那样委婉化。
(61a)我来月经了。
(b)我月经来了。
8)§3.4所讨论表示“去”的“来”是极强标记用法,受制于转喻机制和反讽原则。“来”为什么能表示真实空间由近及远呢?原因是言者以对方所在的家、家宅、公司、办公室等为中心,而放弃以自己一方的方位为中心,以显尊重或亲切。这是“以家宅为基础”(home-based)的用法。[何兆熊等,2000:76;Levinson,2001(1983):84]
9)作为话语标记的“来”(强标记用法,见 §3.5),受制于隐喻机制、生动原则和最省力原则——语用化(泛化、虚化、功能化)程度极高。如“一来……二来……”,表示列举,是如何由现实空间的移动虚化为表示列举事件的先后的“一/二来”的,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这个虚化的“来”与上文说的作为副词或话语标记“后来”的“来”是同一个演化方式。同样,话语标记(相当于状语)的“说来”,相当于“说起来”,表示交际者从没提起到提起的过程,是话语行为由远及近的移动。比较“让我从刚才没说X的状态进入开说X的状态吧”,“说来”显然是遵守最省力原则的,其语用目的是省力和口语化(语效)。
10)表示曾经发生过的事情的“来(着)”(强标记用法,见§3.6),对“来”的质(准则)有较大的偏离,相当于“你说曾经……了,是不是呀?”偏离方式准则,受制于隐喻机制、最省力原则和生动原则,能达随便、亲昵的口吻(语效)。
11)“来”的习语(化)表达式都是各种程度的强标记用法(见§3.7)。A.就双字结构来说,“后来”是高度隐含的习语,相当于“以后跟着来的/这以后发生的”。“后来”有时在对现时、现实(而非过去事件)的描述或陈述中,作为话语标记语,起到的作用就是“还有呢/我还没说完呢/下一点”。“胡来”的“来”是万能动词,相当于“胡说/胡写/胡闹/胡唱/胡开玩笑”等,以图省力、含糊、随便等语效。B.看三字结构的一例“来不得”和“来复枪”。前者似乎可改为“不得来”,但意思不同。“不得来”是禁止“来”,“来不得”往往后续名词短语,如“来不得半点含糊”,相当于“半点含糊都是不允许到来的”,可见所求为省力、含糊和生动的语效。“来复枪”是对英语单词rifle的拟音,与“步枪”相比,具有陌生化(异域风情)的味道。试想,我们若改说“说起来像‘来复(枪)’其实是步枪的一种的那种常规武器”,该多么费力!C.四字结构的例子“来而不往”中的“来”和“往”什么省而不说,相当于“你给我什么东西/态度我就却不给你同样的东西/态度”,所得为省力与生动的语效。因此我们常说“有来有往”(指礼物等合意的事物,或表示揍/骂一顿这样的不合意的事物)、“有来无往非礼也”,甚至进一步紧缩为“来往”。“卷土重来”的“来”和“来”的事物已经隐喻化了,“来”有时是“去”,但不习惯说“卷土重去”。D.六字以上结构都与四字结构相似。
12)“来”的连动式(见§3.8)若表示虚拟空间的移动,如例(59)的“……打骂孩子来出气”,偏离了质准则——这里的“来”已经不是真正的“来”了,相当于“以便/以图/是为了”。该用法受制于隐喻/转喻机制和最省力原则。须注意的是,“来”这个“焦点标记词”用于(母)构式(构式1)“VP1+(NP1)+来 +VP2+(NP2)”还是用于(分)构式2“PP+(NP1)+来+VP+(NP2)”是有区别的:一般来说,构式1的焦点为“来”后成分,构式2的焦点为“来”前成分。
5.结语
传统语义学一般用“辐射型、连锁型”来解释词义的变化。认知语义学的著作则从泛隐喻的角度把词义的诸多变化当作隐喻化思维的手段和产物。有些认知语言学理论家有时讨论词语的语法化问题,即由实到虚的发展,如“在,为”的动词向介词的过渡。我们发现,除此以外,应该对词语意义变化的理据作一些解释。词语是死的,词语使用者是活的,他们组词造句总是要实现语用目的的,而为了实现千差万别的语用目的,他们就不得不活用有限的词语和词义,于是派生出种种有标记的用法。上文对“来”的有标记用法作了初步探讨,有些问题还有待深入研究。上面的分析很大程度上也适用于对“去/come/go”甚至“吃(饭、父母)、打(小孩、字)、唱(戏,哪一出)”等字词的考察。
还要说明一点,“来”与“去”虽然互为反义词但常常是不对称的[“来一斤牛肉”和“去(了)一斤牛肉”是很不同的],同样,“来/come”、“去/go”也常常是不对称的(表示虚拟空间移动的“来/去”与英语的come/go有时相通相同而有时却相差甚远,如“来往”与come and go)。此外,“来/去/come/go”的肯定与否定也常常是不对称的。如,“来得容易,去得容易。/Easy come,easy go.”是谚语,而改为否定式还是谚语么?
下面看看李行健等(2004:777)的两个“来”“用在诗歌、叫卖声里作衬字”的例子。可见“来”不能改为“去”,不能译为come,当然也不能译为go,而且肯定不能改为否定。
(62)“二月里来呀,好春光。”(歌曲专辑《茶山情歌》的歌曲“二月里来”的歌词)
(63)“磨剪子来抢菜刀。”(现代京剧《红灯记》台词)
以上对“来”的分析尤其是§4(“来”的语用化概述),基本沿用了Wilson(2004)创导的“词汇语用学”(lexical pragmatics)的基本思想和思路,对“来”(类)构式(没有涉及淮南话、山西话、上海话等方言特殊的“来”)进行粗浅的认知语用探究,以求教大方。
[1]Grice,H.P.Logic and Conversation[C]//P.Cole & J.Morgan.Syntax and Semantics,Vol.3:Speech Acts.NY:Academic Press,1975:41-58.
[2]Haiman,J.Natural Syntax— Iconicity and Erosion[M].Cambridge:CUP,1985.
[3]Levinson,S.C.Pragmatics[M].Beijing: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CUP,2001(1983).
[4]Miller,G.A.& Johnson-Laird,P.N.Language and Perception[M].Cambridge:CUP,1976.
[5]Sperber,D.& D.Wilson.Relevance: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M].Beijing: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Blackwell,2001(1995).
[6]Talmy,L.Lexicalization Patterns:Semantic Structure in Lexical Forms[C]//T.Shopen.Language Typology and Syntactic Description, Vol. III:Grammatical Categories and the Lexicon.Cambridge:CUP,1985:57-149.
[7]Wilson,D.Relevance,Word Neaning and Communication:The Past,Present and Future of Lexical Pragmatics[J].Modern Foreign Languages,2004(1):1-13.
[8]Zipf,G.Human Behavior and the Principle of Least Effort[M].Cambridge:Addison-Wesley,1949.
[9]陈前瑞.“来着”的发展与主观化[J].中国语文,2005(4):308-319.
[10]董晓琨.焦点标记“来”[J].世界汉语教学,2006(2):20-30.
[11]端木三(美).重音、信息和语言的分类[J].语言科学,2007(5):3-16.
[12]干红梅.再谈“来着”[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5):61-65.
[13]何兆熊等.新编语用学概要[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14]侯国金.语用标记理论与应用:翻译评估的新方法[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a.
[15]侯国金.语用标记价值论的微观探索[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b.
[16]侯国金.语用学大是非和语用翻译学之路[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
[17]侯国金,张妲.假指令句[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2(2):17-20.
[18]李明.趋向动词“来/去”的用法及其语法[C]//林焘.语言学论丛(29).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291-313.
[19]李行健等.现代汉语规范词典[Z].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语文出版社,2004.
[20]梁银峰.汉语趋向动词的语法化[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7.
[21]刘丹青.汉语中的框式介词[J].当代语言学,2002(4):241-253.
[22]刘慧.动词后“来/去”充当的趋向补语与宾语的语序问题[J].语言应用研究,2011(2):46-48.
[23]刘兴策等.现代汉语双序词语汇编[Z].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
[24]刘月华等.用现代汉语语法(增订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25]唐秀伟.动词前“来/去”考辨[J].北方论丛,2010(4):63-65.
[26]王国栓.“来+VP”“VP+来”两格式中的“来”[J].南开语言学刊,2005(1):165-172.
[27]王丽彩.“来”、“去”充当的趋向补语和宾语的次序问题[J].广西社会科学,2005(4):155-156.
[28]王寅.象似性原则的语用分析[J].现代外语,2003(1):2-12.
[29]文旭.运动动词“来/去”的语用意义及其指示条件[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7(2):91-96.
[30]辛承姬(韩).连动结构中的“来”[J].语言研究,1998(2):53-58.
[31]邢向东.陕北神木话的话题标记“来”和“去”及其由来[J].中国语文,2011(6):519-526.
[32]张爱玲.“看来”的主观化[J].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7(3):384-89.
[33]张全生.从“来”的语法化看焦点结构与焦点标记的产生[J].语言科学,2011(6):618-628.
[34]张谊生.概数助词“来”和“多”[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3):80-84.
[35]赵志清.再谈“来着”——基于语料库的考察[J].临沂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10(2):90-94.
[36]朱德熙.语法讲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37]左双菊.“来/去”带宾能力的优先序列考察[J].汉语学习,2007(4):71-78.
[38]左双菊.“来/去”语义泛化的过程及诱因[J].汉语学习,2011(3):59-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