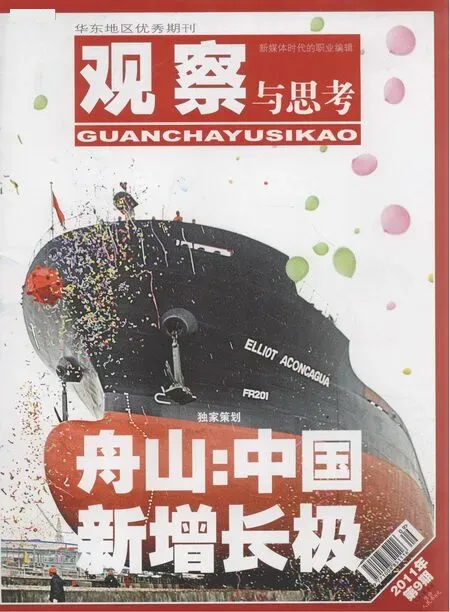基于社会心理视角的网络谣言成因分析
□ 王锁明
基于社会心理视角的网络谣言成因分析
□ 王锁明
近年来,通过网络介质传播的、未经证实的却又似是而非的各种谣言时有发生,严重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引起社会的恐慌,已成为当前我国社会各界较为关注的一大话题。从社会心理的视角来看,网络谣言是多种社会心理因素的综合所致。探讨网络谣言产生和传播的社会心理因素,对于我们及时把脉社会情绪,加强社会心理建设,提高网民素质,形成良好文明的网络环境,从而有效预防和治理网络谣言具有现实意义。
谣言 网络 成因 社会心理因素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营造良好的网络环境,必须加大对网络谣言的防治力度。而要有效防治网络谣言,我们首先必须深挖网络谣言产生和传播的原因,如此才能真正遏制其蔓延。而对于网络谣言的探讨,无论是其成因还是防治,都是不能忽视社会心理因素的。如果离开或无视其中的社会心理因素,那将是片面的、不完整的。本文中,笔者拟从社会心理因素的视角来探讨网络谣言的成因问题,以期对预防和消解网络谣言有所裨益。
一
在中文语义中,谣言往往是“没有事实根据的传闻,捏造的消息”①夏征农主编:《辞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第458页。,是凭空想象或根据主观意愿编造的传言。谣言作为一种舆论现象早已存在,通常将制造谣言的行为称作“造谣”,将传播谣言的行为称为“传谣”,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社会情绪、社会心态和社会透明度等方面的特征。例如,“2008年我国发生的贵州瓮安事件、四川柑橘事件等,从事件发生之初的谣言盛行到事件结束的谣言平息,诸多公共事件里可以说是谣言在扮演着公众解读事件始终的晴雨表的角色。”②陈万怀:《传播学视角下网络谣言的认知与消解》,《新闻界》2008年第6期,第50页。而互联网的发展,则使谣言找到了最便利的发展平台。事实正是如此,近年来网络谣言常有发生。
所谓网络谣言,一般是指利用互联网平台,通过网络介质(如博客、微博、BBS论坛、社交网站、电子邮件、即时通讯工具等)传播的、未经证实的却又似是而非的传言。它主要涉及公众感兴趣的或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信息,其中既有针对公民个人的诽谤,也有针对公共事件的捏造,例如,公众人物的日常工作、家庭生活、人际交往,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日常公共活动,公共突发事件的原因、伤亡情况、处理进展等。与口头谣言相比较,由于网络的传播速度快、信息量大和覆盖面广,所以当谣言和网络结合起来形成网络谣言时,其舆论影响力和社会危害性就大大增强了。作为一种畸形舆论,网络谣言严重扰乱人们的思想,败坏网络信誉,会引起社会的恐慌。如果处理不当,极易破坏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健康的舆论氛围,因此必须坚决予以遏制。
目前,学界对网络谣言成因与防治的研究,大多是从政府部门监管、法律法规处罚、网络媒体责任和普通网民自律等方面展开的,而从社会心理因素层面进行探讨的并不多见或语焉不详。然而一个基本的事实是,网络谣言的传受主体是普通网民,他们的心理状态必然影响到网络谣言的接受和传播,所以在探讨网络谣言产生与传播的原因时,如果离开了社会心理因素的作用,那么“谣言止于公开”、“谣言止于法制”和“谣言止于智者”等就不能很好地发挥其应有效应。而从社会心理因素的视角来探讨网络谣言的成因,那必将有助于把脉社会情绪的走势,加强社会心理建设,提高网民素质,培养健康心态,消除网络谣言得以产生的“市场”,阻止它在社会上的扩散与传播,从而将其负面影响降到最低程度。
二
从广义上讲,社会心理不仅是我们探讨网络谣言成因必须考虑的一个因素,而且也应该成为我们分析网络谣言成因的一个崭新视角。概括起来,笔者以为导致网络谣言产生和传播的社会心理因素主要有十种:
一是娱乐心理。在当今网络时代,快节奏的生产、生活使得人们的日常生活单调乏味,而八卦谈资则可以让这种平淡生活充满刺激、增添情趣。可以说,现实生活中有些人在网上传谣纯粹是出于一种娱乐心理。有研究者就这样说过,“为什么会传谣?因为相信谣言是真的,或者认为传谣好玩,无害,为娱乐而传播它。”①张勇军:《对控制网络谣言的探讨》,《管理与财富》2009年第4期,第152页。这种出于娱乐心理而传谣的,大致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少数人有意迎合部分网民的娱乐心理,编造一些所谓的事实真相,不择手段地抢“眼球”,以吸引“粉丝”关注,为自己的博客或微博增加点击率或浏览量;另一种情况是有的网民只是觉得网络谣言好玩而不考虑对他人的伤害,听风就是雨,胡乱编造一些娱乐性消息到处乱传,致使网络谣言快速传播和扩散。
二是猎奇心理。网络谣言之所以能传播开来,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利用了一些网民求新、求奇和求异的心理特点。一般来说,公众人物、影视明星的私生活和“高层”人士的有关“秘闻”常常是网上谣言的一大主要话题,而谣言制造者正是抓住人们的这一猎奇心理,迎合一些人捕捉“阴暗新闻”的不良嗜好、低级趣俗,将道听途说来的消息,在未经核实的情况下编造故事或花边新闻,炮制一些公众人物、影视明星和“高层”人士的香艳丑态、小道消息,利用互联网这一特殊渠道加以发布和转载。这在主观上虽无多大恶意,但在客观上却产生了不良影响,造成各种传言充斥网络的不堪局面。
三是怀疑心理。网络谣言之所以产生和流传,也是与权威信息的缺失、滞后或模糊,从而导致网民对公开的、官方的信息不信任有很大的关系。在现实中,网民因不信任权威信息而传谣的有三种情形:一是有的地方政府部门对突发事件的处理,让网民产生较差的心理感受,增强了他们对政府部门的不信任感,甚至使他们更倾向于相信谣言,谣言借机散布开来;二是长期以来,一些传统媒体以报喜不报忧或少报忧的方式对突发事件进行信息处理,使其在相当一部分网民中的信任度被“大打折扣”,同时也伤害了传统媒体的公信力,以致当重大事件出现后,一些传统媒体出面澄清网络传言时,公众却对这种澄清持普遍的不信任态度,有的甚至还从反面进行解读;三是一些不合理、不公平的社会现象不仅没有及时消除,还长时间地存在,所以一旦有谣言出现,相当一部分网民的态度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有的还主动参与到传谣的行列中来。正是上述的种种不信任心理,加剧了网络谣言的传播,使之从局部延伸到无限的虚拟空间而不断地扩散和蔓延。
四是较真心理。网络谣言的盛行,也是跟政府部门对消息的发布与民众对信息的需求存在比较大的供求矛盾分不开的。近年来我国在推进政务公开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在处理疫情灾情、群体冲突等突发事件方面,政府信息公开机制尚不健全,信息公开迟滞现象时有发生,广大群众不能及时全面了解突发事件的真实情况,但他们内心又迫切地希望了解事件的真相,而此时有关部门却不是及时发布信息,反而是沿袭惯性思维,习惯于封锁消息,以致官方信息渠道不畅,而各种网上传言“满天飞”。“大道不走小道走”,这种教训在现实中并不少见。在某种意义上,人们已将网络传言视为“倒逼”事件真相的一个主要途径。大量事实表明,网络谣言往往是基于一定的事件,尤其是一些重大突发事件而形成的,当这些事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而权威信息却不作为或作为不够,这在无形中就给网络传言提供了生成条件,并为其传播、泛滥预留了舆论空间。可以说,你越是“捂盖子”,越是不敢讲、不愿讲,就越会给人有“猫腻”感。网络谣言的产生和事件的重要性与模糊性成正比关系,也就是说,事件越重要而且越模糊,网络谣言产生的效应也就越放大。为此,政府部门应将公开透明作为常态,及时满足公众的知情权,从而走出那种“事发-隐瞒-瞒不住-流言四起-被迫公布真相”的尴尬局面。
五是恐慌心理。在社会转型期,网络谣言迎合了转型期一些人内心的不安全感。事实上,一些网络谣言就经常依存于一些重大的突发事件,如瘟疫、地震、食品安全、世界末日等灾难性事件。众所周知,这些事件往往与每个网民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因而在面临突发性的危险事件时,人们本能的应激反应便是震惊和恐惧,如果此时主流渠道的权威信息缺失或模糊,那么势必将导致一部分网民遇事朝较为担忧的方向考虑,对突发事件的进程产生种种不好的猜测,强化对相关网络谣言的依赖程度,进而加剧他们的不安全感和恐慌心理。于是,在这种个体生命随时受到严重威胁的极度恐慌的状态下,他们便会不加思考、不去深究,仅凭自己的主观臆断,轻信各种非正常渠道的信息。例如,近年来食品安全事件频发,就使得公众对食品安全的信任度大大降低,也为一些网络谣言的产生、蔓延创造了条件。
六是焦躁心理。从社会心理的视角来看,大多数当代人或多或少存在精神隐疾,而在某个临界点都有可能激发起内心灰色的一面。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的凸显期,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许多前所未有的风险和挑战,其不确定性大大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很难为自己的未来制定出清晰的、准确的预期,这就难免会在心理上、在思想上产生迷惘、急躁和焦虑心态,进而衍生出怀疑、猜忌、不满和攻击等负面情绪,而在虚拟的、身份隐蔽的网络空间,这些情绪极易酝酿膨胀而成为一些网络谣言的诱发因素。由此可见,网络谣言的滋生与蔓延,与现实生活中人们的某些焦躁情绪有着直接的关联。当然,这些因素并不是谣言产生的主要原因,但却是谣言大范围传播和蔓延的社会心理基础。
七是盲从心理。在现实中,有些网络谣言一定程度上迎合了人们的某种心理预期,因而人们愿意相信它、传播它。此其一,其二,“网络谣言的扩散往往与一些网民以感性的姿态,对谣言缺少理性思考的跟风紧密相关。”①白树亮:《网络谣言成因及治理对策研究》,《新闻界》2010年第4期,第83页。事实上,有些网民的认识不够高、警惕性比较差,在很大程度上还存在着“随大流”的思想意识,他们对待传言缺乏基本的分析和判断能力,往往不问是非曲直就随声附和、信以为真,一味地从众。如果说历史上许多谣言的产生和传播,大多是基于迷信或无知,那么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一些网络谣言的滋长,更多的是打着“科学”的旗号,利用大多数群众对科学知识的盲从来实现和表现出来的。例如,近年来伴随着冰雪、旱涝和大地震等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有的人将这些灾害的原因归结为日月食、流星雨等正常的天文现象并搬上网络世界,这极有可能俘获那些科学知识有限而迷信思想浓烈者的“芳心”。
八是侥幸心理。互联网作为一种特殊的生活交流空间,其开放性、自由性是前所未有的,但同时也伴生着相当的隐藏性和匿名性,匿名、自由和交互性强的特点为网民隐藏了身份,因而有些网民就把网络视为纯粹的虚拟世界,更是把在网络环境中发布、传播不实信息当成自己的言论自由,认为自己的匿名身份不需要承担任何社会责任和现实后果;再加上有效制裁和责任追究网络造谣和传谣的难度大、成本高,这在客观上也助长了网络谣言的滋生和蔓延。可以说,网络谣言之所以形成并迅速扩散开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与不少网民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道德缺失、行为失范的情况有关,他们在认知观念上存在偏差,抱有“法不责众”、“法不罚众”的侥幸心理,因而一遇到网上某些刺激性信息的挑逗,他们便图一时之快,穿着隐身衣、戴着假面具,跟风而上、围观起哄,甚至以参与传谣为乐趣。虽然这部分网民并没有蓄意制造什么谣言,但却无心地传播了流言蜚语,所以他们在谣言的传播过程中扮演了实际上的直接责任者角色,在很大程度上起了极其恶劣的负面作用。
九是宣泄心理。在现实中,极少数对社会某一现象、某一群体有不满情绪的个体,他们的心态原本就不正常,而网络提供的人人握有“话筒”、人人可当“发言人”的角色便利,使他们实现了由纯粹的“受众”向“传者”的身份转变,因而当他们一看到或听到某些不合理、不公平的事件或问题,就紧抓不放,利用公众的猎奇心理将事件“添油加醋”、扭曲放大后搬上网络,误将网络视作其个人发泄情绪、表达不满和诋毁他人的“暴力工具”。这具体来说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发布谣言者平时与他人有纠纷或矛盾冲突,但他们法律意识淡薄,总想着如何报复他人,而网络的隐匿性则提供了他们对他人贬低或人身攻击借以发泄私愤的好机会;第二种情况是某些人出于仇官心态,于是就在网上放大一些领导干部在作风和工作态度上的问题,捏造一些领导干部的性丑闻或贪污受贿等假新闻以吸引“眼球”;第三种情况是一些人对当前转型期出现的社会问题有负面情绪,却又“很难在社会舞台上找到被主流文化认可的表达机会、宣泄途径、减压方式和释放场所,从而处于一种‘欲说还休,欲罢不能’的境地”①段兴利:《网络意见领袖的产生、特征及培养》,《科学·经济·社会》2010年第3期,第79页。,因此一旦有网络传言触发这些人的不满情绪共鸣时,他们就通过对网络谣言的参与、传播而趁机宣泄自身的负面情绪,表达自己对现实中一些现象的不满。
十是挑拨心理。如上所述,当下我国正步入改革攻坚期、社会转型期和矛盾凸显期,改革发展中诸多不可预知的矛盾越来越集中出现,而此时公众的焦虑情绪、激进思想也日益显现出来。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伴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步入快车道,对之国际社会不乏肯定者,但也有一些极不友好人士竭力“矮化”、“丑化”中国的国际形象,他们企图遏制我国的和平发展。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为网络谣言的产生提供了社会土壤。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一些境外敌对势力和境内极少数别有用心者趁机作乱、浑水摸鱼,他们借助互联网,利用我国在改革发展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炒作热点问题,夸大、扭曲和捏造相关事件,使之成为激化社会矛盾的“催化剂”,借以煽动群众的不满情绪,挑拨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制造社会混乱,以期实现其不可告人的政治图谋。
三
由上可见,导致网络谣言产生和传播的社会心理因素是复杂多样的,无视或夸大这些社会心理因素的作用既是片面的,也是有害的。在这里,我们通过对导致网络谣言产生和传播的社会心理因素进行探讨和分析,旨在呼吁在大力加强经济政治层面建设、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所普遍关心的现实重大问题的同时,还需要努力推进社会心理文化层面的建设,“加强网民媒介素养教育,提高网民针对网络信息的思考判断能力”②,强化其责任意识、担当意识和自律意识,弘扬社会正义,形成文明良好的网络环境,以有效规避网络谣言的危害。这对于我们正确认识网络谣言的产生与传播,以疏导公众的负面情绪,营造惩恶扬善、明辨是非的社会氛围,促进社会舆论的健康运行,从而确保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发展都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王锁明,男,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南京 210093)。
责任编辑:徐友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