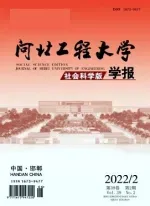和谐视域下孔孟仁爱思想与当代人精神家园的找寻
张 明
(中共辽宁省委党校 党建教研部,辽宁 沈阳 110004)
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的社会意识形式,是系统地、自觉地反映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的思想体系。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意识形态大厦的根基,对当时的社会和谐稳定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也构筑了无数中国人的精神家园。“仁爱”是孔孟及儒家思想文化基础和精髓,影响了中国历史几千年文化的走向。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和市场化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人们精神家园的分裂和失衡,如何帮助更多的人们找寻到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是意识形态建设中面临的突出问题。我们对孔孟仁爱思想的扬弃继承和大力弘扬,是传统文化的现代创生,也是建构当代人精神家园不可或缺的人文资源。
一、“仁之心”与“爱之举”:孔孟仁爱思想的理论阐释
(一)总结与奠基:孔子的仁爱思想
“仁”在孔子之前的诸多典籍中就有零散的、不系统的论述,孔子对仁作了理论的概括和升华,形成了儒家思想的核心与精髓。孔子的仁学具有爱人、敬、宽、信、敏、惠等诸多内涵,但仁爱思想则是孔子仁学之最基本含义。“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仁者莫大于爱人”(《论语·雍也》)、“君子学道则爱人”“恭,宽,信,敏,惠……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论语·阳货篇》)。由于孔子提倡“仁礼并重”,所以他强调的“爱”是有等级贵贱、亲疏远近的差别之爱,但他也强调“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修己以安人”(《论语·宪问》)、“节用而爱人”(《论语·学而》)、“宽则得众”(《论语·尧曰》),可以说时代的局限性并没有掩盖孔子爱“人”的广泛性中蕴含的人本主义和人道主义光辉。
孔子注重仁爱思想的理论建构,他的仁爱思想立足于修身——“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完善主体的“仁爱之心”;“爱人之举”集中体现在血缘亲情之中——“亲亲”、“爱亲”,推衍到亲情之外——“爱人”、“泛爱众”(《论语·学而》)。他用“克己修身”的君子人格、血亲之内的“家族之爱”、血亲之外推衍出的“天下大爱”,共同构筑了“身、家、国和天下”多维一体的价值系统,揭示了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奠定了家国一体的德性主义理想的追求传统。
孔子仁爱思想的践行主要通过“忠恕之道”实现的。“诚心以为人谋谓之忠”(《论语正义·学而》),也就是说“忠”要诚心诚意主动地与人为善、爱人以德。“推己心以及人,要如己心之所欲者,便是恕”(陈淳《北溪字义》),也就是说“恕”要推己及人、“以己之心度人之心,以及量人,设身处地”[1]p67。“己欲立立人,己欲达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孔子“忠恕之道”的高度概括,并作为内在精神原则指引和规束着无数人们进行着爱的秉怀与布施。
孔子在仁爱思想系统的奠基之初,便提出“克己修身”是为了更好地去爱他人、爱天下,爱人也是为了更好地完善自己的人格从而达到仁爱的完美境界,二者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经过后继儒士的丰富完善,“修身爱人”的思想体系既为人们提供了“人伦日用”的现实此岸效用,又具有了“安身立命”的终极彼岸价值,进而共同构筑了传统社会无数人们的精神家园。
(二)继承与发展:孟子的仁爱思想
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仁爱”思想,在肯定“仁者爱人”的基础上,对仁爱的合理性进行了论证和哲学层面上的阐释。也就是说,在承认“人应该仁爱”的前提下,对“人为什么能够仁爱、仁爱实施的现实可能性”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仁,人心也”(《孟子·告子上》),与孔子相比,孟子更“重内轻外”、 专注“心性”,倾力探求存心养性之道。孟子的仁爱思想是把“性善论”作为逻辑起点的,“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人先天具有道德善性,它蕴藏在人的“四心”中(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孟子把“仁爱”之心归于人之天性,为人们自觉践行“仁爱”提供了合理的人性基础。
孟子的仁爱思想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情感修身”,另一部分是“践行爱人”。“情感修身”就是对自己进行道德情感的自我修养、磨练和完善,使之具有践行仁爱的情感基础和能力;“践行爱人”就是在实践中用什么样的方式和途径真正把仁爱施于他人,普爱天下。
在修身上,孟子首先注重开发和培植人的自然情感——“恻隐之心”,也就是人作为类存在对他人不幸和痛苦所具有的悲悯、体恤、不忍、怜爱情感。“恻隐之心”的存在是“仁爱”产生的本原和根据,人们要善于守护和充分扩展并笃实践行这种爱的情感,这才能使仁爱的实现成为可能。经由孟子的阐释,“恻隐之心”不仅成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能情感的表达,而且成为人存在的精神需要和价值确证之一。在培养“恻隐之心”基础上,孟子进一步提出修身的高层次要求——“与人为善的爱人情怀”,“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孟子·公孙丑上》),也就是说作为一个有道德的人除了同情怜悯别人的不幸外,也要有伸手援助的爱的情怀,这是道德情感表达和人性提升所不可缺少的情感积淀。如果把心怀“恻隐之心”归于人的情感本能的话,“与人为善的爱人情怀”则是出于人们理性的思考和道德的自觉。此外,孟子也把“修、齐、治、平”作为人生价值的理想追求。由于把人生目标出发点建构在仁爱基础上,所以终极的“平天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就是“爱天下”,即“爱亲人、爱他人、爱天下”大同理想的实现。为了实现仁爱的人生远大理想,孟子又提出了应具备“浩然之气”的“大丈夫”品质,“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孟子·尽心上》),“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谓之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这些人格修养和优秀品质是仁爱终极理想得以实现的必备条件和有效保证。
在仁爱的践行上,要求把同情、不忍、怜爱等情感积淀施于他人,把主体的仁爱精神外化和对象化。孟子把仁爱的推行寄于三大环节——“爱亲”、“爱人”、“爱物”,“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亲亲”是仁爱的基础和出发点,由于父母与子女间的生育、抚养与敬顺、赡养关系,兄弟姐妹间的一母同胞、朝夕共处的关系等,血缘纽带和血亲认同使“爱亲”成为人的自然本能之一,也是培植仁爱情感的摇篮;“爱人”是仁爱的中心和主体,是仁爱情感在纷繁社会关系中对“血缘围栏”的突破。孟子的仁爱思想并没有停留于“亲亲”的起点上,而是超越了血亲向外推衍开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继承了孔子“推己及人”的思想,孟子的仁爱思想中具有了更浓厚的“推衍意识”;“爱物”是仁爱的升华与超越,它标志着人的仁爱之心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层次和境界。“君子之于禽兽,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孟子·梁惠王上》)、“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孟子·梁惠王上》),人们的同情、怜爱之情不仅要爱亲人、爱人类,也应该尊重、保护、怜爱禽兽草木等与人的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之物。仁爱思想在物上的推衍不仅表明人们对自然规律愈加领悟和尊重,而且表明人的主体性与道德自觉性的进一步增强和提高。
孟子正是在仁爱基本精神基础上“爱亲”、“爱人”、“爱物”,通过“推己及人”、“推人及物”实现了三个环节的依次递进和相辅相成,进而也奠定了传统人性认同的“向内反求”的基调和天人合一的德性提升模式。可以说孟子是在仁爱思想基础上和仁爱大同理想的引导之下建构了其一系列伟大思想,也初步建构了中国传统伦理精神的雏形,影响了其后几千年中国文化传统的走向以及国民性格的形成。
二、“分裂”与“失衡”:当代人精神家园的“失和”现象
(一)人类精神家园的追寻
人类通过对客观环境的改造和自身生存状况的改善,逐步构建了人类的“物质家园”,与之相对,人类追求“真善美”以满足自身精神需要、改善精神存在状况的过程就是人类建构精神家园的过程。灵魂上的终极皈依、精神上的抚慰与庇护、快乐欲望适度满足后的愉悦、生存价值实现后的幸福感等都是人们建构精神家园必不可少的“木料瓦石”。
从人的个体层面看,人的精神完满实现主要有三个构筑来源:一是虚幻中“神灵”给予的——终极信仰的精神皈依,它来源于人们对超自然、超现实力量的向往和崇拜。二是交往中他人给予的——人际关系中的快乐、幸福感受,它来自于人际关系的和谐与亲情、友情、爱情等情感世界的完满。三是反思中自己给予的——道德情感的体悟和道德价值的实现。通过“内省慎独”对自己的德性善举给与肯定、赞扬,并由此产生对自我价值的认同与愉悦的心理反应。三个来源充实与否决定着一个人精神世界的完满与否,无数个体的精神追寻便决定了整个人类精神家园的和谐与否。
工业革命以来,现代化过程中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人们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同时,也导致了传统道德和正统文化被解构、人们精神家园迷失的消极后果。鲍曼在《后现代伦理学》提到“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强烈地感受到了道德模糊性的时代,这个时代提供了以前从未享受过的、选择的自由,同时也把我们抛入了一种以前从未令人烦恼的不确定状态”[2]p24。西方各国后现代文化的兴起和诸多现状昭示了“现代性”带来的精神阵痛,这种阵痛也开始困扰现代社会中无数人的心灵。
素养考查分析:这是一道数学应用题,综合考查了组合学、概率论、导函数、函数的单调性、函数的最值、数学期望等基本知识,以及运用组合公式、求函数的导函数,判断函数单调性、计算数学期望等基本技能.
(二)现代性分裂失衡的典型表征
在描述精神家园分裂与失衡现象之前,我们需要明确两个前提:第一,精神家园的分裂失衡现象不具有普遍性,不是当前人们精神状况的主流。第二,精神家园的分裂失衡现象虽然是一部分人的心理状态,但其现实和潜在危害是十分严重的。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也是人们观念思想的转型时期,传统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逐渐失去了对社会成员的影响力和约束力,而新的、“现代性”的价值观念和体系尚未得到共识和形成,从而使一些人产生了存在意义的危机,精神世界也出现了一些价值和道德的“真空”。
从人生终极价值和信仰的视角看:终极追求是人对现实和人本能性的超越,是人活着的价值和意义的终极追问。近现代以来,科学主义的兴起和对人性自由的急迫向往使“上帝死了”,宗教作为很多人精神皈依的家园渐渐被放逐;政治运动的挫折和自我价值意识的觉醒,使政治信仰成为“乌托邦”而渐渐被冷落;个性的自由解放和民主主义的疯狂呐喊,使道德的崇高被消解而不再被信奉和遵从。摆脱了种种“束缚”的人们赋予金钱、权力、美色以至高无上的价值,放纵地享受着“自由”。生物欲望满足后的快感、物质财富获得后的荣耀感、利益博弈得胜后的成就感,成为其价值实现的精神寄托。宗教信仰的丧失意味着人终极天国的失落,政治信仰的失去意味着崇高奋斗理想的消逝,道德信仰的虚无意味着人欲望堕落的狂欢。因为缺乏了信仰和终极价值的思索,人在自己的精神世界最终不能证明自己,只有通过外部刺激(金钱、权力、生理欲望)才能使自身意义和价值得以被自己意识到,所以为了保持自己的价值实现就必须不断地寻求外部刺激,主体存在的主动性渐渐丧失,而异化为膨胀欲望和外在客体的奴仆。“神性”的消逝,德性的丧失,“兽性”的本能放纵,诱发了人们精神家园的全面失落。
从现实人际关系的视角看:市场经济讲究竞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生物学的弱肉强食原则被很多人片面夸大成“人对人之间就像狼一样”、“他人即地狱”。面对彼此之间频繁的利益博弈,很多人在交往言行中战战兢兢,谨慎设防,更有甚者为了获利不惜违背良知、损人利己。人与人之间经常互相猜忌怨恨,彼此间缺少了最基本的真诚、信任和同情,多了几分冷漠与残忍。亲情、友情、爱情是一个人精神上的避风港和快乐的源泉,也是一个人精神家园的三根“擎梁之柱”,然而这些温馨港湾却被金钱物欲、功名利禄冲击得伤痕累累,很多人甚至发出疾呼:“这个社会真情到底还有多少?”高水平的物质条件被享受之后,并没有给人带来所期望的精神上的充裕与幸福,反而感到了更大的压力、空虚、甚至是痛苦。
从自我价值衡量标准的视角看:市场经济追求效益原则,“金钱至上”自然成为了很多人的不懈追求,这也逐步导致了人们价值衡量和评价标准的改变。在以往的自我价值评价时,人们往往注重“尽心知性”培养自己的道德情感,“修身养德”追求心灵的安宁无纷扰,其尊严感、荣誉感、成就感、愉悦感的实现被赋予了浓厚的道德内涵。但当前很多人的价值衡量标准被逐步扭曲,往往单一倾向于“钱挣多少、官有多大、房有多豪华、车有多高级”等直观物化的尺度评价,由于道德带给人的愉悦感受性大大降低,道德水平和境界的衡量标准被逐步淡化或剥离于人的价值评判系统。价值衡量标准的被扭曲带来两种后果:由于直观物质利益的价值地位的至高确立,一部分人成为被动的“道德失落者”,即为了经济利益和“自我价值”而表现出心口不一、言行不一、昧心行事,往往是行为过后承受着良心的拷问与谴责。他们不敢或不愿面对自己良知的审视,如愿以偿的快乐表面往往掩饰着一颗不快乐的心;另一部分人则成为了主动的“道德自我流放者”,即为了金钱财富、功名利禄不惜悖德损人,甘愿让自己的精神家园堕落沉沦——摒弃道德观念、拒绝道德评价和反思。但由于人的存在毕竟不是单一动物性的简单满足,也具有人性完善的高级精神需要——心灵需要呵护,精神需要寄托。抛弃了道德支撑的精神家园是空旷和摇摇欲坠的,食欲、性欲、权欲等直观地被满足之后仍会感到莫名的空虚,只有重新把自己暂时性地推入物欲横流中才能找到自我、确证自己活着的价值,实质上这是人精神家园丧失的最直接表现。
综上所述,虽然这些精神上分裂失衡现象不是普遍的,但其客观上大量的存在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为了弥合和消除这种“精神裂痕”,除了现实的体制完善等努力之外,应注重到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中去寻找妙药良方。
三、“弥合”与“重塑”:孔孟仁爱思想对建构“和谐家园”的现实价值
当代人精神家园的分裂与失衡实质上可以归因于“爱的殒落”,因为爱的终极追求的丧失和爱的情感的淡薄,纵容了欲望的放纵、消解了社会的道德规范、破坏了个体心理世界的平衡与人际关系的和谐,所以要弥合人们精神家园的“裂痕”必须从“呼唤爱的回归”入手,重塑当代人的精神家园。挖掘和丰富孔孟仁爱思想便是当代人建构家园不可或缺的人文资源:
(一)仁爱与“安心立命之所”的构筑
西方文化中终极价值问题往往归结于宗教信仰,而中国文化中的终极关心问题,是如何成德、如何成就人品的问题,无论贫富贵贱都是如此。这个成德的依据就是中国文化之动原,也可以说,中国文化中终极价值问题往往归结于道德信仰。
在孔孟“成德成圣”思想体系中,以“仁爱”为基础和纽带设立了一个“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错落有致而严密的精神系统。无论孔子的“仁者莫大于爱人”、“修己安人”、“泛爱众”,还是孟子的“仁者爱人”、“亲亲、仁民、爱物”都是对人的生命价值意义的追寻与内在超越,而不在于追求外物。孔孟仁爱思想把个人价值的实现与社会价值实现完美地结合起来,个人“成德或成圣”的修为是出发点,造福社会“爱天下”是终极。“修身、齐家、平天下”可以转化成“爱己、爱亲、爱天下”,三者之中,任何一个都可以是奋斗目标的终点,也可以是迈向下一目标的起点,无论走到哪一步回首反思都可以心有所得、心有所安:“修身爱己”则问心无愧,“齐家爱亲”则心安理得,“博爱天下”则心满意足。孔孟的仁爱思想正是通过主体道德修养的内在超越,比较完美地解决了人生终极托付的问题。
(二)仁爱与“自我和谐”的培植
关于“和谐”,《左传·襄公十一年》中载:“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此处的“和”与“谐”是指协调和关系融洽的状态,这也蕴含了我们常说的“和谐”之主要含义:“和谐”是指在一个系统之中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相互作用、相得益彰使彼此关系协调,进而使整个系统运行达到相对稳定和平衡的良性状态。“人际和谐”、“人物和谐”是在人类社会大系统中,处理人类彼此关系、人类与非人类关系的一种理想状态。但其实现,本质上却可具体归结于各个人类个体“自我和谐”的实现,个体的精神世界内部的相对稳定和良性平衡便是“自我和谐”。大众消费时代和物化思潮的到来,使当代人的“自我和谐”面临了两个主要挑战——“欲望失控”和“心理失衡”。对孔孟仁爱思想弘扬完善,正有利于弥合“自我和谐”中的两道“裂痕”。
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竞争和利益导向使人们的心理平衡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仁,人之安宅也”(《孟子·离娄上》),“仁爱”情怀对人格完善和平衡心态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爱的基础上催发的“浩然之气”,使人“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具有良心上安全感;对自己“仁爱之心”的体会和肯定是对自我的精神鼓励和价值认同。同时讲仁爱的人往往是宽容的,面对失意、暂时的不公和冲突往往能坦然处之;讲仁爱的人往往又是理智的,能较好地调节好生活和工作中压力,很少一味攀比、牢骚满腹。所以这样的人能够经常保持心情舒畅和身体健康,心理平衡中是自我的和谐。
迷茫、彷徨、躁动的当代人所缺少和需要培植的正是这种“仁爱的情怀”,因为这是实现自我和谐的最主要途径,也是实现“人际和谐”、“人物和谐”的必要基础和前提。
(三)仁爱与“人际和谐”、“人物和谐”的实现
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冲突加剧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在此不再赘述。重在审视探讨孔孟仁爱思想对当代人 “人际和谐”“人物和谐”的实现有何现实意义。
“不忍之心”和“恻隐情怀”——处理“己他(它)关系”的情感基础。孟子强调“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皆有怵惕恻隐之心”(《孟子·公孙丑上》),怜悯同情之心是对他人(它物)的痛苦和不幸遭遇,在自己感情上发生共鸣而产生的悲怜、不忍和体恤的情感,是道德行为产生的情感基础和源头,也是维系人们精神世界的情感纽带。现代社会的利益导向和残酷竞争已不可避免,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却不是单纯的“弱肉强食”,也不是单纯的“经济交易”,而是超越利益的“爱的传递”;人与自然万物之间也不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而是协同进化、和谐共生的关系。当代人在内心深处拥有了浓厚的恻隐和慈悲情怀,才能真正铺就“人际和谐”、“人物和谐”的情感基石。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立人,己欲达达人”——处理“己他(它)关系”的思维方式和基本原则。“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孔孟仁爱思想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提出了“爱的要求”,更在于其推延的思维方式,也可称之为“换位思考”。“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要想得到别人的尊重和爱护,自己首先要去尊重和爱护他人;拓展到人与自然物的范畴便是:人要想得到自然的恩泽使自己受益,人就必须尊重自然的固有规律、爱护保护自然。此外,“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立人,己欲达达人”也包含了“不伤害”和“双赢”的意蕴。在日常交往之中,自己不希望被伤害所以就不要去伤害别人,自己要获利收益也要让别人获利收益,以实现利益的双赢;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上,人类不想受到自然规律的惩罚,就要尊重自然、爱护万物。自然万物得到了休养生息和欣欣向荣,人类也会从自然中获得更多的收益,也达到了人与自然的双赢共生。这种思维方式和基本准则是当代人达到“人际和谐”、“人物和谐”的前提和重要保证。
“修己以安人”和“与人为善”——处理“己他(它)关系”的价值升华。“修己以安人”,“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孔孟仁爱思想价值取向立足于“自己”,却追求“爱他人”。“安人”就要关心他人的生命健康“安全”,通过自己的德行善举使他人的生计得以“安顿”抚慰,使人际关系得以“安宁”和谐;“与人为善”则要求宽容善待、伸手抚恤他人,给深处痛苦和不幸中的人以真切的关怀和抚慰,使之摆脱痛苦与困境、得到温暖和看到希望。当代人面对残酷的利益博弈和个人享乐思潮的考验,应该有超越欲望本能的勇气和毅力,怀有“安人”、“善人”,甚至是“善物”的价值追求。人与人之间不仅存在利益交易关系,更应该是道德情感的共融。这不仅有利于个人的道德修养和人格完善,更有利于缓解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冲突,促进“人际和谐”与“人物和谐”状态的实现。
“爱的殒落”使当代人的精神家园出现了分裂失衡,所以发掘和丰富仁爱思想的现代价值是弥合人们精神裂痕、重塑精神家园的明智选择。
[1]肖群忠.道德与人性[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
[2][英]齐格蒙特·鲍曼.后现代伦理学[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