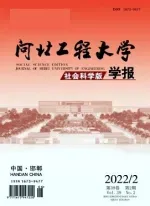晋察冀叙事诗的史诗意义探讨
孟文博,丛 鑫
(1.山东大学 威海分校,山东 威海 264209;2.燕山大学 文法学院,河北 秦皇岛 066004)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晋察冀显然代表着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和政治场域,从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到1945年抗战胜利,这里一直都是抗日的前沿,战争中血与火的浇灌使这里生长出的艺术之花呈现出与其他历史时期与政治场域迥异的美学特色,而在这些艺术之花中,有“一丛奇葩”特别引人注目,那便是以田间、邵子南、史轮、曼晴、邓康等为代表的战争诗歌创作,尤其是其中的战争叙事诗,真实而又生动地记述了壮烈的战争场面以及战争参与者的精神风貌,同时具有着很高的的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显现出一种特殊意义上的史诗性特色。
一
自十九世纪末中国人开始被迫睁眼看西方之时,无论是诗人还是学者,都产生了一种“史诗情节”。梁启超参照荷马、莎士比亚、米尔顿等人的史诗之后感叹其“动亦数万言,伟哉!勿论文藻,即其气魄,固已夺人矣。”[1]而王国维则在对比西方史诗后批评中国古代诗歌:“咏史怀古感事赠人之题目,弥满充塞于诗界,而抒情叙事之作,什伯不能得一”。[2]“接受一种文学形式,同时意味着接受其蕴含的文化精神与审美趣味”。[3]第一代学贯中西的知识分子的文学“自卑”其实正代表了他们对民族精神的审省与焦灼,因此,呼唤创作“雄浑”、“刚健”的“国魂文学”便成为当时文化精英的共识。1937年,全面抗战的爆发为实现这种“共识”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契机。在度过抗战伊始“性急地向民族战争所拥有的意识形态或思想远景突进”[4]的文学创作激情期后,诗人们深切的感到“伟大民族革命的时代,必须有伟大的民族革命的史诗”[5],于是从沦陷区到国统区,长篇宏制式的诗歌创作开始纷纷涌现,这些长篇诗歌的出现可以说开创了诗歌创作史上的新纪元,但它们却并非都是经典之作,当时有诗论家就曾批评说:“目前许多长诗,是有着许多没有‘诗’的——不足以表现诗的情绪和意境的空疏的语言,和没有生命的形象,杂芜其中,于是变成一首很长很长的‘长诗’。这好像未淘过的一堆矿砂,里面的金子只是几粒,而沙子却是一大堆。这毛病是诗人企图把情感扩张,可是他的感情只有一点点。……结果,本来可以写成很动人的诗,也变成贫血的没有生命的苍白的语言了。”[6]这样的“长诗”恐怕很难被认作真正意义上的“史诗”。
黑格尔在其《美学》中对“史诗”有着这样的界定与论述:“史诗以叙事为职责,就须用一件动作(情节)的过程为对象,而这一动作在它的情境和广泛的联系上,须使人认识到它是一件与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的本身完整的世界密切相关的意义深远的事迹。所以一种民族精神的全部世界观和客观存在,经过由它本身所对象化成的具体形像,即实际发生的事迹,就形成了正式史诗的内容和形式。”[7]因此,“一般地说,战争情况中的冲突提供最适宜的史诗情景,因为在战争中整个民族都被动员起来,在集体情况中经历着一种新鲜的激情和活动,因为这里的动因是全民族作为整体去保卫自己。”所以,“只有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战争才真正有史诗性质”。[8]具体到史诗的创作上,黑格尔非常强调诗人对他创作题材的熟悉,他说:“诗人必须完全熟悉他所描述的情况,关照方式和信仰,对他基本上仍是现实的题材只须提供诗的意识和描述的艺术。”[9]“真正的史诗作者……对所描述的世界,从在个人内心中起作用的那些普遍力量,情欲和旨趣到一切外在的事物,却都要了如指掌。”[10]黑格尔是在研究了大量西方经典史诗之后得出上述观点的,对照他的观点,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无疑是中华民族史诗书写的最佳题材,而作为这场战争的亲历者,晋察冀诗人又无疑具有无可比拟的创作优势,他们曾真切的长期置身于战斗生活之中,和战士们一起冲锋陷阵,和后方群众一起支前劳军,他们的心跳与那个炽热时代的强烈脉动同步,他们本身就是坚毅不屈“民族精神”的组成部分,他们的真实经历与情感凝聚成为一首首的叙事诗,生动记述了“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的本身完整的世界密切相关的意义深远的事迹”,具备了“史诗性”的基本内涵。
自然,晋察冀叙事诗多为中短篇创作,不符合人们一般意义上理解的“史诗”均为鸿篇巨制的特性,但事实上,黑格尔也并没有把诗篇的长短作为“史诗性”的必然参考条件,他最强调的还是对一个伟大时代“民族事业”的记述和“民族精神”的弘扬,而当今也有学者在研究长篇小说创作的现状后指出人们对“史诗性”概念理解的偏颇,他说:“长篇小说的表现史诗性或者说获得史诗性,不但不一定要大部头,而且可以是精炼的小部头。所谓‘史诗性’,也应该有多种美学形态。既可以浓墨重彩气势磅礴,也可以精炼简洁温婉平和。”[11]由此可见,晋察冀的叙事诗也不应因其篇幅的短小而被完全排除在“史诗”范围之外。
二
黑格尔曾提出,正义的民族战争提供了一个“最适宜的史诗情境”,“用战争情况做史诗情节的基础,就有广阔丰富的题材出现,有许多引人入胜的事迹都可以描述,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英勇”。[12]而当时许多文艺家认为:“自从抗战开始以来,英雄慷慨的事迹,惊心动魄的场面,只要稍加注意,无时无地不是俯拾即是的。”[13]因此“现在我们亲历着的伟大的斗争,它本身就是一部雄伟壮烈的史诗。”[14]晋察冀诗人作为战争的亲历者,对战争中“英雄慷慨的事迹,惊心动魄的场面”有着最直观的感受,这些感受被凝聚在一首首叙事诗里,使其具备了史诗的最基本意义。
在这些叙事诗中最震撼人心的人物形象要算那些作战在第一线的英勇战士了。像邵子南的《模范支部书记》、《大石湖》,丹辉的《第七次》,曼晴的《巧袭》等,通过这些诗篇我们看到英勇的战士如何“到了正激烈战斗着的堡垒跟前,/让死亡突然降临在敌人的阵地。”看到战士直至牺牲都不放弃自己的枪:“人死了,枪还在,枪在就又打得响。”这些战斗多为诗人亲自参加,因此在叙事诗中表现的生动形象,诗人鲁藜认为:“战争是一切社会生活最复杂的最高级的运动,在伟大的抗战的十六月中,有多少血与肉、生命与意志构成的民族光辉的故事、场面与出现在这个战争里的民族英雄,新的典型呢?未来的伟大纪念碑的收获者,应该是在今天。”[15]晋察冀正是以叙事诗的形式树立起了雄伟的“纪念碑”,一方面真实揭示出当时真实的战争场景,一方面又展现了我军战士英勇无畏的战斗豪情。
晋察冀叙事诗中感人至深的人物形象还包括众多英勇不屈热情拥军的后方民众,像田间《下盘》一诗中为送公粮殒身的老人李和,《拜年》中慷慨劳军的李存山。曼晴《女房东》中那像“母亲般”慈爱的女房东,徐明《担架队进了村庄》“好象母亲安慰儿郎”一样照顾伤员的“老太太”。商展思《黎明之前》中为掩护伤员,亲手捂死自己的娃娃的村妇女主任王桂花。毛泽东说过:“战争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正是这些不甘做亡国奴的广大后方民众构成了人民战争的浩瀚海洋,他们是中华民族在危难时期的坚强脊梁,是保证抗战最终胜利的决定性力量。晋察冀诗人们饱含着深情把这些动人的事迹记入叙事诗,让我们能够在七十多年后触摸到他们炽热的胸膛和不屈的灵魂,真切理解那场伟大民族战争胜利的最终原因。
30年代中期,“战斗的小伙伴”田间带着他村野的粗犷和泥土的芬芳跃上诗坛,让胡风惊讶于“这些充满了战争气息的,在独创的风格里表现着感觉的新鲜和印象的泛滥的诗,是那个十七八岁的眼神温顺的少年写出么?”[16]然而胡风同时也承认,田间虽然是“创造自由诗体的最勇敢的一人”,但“他自己所创造的风格却还不免露骨的留着了摸索的痕迹,不能圆满地充分平易地表现出他底意欲的呼吸,他所能拥抱了的境地。”[17]真正促使田间转变提高的是抗战爆发后他来到晋察冀根据地的经历。正如作家孙犁所说的:这一时期“诗人从生活上接近了边区的新人物,促使他重新考虑他的形式。”[18]实际战争生活的洗礼让他“以时代的眼光来照耀出边区新的家庭和新的物之成长,以及群众怎样为保卫家乡和国而斗争。”[19]田间这一时期的叙事诗作如《下盘》、田间的诗作如《拜年》、《偶遇》、《山中》等,所表达的内容无一不是诗人亲耳所闻甚至是亲身经历,它们从一个侧面形象反映了诗人深度融入斗争生活,接受战争洗礼的过程。如胡风所论:“无论是诗人底创作欲求或他所拥抱的生活现实,都经过了而且在经过着战斗锻炼和思想锻炼的过程,因而他初期所追求的歌谣底力学终于得到了变质的结果,成了能够表现新的社会内容的美学的面貌,在作品上有些完成了浑然的旋律。”[20]因而“田间是第一个抛弃了知识分子底灵魂的战争诗人和民众诗人。”[21]而正是在这样的经历基础之上,田间于1947年创作出长篇叙事诗《她也要杀人》,成为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晋察冀的其他诗人们和田间一样,都真切地经历感受着战争生活,把他们亲身的所闻所见写成了叙事诗,像邵子南的《运输员和孩子》、《骡夫》,曼晴的《站岗的》、《巧袭》,方冰的《人民的葬礼》,徐明的《担架队进了村庄》,陈辉的《妈妈和孩子》,孙犁的《梨花湾的故事》等等。这些作品都成为我们今天了解当时知识分子真实生活,窥探他们心路转变历程的第一手资料。
三
如果我们把晋察冀的叙事诗比作一座座抗战纪念碑的话,那么这些纪念碑显然不是以其宏大而著称,中短篇的体裁使诗人能更灵活地体现出多样化的艺术风格,在雄浑壮美的基调上,这种多样化的艺术风格为晋察冀叙事诗的史诗性增添了多彩的亮色,同时也把现代左翼诗歌创作向前推进了一步。
中国的革命诗歌产生于20年代的中期以后,是当时国际国内风起云涌的革命斗争的直接产物,因此表现出了与此前各诗歌流派迥异的艺术风格。鲁迅曾评价当时革命诗人殷夫的诗“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22]。然而早期普罗诗派把诗歌作为政治传声筒,注重宣传力度而忽视艺术价值,造成其艺术水准普遍较低,这种偏颇一直影响到了后来的中国诗歌会。正如诗歌评论家龙泉明所论:“从诗的艺术性来看,中国诗歌会绝大多数诗篇不成其为诗,能流传下来的精品极少。”[23]
作为中国诗歌会的继承者,晋察冀诗人们真实经历了的战争的洗礼,长期的战争生活促助诗人们的心态由最初的躁厉虚浮而变得深沉洗练,从而让他们有更多的心理空间去构思更具美学特质的诗歌作品。早在传统时代,文言叙事诗就没有完全排斥抒情因素,到了晋察冀时期,火热的战争经历让诗人们总有充沛的感情想要抒发,这种感情被他们以艺术的方式融进叙事诗的创作,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叙事抒情相结合的战争诗歌样式。邵子南的《死与诱惑》写一位工会干部被捕后坚定抵抗敌人的威逼利诱,最后光荣牺牲的事迹。诗人在“说明”中这样写道:“想把它写下来,但又想,与其写事实,不如留下他的精神,所以写成了上面这个样子。”“这个样子”的叙事诗有机结合叙事与抒情两种因素,往往更具有情感冲击力。比如诗人在诗的结尾这样写道:“他沉静地与死并排走着,/有如农夫伴着他的犁走进地里,/进入渺茫的国土。//他,没有死,/他,变成一道电光,/穿透一切心壁/,照亮黑暗。/他是真理,/大众的精英的真理。”类似的还有史轮的《我永远敬念你超人的灵魂》等篇。黑格尔曾说:“史诗并不完全排除抒情诗和戏剧体诗的题材,不过不把这两种诗的题材形成全部作品的基本形式,而只是让它们作为组成部分而发生作用,不能因为采用它们而就使史诗丧失它所特有的性格。”[24]而这些叙事诗恰当地增加抒情因素,对其厚重的史诗性正是一种有益的衬托,使表现的主题更加鲜明,也增强了艺术感染力。
晋察冀的许多诗人还擅长把象征手法融入叙事诗,像鲁藜在他的《树》一诗中以“树”来象征烈士张德海的献身精神将在中华大地上根深叶茂,生生不息。而在《红的雪花》中,“血和雪相抱/辉照成虹彩的花朵”,正象征了“战死的同志”的圣洁灵魂。方冰在其《歌声》种记述了他在一个“劫后的山村”里听到“牧羊人”歌声时的激动心情,那时他“突然感觉到”这歌声正是“晋察冀的精神!”除此之外,晋察冀叙事诗中甚至还有着更加“另类”的作品,像秦兆阳的《乌鸦国王的烦恼》,全篇竟然以寓言的形式写成,他把喜欢光头穿漆黑大氅的蒋介石比作乌鸦国王,向部下下达荒谬的命令,结果惹得“王后”一顿痛骂,最后只好作罢。
多样的形式以及某些现代手法的运用使我们看到,即使是在相对封闭的根据地,文学创作的“民族化”与“现代化”,“政治性”与“艺术性”之间的矛盾并非不可调和,作为文学生长沃土的生活无处不在,何况在当时的晋察冀,这生活又是如此丰富而火热,寻找对这生活的多样表达,已成为诗人们自然的选择。
晋察冀作为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的政治场域,战争的紧张与残酷使置身其中的诗人并没有太多的余暇去精雕细刻每一首诗歌的形式美,因此晋察冀叙事诗在整体上体现出粗犷风格与史诗气度外,也显得有些芜杂,不少诗作因率直粗粝或者过于直白而缺乏诗意,但历史河床里的黄金并不因为伴随它的泥沙而失去光泽,这些叙事诗和它们所记述的历史距今七十多年,期间中华大地上的社会面貌与意识形态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当我们今天跨越七十年的时空再去抚触它们时,依然能被这些诗作中所澎湃昂扬的革命英雄主义和乐观精神所深深震撼。同时,晋察冀诗人们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始终执着于艺术探索,把诗歌首先当做艺术品来创作,从而让其作品在整体上展现出异彩纷呈的美学特色,其精神也让我们深深感动。研究历史不仅在于了解过去,更重要的是镜观当下,由晋察冀的叙事诗而反思今天的诗歌创作,虽然也是花样百出,却总感觉缺乏一种内涵与精神能够真正打动我们,也许在这“无名”时期,诗歌创作可以仅仅成为一种个人情感的宣泄途径,或者说诗歌在意识形态的稀薄期也有理由卸去曾经的历史重担而以更加轻松自由的姿态呈现于世。但是我相信很多人也在思考,在我们这个曾被称为“诗的国度”的国家里,诗歌一定要以这样的面目存在吗?曾经被几代人所呼唤的具有极高艺术价值的宏大“史诗”,能否在这样的土壤里成长起来?晋察冀叙事诗作为一个历史的存在也许回答不了这样的问题,但它们至少能给我们一些启示,甚至某种引导,而在同时,这“一丛奇葩”也有待于我们做进一步的研读和开掘。
[1]梁启超.夏威夷游记[A].徐中玉.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文学理论集(1)[M].上海: 上海书店,1994:677.
[2]王国维.教育偶感[A].王国维文集(3)[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6.
[3]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311.
[4]胡风.今天,我们的中心问题是什么[J].七月, 1940,5(1).
[5]穆木天.建立民族革命的史诗的问题[J].文艺阵地,1939,3(5).
[6]周钢鸣.论诗创作发展的偏向[A].周钢鸣作品选[M].桂林:漓江出版社,1985:264.
[7]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册)[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114-115.
[8] 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册)[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138.
[9] 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册)[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118.
[10] 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册)[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120.
[11]李运抟.“史诗性”与“大部头”的失调[N].人民日报,2000-08-05(6).
[12] 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册)[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137.
[13]谈题材与主题.短论[J].文艺月刊,第十一年号,1941-09-16.
[14]博古.祝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J].七月,1938(11).
[15]鲁藜.目前的文艺工作者[J].文艺突击, 1939,1(4).
[16]胡风.田间底诗[A].胡风评论集(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405.
[17] 胡风.田间底诗[A].胡风评论集(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406-407.
[18]孙犁.一九四○年边区文艺活动琐记[A].孙犁文集[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159.
[19]何洛.四年来华北抗日根据地底文艺运动概观[A].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文学运动理论编[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2:679-680.
[20]胡风.给战斗者·后记[A].胡风评论集(中)[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455.
[21]胡风.关于诗和田间底诗[A].胡风评论集》(中)[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101.
[22]鲁迅.白莽作《孩儿塔》[A].鲁迅全集(第 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94.
[23]龙泉明.中国新诗流变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211.
[24] 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册)[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