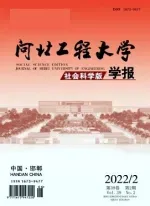论受益格式标记“给”
张东赞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5 )
谈及汉语的特点,除了其所具有的语言共性这个“质”之外,还有汉语自身的“量”,正是这个“量”导致了汉语和其它语言之间的差别。我们常以西方语言作为标准来衡量汉语,比如说汉语缺乏形态。不过汉语是不需要依靠形态来表示其主要的语法意义的,汉语可以说是一种语境依赖型语言,语境提供了汉语消除句法结构自身无法因语义丰富而产生歧义的信息。这并不是说语境对其它语言没有作用,而是对于形态较发达的语言来说,句式自身的形态对于语境的依赖没有汉语高。从这个角度说,汉语的句型应该是比较丰富的尤其是现代汉语,汉语自身的发展也表明了这一点。汉语在发展的过程中其句型是在不断丰富的,以“被动”句而言,上古汉语表示被动主要是采取句法的形式,主动语态和被动语态的句法格式是一样的。如“昔者龙逢斩,比干剖,苌弘胣,子胥靡”。是否表示“被动”需要在一定的语境下来判断,之后汉语逐渐有了表示被动的“见”字句、“为”字句,最后形成了具有形式标记的典型意义的“被”字句。汉语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些有形式标记的句法格式,而这些句法格式的形成和西方语言的形态标记是不同的,本文试图对受益格式标记“给”进行简单的探讨。
一、句法结构对同一语义范畴的词的影响
我们在谈论词的语法功能变化的时候,往往着眼于单个词在句子中的共时或者历时的变化,较少的讨论概念意义相近的一组词在受到句法格式发展的影响而产生的变化。由于受到同样句法格式的影响,有些基义相同或者相近的词,在发展过程中会有相近的发展轨迹,在这里,我们考察几个相关词的发展情况:
赠《说文》:“玩好相送也,从貝曾聲。”
送《说文》:“遣也。”
给《说文》:“相足也。从糸合聲。”
之所以考察这一组词语,是因其基义相近,都有“一方使另一方收益”这样的核心意,可以抽象为“位移受益”,我们不妨称之为“受益类动词”,但这组的陪义有所不同,这也决定了它们的用法和使用环境乃至使用频率的不同。
⑴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诗·郑风·女曰鸡鸣》
⑵我送舅氏,曰至渭阳。何以赠之?路车乘黄。《诗·国风秦风·渭阳》
在上古汉语中动词“赠”的主要用法主是:“赠+受益者”,此用法在西周的语料中是最常见的,此外“赠物+赠+受益者”的情况也很常见,在战国时期的语料中常可见有“赠+赠物”的情况:
⑶执披者,旁四人。凡赠币,无常。《礼记·既夕礼第十三》
⑷大丧,赞赠玉、含玉。作大事,则戒于百官,赞王命。《周礼·天官冢宰》
其中⑴句中,从古汉语语法的角度结合语境来看,“杂佩”应该是作为状语使用。为宾语的情况如⑵,指示代词放在动词前做前置宾语,这符合上古汉语的语法习惯。东汉六朝之后“赠+受益者+赠物”这种双宾语结构比较常见了。
⑸虽生刍之贱也,不能脱落若子,故赠君生刍一束,诗人所谓生刍一束,其人如玉。《西京杂记》
⑹将与故人诀去徒卒赠高祖酒二壶。《西京杂记》
在古代汉语中“名—动”主谓关系的叙述句和“动—名”关系的非主谓句是基本的句式。所以动词“赠”的用法基本都符合这个基本的句式,但动词“赠”的内在语义关系涉及到动作发出者、赠送物和受益者,所以东汉以后在原来基本句式的基础上,动词“赠“进入到双宾语结构。
送,谴也。主要是送行之意,所以在上古汉语中主要的用法:送+人物名词
⑺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赠之?琼瑰玉佩。《诗·国风秦风·渭阳》
⑻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国风·鄘风》
上古汉语中“送”主要是“遣送”的意思,严格意义上没有“受益”之意。但是在汉语发展中正如“赠”一样可以名词做状语的形式可以出现。
⑼秦伯召公子于楚,楚子厚币以送公子于秦。《国语.晋语四》
“厚币”作为方式状语,是古代汉语中一个很常见的句法形式。汉魏时期经常可见到“送”的宾语是事物名词的情况。
⑽闻汝与何迈谋共废我,汝自量体气何如孝武。寻当遣使送药与汝。(《魏书·刘 传》
⑾刘雍自谓得其力助,事之如父,夏中送甘蔗,若新发於州。《宋书》
“送”出现在双宾语结构中在汉魏时期也已经可见。如:
⑿我死,官属即送汝财物,慎毋受。汝九卿儒者子孙,以廉洁著,可以自成。(《汉书》)
⒀傅子方 送我五百钱,在北墉中,皆亡取之。(《风俗通义》)
“送”原义为“遣送”,不过遣送的对象主要是人但是也不排斥物的情况,当对象是物的时候,那么就有一个潜在的受益者,所以“送”进入双宾结构有其语义上的依据的。
给,上古汉语中主要是“供给使用足”之意。动词“给”的宾语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物。
⒁今割国之锱锤矣,而因得大官,且何地以给之。
⒂臣多谏於太子者,曰:“雪甚如此而行葬,民必甚疾之,官费又恐不给,请弛期更日。
在具体的使用中,“给”常用于“名—动”叙述句中,只是做主语的名词受事主语,这和古代汉语中表达主动和被动可用相同的句法形式有关。“给”用在双宾语结构中在六朝时代已经比较常见:
⒃二县官长及营署部司,各随统检实,给其柴米,必使周悉。(《宋书·文帝纪》)
⒄乃学击剑骑射,招聚少年,给其衣食,往来南山中射猎,阴相部勒,讲武习兵。(《三国志·鲁肃传》)
这一组动词,其功能的用法有趋于一致,除了语义因素外,汉语语法结构也影响了它们的用法。都可以进入到双宾结构,三个动词的基义虽然相同,但陪义是有差别的。“赠”的陪义侧重的是“好”的东西比较正式的转移,“送”侧重的对象是人,而“给”则是一般意义上的满足。陪义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它们使用的场合和频率的不同。
二、格式标记“给”
“语法化”通常指语言中意义实在的词转化为比较虚化的、表语法功能的成分这样一种过程或现象, 中国传统的语言学称之为“实词虚化”。语法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重新分析的过程,是语言成分之间的重新组合引起了一些单位的功能上的变化,虚化的成分主要是功能上的减弱,在概念意义上没有大的变化,只是侧重的点有所不同。
动词“给”的不论是在“动—名”结构还是双宾句结构。其宾语都是名词性成分。不过至少在唐代口语中已经出现了“‘给’+人称代词+事件”的句法形式。如:
⒅张天右道:“老千岁说得不差,他果肯给我陪罪,也就罢了,”程咬金道:“既如此,老夫即同行。《薛刚反唐》
⒆长安城中人人怕他,故此人给他起了一个浑名,叫做“通城虎”。《薛刚反唐》
以上两个句子中,“给”后面跟的是一个事件,而不再是一个名词或者代词。以上句子中“给”的动词性功能相对减弱了,但是其概念意义并没有大的变化。我们认为“给”已经成为“受益格式标记”了。当“给”作为动词时,受益者接收的是具体的事物,当“给”作为格式标记时,受益者接受的是整个事件。这在现代汉语中更为常见。如:
⒇ 他给我买了好多书。
按照美国语言学家罗纳德.兰艾克为代表的认知语法认的观点,“给”能够和句中的主要动词相结合完全是因为两者之间的概念重合。为了得到⒇的结构,首先要得到“给我”和“他买了好多书”两个下位结构。然后“他”和“给”的射体相对应,“买了好多书”这一事件充当“给”的事件。相同的概念成分重叠之后,得到以上的符合结构。因此我们认为“给”在由动词发展成为格式标记的过程中,双宾语的基本的句法结构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三、余论
汉语句式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些格式标记,但是这些标记的形成和自身的语义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句法结构对其形成也有重要影响。汉语发展的过程中汉语句式不断丰富,其中一些句法格式标记起到了区分作用,这对于分解汉语因句式简单而句法结构语义复杂而造成的歧义问题无疑有着重要的作用。就注意力系统来说,句法格式标记对于儿童学习语言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1]蒋绍愚.汉语词汇语法史论文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2]罗纳德·兰艾克.认知语法十讲[M].北京:外语教学与出版社,2007.
[3]沈家煊.“语法化”研究综观[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4(4):.367-377.
[4]王力.汉语史稿.北京:中华书局[M].2004.
[5]张志毅,张庆云.词汇语义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