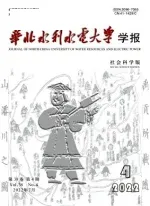论高校法学教育的定位与特色发展
李德恩
(九江学院政法学院,江西九江332005)
论高校法学教育的定位与特色发展
李德恩
(九江学院政法学院,江西九江332005)
在就业压力之下,高校法学教育的人才培养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但法律专门人才的素质要求是全方位的,单纯依靠高校法学教育难以完成对法律人才的培养任务。我们必须建立一体化的法律人才培养体系,并在这一体系里寻找高校法学教育的准确定位。本科法学教育应以法学理论教育为主,并注意与法律硕士的职业教育以及司法考试相衔接。在准确定位的基础上,高校法学教育应该探索地域特色、学科特色和民族特色,走特色发展之路。
法学教育;人才培养体系;特色发展
一、构建一体化的法律人才培养体系
自从1977年恢复高考、特别是高校扩招之后,中国法学教育实现了快速发展。不过,这种发展主要体现在培养的规模上,而培养的质量却没有同步提高。法学教育规模的迅速扩大甚至成为法科学生就业的障碍,扩招之后法科学生的就业率逐年下滑,在2007年就已跌至谷底,在文科名列倒数第一,相当多的毕业生从事与法学无关的职业。即使是跨入了法律职业门槛的毕业生,其职业技能也备受质疑。法学毕业生缺乏提供法律服务所需的基本技能成为社会的普遍认识。许多法学教育界的人士也承认,法学毕业生与合格的法律实用人才还有一段距离,绝大多数法律实用人才都是到了工作岗位后才逐渐培养起来的。法学教育的现状引发了学界对法律人才培养模式的反思,教育界甚至一度出现了取消法学本科教育的主张。①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就主张取消法学本科教育,到硕士阶段再学习法律。其核心就是效法英美法系国家,将法学教育定位为大学之后的职业教育。这意味着从根本上颠覆我国现行法学教育体系以及教学模式,尤其是高昂的成本以及改革前景的不可预期都使得这种主张难获赞同。
实际上,我国并非没有本科后的法学教育。从1996年开始的法律硕士教育很长时间都只招收非法学专业的本科生,定位于培养复合型、实务型的高级法律人才。但是,在两到三年时间里,既要完成法学基本知识的传授,又要进行法律职业教育,法律硕士的培养难度可想而知。由于法律硕士没有经历过专门的法学教育,入学后还不得不开设法学基础课,本来应该培养学生实务技能的实习也由于具有实践经验指导老师的缺乏和学生人数众多之间的矛盾而不得不采取粗放式的管理。这反映出学校和老师都没有对培养法学实务型人才做好准备。从法律硕士的培养目标来说,其教育方式应该既不同于注重通识教育的法学本科生,也有别于偏重学术研究的法学硕士。目前,用人单位,即使是实务部门,也更愿意聘用法学硕士甚至是法学本科生,处处充满了对法律硕士的歧视。法律硕士教育的境况说明对“本科后法学职业教育模式”的推崇多少有些“叶公好龙”的成分,也说明系统接受法学理论教育的重要性。2010年,在大学生就业压力越来越大以及扩大专业硕士招生的大背景之下,教育部开始允许法学专业的学生报考法律硕士。这一举措有利于实现高校法学教育体系之中理论知识教育与职业技能教育的有效衔接。
对法学教育现状的质疑需要辩证看待,既不能漠视社会的批评,也不能据此全面否定现行的法学教育模式。一方面,在培养法律专门人才的目标上,法学教育不能失位,应反思法学教育在培养法律人才中的失误和存在的问题,勇于自我纠偏。另一方面,法学教育也要避免因为社会的质疑而僭位,这种质疑其实充满了对法律专门人才培养机制的误读成份——高校法学教育的产品就应该并且已经是合格的法律专门人才。从系统的观点来看,虽然高校法学教育在法律专门人才培养机制中的作用不可替代,但它终究只是法律专门人才培养体系中的一环而已,如果没有与法律职业资格准入制度、法律职业培训制度等形成环环相扣,也难以完成培养法律专门人才的任务。
法学专业毕业生与合格的法律专门人才还有一定的距离,这既有法学教育自身的因素,也与法律人才培养体系、法律资格准入体系的不健全密切相关。为此,长期从事法学教育管理工作的霍宪丹先生曾提出构建一体化的应用类法律人才培养模式的设想,形成“法律人才培养的共同体”,包括法学学科教育、法律职业教育、一元化的法律职业资格制度和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制度、法律职业技能培训、终身化的法律继续教育和学习[1](P68-69)。这种以系统的眼光来审视法律专门人才培养体系的做法无疑是值得肯定的,高校法学教育的准确定位也应建立在法律专门人才的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的理解上。不过霍宪丹先生继而提出,这种人才培养模式各个环节之间不能中断或错位,如不能用学科教育代替职业教育,或将职业技能训练任意前置到学科教育中去。笔者却认为,法律人才培养体系的各个环节各有侧重,人为割裂各个环节之间的联系将导致各自为战,不利于法律人才的培养。实际上,高等学校法学学科教育同时蕴含职业教育的因素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实践。在强调法律人才培养体系各个环节分工的同时,更应重视各个环节之间的衔接与协调,这才是一体化法律人才培养体系的应有之义。
二、高校法学教育在法律人才培养体系中的定位
普通高校本科法学教育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表面看来,这似乎是一个已经取得共识,无须深入讨论的问题。笔者浏览了诸多高校法学本科学生的培养目标,普遍定位于培养“高层次的法律实务人才”,只是在用语上存在细微差别。但什么是“高层次的法律实务人才”却存在不同的理解。狭义的理解指的是从事法官、检察官、律师职业的人才;广义的理解则是掌握法律专门知识、具备法律服务技能的实务人才,既包括了从事法律职业的法官、检察官、律师,也包括了那些服务于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法律专业人才。狭义的理解则导致法学本科教育走向精英教育、职业教育,广义理解下的法学本科教育则会成为一种大众化教育、通才教育,而职业技能的培养虽然也应该受到重视,但却并非本科阶段的中心工作。
从我国高等教育,特别是法学教育的发展现状看,采取广义的理解更为适当。本科阶段要开设的专业课程非常多。以北大法学院为例,本科各专业必修课就有17门,再加上每一专业的必修课,必修课总数一般都超过20门,这还不包括选修课程以及一些公共课程。其他法学院开设的课程也大同小异。在完成这些专业基础课的学习之后,还要进行专门的职业技能教育实在勉为其难。并且,我们也要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即相当一部分法学毕业生并不从事法律职业,将法学教育定位为仅仅培养司法人才也与我国法学教育发展的现状不相吻合。法学本科教育的目标和功能应该是把学生培养成为高素质的优秀公民和高素质的法律职业工作者[2](P14-21)。
司法职业人才需要具备的素质要求是全方位的,不可能单纯通过学校教育就能够全部获得。苏力教授在谈到法学教育与提高法官素质的关系问题时指出:“司法职业就是这样的一个领域或职业,它不是一个纯粹理性的事业,也不是传统的精密科学的学科。从事这种司法职业的人,例如法官,需要有一定的文字阅读和表达能力,从而能够运用书本告知的法律知识,但是一位合格法官的最基本能力是他的基于经验的判断力。”[3]因此,必须建立一体化的法律人才培养体系,高校法学教育应该完成法学基本理论的教学,并适当开设一些培养法律服务技能的课程,做好与法律人才培养其他环节的衔接工作。“学会像律师那样去实践和学会像学者那样去研究,其实并不是相互矛盾的,相反它们往往并行不悖。”[4]这就是说,本科阶段的法学教育虽然不能定位为职业教育,但也应该并且能够贯穿职业教育的精神。实现高校法学教育的准确定位需要走出高校法学教育培养“成品型”法律专门人才的误区,树立在一体化法律人才培养模式之下准确定位高校法学教育的观念。
从广义的角度理解“高层次的法律实务人才”,本科的法学教育则应该注重基本法律知识体系的教育,并做好两个衔接工作,即本科法学教育的基础理论教育与法律硕士的职业教育的衔接、本科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的衔接。这就需要开设一些实际操作课程,如律师诉讼技巧、法律文书、非讼处理、谈判技巧、司法实务等作为选修课,既考虑学生应试的需要,又可照顾学生个人的兴趣倾向,增加课程设置的灵活性,以培养出更具特点的法学人才[5]。在培养目标上,只有两者兼顾,即提倡通识性教育,传授各种职业都需要掌握的内容,而不能人为地将所有在法学院系学习的学生从人学之初就定位为只能从事法律职业的学生,并进而制定以司法考试为目标的教学计划[6]。现行的司法考试制度也有值得改进的地方,它使得大批未经正规法学教育、记忆力强的学生只要通过几个月的努力就通过了考试,这对提高法律从业人员的素质来说并非好事。我们无法通过司法考试考察学生运用法律进行思维的能力和言辞辩论能力,更无法通过这一考试培养学生的法律信仰。所以,以司法考试作为法律职业的惟一准入标准存在较大的缺陷。未来司法考试的考生资格应设定法学专业的限制,使接受法学教育和通过司法考试成为法律职业准入的双重门槛。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法律职业的准入控制中,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的结合,通过优势互补,在管制的成本和有效性方面都能起到非常好的效果。”[7]这样也有助于实现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的有效衔接。
德国法官的职业能力、职业伦理为世人所称道,赢得了民众的高度信任。德国司法体系的良好运转是以高素质的法官队伍为基础的,德国的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准入制度可以为我们提供参考。德国的法学教育采用的是“双轨制”。所谓的“双轨制”,指的是德国的法学教育由大学基础教育阶段和见习阶段两个部分组成,是一种学术教育与职业教育相结合的体制。参加司法考试则安排在每一阶段的学习之后。基础教育阶段系统学习法学专业知识,取得所需学分之后才可以参加第一次司法考试。通过第一次司法考试的人员要经过两年的见习期、获得法定见习单位出具的证明之后方可参加第二次司法考试,通过者才能获得法律从业资格[8]。德国双轨制的法律人才培养,其实质就是将法律人才培养划分为两个相对独立、功能各异的阶段来完成。从我国法学教育的发展现状来看,德国双轨制的法律人才培养模式比美国大学之后的职业教育更具借鉴价值。
与德国相比,我国现行的法律职业准入很不完善,既没有将法学教育作为取得法律职业资格的门槛,也没有专门的培养职业技能的见习阶段。取得律师执业证虽然要求一年的实习期,但这只是一个常规的程序而已。初入法律职业的人员既有可能缺乏系统的法律知识,也有可能缺乏基本的法律事务操作技能,其职业素养受到质疑也就不足为怪了。缺少见习阶段以及相应的考试,毕业生到工作岗位之后才被真正培养为法律实务人才也有其合理的成分。这就意味着,法律人才的培养机制需要以系统的视野对法学教育、职业培训、法律职业准入制度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改革和完善。
三、高校法学教育的特色化发展
中国地域辽阔,各地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很不平衡,对法律的需求、对法律从业人员的需求、对法律从业人员素质的要求都有很大的不同,这与小国甚至是现代化水平很高的大国培养法律人才的模式都有较大的差异。因此,中国高校法学教育的准确定位还应走出培养目标定位趋同化的误区,鼓励不同层次、不同地域的高校走特色化发展之路。
第一,高校法学教育的定位应体现地域特色。中国经过30多年的时间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但各地的发展水平很不平衡。纠纷的类型、解决纠纷的方式、对法律服务的需求程度在不同地方均有很大不同,这就决定了高校的法学教育不能千篇一律,而应根据学校位置以及办学条件、生源情况等形成自身特色。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从2010年开始试办法学本科背景的全日制法律硕士特班,简称为“法科特班”,为法学本科背景的法律硕士教育的专精化探索新的模式。其基本做法是从法学本科的第四年开始,选拔优秀生源进入“法科特班”,以“3+3”的模式进行法律硕士的职业教育。而中西部的法学院,特别是一些新办地方本科院校的法学院,其培养人才的目标则应瞄准基层,瞄准广大农村地区的法律人才需求。近年来,九江学院法学专业毕业生很多都进入了基层的法律服务市场,甚至有的当上了村官,在带领村民脱贫致富的同时,也利用自己掌握的法律知识在解决村民纠纷、维护村民权益、倡导守法经营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二,高校法学教育的学科特色也值得鼓励。近年来,部分财经类高校的法学教育发展迅速,赢得了良好的口碑。例如,山西财经大学作为一个地方院校,其学校及法学院管理层敏锐地意识到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对财经类法律人才的需求将会剧增,利用学校在经济学和管理学方面的学科优势,着力培养经济法律人才,在法学教育中形成了自身特色。上海财经大学、江西财经大学等高校在法学教育的特色化发展方面,也都走在了前列。财经类院校的法学教育已经成为我国法学教育的一道独特的风景。冀祥德评价说:“部分财经高等院校法学专业人才培养经验昭示出,不同类型的院校基于不同的地域、专业和行业探讨特色化的教育方式、教学模式非常重要。”[9](P29)也就是说,法学教育的学科特色不应只局限于财经类院校。
第三,高校法学教育还可以体现民族特色。我国的程序法针对少数民族有很多特别的规定。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1条就规定: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民事诉讼的权利。在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共同居住的地区,人民法院应当用当地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进行审理和发布法律文书。人民法院应当对不通晓当地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提供翻译。《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也都有类似的条文。这些法律规定要求法律从业人员通晓民族语言、熟悉民族风情、掌握民族法规。市场对民族法律人才的需求也应引起法学教育界的重视,特别是民族自治地方的高校法学院或专门的民族大学法学院可顺势而为,形成自身特色。国家在司法考试的政策层面,也要为少数民族法律人才的培养进行一定的倾斜,针对特定的地区放宽报名资格以及合格分数要求。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到大众化时代,高校法学教育走向精英教育的主张与这一趋势相背离。实际上,我们可以从另一角度看待大众化教育对法学教育的影响——或许正是由于法学的大众化教育,才使得我们通过法律职业准入遴选的法律职业人才真正称得上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精英;大众化教育所产生的法律人才进入法律职业以外的其他行业,也能助推社会的法治水平。大众化时代的高校法学教育必须具有依靠自身特色而形成的比较优势,否则,即使没有高教政策的调整,市场的力量就足以淘汰那些办学没有特色、缺乏竞争力的高校法学教育。
[1]霍宪丹.法律教育:从社会人到法律人的中国实践[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
[2]张文显.法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3]苏力.法官素质与法学院教育[J].法商研究,2004,(3).
[4]汪习根.美国法学教育的最新改革及其启示——以哈佛大学法学院为样本[J].法学杂志,2010,(1).
[5]吴情树.我国法学教育的未来走向[J].高教发展与评估,2009,(4).
[6]郭翔.论司法考试与法学教育的关系——兼与周详、齐文远两位先生商榷[J].法学,2010,(2).
[7]郑成良,李学尧.论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的衔接——法律职业准入控制的一种视角[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0,(1).
[8]于博.德国的法学教育及对我国的启示[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0,(3).
[9]冀祥德,孙远,杨雄.中国法学教育现状与发展趋势[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On Positioning and Characteristic Development of Leg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LI De-en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Law,Jiujiang University,Jiujiang 332005,China)
Under the pressure of employment,the personnel training of leg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is facing an unprecedented challenge.But the quality requirement of legal personnel is very comprehensive,and can not be fulfilled only through university legal education.We must establish a legal personnel training system,in which we can find the exact location of leg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The undergraduate legal education should be based on legal theory,and pay attention to join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of the master of laws and the judicial examination.On the basis of the accurate positioning,the leg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should explore characteristic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subject and the nationalities.
Legal education;Legal personnel training system;Characteristic development
G64
A
1008—4444(2012)02—0145—04
2011-01-02
江西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一体化法律人才培养模式下普通高校法学教育之定位研究》(10YB342)
李德恩(1969—),男,四川隆昌人,九江学院政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责任编辑:宋孝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