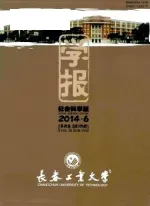“理论高峰”之后
——特里·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述评
王 翠
(北华大学 外语学院,吉林 吉林132013)
“理论高峰”之后
——特里·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述评
王 翠
(北华大学 外语学院,吉林 吉林132013)
笔者认为,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并不标志着“理论死亡”,而是标志着“后理论”时代的来临。在该书中伊格尔顿分析了文化理论的兴衰原因,指出现代变革所带来的社会问题:道德沦丧、金融风暴、恐怖主义等,同时指出文化理论的发展不能脱离人类的基本问题,方能获得发展的动力。本文主要探讨理论是否真正死亡,对理论的误读及“后理论”时代来临的特殊意义等问题;指出能够理解和调动理论即能使实践理论化,而不至于成为教条主义者或纯粹的经验主义者,是理论存在的真正理由。
伊格尔顿;理论;反思
百年前,梁启超奋力呼吁:“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当今世界,知识更新愈加迅猛,文化交往愈加深广。全球化与本土化两极互动,构成了这个时代的文化动脉。在众多的西方书籍被译介到中国来的同时,何为经典的概念发生了偏移,如何解读、用哪种方法解读也成了一个时尚的话题,尤其对理论所产生的焦虑及其是否应该存在之争,一直都未停止过。理论真的死亡了么?为何有人宣称“理论失败”了?理论对我们阅读文学文本的经验和理解究竟有什么用呢?
一
众所周知,自20世纪初,出现了众多颇具影响的理论:有发轫于胡塞尔的现象学理论,产生于对圣经进行解释的批评实践的阐释学理论,源自心理学的格式塔理论,根源于历史和现象学的接受理论,产生于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源于海德格尔的结构主义理论,发端于政治态度的女性主义理论,分别来自于各所属学科和符号学理论的符号学理论和精神分析理论及实用主义理论等等。[1](P10)每一种理论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之后,便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进入新的世纪,我们还在用这些理论解读文本,有人针对这一现象便宣称理论的时代已经结束。在《理论之后》的开篇伊格尔顿指出:文化理论的黄金时代早已消失。雅克·拉康、阿尔都塞、巴特、福柯的开创性著作远离我们有了几十年。R.威廉斯、L.依利格瑞、皮埃尔·布迪厄、朱丽娅·克里斯蒂娃、雅克·德里达、H.西克苏、F.杰姆逊、E.赛义德早期开创性的著作也成了明日黄花。而且伊格尔顿还指出其中的一些人已经倒下:罗兰·巴特丧命于巴黎洗衣货车之下;福柯被艾滋夺走性命;阿尔都塞被送进精神病院;而且拉康、威廉斯、布迪厄也去见了上帝。[2](P1)
伊格尔顿特别指出的是与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种种变体联系在一起的以法国知识分子为主题的那些人,这些人主宰了20世纪70和80年代的思想。然而,如果继续阅读的话,就会发现接下来伊格尔顿对书名做了阐释:如果这本书的书名表明“理论”已经终结,我们可以坦然回到前理论的天真时代。[2](P1)但现在的时代已经与以往时代不同了。伊格尔顿指出新世纪终将会诞生出自己的一批精神领袖。[2](P2)
当上个世纪60年代有人宣称小说已经死亡之时,出现了约翰·福尔斯的《法国中尉的女人》,直到现在如丹·布朗的小说《达·芬奇密码》、《失落的秘符》等依然畅销全球。进入新的世纪,理论虽相对还处在沉寂之中,然而这种宁静也许正像是女人妊娠期一样,在孕育一种新的生命。文学是艺术的一个门类,只要艺术处于兴盛而不是瓦解,理论自然也不会沉寂。新的时代召唤新的理论。
二
特里·伊格尔顿在其《理论之后》一书中试图从开篇就对当今世界的形式做出回应。对他来说,理论中缺失的“另一半”并不是文学、读解、文化或美学,而是政治。在他的脑海中,理论不是福柯、德里达、西苏等人的那些“高级理论”(h i g h t h e o r y),而是“后现代主义”,他心中的“后现代主义”其实等同于近年来的文化理论。
进入新的世纪,理论的概念也与传统的概念发生了一些偏移与变化。理论从哲学吸取营养,以文学批评为依托,逐渐从文学理论膨胀为文化理论,涵盖了冠以文化的各个领域。“文化理论”成了整个学术研究领域中笼罩一切的术语。这些理论在全球范围内促进了对一切话语形式的重新阐释和调整,成了激进的文化政治的一部分,而“文学的”不过是其中一个多少有点意义的再现形式。
自1985年以来,批评理论与时间的发展在集合形态上是多样的、不平衡的。随着多元化的发展,对我们来说,现在好像再没有什么单一的正统观念要遵循;再没有什么新运动要追赶;再没有什么困难的、充满哲学意味的理论文本要读了。然而,这只是对理论的误读。理论的误读会导致理论的衰亡。“理论的失败”意味着它和实践分开了。答案就包容在一些与理论失败观念交叉存在的谬说中。第一个谬说认为理论在观念的、创造的、批评的话语的等级序列中处于高位,发挥着特殊的作用,而不承认理论与时间相互印证、相互改变的辩证关系。第二个谬说认为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于它所揭示的种种假说与意识形态之外,它本身不是一种社会文化实践。第三个谬说是前两个谬说的结果,他似乎在宽广的十字路口设置了一种僵硬的选择,要么是自动的、无法穿透的理论的死胡同,要么是批评实践的通衢大道、可运用的语言和与文学文本的直接接触。[3](P11)伊格尔顿曾从反面论述了这一点,指出正因为所有社会生活都是理论的,因而所有的理论都是一种真正的社会实践。
托马斯·库恩曾说:“科学家们从来不会单独地学习抽象的概念、法则、理论等。相反,他们是在历史的、教学的环境下首先接触到这些认知工具的,在应用中并通过应用来展现认知工具。一个新理论的出现总是伴随着它在某一范围具体自然现象中得到应用;否则的话,这一新理论甚至都不可能被接受。”[4](P5)
科学研究虽有别于人文学科,但如果理论一旦被当成文本来阅读,脱离现实社会,或只是在象牙塔中的理论,那么它就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其结果必然走向死亡。由此可见,我们目前谈论的理论的衰落指的是我们对理论的误读,而不是理论本身过时。如果理论意味着对我们指导性假设进行一番顺理成章的思索,那么它还是一如既往地不可或缺。[2](P3)
伊格尔顿指出:毫无疑问,新世纪终将诞生出自己的一批精神领袖。然而新的时代要求有什么样的新思维呢?正如麦奎伦等编的《后理论》导论中所说的,在一定意义上,“后理论”所昭示的不过是“即将到来的”理论而已。伊格尔顿的“后理论”其实是“更多的理论”,在一种更宏伟、更负责的层面上,向后现代主义逃避的那些更大的问题敞开胸怀。这些问题包括道德、形而上学、爱情、生物学、宗教与革命、恶、死亡与苦难、本质、普遍性、真理、客观性与无功利性等。人类生活的社会是联系的,各个层面也是相通的。人们感到,20世纪70和80年代盛行的“理论”现在已经被取代,或者完全被吸纳进新的理论或种种理论中,这些理论更应该被理解为一种行动而不是文本或立场观点。
新的千年开端的一些著述奏响了新的调子,一批论著的标题告诉我们,一个新的“理论的终结”,或者说得模糊一点,一个“后理论”转向的时代开始了。于是我们可以读到瓦伦丁·卡宁汉《理论之后的读解》(2002),让米歇尔·拉巴泰的《理论的未来》(2002),特里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2003),以及《后理论:批评的新方向》(1999),《理论还剩了什么?》(2000),《生活:理论之后》(2003)等文集。[3](P326)
提出“后理论”时代的一些学者其实未必全然反对理论,而是反对尽数十年来理论逐渐走向空泛,脱离文学和文化研究实践的倾向,或者说反对理论背离传统审美批评,背离经典文本分析的倾向。所有的理论文本,一旦脱离其生存,发展,变化的文化历史语境,就会成为难以理解或者会被误读的原因。
三
艾布拉姆斯指出,在文学史上,甚至在希腊罗马古典时期,某些范式已经确立,所谓新潮理论,的确有新意,但并不是横空出世,而是在旧有模式上翻新在理论背景上前行。理论在批评实践中的有用性,事实上也就是不可或缺性。文学研究的领域充满复杂性与多样性。过去30年来的理论论争留下了不少重大教训:所有文学批评活动总是要有理论来支撑。“理论”不再显然是单一的、令人敬畏的(尽管依然是“困难的”),理论是要被使用的、批评的而不是为了理论自身而被抽象研究的。把文学研究推向各种形式的“文化研究”,对大量非经典的文化产品进行分析却成为更普遍的潮流。最近出现了“文化理论”的发展,如: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同性恋与酷儿理论等,都大大超越了“文学的”范畴。[3](P10)
这个批评叙事的时代,依据人们观念的不同,可以被看作最好的时代,现代性使人们享受着从未有过的奢华;也可以被看作最坏的时代,因为现代性给人带来更多精神焦虑,深入人们生活中的各个层面,其中包括文学、艺术和理论。拉曼·赛尔登(2006)指出:一定程度上对理论的熟悉很可能使阅读不再是一种天真的活动。我们应认识到,没有任何文学话语是没有理论的,甚至对文学文本明显的“自发性的”讨论事实上的(也许不是很自觉的)理论化。而且,理论对我们的阅读远不会造成贫瘠的效果,审视文学的新方式将使我们与文本的关系充满活力。
正如艾布拉姆斯所言,对人文主义真理的追寻可能没有终点。虽然《理论之后》不无偏颇之处,但伊格尔顿在《理论之后》结尾处说:“我们永远不能在‘理论之后’,也就是说没有理论,就没有反省人生……它(指后现代主义)需要冒冒风险,从使人感到窒息的正统观念中脱身,探索新的话题,特别是那些它不愿接触的话题。”[2](P213-214)伊格尔顿的“后理论”其实是“更多的理论”,在一种更宏伟、更负责的层面上,向后现代主义逃避的那些更大的问题敞开胸怀。[3](P338)今天的电子信息时代,尽管文学这一古老的形式受到严峻挑战,但它仍不断地激发人们内心的爱,对人自身的洞察。我们应该给予这个时代更多的思考,这也许是伊格尔顿的真正用意。
[1]〔德〕沃尔夫冈·伊瑟尔.怎样做理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
[2]〔英〕特瑞·伊格尔顿.理论之后[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3]〔英〕拉曼·赛尔登,彼得·威德森,彼得·布鲁克.当代文学理论导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4]Kuhn,S.Thomas.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M].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70.
王翠(1979-),女,北华大学外语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西方文学与文论研究。
——《批评家的任务》与特里·伊格尔顿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