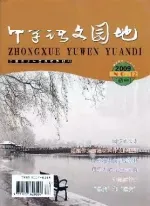别离醉 知心泪 迁谪恨
——浅析《琵琶行》的景、情、意
彭跃奎
《琵琶行》是中学语文课本中的经典课文,长期以来作为描写音乐的千古绝唱,被人们广为重视和传承。所有教辅资料都重点紧紧围绕音乐描写进行鉴赏,人教版教师教学用书的教学建议更是要求只需品味主旨句“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具体内涵和感知诗中音乐描写的美好意境,其余如全篇的结构艺术、景物描写等可以三言两语带过或略而不讲,这让我很难理解和接受。况且整个高中教材所选唐诗三巨头之一的白居易的诗就仅此一首,而李、杜二人的诗在高中五册教材是一个独立的诗歌单元,教参对白诗作如此要求很难让学生对白居易的诗歌成就有一个较深刻的认识。
毋庸质疑,历代用诗歌来表现音乐的作品很少,堪称精品的就更罕见。白居易在《琵琶行》中对音乐的描写可以说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是描写音乐的极品,成为千古绝唱,自唐以来历咏不衰,后人评价是“摹写声音之至文”。
浔阳楼楹联云:枫叶四弦秋,枨触天涯迁谪恨;浔阳千尺水,句留江上别离情。从景、情、意三方面提醒我们,这是我们教学和鉴赏本诗的根本。据此,本文便从“别离醉”、“知心泪”、“迁谪恨”这三个方面进行解读。
其一、别离醉
江淹说:“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他甚至咏叹离别能够“使人意夺神骇、心折骨惊”。离别就意味着伤感,从古到今,离别都最能让人感慨万端。
《琵琶行》的第一节写白居易给他的朋友送别。“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离别本身就叫人不快,秋季相送格外难堪;此时又秋风飕飕,落木萧萧,秋花惨淡,秋夜漫长,凄凉寂寞之情不禁油然而生;又复之以夜色苍茫暗淡,江水迷蒙凄清,给人一种人生飘乎,离合无常之感,于是心情也倍加怅惘空虚,凄暗孤寂。
诗人在开篇缘情写景,触景生情,象高明的丹青手,浓墨重彩,多层意象叠加,使人感到这种别离是何等痛苦,这对挚友的分手是何等的艰难。
凄清哀婉的送别本已让人辗转伤怀,进入了深沉悠远的离情氛围,但诗人却还要不断的渲染。“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客不发”。诗人写迁谪之人相送,主、客二人失意,情形倍加难堪,使人读来沉郁苍凉;而酒宴前又没有歌女侍应、管弦相和来渲染依依惜别的感人气氛,当然就更加显得寂寞难耐,只有感慨万端,一醉方休了;偏偏此时又暗暗地传来了低沉抑郁的旋律,仿佛整个天宇都被笼罩在压抑伤痛之中,使主客双方的惜别之情在这瞬间都达到了顶点。
一首诗,如果既包含了诗人心潮的起落,又展示出长久以来多舛命运的感情积淀,寄无限人生感慨于依依惜别之中,那么它所表达的离情别绪就必然更加震人心魄。
本诗开篇,诗人巧妙利用送别时的时令节侯、景物气象等特点组合的意象,创设出峰断云连、辞断意属的审美意境,把一段浓浓的深情,深婉含蓄地藏在简淡的、似乎是不经意间得来的景中,让读者去发现、去抽取,去感受意象的斑斓色彩及其背后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其二、知心泪
“相识满天下,知音能几许”传达了千百年来人们渴望沟通,渴求理解,希望呼唤与被呼唤的共同心理。
白居易在他的《与元久书》中指出:“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未有声入而不应,情交而不感者。”这本是针对诗歌而言的,但他所提倡的新乐府诗,是一种可以入乐的声诗。《琵琶行》就用诗歌的旋律,写出了音乐的旋律,又从音乐的旋律中传达出感情的旋律,它聚合着演奏者的情感和诗人欣赏时的感情。正是这声情,这旋律搭建了通向知音的桥梁,让琵琶女和诗人敞开了心扉,用彼此全部的真诚与理解去奏响了一曲心灵的和声。
《琵琶行》的心灵和声、知心苦泪,首先表现在主客二人情感的和谐默契上。
诗人遭贬江州,又逢与客别离,离愁难以排遣,只好借酒浇愁,可是此时此景,主客二人谁都提不起兴致。去者浪迹天涯,归途杳杳;留者前途未卜,心绪茫茫。“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互文见义,客人下马,主人也下马;客人登舟,主人也登舟;主人举酒,客人也举酒;主人因无奏乐饯行感到难堪,客人也因无奏乐别离感到别难。“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客不发”。琵琶声让主客二人同时转移了离别的痛苦,一个忘记了归家,一个忘记了启程。其灵魂间的默契,情感间的共鸣,心息间的相通,让人感到他们二人游丝般的神魂交融是多么细微,慰勉是多么熨帖。
心灵和声、知心苦泪。主要表现在诗人与琵琶女感同身受、情意合一上。《琵琶行》借着叙述琵琶女的高超演技和她的凄凉身世,抒发了作者个人政治上受打击、遭贬斥的抑郁凄悲之情。“我闻琵琶已叹息,又闻此语重唧唧。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写诗人听完琵琶曲嗟叹不已,此时又听她自述身世,更是叹息不定。同是沦落天涯的不幸之人,只要心灵相通,何必一定要曾经相识!一个“同”字,说明每个人的经历虽然是独特的、具体的,但对某种情景或者经历的感受,却可以是相通的。“同”是诗人从琵琶女的演奏曲和自述身世后获得的一种心交神契的美感和喜逢知己的快意,是心心相印、彼此共鸣而获得的慰藉。于是,诗人也推心置腹地向琵琶女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在此,诗人已把一个倡女视为自己的风尘知己,与她同病相怜,写人写己,哭己哭人,宦海的浮沉、生命的悲哀,全部融合为一体。诗人与歌女,一个独守空船,借乐诉怨;一个送客江头,有酒无乐。一个“艺压京城、艳盖群芳”(色艺双绝),一个“身居高位、名动京师”(高官厚禄)。一个已“年老色衰、漂泊憔悴”(委身商人),一个则“谪居卧病、飘零天涯”(沦落凄凉)。一个善弹,一个善听(善写)。琵琶女用一支琵琶曲向白居易倾述了她坎坷曲折的人生,白居易用文学艺术形象再现了琵琶女精湛的演技,更是借此尽情地倾述了自己的悲愤之情。是琵琶的旋律契合了彼此心灵的贴近,而他们心灵的真正沟通还在于互道生平后的那“同是天涯沦落人”。共同经历、不幸感受的灵魂被燃烧了起来,在“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的共鸣中演绎了一出千古传诵的充满哀婉之情的知音故事。
心灵和声、知心苦泪。还表现在听众被琵琶女音乐的声情所同化上。“东船西舫悄无言,惟见江心秋月白”。写所有那些移船靠近来听乐曲的人们都像着了魔一样,在乐曲的余音中悄然无声,以至曲终而人犹醉。这里甚至还有人与自然的息息相通,茫茫的江水上,江面微波荡漾,倒映在水中的明月,似乎也盛满忧愁,弥漫着凉意,将人们引入一个凄清和悲凉的意境。这是美妙绝伦的琵琶声引发的每一个人内心的郁闷和苦痛的结果,它渲染了当时凄清的气氛又衬托出琵琶女弹奏的高超技艺,给人造成余音绕梁的感觉。“凄凄不似向前声,满座重闻皆掩泣”。是琵琶女听了诗人的一番真诚的倾诉后十分感动,她久久地伫立着,然后退回原处,重新坐下来拨弄弦丝,音乐变得更加急促而凄凉。而这凄凉的音乐又与刚才的不同,满座的听众被感动得低声啜泣。如果“东船西舫悄无言,惟见江心秋月白”只是受音乐艺术美的感染,那么“凄凄不似向前声,满座重闻皆掩泣”就是在了解琵琶女身世和内心世界后情感的契合了。
其三、迁谪恨
《琵琶行》作于唐宪宗元和十一年秋,时白居易四十五岁,任江州司马。白居易在元和十年以前先是任左拾遗,后又任左赞善大夫。元和十年六月,唐朝藩镇势力派刺客在长安街头刺死了宰相武元衡,刺伤了御史中丞裴度,朝野大哗。藩镇势力在朝中还进一步提出要求罢免裴度,以安藩镇的“反侧”之心。这时白居易挺身而出,率先上疏请急捕刺杀武元衡凶手,坚决主张讨贼。但因他屡次上书针砭时弊,写下了《新乐府》、《秦中吟》为代表的“讽喻诗”,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揭露了统治阶级的腐朽和罪恶,得罪了宪宗和官僚集团,于是有人就趁此诋毁他官小位卑,擅越职分。再加上有人给他罗织罪名,遂被贬之为江州司马。中唐时期这个职位是专门安置“犯罪”官员的,是变相发配到某地去接受监督看管。这件事对白居易影响很大,是他思想变化的转折点。次年他写下《琵琶行》。开始“吏隐”,思想从“兼济天下”转向“独善其身”,闲适、感伤的诗渐多。以叙事长诗《长恨歌》、《琵琶行》最有名。
白居易本来怀有伟大抱负和理想,长安城也才是他施展抱负的地方,他被贬之后,表面上安于现状,可是不能施展抱负一直是他心头的一件憾事。这首叙事诗,主要记叙白居易贬谪江州时,在一个萧瑟的秋夜,送客浔阳江头,偶逢琵琶女之后演绎出的一个美丽而忧伤的故事。琵琶女是一个演奏的高手,她通过自己的演奏诉说自己悲惨的遭遇和内心的哀愁,所以其出场弹奏时旋律低沉抑郁。而白居易则是一个听曲的高手,他通过听琵琶女的演奏,由琵琶女的遭遇联想到自己遭贬,心情十分低落,并从琵琶女苦难的身世联想到自己政治上的坎坷失意,顿时触发了天涯沦落的痛苦心境,悲怆之意油然而生,漂泊流浪之意渐渐浓稠,于是饱蘸满腹辛酸之泪,尽情倾述悲愤之情。继而琵琶女借琵琶曲刚劲急促、震撼人心的节奏,来宣泄她隐藏在心头的幽愁暗恨,也将白居易心头的不快之情一泄而出。演奏结束时“四弦一声如裂帛”,这裂帛,是琵琶女心的碎裂,也是诗人被贬九江之后,伟大抱负被撕裂,是愤激的哀号。
总之,诗人不但写出了琵琶女音乐技艺的高超,而且通过乐曲的变化,表达出演奏者内心情感的起伏变化,让人如闻其声,如感其情。白居易和琵琶女,一个笔下写忧怨,一个弦上弹忧怨,他们都有一样的愁怨,诗人用湿漉漉的诗行写出了用湿漉漉的眼泪浸泡得湿漉漉的心。
尘世太污浊、黑暗,诗人报国无门,请缨无路,贬官九江,地势荒僻,环境恶劣,孤独寂寞,举目伤怀。其悲哀苦闷完全是由于他政治上受打击造成的,但是这点他没法说。他只是笼统含糊地说了他也是 “天涯沦落人”,他是“谪居卧病”于此,而其它断肠裂腑的伤痛就全被压到心底去了。这就是他耳闻目睹一切无不使人悲哀的缘由,也是他蔓生迁谪之恨的缘由。
枫叶四弦秋,枨触天涯迁谪恨;
浔阳千尺水,句留江上别离情。
上联简洁地交待了白居易在浔江头遇琵琶女,感触到被权贵排挤和朝廷贬谪的遗憾以及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悲哀。下联既包涵了诗人对客人难分,又包涵了诗人对琵琶女的同情。联语精工细绘,自然浑成,爱与恨的对比描写富有强烈的感情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