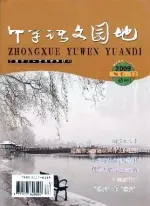母语诗教的赓续与探求——东北师大附中第二届语文学术节侧记
李跃庭 沈月明
[作者通联:李跃庭,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语文教研室;沈月明,长春教育学院中文系]
在“合作教研,学术为先”这一宗旨的指引下,为了推动语文教学迈向专题研究,加强语文学术思想交流,实践语文先进教育理念,推动语文教学健康发展,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语文教研室于2012年5月18日在吉林长春自由校区举行了主题为“诗歌教学与研究”的第二届语文学术节。来自辽宁、吉林、黑龙江的七百余位中学语文教师参加了本次学术节活动。活动邀请了来自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吉林省教育学院高中部的知名专家和学者担任点评嘉宾。
本次学术节的活动由四个环节组成:诗歌教学观摩课、“诗歌教学与研究”主题论坛、专家点评、名家讲座。在名家讲座环节,主办方邀请了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著名当代诗人、文学评论家王家新先生,做了题为《诗人眼中的诗歌教学》的主题报告,王家新先生从诗人创作、学者批评等多元角度对诗歌的教学与研究进行了精彩的讲解,得到了与会教师的一致好评。
以下,笔者将重点围绕学术节的诗歌教学观摩课、“诗歌教学与研究”主题论坛两个环节来传达自身的感悟与思考。
看点之一:《神女峰》——知人论世,古今贯通
在诗歌教学观摩课环节,东北师大附中的李跃庭老师执教人教版选修教材篇章——舒婷 《神女峰》。他灵活地运用“知人论世法”和“古今贯通法”,针对学生普遍感到困惑的疑难意象 (如 “远天的杳鹤”“春江月明”“金光菊和女贞子的洪流”)和情感(“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进行分析。深化了学生对舒婷诗歌创作的女性立场的理解,进而增强了他们对“朦胧诗派”创作风格的体认。学生深情而精彩的朗诵,师生睿智而深刻的对话,都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看点之二:《定风波》——文本细读,中外比较
在诗歌教学观摩课环节,田宇老师执教人教版必修教材篇章——苏轼《定风波》。他引导学生运用“文本细读法”,对《定风波》的散文小序与词作正文进行交互阐释,从而发掘出对词作内涵的崭新的认知;同样难能可贵的是,他引入了奥地利诗人里尔克的名作《豹》,与《定风波》进行“参较式阅读”,从而拓展了学生对诗歌意境与诗人心境的理解,给与会者耳目一新之感。
当然,本届学术节的最大看点莫过四位资深教师在“诗歌教学与研究”主题论坛中的精彩发言。
看点之三:诗歌选篇与教学刍议
在主题发言中,东北师大附中语文学科首席教师、吉林省语文名师工作室主持人孙立权老师引用了美国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的话语,强调诗不仅是表述人类经验的最简洁方式,而且它还为任何语言活动提供最高标准。他还引用了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言论,凸显了“伟大的诗人就是本民族的教育家和未来伦理的预言家”这一判断。
孙立权认为,诗歌教育不仅是语言教育,还是审美教育、艺术教育、伦理教育。在今天这个视觉文化时代、读图时代、感官盛宴和物欲霸权时代、美被钝化的时代,在今天这个学校处于应试教育环境,学生的大脑被流行歌曲、动漫、西方大片充斥的时代——纵论诗歌教育,可谓意义非凡。
在孙立权看来,当前诗歌教育的首要问题是——你把什么呈现给学生。所以,他针对以往中学教材中选取的3篇诗歌作品,从不同角度进行审视和反思。如柯岩的《周总理,你在哪里》(1977),对王洪涛《莉莉——写给在抗战中牺牲的小女儿》(1963)一诗的意象、写法的模仿性问题,贺敬之创作于风雨如晦、饿殍遍野的“三年困难”时期的《桂林山水歌》的规避苦难、粉饰现实问题、艾青的《给乌兰诺娃——看芭蕾舞<小夜曲>后作》的观念先行、精神矮化问题。他的质疑和批判,可谓见微知著,发人深省,引发了与会者强烈的共鸣和普遍的认同。
在这一背景下,孙立权对于我国当前的中学诗歌教学明确地提出了五点建议:
第一,应该重视教材中的诗歌选篇问题。他指出: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教材65课79篇选文中,只选入了3首新诗《雨巷》《再别康桥》《大堰河——我的保姆》,且都来自于中国现代诗歌。高中必修教材里既没有选入以舒婷、顾城、食指、海子等人的创作为代表的中国当代诗歌,也没有选入从普希金、泰戈尔到惠特曼、帕斯捷尔纳克为代表的外国诗歌。
第二,应该改变单一的诗歌解读模式。他建议综合运用知人论世法、文本细读法、精神分析法、原型批评、评点法、变换分析等多种手法等来解读诗歌,而非单纯从社会学或意识形态角度切入。他以《孔雀东南飞》《琵琶行》等古诗和《雨巷》《烦忧》等新诗为例,探讨了多元解读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第三,应该杜绝诗歌教学中的试题化倾向。在当下的应试教育体制下,按照高考诗歌鉴赏题的命题模式,将内涵丰富的诗歌作品拟题训练,是中学诗歌教学中的普遍现象。但是,这无疑会把无限丰富的诗歌教学引向机械的套路,严重戕害诗歌审美。
此外,孙立权还就诗歌教学中应重视吟唱、朗诵,师生应该共同的读诗、背诗、写诗等问题进行了富于见地的阐发。东北师大附中青年语文教师王宏伟、万代远也先后登台献艺,为与会者吟唱了古诗《长干曲》,博得了阵阵掌声。
看点之四:诗,何以最高
东北师大附中语文学科带头人、学科组长王玉杰老师在发言中首先引入了19世纪俄国文艺理论家别林斯基的经典论述——诗是最高的艺术体裁。但她并未将其作为毋庸置疑的前提看待,而是从“源”“痛”“和”“情”“准”这五个维度入手,重新对“诗,何以最高”这个命题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深刻的论述。
何谓“源”?王玉杰历数了中国、古希腊、两河流域、古印度等不同地域文明的文学发展渊源,从《诗经》说到《荷马史诗》,从《吠陀》言及《罗摩衍那》,强调诗歌伴随着神话和宗教产生,带着原初生命的特质,带着宗教的神圣,它是各民族文学艺术的源头。
何谓“痛”?王玉杰认为:诗歌,最大限度地承载了人类的痛苦。从这一点来说,诗歌具有哲学的神圣。因为人生的本质就是痛苦。痛苦联结着生活和生命,诗,给了痛苦可以言说的可能。《诗经》的“寤寐思服,辗转反侧”和《离骚》的“宁溘死以流亡兮”,《荷马史诗》的“铜尖扎进厄开波洛斯的前额,深咬进去,捣碎头骨,浓黑的迷雾蒙住了他的眼睛”等名句无不与痛苦息息相关。后世更有无穷诗歌,记载着,呼唤着,消除着,铭记着,升华着人生的痛苦。范仲淹的“将军白发征夫泪”,纳兰容若的“何事秋风悲画扇”,济慈的“将你的哀愁滋养于早晨的玫瑰”,泰戈尔的“我的心和不宁的风一同彷徨悲叹”……一部《红楼梦》,最惊心的痛苦,在诗上;古今第一快诗《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是乐吗?背后都是痛。
何谓“和”?王玉杰之所以用“和”来定位诗歌艺术,源于她认为诗歌就是造型、造音、造境三个方面和谐统一的艺术,它将视觉在空间里欣赏的艺术、听觉在时间里欣赏的艺术、想象在心灵里欣赏的艺术融为一体。除了诗歌,没有任何一种艺术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
首先,作为造型艺术,诗歌,凝结最美的词采,构筑最美的意象,引发人最美的感受。如徐志摩的《沙扬娜拉》里“不胜凉风的娇羞”的水莲花,如他的《再别康桥》中的“在我的心头荡漾”的“波光里的艳影”,如北岛的《回答》里的“镀金的天空”中飘满了的“死者弯曲的倒影”。
其次,作为造音艺术,诗歌,看着有节奏,读着有韵律,读出来,就知道了美。如陈敬容的《窗》“空漠锁住你的窗锁住我的阳光重帘遮断了凝望留下晚风如故人幽咽在屋上”当然,裴多菲的《我愿意是急流》、席慕容的《一棵开花的树》无不体现出音韵之美。
再次,作为造境艺术,诗歌,用最简单的文字,最丰富的外延,触动你的心弦,想象一动,境界全出。如盛兴的《铁轨铺到哪儿》“人一旦卧到了铁轨上,我们就无法阻止火车隆隆开来”。显然,遥远的蓝天白云,横倒的树木,无边的铁轨,高昂的车头,飞转的车轮,静候的生命,诗里都没有,然而一个火车隆隆开来,你心中就什么都有了。再如北岛《和平》“在帝王死去的地方那支老枪抽枝,发芽成了残废者的拐杖。”我们可以想象,暴政专制的废墟,废旧的老枪,新嫩的树芽,残废者扭曲的肢体,这些都是和平的代价。
何谓“情”?王玉杰说:诗的本质在于抒情,郭沫若将诗人的心比作海,灵感比作风,大风大浪则抒发雄浑之情,小风小浪,则抒发冲淡之情。正如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正如叶芝的《当你老了》“只有一个人爱你朝圣者的灵魂,爱你衰老了的脸上痛苦的皱纹。”正如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女人啊,当你再度向财富致敬,向名利欢呼,向权力高举臂膀,请不必询问那只曾经歌咏的画眉,它已不知飞向何方,因为她的嗓音已经干枯喑哑,为了真实、尊荣和洁净灵魂的灭亡。”
何谓“准”?在王玉杰看来:诗,是衡量诗以外事物美的最高标准。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可以用诗来形容:诗一般的风景,诗一般的国度,诗一般的语言,诗一般的年华,诗一般的时代……就连其它文体,都乐意用诗歌来评价,鲁迅评历史散文《史记》,用诗歌为标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古小说中讲到言之凿凿的事物时,总是“有诗为证”。
由以上五点可见:诗歌,彰显着至爱大美,和着音乐舞蹈,直抵人生哲学意义的痛苦,引领人走向生命最高存在形式的诗歌,我们依然应该承认它是最高的语言艺术形式。
王玉杰表示,虽然诗歌现在走向了一种时代的枯竭状态,但她相信有更多热爱诗歌的人在坚守,这次学术节活动,就是很好的证明。我们从未放弃过读诗,更不会放弃诗意,也不会放弃尝试写诗。她用一首自己创作的诗歌《矿工》,与在座的同仁分享了诗情和诗意。
看点之五:诗歌教学的“隔”与“不隔”
东北师大附中语文学科副主任、市级骨干教师张继辉老师则化用了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评论诗歌的艺术境界时所使用的“隔”与“不隔”的概念,基于自身在常规教学中授课、听课、评课过程中积累的经验与识见,他与在座同仁分享了他对诗歌教学的感受和体悟。
张继辉认为:在诗歌教学中,因为诗歌文体的特殊性和距离感,出现“隔”的情况常常要高于其它文体的教学,而追求诗歌教学中“不隔”的境界,是教师应该思考和研究的。他分别从五个方面对“隔”与“不隔”的诗歌教学现状进行阐发。
首先,教师应该有对作品的深入研究和真切的个人体验,即做到教师同作品本身的“不隔”。他以孙立权老师讲授食指的《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为例进行说明。《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是一首描写知青上山下乡告别北京的惊心动魄的诗。孙老师通过对诗人和那个时代深切的体察和感悟,辅之以饱含深情的语言,将这首诗讲得同样动人心魄,余味无穷。学生和听课者都自觉的进入了教者制造的情境之中,进入到诗人的内心世界,为之感动,为之反思,这样的课堂正是“不隔”的真正境界。换句话说,诗歌课堂的“不隔”,要求教者首先像个诗人。
其次,列举出学者季镇淮回忆当年闻一多在西南联大讲《楚辞》时的情景,国学名家刘文典在为学生讲解谢庄的《月赋》时特意选择了阴历五月十五之夜的典故,强调在课堂之上创设情境、营造充满诗情画意的教学氛围,对于诗歌教学而言,尤为重要。
再次,投入情感的诵读是拉近教师、文本和学生之间关系的另一重要手段。读《将进酒》就应化身李白,有“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的洒脱放旷,读《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便俨然杜甫,有“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的涕泪纵横,喜不自胜。恰如朱自清在《朗读与诗》里面说 “只有朗读才能玩索每一词每一语每一句的义蕴,同时吟味它们的节奏。默读只是‘玩索义蕴’的工作做得好。唱歌只是‘吟味节奏’的工作做得好——却往往让义蕴滑了过去。”
第四,诗歌作为阅读文本在表意上的模糊性,决定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充分尊重学生对于诗歌的个性解读,这样才能充分激起学生的参与性和创造性,拉近师、生、文本之间的距离。他以唐人司空曙的“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一句为例,介绍了他和学生之间是如何进行对话和理解的。他认为,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学会接纳学生对诗歌的某种程度上的 “误读”或者“曲解”。学会放下自己已有的固定思维,站到学生的视角去接纳和理解学生的认识,给以中肯的评价,使学生在创新性的解读中获得思考的乐趣。
最后,诗歌课堂产生“隔”的现象,除了以上几方面做的不够,还有教学内容的适切性不够,教师语言过多术语的使用使学生产生理解上的疏离,也可能造成了课堂的冷场。
看点之六:像他们那样优雅地活着
东北师大附中语文学科带头人、市级骨干教师刘勇在他的发言中,重点探讨了“如何实现诗歌教学的建构与回归”这一个问题。
首先,刘勇从六个方面反思了自身在诗歌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无疑,这些现象在今日的中学诗歌教学中也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
第一是经验式推理与主观化定性(作家与主题)。怎样才能快速的读懂一首诗?先看题目,再看作者。题目里有羌笛那就是边塞之作,有古迹那就是感慨物是人非,写历史名人基本都是和自己对比,林阴小道、乡间小桥、毛驴骏马的基本都是羁旅愁思,登山就要思乡,临水就要感慨时间流逝,盛唐诗基本皆大欢喜,中晚唐诗就是哀民生之多艰。
第二是模式化归类与技术化切割 (风格与技巧)。在教师的教导下学生们的视觉能力格外增强。看见颜色的词格外注意,那可是色彩渲染,看见景物的词格外注意,那基本就是寓情于景,景中含情,情景交融,看见前边一个月亮后边一个流水的格外注意,那就是动静结合,看见结尾一句是景物描写,那就是以景结情。
第三是以情感挖掘替代意境体验 (情感与审美)。一首诗反映了作者感怀伤世的心情,表达孤独寂寞的感情,表达壮志难酬的感情,表达思念家乡思念亲人的感情,等等,学生们已经成功的学会了各种套话,不假思索脱口而出的样子,仿佛医生给病人看病,能说出病因,却感受不到病苦。白瞎了小桥流水,浪费了无边落木,糟蹋了一树梨花,亵渎了半亩方塘。
第四是以完成背诵替代忘我吟咏 (背诵与诵读)。背诵是现实诗歌学习的初级目标,有时却也成为终极目标。本来是忘我的吟咏,纵情的歌唱,此刻全都变成山东快书,上气不接下气。
第五是以知识掌握替代文学感受 (学习与体验)。对于刘禹锡的《乌衣巷》,学生们很快就会说出这首诗的主题,技巧,但是当我和他们说起野草花的孤独,说起夕阳的惆怅来,却少有人应和。
第六是以全体感知替代细节感知 (整体与局部)。读起“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学生会立刻反应:这是首悼亡诗,但与我无关。读起“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学生也知道:诗人在思念母亲。在林林总总的诗歌里,“一言以蔽之”似乎百试不爽。
刘勇进而追问:诗歌教学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他做了六个形象生动的比拟:
第一,做题是诗歌死亡的凶手。
第二,背诵是诗歌尴尬的活着。
第三,写作是诗歌无奈的重生。在这一方面,刘勇说:我们没有必要把每个人教育成诗人,但我们完全有必要把每个人教育成具有诗歌精神和诗意情怀的人。诗歌教育应该承载的是一个人对自由、理想、创新和开拓的追求,教育的是冲动激情之下的直接表达。
第四,读诗是灵魂的握手。
第五,读诗是生命的对话。在这一点上,刘勇强调:只见文字不见人,只见技巧不见情,只见主题不见人的期望与悲哀,其实我们就等于和诗人擦肩而过,一次又一次的邂逅又能怎样,不过是形同路人而已。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不管他送别的是谁,读罢是否想起了一个无语凝噎的诗人泪光闪闪?是不是里面也有无数的我们的某次分别的影子?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如果只是出现了画面感,没有让自己去体验化作一只鸟儿在天地间飞翔的无依靠感,没有从高处俯瞰大地的飘渺感,一切解说都是乏力的。他还以昌耀的《边城》、北岛的《远景》、洛夫的《清苦十三峰》、冬箫《我的诗》等作品为例,指出诗人们的文字的形象感背后其实更多地是人生与生命的苍凉感。每一个诗人的背后都站着无数的你和我。
第六,读诗是感官的跳舞。刘勇认为:诗人是上帝留在人间的长不大的孩子。诗和诗意,是一个美好时代的指针。一个生机盎然、和谐美好的时代,需要自己的诗人,需要涵养诗意。我想说的是,学诗是在学养生,学诗是在学关爱,是在学淡定,是在学优雅。一个愈加完整、统一的世俗世界,人心越是物化,越是无法真正找到心灵本身。他提出的是像诗人们那样优雅地活着,让我们都回到现实里,不怕精神与现实同拍。
其实,刘勇所谓“像他们那样优雅地活着”就是呼唤我们要保留孩童一样纯真的想象,在万物之间建立起联系,关注到有限与无限的宇宙万物,把自己的灵魂交付自然,感受无限的机趣,体悟与穿梭在自然与时空里,在艰难与失意中不屈和坚守,在情感与名利中快意与淡然,在入世与出世间悲悯与忘情。在他看来,虽然每一个接触诗歌的灵魂,虽然未必都成为缪斯的宠儿,但是却都可以高昂着我们的头颅,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显露一点优雅的姿态。不追随,不盲从,不粗心,不错过。
“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假如有一天,在母语诗教的赓续与探求的旅程中,我们不必再去慨叹“读什么”“为什么要读”“如何去读”这一类问题时,想必我们终于在内心中明了“诗,何以最高”的追问,从而由“隔”走向“不隔”的境界,真正实现了“像他们那样优雅的活着”——诗意的栖居,海德格尔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