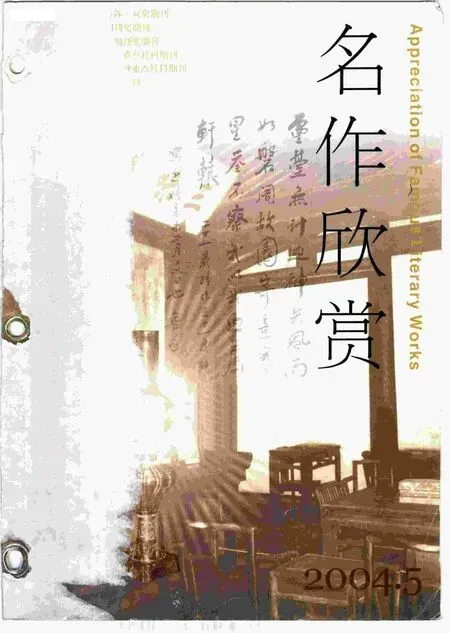《汉书·地理志》的文学地域观
⊙谢祥娟[上海大学文学院, 上海 200444]
华夏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地大物博、物产丰富之说,可贵的是,在如此广阔的中华大地上,各地的自然条件和人文景观没有出现千篇一律的现象,正相反,不同地域呈现出了各具特色、与众不同的地理风貌、风俗文化以及行为习惯等。我国古代很多历史学家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点,比较典型的是一代文化巨匠司马迁,他在其《史记·货殖列传》中分区介绍各地的经济状况时,向我们展示了各地域别具特色的地貌、风俗和物产资源等;另外,去之不远的班固著有《汉书·地理志》一文,此文包括上下两卷,是班固杰出的古代历史地理作品。虽然文章大致内容、著作体例明显是继承司马迁《货殖列传》而来,但其系统较《货殖列传》更为详尽完备,内容更为充实丰富,从中我们可以对中华民族“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①的地域文化特征一览无余,大大扩展了史学研究的范围。如果对二者进行仔细比较,就会发现:两篇杰作虽然都描述了各地的地理环境和民风民俗,并指出了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但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还进一步从不同地区的地域风俗文化差异中去解释各地文学样式的内容特点和发生发展,这可以算是班固比司马迁高明之处。
众所周知,文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对特定的物质条件(环境)的反映,而换句话说,某一地区特定的地域环境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当地文学样式的内容和风格。谈到特定的地域环境,从《汉书·地理志》中可以看出,班固不仅看到了其中的自然地理环境对文学的影响作用,更应该注意的是,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充分地展示了社会历史文化环境与文学样式之间的相辅相成作用。
一、自然地理环境与文学
文学即人学,人与自然环境之间互感互动的关系同样适用于文学和自然地理环境。一个地区特有的自然地理环境势必会影响当地文学样式的内容,也就是说,特定的山川地貌、溪谷河流等会成为其地域文学创作的重要素材,文学作品是记录当地自然风貌的重要工具。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很好地贯彻了这一原则,如:
(1)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故《秦诗》曰“在其板屋”。
(2)魏国,亦姬姓也,在晋之南河曲,故其诗曰“彼汾一曲”;“ 诸河之侧”。
(3)临甾名营丘,故《齐诗》曰:“子之营兮,遭我 之间兮。”
例句(1),天水和陇西属于秦地,秦诗中反映的是两地以板为屋的民居特色;例句(2)诗歌反映的是魏国的地理位置;例句(3),《齐诗》中反映的是地域名称。
以上三例中的诗句内容是对当地自然地理环境的直接反映,除此之外,还有几处比较特别,如下:
谷汲,男女亟聚会,故其俗淫。《郑诗》曰:“出其东门,有女如云。”又曰:“溱与洧方灌灌兮,士与女方秉菅兮。”
卫地有桑间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会,声色生焉,故俗称郑、卫之音。
郑卫之音,作为封建社会里靡靡之音的代名词,其实就是郑卫两国的民间音乐,它有别于传统雅乐的地方在于表达情感的热烈、奔放和大胆。正因为如此,它历来受到包括班固在内的传统封建士大夫的排斥。从以上两例可以看出,郑卫之音的一些诗篇是对两地民风民俗的反映,而在班固看来,郑卫两地之所以产生淫俗声色,是由各地的自然地理环境决定的。据班固的描述,两地均有山有水,且地势险阻,交通不便。处在这样一个山谷幽幽、溪水清清的闭塞之地,青年男女容易产生一些异于他地的浪漫气息,班固的看法也不无道理。以上两例句中的郑卫之音描写的是两地的风俗文化,而这些风俗文化的形成是由两地的自然地理环境造成的,这表明此处的文学样式虽然没有直接以当地的自然环境为素材,但文学作品风格的形成却与自然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而当地的民风民情可以说是联系二者之间关系的纽带。
自然地理环境作为一种客观存在,是文学等社会意识产生的物质基础。不同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不同,受其影响的文学作品也呈现出了千差万别的特色,可以说是一地有一地的文学,这就从客观上丰富了文学创作领域,有助于文学作家作品朝风格多样化发展。
二、社会历史文化环境与文学
相比自然环境而言,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更多地注意到了社会环境与文学之间的相互关系。具体来说,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充分地意识到了诸如先王遗风、民族融合、地方长官的政策和榜样的作用、朝代更替和属地变迁、历史文化渊源、统治者的政策以及历代文学传统等社会环境因素对文学产生的影响和制约。
先王遗风的影响作用表现在:
昔后稷封 ,公刘处豳,大王徙岐,文王作酆,武王治镐,其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穑,务本业,故《豳诗》言农桑衣食之本甚备。
唐有晋水,及叔虞子燮为晋侯云,故参为晋星。其民有先王遗教,君子深思,小人俭陋。故《唐诗·蟋蟀》《山枢》《葛生》之篇曰“今我不乐,日月其迈”;“宛其死矣,它人是 ”;“百岁之后,归于其居”。皆思奢俭之中,念死生之虑。
民族融合的影响作用表现在:
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故《秦诗》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及《车辚》《四载》《小戎》之篇,皆言车马田狩之事。
地方长官的提倡和榜样的作用对文学的影响表现在:
景、武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
朝代更替和属地变迁的影响作用有:
河内本殷之旧都,周既灭殷,分其畿内为三国,《诗·风》邶、庸、卫国是也。 ,以封纣子武庚;庸,管叔尹之;卫,蔡叔尹之:以监殷民,谓之三监。故《书序》曰“武王崩,三监畔”,周公诛之,尽以其地封弟康叔,号曰孟侯,以夹辅周室;迁邶、庸之民于洛邑,故邶、庸、卫三国之诗相与同风。《邶诗》曰“在浚之下”;《庸》曰“在浚之郊”;《邶》又曰“亦流于淇”,“河水洋洋”,《庸》曰“送我淇上”,“在彼中河”,《卫》曰:“瞻彼淇奥”,“河水洋洋”。
历史文化渊源的影响作用有:
陈国,今淮阳之地。陈本太昊之虚,周武王封舜后妫满于陈,是为胡公,妻以元女大姬。妇人尊贵,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陈诗》曰:“坎其击鼓,宛丘之下,亡冬亡夏,值其鹭羽。”又曰:“东门之 ,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此其风也。
历代文学传统的影响作用有:
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以显名。汉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之娱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而淮南王安亦都寿春,招宾客著书。而吴有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
最后谈一谈统治者的施政政策对文学的影响作用。关于这一点,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引用齐地齐诗的例子加以说明。他首先通过诗句“ 我于著乎而”,指出齐诗“舒缓”的特点,然后又在后文中解释了齐诗具备这一特点的原因:“初太公治齐,修道术,尊贤智,赏有功,故至今其士多好经术,矜功名,舒缓阔达而足智。”正是由于最初姜太公的治国政策,才最终使得齐地人民形成了“舒缓阔达”的风俗和性格特征,反映在文学上就造成了齐诗的“舒缓之体”。这也说明,在古人的著述中已经产生了“以地域特点评判文化特征的一种思维定式和写作习惯”②。
通过以上多段引文,我们就能很清楚地看到社会环境因素对文学领域的巨大影响;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社会环境因素对文学的影响制约作用在很多情况下同样是间接的,而处在二者之间的媒介仍然是各地由种种因素形成的风俗习惯。班固在叙述其创作《汉书·地理志》的缘由时引入了“风俗”的概念:“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唐孔颖达疏中认为这一说法:“是解风俗之事也。风与俗对则小别,散则义通。”③按照班固之意,由自然条件不同而形成的习尚叫“风”;由社会环境不同而形成的习尚叫“俗”。总而言之,风俗作为一种整体的行为模式,是由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共同塑造而成的。从这一点出发,风俗同文学可谓是一脉相承的。
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不仅提到了自然地理环境对文学的影响,而且更加倾向于社会历史文化环境对文学的影响作用,一方面,这表明班固是用全面的辩证的眼光看问题的,另一方面,因为自然环境相对而言是一个较为静止的概念,而社会历史文化环境则是一个比较动态化的概念,班固更多地注意了后者对文学的影响,这充分表明班固也是用发展变化的眼光看问题的,这就体现了班固的进步性。
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涉及到的文学作品几乎全是《诗经》,这固然与《诗经》本身的特点有关,但笔者认为,这也可以反映出班固作为一位具有浓厚正统意识的史学家所具有的那种根深蒂固的宗经观念,及其所处朝代的特殊时代风气。
在班固之外,汉代还有一些学者如王逸、郑玄等都曾论及各地民风与文学的关系。如王逸在其《九歌章句序》中说:“《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④正是源于楚地有“信鬼而好祠”之风,屈原才依据民间祭神乐歌改作或加工而成了《九歌》,因此使得《九歌》具有楚国民间祭神巫歌的许多特色;而郑玄的解经之作《诗谱》,则根据《尚书》《春秋》《史记》等书中有关史料记载,分别说明《诗经》十五国风、二雅、三颂产生的地域、时期、社会背景等,并排比谱系,显示了《诗经》各部分与时代政治、风土人情的关系。从生活年代来看,班固在王逸和郑玄之前,因此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所涉及到的地域风俗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应该对王郑二人有所启发,不仅如此,东汉之后,犹有众多文人学者注意到了文学地域性这一现象,并有许多杰出作品问世,虽然不能说这些优秀之作都受到班固《汉书·地理志》的影响,但完全可以说班固较早地意识到了地域文化与文学之间的这种关系,并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论述,从其所处时代而言,其眼光是超前的,其思想是具有前瞻性的,为中国文学及史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① 荀悦:《汉纪》,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03页。
② 王永:《先秦“愚宋”现象与〈汉书·地理志〉之地域文化观》,《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第2期,第57—63页。
③ 《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59页。
④ 黄灵庚:《楚辞章句疏证》,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742—7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