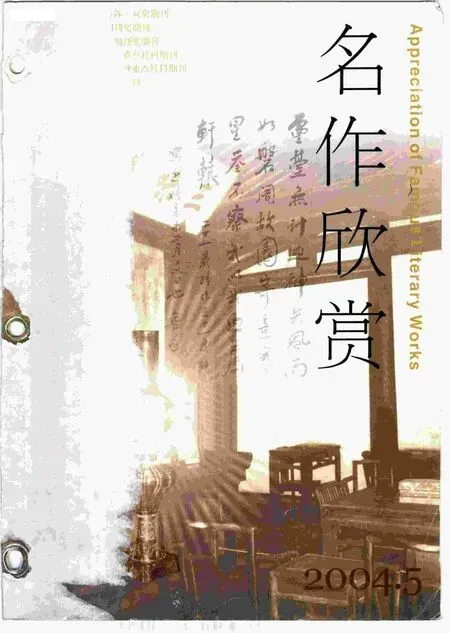映现与隐喻:《红楼梦》诗词对于形象建构的功能解析
⊙谢中元[佛山科学技术学院文学院, 广东 佛山 528000]
鲁迅说“自《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①,《红楼梦》把最具韵文学诗性特质的诗词与小说叙事文学熔于一炉,任诗意和写实氤氲为一体。诗词是《红楼梦》小说的魂魄。本文拟对小说人物自作诗词、叙述者评论诗词之于形象建构的功能略作探讨。
一、《红楼梦》诗词之于形象塑造的映现功能
大观园是诗性王国的巨型隐喻,女性化的宝玉,诗性的女子,通过咏诗、作诗、题诗、赛诗等一系列诗歌事件演绎着生命的诗意栖居。文本用诗性空间博弈专制伦理,宝玉、黛玉依靠纯粹的精神爱恋抵制名利逻辑,以此为契机建构了世俗烟火之外的纯美叙事。
首先,以客观立场或透过人物“第三只眼”传递的评论诗映现了人物的形象内涵。
小说第三回写宝玉黛玉初次见面的两首《西江月》,正是以否定的辩证法,映射出人性的复合性。如“: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时光,于国于家无望。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纨绔与膏粱,莫效此儿形状。”此段诗词没有辐射出纯古典的诗性意境“,痴痴傻傻”的视觉形象确为贬笔无疑。但颇具抒情张力的价值判断已潜藏其中。贾宝玉身居于珠围翠绕、艳婢姣童相伴的衣食享乐环境,备受宠爱,理应毫无“愁恨”,但贾宝玉偏偏“寻愁觅恨”。其仇恨来自于骨子里的价值取向,他对贾雨村等钻营官场之流不以为然,大骂八股文“不过饵名钓誉之阶”,阔论“仕途经济、应酬庶务”都是“混账话”,将家族责任与阶级诉求狠狠地予以嘲弄解构,任自己逍遥于功名利禄的游戏规则之外。掌握着话语命名权的其父贾政等贬斥宝玉“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这是伦理道德考量的自然逻辑。宝玉却悬置“三纲五常”伦理法则,对大观园年轻女子“昵而敬之”“、爱博而心劳”,肆意宣布“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儿是泥作的骨肉”,表征着审美无功利的美的理想。《西江月》以似嘲实赞的狡狯之笔,映现着贾宝玉的形象内涵。再如第三回描述林黛玉的词: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一双似泣非泣含露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比西子胜三分。全词没有细致勾勒其形、其态,但运用比喻手法展露了“病”“、泪”、心机聪敏、体态婀娜等。该段引入意象摹拟、虚笔写意的手法,描摹富于病态、风流绰约的美人,携带着男性悲天悯人的审美视角,没有一笔写“美”却又美到极致,关键是深入心理维度,把黛玉的鹤立鸡群、孤高自傲批示无疑。
其次,人物自作诗词映现了形象个性。
诗是大观园疗救生存大患的丹药,诸芳成立海棠诗社,宝黛之间以诗传情,香菱学诗,都是以诗衬人的经典情节。黛玉的风流别致、宝钗的含蓄浑厚、湘云的清新洒脱均有赖于诗词的冶炼,人物自作诗词不仅彰显性格特点,还要契合其为人行事及身世经历。如薛宝钗这一典型的封建才女,她出身皇商,端庄秀丽,口不臧否人物,博学敏捷。其性格特质与风格完全可从《咏白海棠》勾勒“,珍重芳姿昼掩门”既是自诫,又是对他人的诫告,体现这位侯门千金对自己高贵身份的矜持与对封建妇德的恪守。“淡极始知花更艳”兼具性格自况和审美追求的双重功能,宝钗罕言寡语、藏愚守拙、以退为进的处世原则,处处显示着一种自律、矜持和自信。最能深刻与宝钗达成同构的是柳絮词,他人柳絮词均不脱哀怨缠绵之迹,而她却以“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的乐观词句粉碎了清心寡欲的外在形象,有一种借东风扶摇而上的理想驱动,张扬出她潜意识里攀附上流的人生诉求。
与宝钗的敦厚平和不同,黛玉敏感多疑,善感使性,其诗也多与此同构。黛玉的《桃花行》就明显流露出“曾经离丧,作此哀音”的动因,被评为“夭亡口吻”(第七十回回评),可见“潇湘子稿”绝不同于“蘅芜之体”。最具诗性的《葬花辞》就极具形象映现功能,“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直抒父母双亡、寄人篱下的悲情,又自视甚高,粪土功名,与整个贾府格格不入。她见证了底层婢女的苦难,以及黑暗势力对人性的压抑摧残,深感世态炎凉、人情冷漠,因此以“未若锦囊收艳骨,一 净土掩风流。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一语标识孤傲不阿的性格。
二、《红楼梦》诗词与人物命运遇合的隐喻功能
《红楼梦》中的诗歌还被用以影射人物命运结局,这些预言、象征、暗示多显含蓄隐约,染上谶语色彩,具有隐喻性、寓言性风格。诗性王国“大观园”的崩塌,诗性身体们“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悲剧陨落,都在诗词的腾挪翻转中一一闪现。
首先,诗词预先隐喻小说人物结局。
如《金陵十二钗图册判词》正册副册十四首、《红楼梦曲》十四首等判词如同薄命女子命运演示的幻灯片,黛钗、元迎探惜、湘云、妙玉等诸人物结局的设定,在宝玉游太虚幻境中的诗词中均已透露。小说用预叙手法,提前隐约透露,尽显跌宕呼应之美。叙事小说若实写这些命运结局,多生坐实板结之感,无法抵达似真似幻效果,诗词的先天优势,就在隐喻含蓄中充分散发出来。此类诗谶了无痕迹地预示着人物的命运走向,但又契合人物性格逻辑的延展。
其次,回目清楚标注为人物谶语。
第二十回“制灯谜贾政悲谶语”呈现贾府众人制作灯谜,通过诗词暗示了除贾环外其他人未来的遭遇,“原(元)应(迎)叹(探)息(惜)”四姐妹即是归宿写照的典型。“能使妖魔胆尽摧,身如束帛气如雷,一声震得人方恐,回首想看已成灰”实指一响而散的爆竹,却隐喻元春荣华富贵瞬息即逝、不幸早死的命运;“天运人功理不穷,有功无运也难逢。因何镇日纷纷乱?只为阴阳数不通”用拨乱如麻的算盘暗喻迎春嫁给中山狼孙绍祖横遭摧残的结局;“阶下儿童仰面时,清明妆点最堪宜。游丝一断浑无力,莫向东风怨别离”以断线的风筝暗示探春在清明节远嫁不归;“前身色相总无成,不听菱歌听佛经,莫道此生沉黑暗,性中自有大光明”则以谜底“佛前海灯”隐喻惜春“独卧青灯古佛旁”的归宿。脂评逐一点出元春之谜预示其“才得侥幸,奈寿不长”,迎春之谜预示其“不得其夫”,探春之谜乃其“远适之凿”,惜春之谜则其“为尼之俄”。
再次,不是谶语但有人物谶语意味的隐喻。
有些作品虽不如谜语意思显豁,但亦有评点者指出其预示与照应功能。如王希廉的回评中就指出:“菊诗十二首与《红楼梦曲》遥遥相照,俱有各人身分。”②(第三十八回回评)明显的例子还有:第六十三回写宝玉与众姐妹在怡红院夜宴,抽签为令,花签上所刻古诗正是擎签人命运的暗语。袭人所抽的签题为“武陵别景”,用旧诗“桃花又见一年春”标注,用“二度春”来隐喻袭人在贾府没落后嫁与蒋玉菡。而薛宝钗的花签题为“艳冠群芳”,用唐诗“拭新曲一支为贺,任是无情也动人”标注,呈现她感情冷漠却又博人好感的特点。再如《咏白海棠》把大观园群芳诸人的思想、情趣、品格、命运显露出来,以“芳心无力”、“缟仙羽化”喻指断线风筝,指正探春离亲远嫁的命运谶言;“胭脂洗出秋阶影,冰雪招来露彻魂”写宝钗与丈夫不归,终陷冷落孤寂的结局。
最后,兼具映现、隐喻作用的。
黛玉的柳絮词既写本身的深切哀愁和悲愤呼声,也有对不幸命运的朦胧预感。“粉堕白花洲,香残燕子楼”,黛玉以曾游百花洲的西施、居住燕子楼的关盼盼等薄命女子自喻,任柳絮被东风摆布,预感着面对绝望时的无能为力。有些诗词虽无审美价值,但功能独具,如第十八回写元妃省春,命众姐妹各题一匾一诗。迎春的“园成景备特精奇,奉命羞题额旷怡。谁信世间有此境,游来宁不畅神思?”显得词句拙稚,内容空洞,枯燥重复,何尝不是她软弱柔细、听之任之的价值表现,也成为透视她悲惨命运的镜子。
从源头追问,曹雪芹悲天悯人、愤世嫉俗的思想在文化专制时代不可能放胆表达,而婉约、隐喻的诗词就成为作者隐蔽表达的方式。从作者和人物身份来讲,名门官宦、家族子弟都应具有高雅品味和诗词修养,以诗词代拟心声显得自然而然。更为关键的是,《红楼梦》“由来同一梦”的人生幻灭感,与诗词所营造出来的空灵缥缈十分匹配。《红楼梦》辅以诗词塑造人物,不仅与角色形象达成了自足的互证互释关系,还通过诗谶激活情节并隐喻了的人物的命运结局,在语用学角度上提升了叙事文本的诗性品格。也可以说,《红楼梦》诗词达到了个性化的高度,拓展了传统代拟诗词在小说中的功能。
①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见《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38页。
② 朱一玄编:《红楼梦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