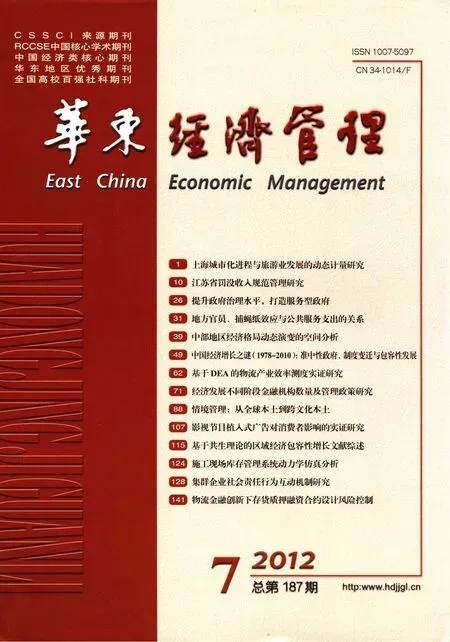双元组织能力:一个整合分析框架模型
沈 鲸
(1.长沙学院 法学与公共管理系,湖南 长沙 410003;2.中南大学 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3)
一、引 言
近年来,双元组织能力(简称为双元能力)的研究越来越受重视。在各类组织文献中反复出现的一个观点是,面对日益复杂动荡的环境,成功的组织既能有效运作当前的事业,又能主动适应明天的需要。具备双元能力的组织能有效平衡和融合管理中的各种悖论。研究者们使用双元能力理论解释了多种重要且复杂的组织现象,双元能力理论被广泛应用于战略管理、技术创新、组织学习和组织设计等领域,在实践中双元能力被认为是组织生存和绩效提升的基础。然而关于双元能力的形成动因和绩效后果至今仍未有统一认识,正如Gupta(2006)所说“虽然我们一致认为应该实现探索和利用的平衡,然而对于如何实现这种平衡我们却知之甚少”[1]。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双元能力的多层次分析框架,以期对双元能力的实现路径和绩效作用机制做出有益探索。
二、研究现状:动因—能力—绩效范式
对双元组织能力的研究除探讨双元能力的本质和内涵外,还包括对其影响因素和结果的研究。动因—能力—绩效范式认为影响企业绩效的直接原因是企业双元能力的强弱,而企业的双元能力又受到内外部因素的影响,企业可以通过控制双元能力来改善绩效。动因—能力—绩效范式较好地概括了双元能力的研究现状(如图1)。

图1 动因—能力—绩效范式
(一)双元组织能力的内部维度
双元能力理论的提出源于对管理中悖论的解决。单词“ambidexterity”起源于拉丁语“ambos”,原意是形容人双手皆灵巧的本领或状态。Duncan(1976)最早使用“organiza⁃tional ambidexterity”(双元组织能力,简称为双元能力)这一术语,借以隐喻组织所具有的既能适应渐进性变革又能适应突变性变革的特征[2]。March(1991)里程碑式的文章激发了对双元能力的广泛研究[3]。如今双元能力被广泛地应用以表示一个组织能同时实施不同的、相互竞争的战略行动的能力,其研究涉及组织学习、技术创新、组织适应、战略管理和组织设计等领域。学者们采取不同的视角和维度,提出了多对“相互竞争”的行动①,然而使用最多的还是March提出的概念:探索(exploration)和利用(exploitation)。国内学者张玉利等(2006)将其内部维度归纳为探索能力和开发能力,探索能力指从事变异、试验、柔性、冒险和创新等活动的能力,探索能力涉及搜索新的组织实践、发现新技术、新事业、新流程和新的生产方式等活动;开发能力包括从事提高效率、复制、选择和实施等活动的能力,通过对已有知识的提炼和传统惯例的承袭来营造组织的可靠性和稳定性[4]。
(二)双元组织能力的动因
双元能力动因一直是双元能力研究的热点,学者们从组织内外部因素提出了种种假设。大多数学者从组织内部出发,他们提出了结构型双元、情境型双元和领导基础型双元。结构型双元认为双元型结构是实现双元能力的保障。虽然双元型结构具体类型很多(如准结构、复杂结构等),但其本质是同时在不同的空间设置彼此相异的结构性机制,并配套相异的文化、结构、战略和制度,以应对对立性组成元素提出的竞争性要求。情境型双元的支持者们认为双元能力是高绩效组织情境的产物,由纪律、张力、支持和信任等因素构成的高绩效情境能使个体自己判断如何在一致性和适应性之间合理地分配时间和资源,从而帮助企业有效地平衡探索活动和利用活动 (Gibson&Birkinshaw,2004)[5]。领导基础型双元观点强调领导者或高管团队的某些特征在塑造双元能力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Mom等提出了“管理者双元性”的概念,把它定义为管理者能在特定时间内整合探索性与开发性活动的一种行为取向[6];Jansen等发现高管团队的某些特征对企业双元能力的形成具有积极作用,这些特征包括高管团队的理念一致性、高管团队的社会整合和高管团队的共同激励系统[7]。
另一部分学者从组织外部寻找动因,包括企业网络因素和环境因素。Lin(2007)通过分析1988—1995年95个企业的数据,发现具有高中心性网络特征和在网络中占据较少结构洞的企业更易采取双元型联盟[8];Jansen等(2005)首次对命题——当地环境条件影响着业务单位同时进行两种创新的程度进行实证检验,他们发现在高动态性和高竞争性环境中企业更可能同时进行探索性创新和利用性创新[9]。Auh和Menguc(2005)发现当面临日益激烈的竞争时,企业更注重追求探索和利用活动的平衡[10]。
还有研究者考察了其他因素。比如Atuahene-Gima(2005)发现市场导向指导着管理者在探索性活动和利用性活动间分配资源的决策[11];Venkatraman等(2007)发现具备丰裕资源的大公司更易获得双元能力[12]。
(三)双元组织能力的绩效结果
虽然学者们普遍认为双元能力是企业长期绩效的关键驱动因素,但实证研究的结果并不一致。一些研究者发现双元能力能直接正向地影响企业绩效,比如He和Wong(2004)首次在技术创新情境下检验了双元能力假说,基于206个制造企业的样本,He和Wong发现:①利用性创新战略和探索性创新战略的相互作用与销售增长率正相关;②探索性创新战略和利用性创新战略之间的相对不平衡与销售增长率负相关[13]。一些研究者认为双元能力对企业绩效具有权变的影响,比如Lin等(2007)通过实证检验发现双元能力的绩效效果不能一概而论,它随着企业的网络情境(网络中心性、结构洞、网络动态性)变化而变化[8]。一些研究者发现双元能力对绩效具有消极影响(Atuahene,2005)[11],还有一些研究者则并未找到双元能力—绩效联系的实证支持依据(Venkatraman,2005)[12]。
(四)存在的问题
通过对研究现状的分析,我们发现虽然双元能力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但动因—能力—绩效范式中的具体内容及各因素的相互关系未能统一,正因如此,虽然双元能力的作用得到肯定,但其形成路径及绩效作用机制依旧处于“黑箱”状态。综合来看,存在以下困境:第一,对动因的研究分散片面,从而缺乏对现实的指导意义。研究者往往基于特定的理论视角,专注于单因素的研究,选择变量涉及内部管理因素、组织自身特征、网络环境特征和外部环境特征。缺乏整合观点,没有具体区分各因素所起作用,存在对前因因素、调节因素、中介因素认识混乱甚至矛盾的现象。第二,对动因的研究大多是割裂的。现有研究多认为结构型动因、情境型动因、领导基础型动因是企业实现双元能力的独立的、相互替代的影响因素,比如Gibson和Birkinshaw(2004)就认为企业双元能力最好的实现方式是情境设计而不是结构设计[5]。然而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各动因之间应是相互增补、相互促进的,所以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探讨各层面各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第三,虽然学者们普遍认为双元能力是企业长期绩效的关键驱动力,也存在着大量对双元能力绩效效果的研究,然而实证分析结果却没有得出一致结论,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没有充分认识到双元能力与企业绩效之间联系的复杂性,没有明确检验效果的内部和外部边界条件;此外对双元能力和绩效缺乏统一的界定也会带来实证结果的不一致。
三、双元组织能力的整合分析框架
Simsek(2009)认为理论研究中存在的分散化、割裂化、简单化问题造成了实践中双元组织能力构建的困境[14]。未来研究将采取综合的观点,进一步整合和扩展现有研究。要提出该领域的整合分析框架,必须:第一,提炼并区分各影响因素的作用和地位;第二,理清各影响因素的相互关系;第三,正确测量双元组织能力和组织绩效。本文构建的双元能力整合分析框架如图2所示。

图2 双元组织能力的整合分析框架
首先,该模型认为双元能力及其绩效效果受组织层次因素、网络层次因素、环境层次因素综合作用影响。其中组织层次因素和网络层次因素起主要动因作用,环境因素调节着双元能力与绩效之间的关系。模型在组织层次选取双元型结构、组织情境和高层管理团队特征作为主要动因。虽然将网络层次因素与双元组织能力联系起来的研究不多,但根据社会经济学观点,企业天然地嵌入在网络中,现实中企业的很多探索活动和利用活动都是通过企业网络来实现,网络已成为企业获取资源的重要渠道,企业网络特征已成为企业行为的重要限制因素和推动因素 (Powell et al.,1996)[15]。借鉴网络观的研究成果,模型认为企业的网络位置和网络成员之间的关系模式将对双元能力形成产生重要影响。权变视角将环境、战略、结构等重要因素间的匹配视为组织获得高绩效的关键(如Burns&Stalker,1961)[16],模型选取环境因素作为双元能力—绩效之间的调节变量以明确双元能力作用的边界条件。
其次,与现有研究不同,模型认为组织层次动因、网络层次动因、环境层次因素不是割裂地、单独地起作用,而是相互影响,三个层次的因素将联合起来对双元能力施加影响。故模型将分析这些变量间的相互作用。比如在组织层次,双元型结构、高绩效组织情境以及高层管理团队特征三动因相互支持、相互补充,三者良性互动共同促进企业双元能力的形成和演进;组织层次动因将对网络层次动因施加影响,组织层次动因的具备有利于网络层次动因的实现。
最后,模型选取探索能力和利用能力作为双元组织能力的两个维度,因为探索能力和利用能力之间的直交关系已基本得到认同(Gibson&Birkinshaw 2004,Gupta et al.2006)[1,5],现有研究中对双元能力的测量存在三种不同方法:用探索能力和开发能力的绝对差代表两种能力间的不平衡程度(He&Wong,2004)[13];用探索能力和利用能力的交互项(乘积)代表两种能力的平衡程度(Gibson&Birkinshaw,2004)[5];用探索能力和利用能力两者的相加值表示双元组织能力(Lubatkin et al,2006)[17]。Edwards指出将任何两个或多个指标连结成一个单独指标时,都有信息流失以至于单独指标在测量时失真[18]。Lubatkin等通过构建回归方程,比较了以上三种计算方式对组织绩效的影响,发现唯有相加方法未达到信息流失的显著水平。故本模型用探索能力与利用能力的相加值来测量双元组织能力[17]。在绩效方面模型用成长性指标和获利性指标来全面衡量组织的长期绩效和短期绩效,具体而言包括销售收入增长率、市场占有率和税前利润增长率三个指标。
四、整合分析框架的主要理论假设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提出一个关于双元组织能力的整合的、多层次的分析框架,故下文将对模型中首次提出的、主要的理论假设进行介绍,对那些已经达成共识和被检验过的命题不做详细分析。
(一)组织层次动因的相互关系
学者们已就双元型结构、组织情境、高层管理团队的某些特征对双元能力的影响进行了充分论述。本文认为三种动因对双元能力构建不可或缺,他们相互支持、相互补充,三者良性互动共同促进企业双元能力的形成和演进。
(1)双元型结构是双元能力构建的基础。钱德勒的“环境—战略—结构”命题认为企业战略应与环境相匹配,企业的组织结构随着经营战略的变化而变化。处于稳定环境中的企业选择单一产品战略和职能结构,动态环境中的企业采取多元化战略和“复杂部门结构”(Engdahl et al.,2000)[19]。双元能力理论的产生以高度动态复杂的环境为背景,日益变化迅速的环境要求企业采取兼顾利润和增长的双元战略,无论是“空间分割”结构还是平行项目结构都是为实施双元战略做准备,双元型结构为管理组织内部冲突、协调差异的文化、员工、战略之间矛盾提供了组织平台。双元型结构的建立不仅使相异的文化、制度、价值观并存,同时也催生了公司的共同价值观和文化,这种共同价值观和文化本身就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所以双元型结构为情境动因的形成提供了结构基础。Gibson和Birkinshaw(2004)认为结构情境是组织情境的重要组成部分[5],Güttel和 Konlechner(2009)则认为半结构和流动的项目结构是结构情境的构成要素[20],由此可见组织情境中包含必要的双元性结构要素。此外双元型结构有利于提高高层管理团队的知识异质性程度和行为整合水平,探索性单元和利用性单元的负责人往往在知识、能力、经历和个性上存在差异,他们使高管团队具备不同的文化背景和观点,从而能优化团队决策,有利于团队在战略认知层面形成悖论认知能力;多样化知识和观点的并存是高管团队成员高质量的沟通和有效决策参与的前提,开放的沟通和决策参与是行为整合的任务性维度(Hambrick,1994)[21];双元型结构还为培育具有双重性思维特征的领导者提供平台。
(2)高绩效组织情境为双元能力构建提供环境支持。情境型动因的实质是“桥”,它将进行不同战略活动的单元联结起来以发挥整体协同效应,Gibson和Birkinshaw(2004)认为情境型双元并不直接创造高绩效,而是通过创造内部环境以形成双元的个人行为和集体行为[5]。首先,高绩效组织情境是双元型结构的整合机制,共同的战略意图、集体价值观和组织文化、个体间持续的知识流动、员工卓越的知识吸收和转化能力成为减少冲突,实现协同效应的自下而上的机制;其次,组织情境支撑的一致的共同目标和价值理念能“压倒”高管团队中由于异质性导致的冲突视角,有利于统一高管团队的理念,提高悖论整合的效率;最后,提倡支持和帮助的组织文化同样能增强高管团队成员间相互信任、相互接纳的情感承诺,促进高管团队成员的合作,保证了团队多样化知识和观点的充分融合。可见高绩效组织情境有利于增强高管团队的理念一致性和行为整合水平。
(3)高层管理团队是双元能力构建的核心。随着市场分化和竞争日益加剧,过去“企业英雄”式的领导者无法拥有解决所有问题的答案,必须与其他组织成员分享领导权力,并且分担对组织绩效的责任。基于经营环境的复杂性和动态性特征,Ireland和Hitt(1999)指出,战略领导的趋势已逐渐从传统上重视伟大的个人领导转变为卓越的团队领导[22]。高管团队最典型的工作任务就是对公司整体绩效和发展方向有重大影响的战略决策。高层管理团队的知识异质性、理念一致性和行为整合对双元能力构建具有积极影响。高绩效的组织情境是通过组织制度、文化建设和组织成员思维方式的转变来自下而上地实现悖论的融合,然而情境型动因作用的发挥离不开领导型动因的支持,因为高管团队既可以影响组织情境的设定,也能够影响组织成员的行为。高管团队能对空间分割的单元实施自上而下的整合,双元能力的早期研究者们尤其重视高管团队的整合作用,Tushman和O’Reilly认为来自高管层的紧密协调才能使结构分割的单元相互支持、免于分离,没有双重性的高管团队双元组织很难构建[23]。双元型结构作用的发挥依赖于领导型动因和情境型动因。领导型动因在三种动因中居于核心地位,它贯穿于双元能力建设的全过程,对双元能力产生直接影响,同时通过培育和管理结构型动因和情境型动因间接作用于双元能力。
三者的关系如图3所示。进而本文提出如下假设:P1a:双元型结构与双元组织能力正相关;P2a:高绩效组织情境与双元组织能力正相关;P3a(1):高管团队的知识异质性与双元组织能力正相关;P3a(2):高管团队的理念一致性与双元组织能力正相关;P3a(3):高管团队的行为整合程度与双元组织能力正相关;P4:双元型结构、高绩效组织情境与高管理团队的上述特征将综合地导致更高水平的双元组织能力。

图3 组织动因的相互关系图
(二)网络层次因素的影响作用
从网络层面上,企业在网络中的位置以及网络成员之间的关系模式等特征极大地影响了双元组织能力。很多研究证明企业在网络中的位置会影响企业的行为与产出,在多数研究中学者们都选择位置中心度(centrality)指标来衡量企业在网络中的位置。
企业的位置中心度对双元能力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中心度越高的企业比外围成员能更多地获得知识溢出效应和信息交流带来的益处,能更充分地识别环境中潜在的机遇和威胁,同时也有利于企业利用外部资源进行探索和利用活动。另一方面过高的中心度对双元能力有消极影响,过高的位置中心度可能会导致信息的过度负担和组织注意力的分散,当信息量超出组织的信息处理能力时,有益的信息和资源浮于表面,反而不利于实现双元组织能力,Koka和Prescott(2002)的研究表明在信息处理能力一定的条件下,当信息量少时,企业只能处理少量的信息;当信息量规模适中时,企业能处理最多的信息;当信息量很大时,由于认知限制企业反而只能处理少量信息[24]。所以网络中心度与双元能力是一种倒U型曲线关系,当中心度小于某一临界值时,网络中心度对双元能力构建具有正向影响,当超过这一临界值时网络中心度越高反而越不利于双元能力的形成。所以模型提出假设P5:网络中心性对双元能力的影响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
网络规模指与焦点企业直接相关联的合作伙伴的数量。网络规模越大意味着企业的关系资源越丰富,越有可能实现规模效应,跨越双元能力实现的阈值限制(lavieD,et al.2006)[25]。网络规模既有利于形成一致共识的知识体系,又能提供使用互补性知识和技能的通道。企业维持更多的网络联结有助于其自身理解什么是重要的知识以及这些知识的来源(Powell,et al,1996)[26],有助于同合作者分享更多的公共知识平台(Uzzi,1996)[27],有利于合作双方减少机会主义行为和降低风险,亦可以让愈来愈多单位形成一致共识的知识诠释,从而增加组织学习的深度(Huber,1991)[28]。另一方面,随着企业网络规模的扩大,焦点企业更可能利用其他网络的信息。企业网络规模的大小意味着焦点企业可以获取的知识资源的丰裕程度,当与企业联系的外部实体数量越多时,网络中知识资源的规模及异质性越强,企业获得外部知识的渠道也就越多,从而增加组织学习的广度。然而过度的网络规模对双元能力构建也有消极影响:网络规模过大会增加企业整合新知识的成本;随着网络规模的扩大越来越多的新知识需要被整合到组织的知识体系中,企业面临着知识整合的技术和组织挑战;其次管理差异化的网络关系需要不同的技巧和流程,交流障碍将妨碍协同效应的形成。然而合作伙伴的确定是企业主动搜寻的结果,Katila和Ahuja(2002)认为出于成本考虑企业不大可能出现“过度搜寻”的情况[29]。所以本文认为网络规模对双元能力表现为积极影响。即提出假设P6:网络规模与双元能力线性正相关。
(三)组织层次因素与网络层次因素的相互影响
当来自网络的知识、信息和资源超过了组织的信息处理能力时,位置中心度将消极地影响双元能力,此时如果组织采用了双元型结构,这种消极影响可能得到抑制。因为结构灵活、联结松散、差异化程度高的探索性单元能更有效地从网络中提取探索性知识和信息;而权力集中、联结紧密、一致性程度高的利用性单元在提取利用性知识和信息方面更有效率。相反在单一结构形式下,整合冲突的资源、信息的意愿和能力都较小。故本文提出P1b:双元型结构正向地调节着网络位置中心度与双元组织能力之间的倒U型曲线关系,也即当组织采取双元型结构时倒U型曲线的顶点将向右上方移动。网络规模扩大意味着组织需要整合的知识和信息内容增多、差异化程度提高,整合所面临的技术和组织挑战增加,整合成本增加,而双元型结构能提高组织鉴别并整合有价值的知识和信息的能力,故本文提出P1c:双元型结构正向调节着网络规模与双元组织能力之间的正向关系,即当组织采取这种结构时,正向关系增强。
高绩效的组织情境在位置中心度、网络规模对双元能力的影响中具有类似的调节作用。高绩效组织情境通过绩效管理和社会支持的一系列“硬性”元素(如纪律和张力)和“软性”元素(如支持和信任)支持并鼓励员工同时追求探索性行为和利用性行为,在高绩效组织情境中员工更有可能打破固有模式,进行跨边界的思考和探索,从而能更全面充分地利用网络资源,员工之间的相互支持和积极互动有利于提高信息收集、甄别、分配、使用的效率,从而使组织更有效地发挥高网络中心性和大网络规模的优势。故本文提出P2b:高绩效组织情境正向调节着位置中心度与双元组织能力之间的倒U型曲线关系,也即在该组织情境中,倒U型曲线的顶点将向右上方移动。P2c:高绩效组织情境正向调节着网络规模与双元组织能力之间的正向关系,即当组织具有高绩效组织情境时,正向关系增强。
Hambrick认为行为整合包括了一个社会性维度(团队成员的合作行为)和两个任务性维度(团队成员的开放沟通和决策参与)[21], Siegel和Hambrick(1996)指出在行为整合性高的高级管理团队中鼓励“认知的冲突”,故团队成员能就各项战略事宜进行充分讨论和辩论,从而更好地利用网络知识和资源[30];Hambrick(1998)认为行为整合能使高级管理团队综合各种知识和视角以迅速回应市场[31]。当行为整合程度高时,高质量的信息交换和集体决策程序能使高管团队更好地协调和管理由位置中心度和网络规模带来的矛盾的信息、资源与利益;行为整合能提升组织对外部机遇的认知程度。相反,当高级管理团队缺乏行为整合时,高层管理者倾向于专注与自己的领域相关的外部资源和信息,排斥任何的“不和谐”因素,高层管理团队将更依赖于正式的规则和制度,甚至陷入“能力陷阱”。所以,本文提出:P3b:高层管理团队的行为整合水平正向调节着网络中心度与双元组织能力之间的倒U型曲线关系,也即当行为整合水平高时,倒U型曲线的顶点将向右上方移动。P3c:高层管理团队的行为整合水平正向调节着网络规模与双元组织能力之间的正向关系,即当行为整合水平高时,正向关系增强。
(四)环境变量对双元能力—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
组织理论强调环境的影响作用,有学者认为环境因素是双元能力作用的重要边界条件(如Siggelkow&Levinthal,2003)[35]。动态性指组织环境的变化程度和不可预见程度,在稳定的环境中由于消费者需求、竞争对手、技术等变化缓慢、因果关系稳定,企业常可通过建立稳定路径来进行管理,企业没有持续创新的压力,深度利用现有能力和资源就能带来丰厚的利润回报。而在高度动态的环境中,迅速且非连续性的变化常导致信息不准确和过时,此时不可能通过规范的战略制定程序获得高绩效,动态环境要求企业扩大信息获取范围,具备战略灵活性。在动态环境中同时追求探索和利用既能使企业的产品和服务避免迅速过时,又能确保系统的效率和稳定的现金流,所以在动态环境中具有双元能力的企业能提升绩效水平,而在稳定环境中通过充分利用现有竞争优势企业更易获得成功。故模型提出P7:环境动态性正向调节着双元能力与组织绩效的关系,即环境动态性越高,关系越强。
环境复杂性程度是指组织环境中的要素数量、差异程度以及要素间的相关程度。复杂性程度高意味着环境要素数量多且差异程度大,它要求企业在进行战略决策时要充分考虑外界环境中多种异质的行为和关系,处于简单环境中时,企业可在现有体系中运营以提高效率,比如年复一年地采用同样的生产程序和市场经验,提供单一的产品,然而在高复杂性环境中单一的商业模式无法满足多样性的需求。Lumpkin和Dess(1995)认为在复杂的环境中采用过分简单的战略制定程序会妨碍组织绩效提升[36],Jansen等(2005)认为在高度竞争的环境中组织若能在扩展当前产品和服务的同时防御好现有市场,则可获得成功[37],刘谷金(2011)认为动态能力能够使企业不断创造出新的产品或服务以维持和更新企业的竞争优势[38]。因为具备双元能力意味着企业有更广的战略选择,能同时进行探索活动和利用活动,所以环境的复杂程度越高,双元能力的绩效效应越明显。也即,P8:环境的复杂程度正向调节着双元能力与组织绩效之间的关系,环境复杂性越大,双元能力对绩效的影响越强。
五、结束语
当前双元组织能力理论被广泛应用于战略管理、技术创新、组织学习和组织设计等领域,双元组织能力理论正发展成为一种新兴的研究范式,然而研究的分散性正成为该研究向纵深发展的一大障碍,公认的整合框架模型的缺乏是目前研究的一大难题。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尝试提出了一个多层次的整合分析框架模型,该模型认为双元能力及其绩效作用受组织层次因素、网络层次因素、环境层次因素综合作用影响,组织层次和网络层次因素是双元组织能力形成的主要前件,环境因素调节着双元组织能力的绩效效果;文章还分析了各组织内动因的相互关系以及组织层次动因和网络层次动因之间的相互关系,为全面理解双元组织能力的前件和结果提供了思路。另外模型对几个潜在变量进行了明确定义,对于通过结构方程模型等工具进行实证研究是具有一定意义的。
然而本文的研究也存在着一些局限:首先,模型是在既有研究基础上选择构念展开讨论,这种方法有利于概念的清晰和收敛,然而也有可能忽视其他的变量。其次,在双元能力—绩效关系中,模型只探讨了环境动态性和环境复杂性两个因素的调节作用,其他的环境或组织自身特征也有可能对双元能力—绩效关系产生影响,对这些因素的深入研究不但有利于理论的完善也具有现实的管理意义。最后,模型是从静态视角对双元组织能力进行解构,然而双元组织能力的本质是一种动态能力(O’Reilly&Tushman,2008)[39],双元能力的实现并不是在某一时点实现探索活动和利用活动的最大化,而是使组织能根据环境的变化而达到动态的平衡,所以未来研究将深挖双元能力作为一种动态能力的性质,既关注双元能力内部维度的动态发展,又关注双元能力实现形式的动态变化和相互转化。
[注 释]
①比如灵活性和效率(Adler et al.1999)、研发宽度和深度(Ka⁃tila&Ahuja,2002),探索性学习和利用性学习(Kang&Snell,2009)、一致性和协调性(Gibson&Birkinshaw,2004)、颠覆性创新和维持性创新(Smith&Tushman,2002)。
[1]Gupta A K,Smith K G,Shalley C E.The interplay between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06,49(4):693–706.
[2]Duncan R.The ambidextrous organization:designing dual structures for innovation[J].The Management of Organiza⁃tion,1976,(1):167-188.
[3]March J G.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 in organizational learning[J].Organization Science,1991,(2):71–87;
[4]张玉利,李乾文.双元型组织研究评介[J].外国经济与管理2006,(1):1-8.
[5]Gibson C B,Birkinshaw J.The antecedents,consequences and mediating role of organizational ambidexterity[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04,47:209-226.
[6]Mom T J M,Van den Bosh F A J,Volberda H W.Understand⁃ing variation in managers’ambidexterity:Investigating direct and interaction effects of formal structural and personal Coor⁃dination mechanisms[J].Organization Science,2009,20(4):812-828.
[7]Jansen,George,et al.Senior Team attributes and Organiza⁃tional ambidexterity:The moderating role of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J].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2008,(7):982-1107.
[8]John.L,Haibin Y,Irem D.The performance consequences of ambidexterity in strategic alliance formations:empirical inves⁃tigation and computational theorizing[J].Management Sci⁃ence,2007,53(10):1645-1658.
[9]Jansen J J P,van den Bosch F A J,Volberda H W.Managing potential and realized absorptive capacity:How do organiza⁃tional antecedents matter?[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05,48(6):999-1015.
[10]Auh S,Menguc B.Balancing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The moderating role of competitive intensity[J].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2005,58:1652-1661.
[11]Atuahene G K.Resolving the capability-rigidity paradox in new product innovation.[J].Journal of Marketing,2005,69:61-83.
[12]Venkatraman N Lee C H,Iyer B.Strategic ambidexterity and sales growth:A longitudinal test in the soft-ware sector[C].Eearlier Version Presented at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Meetings,2005.
[13]He Z L,Wong P K.Exploration vs.exploitation:An empiri⁃cal test of the ambidexterity hypothesis[J].Organization Sci⁃ence,2004,15:481-494.
[14]Zeki Simsek.Organizational Ambidexterity:Towards a Multi⁃level Understanding[J].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2009,46(6):597-624.
[15]Powell W W,Koput K,Smith D L.Interorganizational collab⁃orations and the locus of innovation:networks of learning in biotechnology[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96,41:116-145.
[16]Burns T,Stalker G M.The Management of Innovation[M].London:Tavistock,1961.
[17]Lubatkin,Simsek.Ambidexterity and Performance in small-to medium-sized firms:the pivotal role of top management team behavioral integration.[J].Journal of management,2006,(10):646-672.
[18]Edwards J R.Problems with the use of profile similarity indi⁃ces in the study of congruence in organizational research.[J].Personnel Psychology,1993,46:641-665.
[19]Engdahl R A,Keating R J,Aupperle K E.Strategy and struc⁃ture:chicken or egg?reconsideration of Chandler’s para⁃digm for economic success[J].Organization Management Journal,2000,18(4):21–33.
[20]Wolfgang H Güttel,Stefan W Konlechner.Continuously Hanging by a Thread:Managing Contextually Ambidextrous Organizations[J].Schmalenbach Business Review,2009,61(4):150-171.
[21]Hambrick D C.Top management groups:a conceptual inte⁃gration and reconsideration of the“group”label[J].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1994,16 :171-213.
[22]R Duane Ireland,Michael A Hitt.Achieving and maintaining strategic competitiveness in the 21st century:The role of stra⁃tegic leadership[J].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Execu⁃tive ,1999,13(1):43-57.
[23]Tushman M L,O’Reilly C A.Ambidextrous organizations:Managing evolutionary and revolutionary change[J].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1996,38:8-30.
[24]Koka B R,Prescott J E.Strategic alliances as social capital:a multidimensional view[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2,23:795-816.
[25]Lavie D,Rosenkopf L.Balaning exploration and exloitation in alliance formation[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06,49(4):749-818.
[26]Powell W W,Koput K W,Smith-Doerr L.Interorganization⁃al collaboration and the locus of innovation:Networks of learning in biotechnology[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96,41(1):116-145.
[27]Uzzi B.The sources and consequences of embed ness for the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organizations:The network effect[J].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96,6 1(4):674-698.
[28]Huber G P.Organizational learning:The contributing process and the literatures[J].Organization Science,1991,2(1):88-115.
[29]Katila R,Ahuja G.Something old,something new:A longitu⁃dinal study of search behavior and new product introduction[J].AcademyofManagementJournal,2002,45:1183-1194.
[30]Siegel P A,Hambrick D.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top management teams[J].Advances in Stra⁃tegic Management.1996,13:91-119.
[31]Hambrick D C,Li J,Xin K,et al.Compositional gaps and downward spirals in international joint venture management[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1,22:1033-1053.
[35]Siggelkow N,Levinthal D A.Temporarily divide to conquer:Centralized,decentralized,and reintegrated organizational approaches to exploration and adaptation[J].Organization Science,2003,14:650-669.
[36]Lumpkin G,Dess G G.Simplicity as a strategy making pro⁃cess[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95,38:1386-1407.
[37]Jansen J J P,van den Bosch F A J,Volberda H W.Manag⁃ing potential and realized absorptive capacity:How do organi⁃zational antecedents matter?[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05,48(6):999-1015.
[38]刘谷金.企业动态能力与企业绩效结构关系研究[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63-67.
[39]O’Reilly,Charles A,Michael L Tushman.Ambidexterity as a dynamic capability:Resolving the innovator’s dilemma[J].ResearchinOrganizationalBehavior,2008,28:185-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