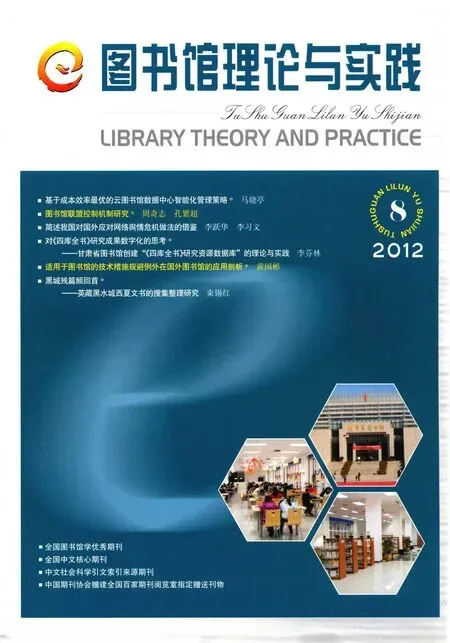明代宦官与图书刊刻考述
●高志忠,温 斌
(1.暨南大学 中文系,广州 510632;2.包头师范学院 文学院,内蒙古 包头 014030)
一
明代官刻比前代较为发达,且首开“内府刻书”之先河,由司礼监主持,这和明代倚重宦官有直接关系,他们不仅把持朝政,也掌握了国家主流出版、传播机构。《北京志·故宫志》“明宫刻书”条记:“嘉靖十年(1531年),司礼监有工匠1583名,其中从事刻书的1200余人,规模相当庞大。经厂内部分工精细,有刊字匠315名,刷印匠134名,折配匠189名,裱背匠293名,笺纸匠62名,裁历匠80名,笔匠48名,画匠76名,黑墨匠77名。[1]486按这样的计算,司礼监1583名工匠中有1200多人从事书籍刊刻,经厂人数占了司礼监总编制的80%之多,可以看出内府刻书的恢弘气势。刘若愚《酌中志》卷18“内板经书纪略”对此有专门记载:[2]
凡司礼监经厂库内所藏祖宗累朝传遗秘书典籍,皆提督总其事,而掌司、监工分其细也。自神庙静摄年久,讲幄尘封,右文不终,官如传舍,遂多被匠夫厨役偷出货卖。柘黄之帙,公然罗列于市肆中,而有宝图书,再五人敢诘其来自何处者。……即库中见贮之书,屋漏浥损,鼠啮虫巢,有蛀如玲珑板者,有尘霉如泥板者,放失亏缺,且甚一日。若以万历初年较,盖已什减六七矣。……祖宗设内书堂,原欲于此陶铸真才,冀得实用。按《古文真宝》、《古文精粹》二书皆出于老学究所选。
上述文献整体介绍了司礼监所属经厂内从事书籍刊刻的人数之多,人员分工之细,以及库内所藏皆历代遗存秘书典籍。并就万历以后,国势衰微,由于疏于管理,经厂所存版片或被当柴烧掉,或被监管人员盗卖掉的状况。从文献中,我们还知道,宦官教育机构内书堂弟子的部分教材与课本,也是于内府刊刻和收藏的,这里也当是他们获取“私书”的来源之一。
关于司礼监刻书在明代刊刻机构中的地位与作用,张琏在《明代中央政府出版与文化政策之研究》中指出,“明代刊刻从盛衰情况看,前期以司礼监刻书为主,正统以降,渐趋寥落,后期以南北二国子监刊刻为主。”他还指出,“就出版数量与地位而言,司礼监刻书种类与数量最多,南京国子监次之,北京国子监最少。”[3]
又《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87,史部四十三《经厂书目一卷》云:“明内府所刊书目也。黄虞稷《千顷堂书目》有此书,亦作一卷。经厂即内番经厂,明世以宦官主之。书籍刊版,皆贮于此。所列书一百十四部,凡册数、页数、纸幅多寡,一一详载。盖即当时通行则例,好事者录而传之。然大抵皆习见之书,甚者《神童诗》、《百家姓》亦厕其中,殊为猥杂。今印行之本尚有流传,往往舛错,疑误后生。该天禄石渠之任,而以寺人领之,此与唐鱼朝恩判国子监何异!明政不纲,此亦一端。而当时未有论及之者。宜冯保科私印,其文曰内翰之章也。案冯保印文,见所作《经书辑音·序文》末。”[4]
这里提及的内府本具体刊印的书目,在《酌中志》卷18《内板经书纪略》中有更为详细庞杂的列举,所涉经、史、子、集各部皆有。
司礼监经厂本的特点是,“册首均钤有‘广运之宝’的印记,雕刻精良,而且均刻有句读,缺点是校勘不精”。[5]57这也印证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说其“往往舛错,疑误后生。”
事实上,《酌中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所提的经厂都很笼统。内府刻书分别在3个经厂进行。《北京志·故宫志》对此给予分别介绍:
汉经厂,设官不详。由太监若干员管理。每遇收选太监,则拨数十名习念佛教诸品经忏。其是否持戒,听其自便。每遇万寿节。正旦、中元等节,于宫中建道场,遣内大臣瞻礼,扬幡挂榜,如外界之应付僧所办之事。其僧伽帽、袈裟、缁衣亦与外界僧人相同,只是不落发。事毕,仍各易太监服色。万历间曾选经典精熟、心性老成、持斋者数员,教习宫女数十人,于佛前作法事,行香念经,如同尼姑,亦不落发。厂在皇城以内。
番经厂,设掌印太监一员,贴厂太监、各司房太监数十员,于各衙带衔。此厂习念西方梵呗经咒。宫中英华殿所供西番佛像皆陈列,近侍太监司其灯烛香火。其隆德殿、钦安殿亦各有近侍太监专陈设。凡做好事,则悬设幡榜。惟此番经厂,乃立监斋神于门旁。本厂内官,皆戴番僧帽,穿红袍、黄领、黄护腰。
道经厂,设掌厂太监一员,贴厂各司房太监数十员,于各衙门带衔。有数十名太监,习演道教诸品经忏。凡建醮做好事,亦隆德殿或钦安殿悬幡挂榜,而云璈清雅,俨若仙音。万历皇帝初欲选宫女数十人,令习道教,为女道士。掌坛太监认为诸天神将甚严肃,恐女子无知,惹咎不便。因而中止。[1]276
通过以上三则文献的介绍,我们可知经厂不仅是皇家刊刻书籍的场所,同时也参与佛、道事务并进行相关戏曲编演等,从而承担着宗教教化和宗教仪礼的作用。此外,从教习宫女方面而言,足见皇家希冀奴婢们都能对佛道有所虔诚,这样一心向善,也便于麻痹其思想,更便于其管理和使用。事实上皇家以佛道仪礼来达到儒家稳定性统治,佛道只是他们进行管理的有力工具而已。
而据《北京志·出版志》记:“内府(皇室) 刻书,大部分是以明朝皇帝的名义编著的有关政教礼治的书。……汉经厂以刻本朝四部各书(经、史、子、集)为主,番经厂以刻佛经为主。道经厂以刻道家著作为主。”[5]这样的分类,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内府刻书以儒、释、道三家为主。
而番经厂又以刊刻藏经为主,这既影响了宦官的信仰也沟通了汉藏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同时也是儒释道三家合流在皇家意识形态的体现。司礼监刻书,就书目种类而言,所刊之书多为经史读本、国家政令及皇帝御制之书。按类别而分,有御制书、中宫御制书,此外还刊刻内府授课之读本、释道经典及殿前对策之试题,还有为数不少的通俗类文学读物。如嘉靖元年(1522年),司礼监刊刻《三国志通俗演义》,凡二十四卷二百四十则。[6]
司礼监刻书中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地方在于,虽然是皇家出版机构,但也有许多私刻、自刻本在这里刊刻。《北京志·出版志》中这样解释自刻本:“所谓自刻本是作者自己出资主持刻印的书本。在北京地区尤为盛行,自刻本有两种形式:一是作者出资委托书坊或雇用刻工,按自己的意图,设计版式行款刻印;二是不但自己出资,还要自己写样上版,然后委托书坊或雇用工匠刻印。自刻本一般校勘精审,刻印精良。若是作者自己手写上版,就更为珍贵。”[5]81
万历年间,宦官金忠曾自刻《御世仁风》[7]敬献帝王,进行劝谕。但他没有选择在司礼监刊刻,而是选择当时刻工精细的安徽新安,这还说明金忠的物质经济雄厚。作者非赢利性刊刻,一是出于个人爱好,一是出于政治利益。
对于司礼监宦官来说,他们常常根据个人的喜欢而刊刻不同书籍。《酌中志》卷5记载:“神庙左右内臣,如孙海、客用之流,日以狗马拳棍导神庙以武,冯(保)则凡事导引以文,蒙养之绩,在冯为多。司礼监所刻《启蒙集》《四书》《书经》《通鉴直解》《帝鉴图说》等书,至今见之者,每为咨嗟叹息焉。”卷7记载:“先监(陈矩) 每暇即玩味《大学衍义补》,或令左右诵听。乙巳之冬,奏进二部,请发司礼监重刊……”卷9:“先监陈矩去世之后,十余年才刊刻完毕《大学衍义补》。累臣曾具草募化同会之人,捐资印造。”卷16记载:“万历年间,惟孙太监隆,先监之同年也,多学善书,曾刻《通鉴总类》《中鉴录》等书。”可见,经厂除了刊刻御制、典制书籍等外,权势宦官完全可以根据个人喜好和兴趣所在进行相关书籍刊刻。
而据《北京志·出版志》记,宦官二十四衙门除了司礼监刻书外,其它一些监局偶尔也会刊刻专业类书籍。如御马监曾刊刻过《马经》一书。[5]89
二
通过以上论述,就司礼监刊刻书籍的目的和意义可以概括为以下两点:
1 整理古籍
书籍刊刻与出版中,很多情况下要进行注释、翻译、校勘、辨伪、考证、版本目录的整理。如宦官扶安、晏宏曾编著目录学著作《通鉴纲目》。《续四库提要三种》卷2中这样说明:“《资治通鉴纲目集说五十九卷前编二卷》明扶安撰,晏宏补校。……此书江南图书馆所藏嘉靖原刊本,附录之以见后世宦官之无李巡其人也。”[8]《酌中志》卷22对此也有记载:“今经厂所贮《晏公纲目》板一部,宏遗物也。内臣多爱,重刷印之。”司礼监由于地处宫廷,藏书丰富,征引弘富,这些有利的客观条件是其他外廷部门所无法比拟的,只是限于工作人员学识有限,或疏于管理,所以不免存在一些讹误。
2 传播文化
宦官刊刻什么书籍原则上是受命行为,是帝王在太平盛世表达文治的需要,他们只是劳务者,但因为宦官职掌了这样的权力,客观上促成了这一事业的发展和有序进行。另外他们有时也利用这样的便利,刊刻自己喜好的书籍。尤其司礼监太监几乎都是内书堂出身,他们是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知识型宦官,所以无论主观上还是客观上他们的行为都对文学、文化的传播作出了贡献。
考察司礼监刊印书籍对文学的贡献,还要从所刻书目说起。按《酌中志》卷18所提供的版目,明末天启、崇祯时期内府所藏内版书中的子部有:《孔子家语》《刘向新序》《刘向说苑》《诗学大成》《事文类聚》《胡僧诗》等等。集部有:《李白诗》《吕真人文集》《御制文集》《草堂诗余》《恩纪含春堂诗》《雍熙乐府》《千家诗》《选诗补注》《唐诗鼓吹》《唐圣三体诗》《神童诗》《祥异赋》《古文真宝》《古文精粹》《击壤集》《步天歌》《四时歌曲》《山歌》。[1]487这些诗文集的刊刻对于保存和传播文学典籍是有贡献的。
当然宦官职掌内府刻书也有弊端。在监管失控的情况下,他们往往将不利于自身的内容从书籍中删除。皇甫录《明纪略》记录了这样一件事情:“《皇明祖训》所以教戒后世者甚备,独委任阉人之禁无之,世以为怪,或云本有此条,因板在司礼监,削去耳。阉人当刑无斩首,惟剥皮、凌迟二条以其刑余之人也。”[9]利用职务之便,将不利于自己同类的律令删除,这和文人将曾经书写给权势宦官的阿谀作品从自己的文集中删除真是不谋而合。
除了官方的集体行为外,一些有学养的宦官也十分注重文化书籍的传承与传播。《酌中志》卷18记:“又累臣曾见《车驾幸地录》所载,正德十五年闰八月内,武庙南征回如镇江,幸大学士杨一清第,曾进抄本《册府元龟》,一部,共一千卷,计二百二本。累臣曾向韩提督世禄言及,幸有一部,然舛错颇多,至不能句,似非杨宅所献之书。李永贞遂雇人借抄一部,仍将原本交还。而抄本一部,闻丁卯冬已有人献于王体乾矣。至崇祯己卯夏,体乾没产,又不知落何人手也。”像李永贞这样的知识型宦官如此善待古籍珍本,无疑促进了文学事业的传播与保存。
职掌百科全书式的皇家书籍刊刻出版,对于司礼监及其下属的经厂宦官来说也会受到这些书籍内容的熏陶、习染乃至教育。同时汉经厂的儒家教化读物;番经厂、道经厂经书的印制,对宦官的政教意识、宗教信仰同样会产生一些影响,如《酌中志》卷22云:“中官最信因果,好佛者众,其坟必僧寺也。”
由于司礼监拥有雄厚的财力、物力支持,又有精良的艺术与技术背景,所以他们所刊刻的书籍十分讲究包装。《北京志·出版志》这样记录:
明代在北京设立的司礼监经厂,是一所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印刷厂,其总人数为1200人,其中从事书籍装帧的工匠就有700多人。
……
明代北京所印书籍的装帧形制,以经厂本最为代表性。它所印刷的经史类书籍,版面行格疏朗,字体楷书端正、大黑口、双鱼尾、注释用双行小字,多采用包背装。藏书家多称“监书天下第一”。其所印《大统历》(附图)有两种装帧方式,一是包背装,一是经折装。……(线装书)最具代表性的是经厂印刷的《大统历》,不但盖有政府公章,并有政府文告,申明不得私自翻印。[5]404-405
1200人中700人从事装帧,可见经厂本很注重包装,尤其一些佛、道经多采用经折装,且配有函套。包装是有很大的宣传效应的,而且已经有了类似今天的版权申明。这些都保证了书籍保存的质量问题。
经厂书籍不但注重装帧,而且还适应不同读者的需要,进行不同层次的包装。“既有供上层使用的豪华本,也有供中下层人士使用的普通本。”[5]404以致被藏书者誉为“监书天下第一”。
还需补充的是,经厂本也普遍用于颁赏,因而流传更广。据《中国古籍善本目录》及《明代版刻综目》等著录,现在的经厂本仍然有数十种之多。[10]
事实上,司礼监经厂不仅是刻书之所,也是藏书之处,收藏的内版书仅天启、崇祯两朝就有160余种。[1]491此外,明代多处宫廷藏书都为宦官所职掌。《酌中志》卷16“司礼监”条下记:
司礼监提督一员,秩在监官之上,于本衙门居住,职掌古今书籍、名画、册叶、手卷、笔、墨、砚、绫纱、绢布、纸札,各有库贮之,选监工之老成勤敏者掌其锁钥。所属掌官四员或六员佐理之,并内书堂亦属之。又,经厂掌司四员或六员,在经厂居住,只管一应经书印板及印成书籍、佛藏、道藏、番藏,皆佐理之。自提督以下,则监官、典簿十余员。第一员监官提督皇史宬,并新房。
“中书房”条下记:“专管文华殿中书所写书籍、对联、扇柄等件。”“御用监”条下记:“掌管武英殿中书承旨所写书籍、画扇,奏进御前,亦犹中书房之于文华殿中书也。”从以上文献可知,司礼监、中书房、御用监多个监局职掌或参与管理宫内书籍、文物珍藏,以及帝、后私人藏书。
同时,包括文渊阁、皇史宬在内的皇家藏书宦官也是参与其中的。总之,宦官广泛参与和职掌宫廷藏书在明代是客观的事实,而这些书籍又是文学、文化的载体,所以宦官无形中对于促进文学、文化的传承与传播作出了相应的贡献。
除了参与宫内藏书的保管外,一些宦官还有私人收藏。汪砢玉《珊瑚网》“名画题跋”条记:“明内监所藏(见沈石田客座新闻) 小李并大李金碧各一卷,王维雪景一大卷(三四丈),阎立本锁谏图,顾宏偃松轴,韩滉班姬题扇,惠崇鬬牛,韩干马五卷,黄筌醉锦图又聚禽图,周昉对镜仕女,董范巨然等卷,李景瑞应图。成化末太监钱能、王赐在南都毎五日舁书画,工柜循环互玩。御史司马公望见多晋、唐、宋物,元氏不暇论矣!并收云南沐府物,计值四万余金。”[11]
宦官私人珍藏书画,一方面说明其文化素养较高,另一方面也有附庸风雅的可能。但不管怎样,他们对于古董字画的收藏与展玩,无疑也是对文化遗产的一种保存和传播。
[1]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北京志·世界文化遗产卷·故宫志[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
[2](明)刘若愚.酌中志[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
[3]张琏.明代中央政府出版与文化政策之研究[M].台北:台湾花木兰出版社,2006.
[4](清)纪昀总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5]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北京志·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卷·出版志[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
[6](明)罗贯中.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7](明) 金忠.御世仁风[M].明刻本.
[8]胡玉缙.续四库提要三种[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9](明)皇甫录.明纪略[M].民国景元明善本丛书十种历代小史本.
[10]张升.明清宫廷藏书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11](明) 汪砢玉.珊瑚网[M].卷47.文渊阁四库全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