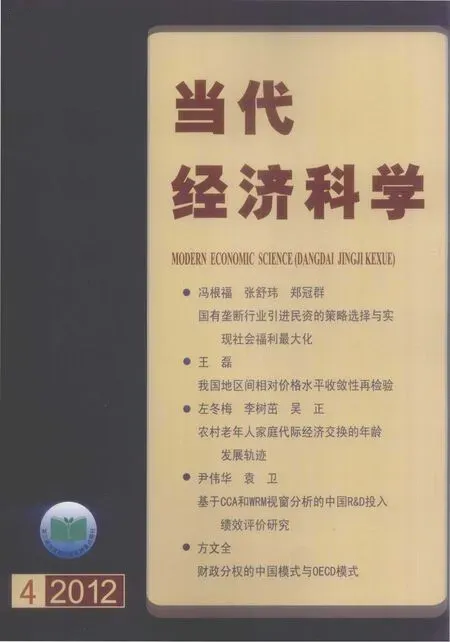我国边缘产业升级过程中的员工技能提升问题研究
宋 林,王建玲
(1.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陕西西安710061;2.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陕西西安710049)
一、引 言
湖北仙桃彭场镇,曾经生产了全国将近一半的无纺布产品,占据全球市场份额的四分之一,产品曾畅销欧美市场近二十年,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最大无纺布制品加工出口基地”。然而,自2010年下半年以来,受到人民币升值、原材料及用工成本上涨和外部经济环境波动等因素影响,彭场镇上大大小小的千余家无纺布企业瞬间减至百余家。2011年过完春节后,维持正常生产的不超过20家,形势的急转直下远远超出了彭场人以往的全部经验和想象①资料来源:刘玉洲,《中国最大无纺布产地急衰,千余企业减至数十家》,中国经济网,2011年03月01日。。目前,整个彭场无纺布生产企业仍沿用“贴牌代工”模式,长期以来在国际市场上缺乏话语权和定价权,由汇率变动和生产成本变动带来的损失都要由企业自己消化,企业的利润主要来源于密集的低成本的劳动力。在外部环境的不利影响下,尽快完成企业转型,调整产品结构,提高产品附加值,已经成为当地政府和企业的共识,当地政府主要通过各种政策优惠来促进企业加大投入、进口最先进的设备,来实现产品升级换代。
业界精英认为,彭场无纺布出口企业面临最大的问题还不是暂时性订单不足,而是严重的人才断层问题。在彭场无纺布产业的升级过程中,存在两大瓶颈:其一,并非所有企业都具有升级改造的能力,很多中小型企业将会被市场无情地抛弃;其二,如何寻找具有特定技能的产业工人来支撑产业升级,已经成为一个更迫切更致命的问题。最近5年,企业普遍感觉工人是越来越难招,彭场无纺布企业里面的普工月薪一般都在2000元以上,这样的工资在当地并不算低,但由于车间工作比较辛苦,无纺布企业能招进来并留得住的大多是40多岁的中年人,更多的是妇女。随着第一代农民工自然衰老而逐步退出劳动力市场,企业要吸引新生代农民工长期自愿留下,已经绝非涨工资那么简单。
彭场无纺布产业面临的困境在我国绝非偶然的案例。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曾经依靠低成本优势占领国际市场的中国制造业正面临着诸多的困难和挑战,产业升级不可避免。在产业升级过程中,产业结构和劳动力市场结构共同决定了产业升级的难度。受影响最大的不是国有垄断企业,也不是外资企业,恰恰是类似于彭场无纺布产业的民营企业集群,这些企业具有两大特征:所处产业是典型的边缘产业,劳动力市场以次级劳动力市场为主。中国制造未来的国际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产业能不能找到合适的发展模式。由于员工的生产技能和企业的技术应用存在很强的互补性,在技术升级的过程中,能否形成一支稳定的高技能的产业工人大军已经成为根本的制约因素。
在职培训在员工技能形成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本文通过在职培训的基本分析框架,探讨我国边缘产业工人技能提升的现实困境。本文结构如下:第二节主要通过文献综述分析员工在职培训的投资决定因素;第三节通过模型构建,分析了我国边缘产业在职培训的投资意愿不足和投资能力不足的双重困境,揭示了不完全竞争下我国边缘产业在职培训“市场失灵”的主要原因;第四节主要结合国外经验分析了政府为克服培训不足的补充行为;最后一节是本文的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在职培训的投资决定:文献综述
贝克尔的人力资本理论构建了在职培训的经典分析框架,贝克尔把在职培训分为“一般技能培训”和“特殊技能培训”两类,一般技能是指可以在很多企业中都能获得相同数量的边际产出的技能,而特殊技能仅在本企业具有价值[1]。对于一般技能而言,在完全竞争市场上,员工的收入等于其边际生产能力,员工为获得一般技能而付出的成本可以获得市场的完全补偿,一般培训的成本应该完全由员工承担。员工既可以直接支付培训成本,也可以通过接受培训期间的低工资而间接支付;由于特殊技能只在本企业有价值,其面对的市场是完全垄断的,对员工来说特殊技能没有市场价值,因而员工缺乏投资意愿,特殊技能的培训成本应该全部由企业承担。贝克尔把现实中的企业培训构解为完全的一般技能培训和完全的特殊技能培训的某种特定组合,在贝克尔的框架中,技术培训不存在“外部性”问题,因此也不会出现投资不足问题。
对于特殊技能培训,贝克尔推测现实中的培训成本可能是在企业和员工之间分担的。为了避免事后由于员工辞职而导致的特殊技能培训成本无法收回,企业可能会在市场均衡工资和员工的边际生产能力之间重新确定工资水平,这样,特殊技能培训的“租金”就在企业和员工之间分享,最优合约意味着特殊培训的成本也应该按相同比例在企业和员工之间分担。Hashimoto(1981)沿着贝克尔的分析,通过引入交易成本,首次构建了一个特殊培训成本分担的正式分析框架[2]。在假定没有外部性和自由进入的条件下,Hashimoto构建了一个两阶段模型,在第一阶段,员工和企业签署一个长期合约,以约定特殊技能培训的投资水平和第一、二阶段工资水平。外部的工资水平和员工第二阶段的生产能力事先是不确定的,在第二阶段开始的时候,员工搞清楚了外部的真实市场工资,而企业搞清楚了员工的真实生产能力,企业将会辞退生产能力低于约定工资的员工,而发现市场工资水平高于约定工资的员工将选择跳槽。Hashimoto假定员工和企业最大化联合剩余,并且第二阶段的工资是根据最小化事先期望的非效率的员工离职成本而设定的,这样,培训成本在企业和员工之间的分担取决于三组变量:工资水平和跳槽率;企业利润和辞退率;以及员工对培训成本的支付能力和支付意愿。在不允许再谈判的情况下,即使事前的培训投资是有效率的,企业的辞退和员工的跳槽都可能会导致事后的非效率。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信息经济学在在职培训分析方面开始广为应用,在不完全竞争和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企业和员工的策略行为成为在职培训分析的重点。不同于贝克尔的分析,在不完全竞争状态下,员工的一般培训成本也可能是由企业分担的,这一结论事实上得到了英国和德国的数据支持[3-4]。企业对员工提供一般性培训可能出于以下几个方面原因:可能是为了降低在市场上直接雇用熟练工人的成本[5-6];一般培训和特殊培训可能存在互补性[7];企业可以通过压缩的工资结构把一般性培训变为事实上的特殊培训[8],压缩的工资结构是指,通过特定的制度结构,使得通过培训,员工未来的生产率增长率会高于工资增长率。在不完全竞争下,员工的离职成本,寻找新工作的成本,自身掌握的一般技能和特殊技能的互补程度,以及信息不对称的程度,都可能让企业基于可压缩的工资结构而提供一般培训。
信息不对称是指提供培训的企业比市场具有更多关于员工培训方面的信息,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提供培训的企业更了解员工的培训状况;另一类是提供培训的企业更了解员工的生产能力。Katz and Ziderman(1990)构建了一个信息不对称情况下企业提供一般培训的分析框架,当存在信息问题,市场上潜在的招聘企业就无法搞清楚应聘人的真实培训状况,因而只能按照市场期望的培训水平给应聘人估价,由于期望工资外生于员工一般培训的投入水平,员工就无法在市场上获取一般培训的全部收益,因而企业会愿意提供更多的一般培训[6]。Chang and Wang(1996)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个信息不对称的正规分析模型,其两阶段分析模型显示,只要员工培训后留在企业的概率为正,并且员工不拥有全部的讨价还价能力,企业就可能对员工提供一般培训[7]。
当外部市场无法有效观察到员工真实生产能力时,逆向选择会影响市场工资的形成[8-9]。Chang and Wang(1995)首次建立了逆向选择分析在职培训的正规模型,其分析假设员工的能力不同,其模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员工接受培训,第一阶段末培训企业按照员工的能力决定其在第二阶段的工资,低能力的员工将获得等于其生产能力的工资,而高能力的员工将获得市场工资。外部企业可以观察到员工的培训水平但无法观察到员工的生产能力,当高能力的员工存在一个外生的跳槽率时,市场形成的期望工资会严格高于低能力员工的目前工资,低能力的员工会全部选择跳槽。由于逆向选择问题,市场工资无法弥补员工的全部边际生产能力,企业投资于一般培训会获得正的边际收益。
当培训活动不可能被完全观察和证实的情况下,“道德风险”问题就会产生,企业可能会在员工接受了低工资外加在职培训承诺的合约后,不提供合约中约定的培训义务或者提供低质量的在职培训[10]。Acemoglu and Pischke(1999)把现实中一般培训更多是由企业而并非员工承担的现象,解释为对道德风险问题的现实应对[4]。
在市场机制下,培训的投入不足问题会经常发生。最优培训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员工培训处于边际社会收益等于边际社会成本的状态,当现实培训低于这种状态时,就出现了经济学上所谓的培训的投入不足问题。培训不足和劳动力市场的特性密切相关。在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中,培训不足主要由个人的投资能力不足和诸如“最低工资”等的制度限制造成,另外,由于培训的投资回收期较长,个人的信息获取能力、风险偏好和理性状态都会影响技能培训的投资决策。当培训的未来收益存在不确定性时,当投资收益需要在投资方之间通过再谈判来确定时,较高的交易成本会进一步影响培训的投资决定;当劳动力市场呈现不完全竞争状态时,员工离职的“外部性”问题会比较严重,培训的投资不足的问题可能会进一步恶化。
Acemoglu(1996)[11]提供了一个员工个人投资能力不足的正式分析框架,当资本市场不完善时,员工就无法在资本市场上借到足够的资金用于培训投资,这样员工只能依靠个人以前的财富积累进行投资,当员工个人的财富积累不足以支付培训投资时,会导致社会最优的培训结果无法出现。在发展中国家,贫穷、个人的资源限制以及不完善的资本市场,会导致潜在的技术工人缺乏支付能力或支付意愿,员工自己支付成本的培训很难有效进行[6]。
在Hashimoto的分析中不允许再谈判,但其分析事实上开启了第二阶段工资再谈判模型的序幕。再谈判是由于相机合约无法事前准确写清楚,不允许再谈判员工的非效率离职就不可避免。再谈判必然牵扯讨价还价,在无摩擦的情况下,讨价还价的均衡结果就是Nash均衡解,即参与方的讨价还价能力决定租金分配的份额[12]。在再谈判过程中,机会主义行为可能会导致某一投资方被“套牢”,当投资者预期到无法收回全部边际收益时,培训的投资不足问题就会出现。由于特殊培训没有市场价值,再谈判会打击员工对特殊技能培训的积极性[2,13],同时,也会对一般性培训产生影响[8]。降低“套牢”问题需要企业建立信誉机制,一些特殊形式的合约也可以起到类似的作用[14-15]。
在不完全竞争状态下,当员工的离职率较高时,在职培训将面临“外部性”的困扰[16-17]。Pigou(1912)最早提出了由于存在外部性问题,企业提供给员工的技能培训可能会低于社会最优水平。Stevens(1994)认为,在不完全竞争状况下,贝克尔的“一般”和“特殊”分类方法并不能涵盖所有的培训类型,她提出了“可转移”培训的概念,当某项培训带给员工的技能至少在本企业之外有一家企业具有一定价值时,这种培训就叫做“可转移”培训[17]。在培训是可转移的情况下,企业的工资支付将会低于员工的边际生产能力,当员工存在一个不确定的离职率时,外部企业就可能从培训中获得一个正的期望利润,就会有企业通过“挖墙脚”的方式吸引技术熟练员工。由于企业和员工在培训决策过程中,无法内在化这种外部性,他们最大化的是企业和员工的联合剩余而并非社会剩余,因而培训投资将会低于社会最优水平。
综上可得,在职培训是企业和员工的一种联合投资,这种投资不光会受双方投资能力和投资意愿的影响,而且还会受制于双方对未来收益的预期以及在未来收益分配中的讨价还价能力,在市场不完善和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较高的交易成本会造成在职培训的投资不足。
三、边缘产业技能培训的投资意愿和投资能力
Doeringer和Piore是早期对劳动力分割理论进行较为全面阐释的经济学家,他们依据薪酬机制和升迁途径等不同将劳动力市场划分为“一级劳动力市场(primary labor market)”和“次级劳动力市场(secondary labor market)”[18]。在分析二元劳动力市场时,他们假设整个劳动力市场分为两个部分:第一类劳动市场工资高、劳动条件好、职业有保障并且有晋升机会;第二类劳动市场则工资较低、工作条件差并且不稳定,很少有晋升机会。
边缘产业的概念是由 Averitt教授提出的,Averitt最早构建了将劳动力市场的运行结果与产业组织的二元结构联系起来的分析框架[19]。一级劳动力市场主要由核心产业(Core sector)的厂商构成,它们生产规模大、资本密集程度高、盈利能力强,因而具备支付高薪的实力;次级劳动力市场大多居于边缘产业(Periphery sector),它们的生产规模和资本密集程度低,产品市场是高度竞争的,而且这种竞争以价格竞争为主。核心产业主要由重工业、交通运输业、通讯业、工商服务业以及公共管理等行业组成,而边缘产业主要由轻工业、建筑业、批发业和个人服务业组成。随后,一些学者根据产业特征对美国和英国的劳动力市场分割进行了检验[20-21],都发现相对于核心产业,边缘产业的员工收入水平存在显著的差异。
在通过在职培训提升工作技能和积累人力资本方面,两个市场的表现迥异:一级劳动力市场的正式组织结构和相对稳定的工作预期对雇主和员工在人力资本积累方面都具有正向激励作用,员工的在职培训的机会较多;而在次级劳动力市场中,员工的不良习惯较多,人力资本较低,而较高的员工离职率又阻碍了雇主向雇员提供在职培训的动力[18],次级劳动力市场的企业很少给员工提供在职培训;由于次级劳动力市场提供的是坏工作(Bad job),这些工作对人力资本的要求不高,并且其薪酬结构并不体现员工的工作技能和人力资本,次级劳动力市场也无法提供员工自己承担培训成本的正确激励。因此,在技能培训和人力资本提升方面,次级劳动力市场一直存在恶性循环。
我国以代工模式发展起来的外向型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典型的边缘产业,以农民工为主的劳动力市场又是典型的次级劳动力市场。虽然我国目前在理论上已经承认农民工是产业工人的一部分,但我国转轨时期特定的“二元体制”结构却很不利于农民工工作技能和人力资本的提高。我国边缘产业的在职培训困境表现为企业和员工的投资能力和投资意愿都不足。从企业方面来看,我国代工企业普遍规模小、资金不足,企业之间的激烈竞争注定利润低廉,很多企业融资能力有限,可用于员工技能培训的资金不足,影响企业投资意愿的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企业生产的不确定性程度很高,大部分企业主要从事价值链低端的组装、制造业务,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缺乏话语权,企业生产缺乏稳定的预期;其二、员工的离职率很高,企业投资于技能培训的“外部性”问题严重。从员工方面来看:农民的整体贫困注定了农民工的个人财富积累很有限,农民工同时缺乏从资本市场获得信贷的能力,其可用于技能培训的个人投资严重不足;目前的“二元体制”导致农民工对未来的预期不稳定,风险规避程度很高,这导致农民工对技能培训的投资意愿不高,同时,由于在职培训和教育水平存在较高的互补性,农民工整体的教育水平低下意味着其投资于技能培训的边际成本较高,这会进一步影响农民工的投资积极性。
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我国边缘产业以前具有的比较优势正在逐步丧失,产业升级迫在眉睫。产业升级产生了对高技能员工的需求,我国现行体制下能否满足高技能产业工人的有效供给就成为问题的关键。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我国边缘产业中的企业发展是分化的,员工对技能的投资能力和投资意愿也是分化的,再加上地方政府合适的政策支持,一些产业升级、企业的技术升级和员工的技能升级可能也会有效实现。本文以彭场的无纺布产业为代表,主要分析地域上有集聚特征的边缘性产业,这一限定主要为明晰产业政策的主体,提高政策的有效性。本文在上述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一个简易模型来分析我国边缘性产业通过在职培训提升员工工作技能的前提条件。
假定存在两个时期,在第一个时期开始前,地方政府决定产业升级,同时企业决定技术升级,为满足技术升级需要提高员工的生产技能,员工的在职培训发生在第一个时期。培训主要提升的是员工的产业生产技能,这种技能员工会理解为特殊技能,因为离开这一行业该技能的市场价值较低,而企业会认为是一般技能,因为该技能极易在本行业的其他企业中应用,这种分歧导致培训成本是在企业和员工之间分担的。假定产品市场是完全竞争的,但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是不完善的,资本市场的不完善意味着有企业和员工可能面临“信贷约束”,出现投资能力不足问题,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善意味着存在一个客观的员工离职率。在第二个时期,企业和员工根据讨价还价能力分享在职培训的投资收益。首先我们分析投资意愿问题,在这一问题的分析过程中假定不存在投资能力限制;其次再分析员工和企业的投资能力不足问题。
(一)在职培训的投资意愿分析
假定在第一时期开始前,员工的技能为0,通过第一时期的在职培训,员工获得的技能为s。C(s)代表在职培训的成本,其中C′(s)>0并且C″(s)>0,当s>0时。培训成本在员工和企业之间分担,员工承担的比例为α,其中(1>α>0)。
在职培训的收入函数为Y(s),其中Y(s)是s的线性函数。
产业的最优培训出现在培训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相等时,即:

员工基于培训的收益为R(s),假定员工的讨价还价能力为β,其中(1>β>0),纳什均衡意味着:R(s)=β·Y(s);
培训之后员工存在一个外生的辞职率q;
对于企业来说,其基于在职培训的效用函数为:

(2)式的最大化意味着如下的一阶条件成立:

整理(3)式得:

员工基于在职培训的效用函数为:

(5)式的最大化意味着如下的一阶条件成立:

整理(6)式可得:

比较(7)式和(1)式,员工的投资意愿主要受两个因素制约:承担培训成本的份额和在培训收益中分享的份额β,当时α=β,员工的投资意愿可以达到产业最优的水平。比较(4)式和(1)式,企业的投资意愿主要受三个因素制约:除了企业承担培训成本的份额(1-α)和在培训收益中分享的份额(1-β)之外,还受员工离职率的影响,即使1-α=1-β,只要员工的离职率为正,企业还是会出现投资意愿不足的情况。
(二)在职培训的投资能力分析
在资本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我国边缘产业很容易出现投资能力不足的情况,Acemoglu(1996)曾构建了一个员工受个人资产约束而投资能力不足的分析模型,他也提出现实中也可能存在企业的资本投入能力不足的情况,但并没有把后者纳入模型。在我国边缘产业中,企业投资能力不足和员工投资能力不足的问题都会出现,本文沿着Acemoglu的思路作进一步分析。
假定员工在资本市场上的信贷能力为零,其用于在职培训的投资来源于以前的个人财富,在此用W(i)代表员工i可用于在职培训的个人财富。当W(i)≥α·C(s)时,员工不存在投资能力约束,员工将按照投资意愿进行在职培训决策;当W(i)<α·C(s)时,员工存在投资能力约束,员工将按照个人财富的限度进行投资决策。员工的个人投资用I(i)表示,那么:

在本文中,企业的投资能力分析仅限于企业承担的在职培训成本能力,企业资本投资不足问题不在本文的分析范围之内。当部分企业存在投资能力不足问题时,其分析过程和员工个人投资能力不足问题类似,不同的是,当企业用于在职培训的投资能力 <(1-α)·C(s)时,在劳动力市场不完全竞争时,这些企业可能会停止在职培训投资而主要采取“挖墙脚”策略,这会进一步增加产业内员工的离职率,“外部性”问题更严峻,这又会进一步降低有投资能力企业的投资意愿,整个产业在技能培训方面可能会陷入恶性循环。
四、政府解决在职培训不足的补充性作用
技能培训不但可以提升一个员工的生产能力,还会带来其他协作员工效率的提高以及团队生产效率的提高,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员工培训所带来的社会收益甚至会不断从一个产业或一个地区的劳动力市场溢出,因此,在职培训的社会收益会高于私人收益。当考虑到投资能力约束、员工离职的外部性问题以及员工的讨价还价能力时,在职培训的投资不足问题会经常出现。对于以次级劳动力市场为主的边缘产业来说,在职培训的“市场失灵”现象会更为严峻,政府恰当的补充性政策对解决这一问题不可或缺,结合上一章的分析框架和国外的经验,在解决我国边缘产业技能提升问题中政府的作用表现为以下方面:
一、投资能力约束问题。在内外部环境发生变化后,不是每一个边缘产业都可以成功升级;在产业升级过程中,也不是每一个企业都有能力完成技术进步,一部分企业将不可避免地被淘汰,因此政府必须对产业和企业的升级可行性要有准确评估。一般来说,当企业存在投资能力约束时,其完成技术进步的可能性也较小,政府的政策目标应该主要针对员工的投资能力约束问题。政府解决投资能力不足问题的手段主要有两种:一是设计特定的信贷产品来弥补在职培训的投资不足,通过打破“信贷约束”来提高员工对技能的投资能力;二是直接提供财政补贴,这一方法常用于救助陷入“低技能-坏工作”困境中的社会弱势群体。考虑到政策的执行成本,我国边缘产业最好借鉴国外通过发行“培训券”的方式来弥补投资能力不足的方法,每个员工需要的发行数量为:a·C(s)-E(W(i)),其中E(W(i))是市场中员工可用于在职培训投资的个人资产的期望值。政府向员工发行培训券,员工用培训券支付企业的在职培训,企业可以用培训券抵税,这种方法在解决员工对培训的投资能力约束问题的同时,也正确地激励了企业向员工提供更多的一般性培训。
二、员工离职的外部性问题。员工过高的离职率一直是影响企业对在职培训进行投资的重要因素,高离职率是次级劳动力市场的一个主要特征,这会大大降低我国边缘产业的企业向员工提供在职培训的积极性。解决这一问题可借鉴英国当年建立的行业培训模式,英国早在1964年就颁布了工业培训法,并成立了27个行业培训委员会(ITBs),基于企业对员工的技术培训会对整个行业的发展带来好处的想法,这些委员会对行业内的企业征收培训费,然后把这些钱用于补贴行业内对员工提供技术培训的企业。基于我国边缘产业的特点,政府可采用建立产业培训组织的方法,这一组织主要由产业内有影响的企业发起,负责提供整个产业的员工技能培训,培训经费主要通过向产业内的企业征收,政府根据财政状况也可以提供相应的财政补贴。在这种模式下,员工在产业内的流动将不会导致提供在职培训的企业面临很高的“外部性”,有效解决企业投资意愿不足的问题。
五、结论和政策建议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后,随着国际贸易的全球化发展,发达国家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低技能工作大量被转包(Sub-contracts)给发展中国家,我国成为世界制造大国正得益于这种国际产业的大转移。在这个过程中,发达国家大量的低技能工人由于工作机会缺失而引发了社会对技能培训问题的高度关注,技能培训的“市场失灵”现象被学者深入研究,各国政府都相继出台了提高低技能工人的支持性政策。我国出口导向型的企业基本上都是发达国家转移过来的边缘产业,随着我国经济近年的快速发展,这些产业原先具有的比较优势已不复存在,产业升级也势在必行,如何提升员工的技能以适应这种变化,目前在理论层面和政策层面都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
近些年虽然中央政府开始关注我国农民工的技能培训问题,但是如何有效实施仍然语焉不详。相对于学历教育,技能培训的影响因素更为复杂,本文从企业和员工两方面分析了我国边缘产业员工技能培训的“市场失灵”现象的现实困境:边缘产业企业生产的不确定性问题、员工和企业面临的投资能力约束问题、“二元体制下”农民工技能培训的理性预期不明确问题、员工高离职率导致培训的外部性问题等。这些因素严重影响了企业和员工对技能培训的投资意愿和投资能力,导致我国边缘产业在产业升级过程中面临较为严重的技能缺失困境,政府的补充性作用对边缘产业的技能提升至关重要。本文的政策建议如下:
第一,高度重视我国产业升级过程中的技能提升问题,通过国家层面的战略规划,有效补充我国边缘产业技能培训的不足,并在微观层面上结合我国的现实情况深入探讨技能培训的有效的运行机制。
第二,针对我国次级劳动力市场员工投资能力不足问题,政府需要提供必要的财政补贴,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提高政府补贴的针对性和运行效率。
第三,借鉴英国的技能培训模式,建立以产业为主导的技能培训体系,克服技能培训过程中跳槽的外部性问题。政府根据产业升级的前景和企业投资能力提供必要的财政补贴,提高企业投资于技能培训的积极性。
第四,借鉴德国经验,建立全国性的培训证书体系,在目前无法消除“二元体制”的情况下,可以把这种技能培训证书制度镶嵌于现行的社会福利和激励机制,用于激励员工提升个体技能的积极性。
[1] Becker G S.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A theoretical analysis[J].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62,70(5):9-49.
[2] Hashimoto M.Firm-specific human capital as a shared investment[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1,71(3):475-482.
[3] Stevens M.An investment model for the supply of training by employers[J].The Economic Journal,1994:556-570.
[4] Acemoglu D,Pischke J S.Beyond Becker:Training in imperfect labour markets[J].The Economic Journal,1999,109:112-142.
[5] Oatey M.The economics of training with respect to the firm[J].British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1970,8(1):1-21.
[6] Katz E,Ziderman A.Investment in general training:The role of information and labour mobility[J].The Economic Journal,1990,100:1147-1158.
[7] Chang C,Wang Y.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under asymmetric information:The pigovian conjecture revisited[J].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1996:505-519.
[8] Acemoglu D,Pischke J S,The structure of wages and investment in general training[R].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1998.
[9] Chang C,Wang Y.A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differences in labor turnover and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J].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1995,28(1):91-105.
[10] Schlicht E.Endogenous on-the-Job training with moral hazard[J].Labour Economics,1996,3(1):81-92.
[11] Acemoglu D.Credit constraints,investment externalities and growth[A].Booth A L,Snower D J.Acquiring skills:market failures,their symptoms and policy responses[C].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43-62.
[12] Nash Jr J F.The bargaining problem[J].Econometrica,1950:155-162.
[13] Williamson O E.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Firms,markets,relational contracting[M].New York,1985.
[14] Kahn C,Huberman G.Two-sided uncertainty and“up-or-out”contracts[J].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1988:423-444.
[15] Prendergast C.The role of promotion in inducing specific human capital acquisition[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3,108(2):523-534.
[16] Pigou A C.Wealth and welfare[M].Macmillan and co.,limited,1912.
[17] Stevens M.A theoretical model of on-the-Job training with imperfect competition[J].Oxford Economic Papers,1994:537-562.
[18] Doeringer P B,Piore M J.Internal labor markets and manpower analysis[M].ME Sharpe Inc,1971.
[19] Averitt R T.The dual economy:The dynamics of American industry structure[M].WW Norton New York,1968.
[20] Oster G.A factor analytic test of the theory of the dual economy[J].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79,61(1):33-39.
[21] Buchele R.Economic dualism and employment stability:Industrial Relations[J].Journal of Economy and Society,1983,22(3):410-418.
[22] Snower D J.The low-skill,bad-job trap[A].Booth A L,Snower D J.Acquiring skills:market failures,their symptoms and policy responses[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111-124.
[23] Vietorisz T,Harrison B.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Positive feedback and divergent development[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73,63(2):366-376.
[24] Acemoglu D,Pischke J S.Certification of training and training outcomes[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2000,44(4):917-9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