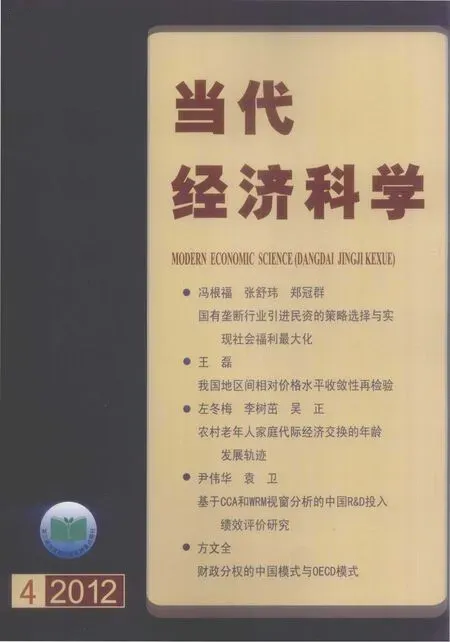农村公共服务绩效评价指标的维度选择与体系构建
王俊霞,鄢哲明
(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陕西西安710061)
一、引 言
“三农”作为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的重要问题,一直受到公众的普遍关注。现实中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偏离农民实际需求的现象,不仅加剧了人们对农村公共服务稀缺资源遭到浪费的担忧,同时,也引起了学术界关于农村公共服务有效供给的讨论,讨论的焦点问题是如何构建农村公共服务有效供给的长效机制,以及如何在现有制度安排和财力基础上提高农村公共服务绩效。回答此类问题则需要对农村公共服务真实绩效进行科学的评价分析。
近年来,关于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绩效评价问题,我国学者界开展了丰富的研究。概括之,有学者研究了医疗、教育、基础设施等具体领域的公共服务绩效评价[1-2],有学者站在综合绩效的角度研究了农村公共服务的现状[3-4]。在公共服务绩效评价的“效率”阶段,绩效评价的维度不免会侧重于从政府机构统计数据出发,研究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供给成本以及效率差异。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许多学者也尝试将国外广泛使用的顾客满意度指数(CSI)方法应用于绩效评价领域[5-6]。与一般公共服务①注:本文中,若无特殊说明,“一般公共服务”和“公共服务”泛指覆盖了农村和城市的公共服务,“农村公共服务”则限定于农村范围。绩效评价类似,农村公共服务绩效评价的研究也呈现出两条清晰的路线,即机构(Agency Survey)和公众评价(Citizen Survey)。丰富的既有文献为评价农村公共服务绩效提供了诸多可循路径,但关于机构、农户评价或者其他方式之间的差异性、适用范围和优劣性却被隐藏于研究假设中。类似于一般公共服务,评价维度与指标体系的选择问题对于农村公共服务也尤为重要。已有文献对农村公共服务绩效评价指标维度论及较少,几乎很少讨论关于公众评价指标和政府机构数据指标的甄别与选择。基于此,本文拟从评价维度选择的角度来研究农村公共服务绩效评价问题。通过本文研究,构建科学合理的农村公共服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为准确判断农村公共服务真实绩效,比较区域间或时间上的绩效差异,进而为制定农村公共服务政策提供决策依据。
二、农村公共服务绩效评价指标维度的相关文献综述
究竟应该采用何种维度来测量农村公共服务绩效?虽然没有文献直接指出答案,但是关于机构和公众评价之间相互比较的丰富研究成果为我们提供了诸多借鉴。关于公共服务绩效评价指标维度的选择问题,集中地体现在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主客观测量手段争论上。随着西方国“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倾听民众呼声、转变政府服务态度作为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方向。在这个大趋势下,公众评价已经成为一项获取公共服务质量信息、测量公共服务“产出”情况,进而提高对公共服务中主要问题的认识水平、鼓励公共服务供给者提高服务质量的重要手段[7]。为了形成区别,人们习惯将以政府机构数据为主的测量手段称为客观测量,而把以公众满意度指标为主的测量手段称为主观测量。
以Stiprk以及Brown和Coulter为代表的学者率先开始对主观评价提出了质疑,认为利用公民满意度来测量公共服务的方法存在着两个严重的问题[8-9]。首先,公民所表达的满意度或期望情况并不能反映真实公共服务绩效,即主观评价模式存在效度不足的问题。其原因主要是公众满意度评价在实际操作中不得不面临概念难界定、统计性错误等复杂问题,以及容易受到个人背景特征的影响[10]。其次,在一些普通公民很少关注的公共服务上,服务质量的变动很难被察觉,以及公众在评价公共服务质量时缺乏足够的了解和知识储备,公众因此只能根据整体印象去代替对该项服务的评价[11]。总之,通过对主观评价模式的批评,研究者主要认为一味地依赖于公众满意度调查的做法将会引致错误的公共政策。针对学者上述批判观点,公众评价的支持者展开了辩论。一方面,直接提出反对意见。对于主观评价容易受到其熟悉人群既定观念以及政府态度等因素影响进而有失效度的论点,主观评价的支持者认为这种批评并没有找到明显的实证证据[12]。同时,不同阶层的公民对公共服务的意识、态度、了解程度都非常类似[13],他们对公共服务的期望和评价能够客观地反映附近区域内的公共服务水平[14],主观评价的效度无需怀疑。此外,公众对公共服务缺乏足够认识不应该称为政府官员拒绝主观评价的理由,主观评价模式理应成为地方民主管理模式的试金石[15]。另一方面,指出客观评价的诸多弊病,例如数据信息的报告和传递过程中容易出现偏误[16],过度关注于数据信息的可测量性而忽略了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对公众需要的回应性[17],以及难以保证公共服务供给的目标同公民实际需求相吻合[18]。
在公众评价或机构评价孰好孰坏的深入探究下,主观和客观两种维度是否不可调和,抑或存在某种协调方法?在反驳批评和自我检查的过程中,研究者发现主观模式和客观模式均存在各自的弊病。针对这些问题,有学者提出在主观评价中“过滤掉”(filter out)收入、年龄、教育水平等因素,使得满意度评价方法更能直观地反映真实绩效[7]。而Brudney和England则提出了一个“公民—政府双元的公共服务协同生产机制”(Citizen-Agency Interaction:Coproduction of Municipal Services)。在此机制下,主观评价与客观评价相互补充。在评价公共服务供给绩效时,有必要同时使用主观满意度和客观指标这两种测量手段。Wang和Gianakis认为不同的目标将导致不同的绩效测量维度,例如主观指标维度虽然适用于管理目标,但是在执行财政资源分配目标时就应该谨慎使用它,有必要建立一个包含了多种测量维度的绩效测量体系[18]。我国学者也在不同领域尝试了经公众和机构评价相结合的方法。公共服务提供机制与方式研究课题组提出了构建将公民满意度和公共服务供给情况相结合的“双元综合评估”模型,并将相关成果应用于了厦门市的实际操作中[19]。在农村公共服务领域,王俊霞和王静尝试将机构与农户评价结合,在农村公共设施和农村公共管理等层面上运用机构数据评价,在农村政治建设上运用农户评价数据[20]。
综上所述,随着农村绩效评价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我国学者也开始尝试农户评价和机构评价数据的有益结合。但是既有文献多为直接的应用或指标设计,很少讨论关于绩效评价指标维度的选择问题。面对学术界关于机构数据和公众评价之间相互冲突的辩论,需要对二者创新性结合的合理性进行充分的讨论和辩解,并发现和反思传统绩效评价中的问题,以求在绩效评价的理论和实践上取得创新。
三、“政府-农户”双元绩效评价体系
(一)“政府-农户”双元绩效评价的内涵
1.传统绩效评价的主客观二分性
在对农村公共服务进行绩效评价时,常会面临一个问题。应该采用机构数据,抑或是农户评价方法?绩效评价的研究者和实践者通常将上述两者之间的比较放置于主观评价与客观评价的比较选择之下。人们习惯性地认为农户评价就是主观评价,而机构数据就是客观评价。这种主客观二分性(objective-subjective dichotomy),使得机构测量方法与农户评价测量方法被人为区分开。一种主要观点认为,机构方法和农户评价方法是相互对立、不能相容的两个概念。理由如下:公众评价与个人背景特征具有相关性,而政府机构数据则不然,两者所包含的是明显不同的两类信息。另外一种观点认为,由于公共服务绩效评价的目的在于反映真实绩效,因此对绩效指标维度的选择应该以客观性为标准;机构数据因其被冠以客观评价之名,相比于主观的农户评价数据通常更能满足客观性要求。在我国农村公共服务绩效评价中,上述主客观二分性的存在影响了绩效评价指标维度的选择。一方面,地方政府官员倾向于选择符合“客观”要求的评价方法,机构数据则恰似符合“客观性”标准;另一方面,虽然学者呼吁、农民要求、政府考虑采用农户评价指标,但畏于其“主观”之名,很少有地方政府将农户评价指标作为绩效评价系统的组成部分。于是,主客观二分性成功地划分了农村公共服务绩效评价中政府行政官员主体与世俗农民主体的相对地位。
2.对主客观二分性的质疑
在既定的主客观二分性之下,来源于机构和农户评价的数据被严格区分开。很少有文献讨论这些术语的准确性,农户评价数据中所包含的个人背景特征是否完全地限制了其适用性和客观性,机构数据又能否保证完全客观或者与个人背景特征无关?
首先,农户评价数据并不是完全的主观测量。一方面,个人背景特征更应该成为客观衡量农村公共服务绩效的必要条件。批评者认为公众评价与个人背景特征之间的相关性,使得农民对农村公共服务评价的驱动因素主要是年龄、收入、地区等特征,而非其真实享用的公共服务情况,公众评价数据由于添加了“杂质”而显得“不纯净”。然而,我们认为完全没有必要实现农户评价与个人背景特征的不相关,反而更应该把个人背景特征作为公共服务客观绩效的重要参考信息。以区域或民族背景特征为例,正是因为各个人群拥有彼此相异的生活经历,所以也就都拥有其各自不同公共服务需求,产生与其他地区或者民族不同的绩效期望和评价。在此情况下,公众评价和个人背景特征之间的相关性,正是检查公共部门能否满足不同群体中差异化公共服务需求的重要证据[21]。另一方面,是否与机构数据一致不能成为判定农户评价指标客观性的必要条件。有学者认为倘若两者符合一致检验,那么判定公众评价数据具有客观性,否则就说明公众评价数据有误或者不准确[8-9]。不难发现上述检验的一个重要预设条件是机构数据本身是客观无误的,然而该预设条件难以成立,具体见下文。以上讨论并不是要推翻关于农户评价数据具有主观性的研究,我们认为农户评价数据同样无法回避主观性。具体来看,农户评价数据的主观性更应该体现在农民主观情绪影响上。以某些特定的农民接触较少的公共服务项目为例,农民往往会通过询问邻里或者借助媒体的方式来了解情况并以此做出判断;然而媒体以及农村邻里往往倾向于以夸大化、负面化以及情绪化的方法来传播信息,则由此构成了农户评价数据的主观性。可以说,由于兼具了主客观性,不能简单地将农户评价数据划归为主观评价。
其次,机构数据并不能保证完全客观。在搜集或者使用政府机构数据时,研究者通常将其命名为客观数据,主要是因为它源于实际且载体为摸得着看得见的实体,有别于公众评价来源于个人期望和感知的特点。但是要求机构数据完全保持客观性同样也只能是理论上的假想,机构数据的主观性体现在人为地对数据直接或间接的主观干预。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当前政府机构数据都面临着真实性质疑,直白地说就是数据伪造问题。数据的伪造行为主要可由两个原因造成。一个原因是政府机构人员的主观偏见,在统计、搜集或者汇报农村公共服务的数据信息时,要么出于偷工减料、要么出于对实际调查数据的不信任,政府机构人员有动机根据自己的主观看法,认为公共服务供给应该处于某一个状态水平,并以此汇报或者修改数据;另一个原因是政府机构人员对高绩效的追求。在官员激励机制下,下级官员通常偏好高绩效数据,以此作为个人晋升以及公共经费膨胀的砝码,相比之下则厌恶低绩效数据。出于上述目的,地方基层官员具有修改、谎报农村公共服务绩效评价数据的动机。随着我国各级政府统计工作的不断规范,数据伪造问题的存在空间将可能逐渐缩小,然而政府机构对绩效数据的间接性主观干预仍难以避免。在我国政府目标考核制度以及追求高绩效的环境下,基层政府部分会主动地把注意力和工作重心放置于上级交代的各种目标和考核任务之下,并将有限的地方政府人力与财力资源倾注于所谓的重点领域。一方面,当上述重点领域与农民需要不一致或者不完全吻合时,有可能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另外一方面,无论这种稀缺资源的投入与转移是否正确,在其加大人力、物力投入以至于产生高绩效数据的整个过程中,恰好反映了人为主观理想和主观情绪因素对客观数据的干预,因此数据也就包含了主观性[21]。不难发现,常被我们冠以客观数据之名的机构数据同样也难以保持完全的客观性①此外,Williams和Kellough的研究表明个人背景特征也对政府机构数据构成了影响,因此以个人背景特征作为主客观性划分的依据也可能不正确。。
3.“政府-农户”双元绩效评价的内涵
既然公众评价和机构数据都兼具主观性和客观性,那么以主客观为标志将其区分开来的做法则需要进一步商榷。换句话说,在选择农民评价维度还是机构评价维度时,不应该以主客观性作为选择判断依据。实际上隐藏在主客观“二分性”之下的关键,是农村公共服务绩效评价主体的选择问题,即应该由政府来评价,还是由农民抑或其他主体来评价。在传统的绩效评价实践或者研究中,一般认为政府作为公共服务供给者和决策者,负责实施绩效评价和制定公共政策,而作为公共服务消费者的农民被严格区分开,只需要提供一些反馈信息或者帮助实现公共服务有效供给。“至上而下”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延伸到了绩效评价领域,降低了农民在公共服务绩效评价中的地位和参与价值,造成农民话语权的缺失。农民即使偶尔参与评价,其在绩效评价中的地位却远低于政府,显得无关紧要。相比之下在我国的农村实际中,政府长期以来在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中严重缺位,而农民却自发地建设了许多公共物品,我国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更加类似于一种“合作生产”机制。这种机制尤其强调农民的公共服务供给主体性,并呼吁农民对于公共服务供给过程的积极、有益、合作性的参与。在农村公共服务合作生产机制下,政府与农民在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中的相对角色并没有被完全割裂,而是呈现出如图1所示的交集。同时,农村公共服务有效供给机制包括了决策机制、资金筹集机制、信息反馈机制、需求发现机制和绩效评价监督机制[22];为了保证农村公共服务有效供给,有必要保证农民在上述系统中的权利和义务实现对等。因此,作为农村公共服务有效供给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绩效评价机制也呼唤农民作为平等主体的参与。

图1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图[12]
一方面,不能因为主客观性的原因将政府机构数据与农户评价数据割裂开;另一方面,农村公共服务合作生产机制呼吁农民在包括绩效评价在内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中的积极参与。由此来看,有必要构建一个“政府-农户”双元绩效评价体系,也即同时融入农户评价和机构两个维度的一种农村公共服务绩效评价模式。在农民维度上,将公民看待为公共服务的消费者,他们主要关注于公共服务的政治功能,即是否合理地回应了公众的需求以及是否公平地分配公共服务。在政府机构维度上,主要站在地方政府的角度,将首要重点置于公共服务的经济功能,即是否具有生产力或投入产出意义上的效率,是否有效地进行了公共项目的规划和评估。
与传统的农村公共服务绩效评价模式相比,“政府-农户”双元绩效评价体系的主要特点在于其综合性。首先,在内容上综合了农村公共服务绩效评价的不同维度。Brudney和England认为,为了评价一项公共服务的绩效,应该从效率(Efficiency)、效益(Effectiveness)、响应能力(Responsiveness)和公平性(Equity)等方面来衡量。在效率和效率维度,一般偏重于进行生产力分析和投入产出分析,因此政府机构数据更加适合用于测量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效率,衡量农村公共服务的价格和数量是否符合效益要求;在响应能力与公平性的维度,农民的满意度和期望数据更适合于衡量农村公共服务是否满足了农民的需求和需要,以及衡量农村公共服务在农民之间的分配是否公平。可以说,政府机构数据和农户调研数据在内容上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绩效评价内容框架。其次,在评价主体上兼顾了政府和农民两个角色。作为农村公共服务的部分供给者与实际享用者,现实中广大农民却处于无法评价公共服务的尴尬地位,农民的重要地位与其享受的权利并不完全相称。农村公共服务绩效评价的制度安排“本身是一种利益规范的制度设计,其价值取向是平衡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前提下保障公共利益的实现。”①赵明,牛忠江.我国政府绩效评估法治化的路径选择和思考[J].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10(5)。。因此,“政府-农户”双元绩效评价体系要求同时兼顾政府与农民的利益,让两者都充分地享有评价农村公共服务的权利。再次,综合了各种不同的评价目标。绩效评价目标的不同是导致绩效评价结果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作为农村公共服务管理者与供给决策者的政府,其进行绩效评价的目标在于实施绩效管理,提高行政绩效;作为农村公共服务享用者的农民,其进行绩效评价的目标则在于反映真实诉求,敦促提高农村公共服务水平。现实中传统的政府绩效评价目标并不完全与提高公共服务绩效相吻合。那么将农户评价与政府评价相结合,无疑会促进不同目标之间的契合,让公共服务绩效评价在整体上尽量贴近正确目标——提高农村公共服务绩效。
(二)综合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尝试及其应用
在“政府-农户”双元绩效评价体系的构建思路指导之下,应该构建一个综合政府和农民两个主体维度,综合农村公共服务效益、效率、回应性和公平性等内容维度,综合不同利益相关者诉求的指标体系。以公平公正、系统全面、连续稳定、真实可靠和操作简便的原则,我们设计了基于陕西省农村现实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它包含了农村公共事业、农业经济发展、农村公共管理和农村社会服务等四个子系统,是对农村公共服务的基本分类。每一个子系统中包含三个主题层,是对子系统的具体描述。每一个主题层分别对应着政府维度和农民维度的测量性指标。由于从不同维度出发对公共物品主题层的描述各有不同,因此不要求政府维度指标与农民维度指标一一对应。将表1中构建的指标体系应用于陕西省部分地区的农村公共品绩效评价中。首先,关于数据来源。我们选取陕西省内的四个市②经过与被调研单位协商,本文中的四个市分别以A、B、C、D命名。作为评价对象,分别从各市统计年鉴、财政局、公安局等政府职能机构获取相应的机构评价数据,而农户评价维度数据则来源于2010年8月至2011年2月期间在上述四个市范围内农村开展的入户调研。农户调研采取等距抽样原则,按照市、县、镇(乡)、村之间1:2:4:8的比例确定调研村庄,每个村庄调研十个农户。农户问卷调查采取访谈形式,由调研人员提出所有问题,根据受访者的回答做出记录并整理出最终结果,调查问卷共发出350份,回收问卷342份,经过整理和筛选,有效问卷数量为325份,问卷有效率为92.9%。其次,关于权重。根据AHP方法首先对子系统赋权,再分别对机构评价维度和农民评价维度中的各个指标进行赋权。采用Satty的1-9标度法,由专家构建判断矩阵并对矩阵内的元素进行重要性比较,再通过一致性检验来对判断矩阵进行确认,所有判断矩阵的CR值均通过了检验③出于篇幅考虑,本文省略了权重向量值、一致性检验结果以及评价基础数据。。再次,关于数据处理。我们将A、B、C、D市范围内的若干农户样本分别求算数平均值,得到每一个市在每一个指标上的农户评价值;将机构评价值进行无量纲处理;最后将正指标和逆指标转化为方向一致。在此基础之上,结合评级数据和权重,分别计算出农户评价维度和机构评价维度的得分。对两个维度下的得分进行归一化处理后,以算术平均法求出综合评价绩效值,结果如表2所示。
根据表2的绩效评价值数据,可以看出不同的评价维度下评价结果的差异性。在传统的机构评价维度上,A市的绩效评价值排名第一;然而在农户评价维度上,A市却排名末尾;两者之间巨大差异,说明了A市范围内的农村公共品供给在某种意义上并没有得到农民群众的认可和赞同。相比之下,C市在机构评价维度上排名第二,在农户评价维度上排名第一,综合绩效值排名第一;该市范围内的农村公共产品既在机构层面上取得了不错成绩,又获得了农村群众的认同,公共品供给的总体效果优异。因此,通过陕西省四个市的绩效评价案例研究,可以发现“政府-农户”双元评价体系具有丰富的绩效评价内容,也能够丰富绩效评价的结果,使绩效评价值不但包含了对政府服务机构工作绩效的考察,更包含了农民的认同与意见。

表1 农村公共服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表2 “双元”评价模式下的得分及排名
四、结 论
农村公共服务的政府-农户双元评价体系构建的障碍,在于公共服务绩效评价研究领域关于主客观二分性的概念界定。本文研究得出,无论机构数据还是农户数据都兼具了主观性和客观性,人为地设定主客观界限从而划分农户评价和机构评价的做法并不完全合理。考虑到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中政府与农民的“双主体”格局以及农民在农村的重要地位,现实操作中更不应该将农民排除在绩效评价的主体之外。农村公共服务的协同供给机制有必要向绩效评价机制延伸,让农民平等地参与到农村公共服务绩效评价中,以此来综合政府和农民两方面的目标和利益。在“政府-农户”双元绩效评价体系的理念下,本文中构建的指标体系需要进一步的实证检验。更重要的是,保证农村公共服务有效供给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进程中的重要目标。在此过程中,一方面需要完善绩效评价体系,它包含了指标标准界定、指标赋权、指标集结和指标筛选等复杂程序,远比本文中涉及的指标维度选择和体系构建复杂,需要更多的理论创新或实践应用;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需要一个政府绩效评价的制度环境,以此来促进规范绩效评价的目标、内容和流程,强化绩效激励与约束,以保证提高农村公共服务绩效。
[1] 贾智莲,卢洪友.财政分权与教育及民生类公共品供给的有效性[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0(6):139-150.
[2] 曾福生,匡远配,周亮.农村公共产服务质量的指标体系构建及实证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07(9):37-40.
[3] 崔元锋,严立冬.基于DEA的财政农业支出资金绩效评价[J].农业经济问题,2006(9):37-40.
[4] 何精华,岳海鹰,杨瑞梅,等.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满意度及其差距的实证分析——以长江三角洲为案例[J].中国行政管理,2006(5):91-95.
[5] 李燕凌,曾福生.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农民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8(8):3-18.
[6] 朱玉春,唐娟莉,郑英宁.欠发达地区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10(2):82-91.
[7] Yang Y C.Adjusting for perception bias in citizen′subjective evaluation:A production function perspective[J].Public Performance & Management Review,2010,34(1):38-55.
[8] Stipak B.Citizen satisfaction services:Potential misuse as a performance indicator[J].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1979,39(1):46–52.
[9] Brown K,Coulter P.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measures of police service delivery[J].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1983,43(1):50–58.
[10] Licari M,McLean W,Rice T.The condition of community streets and parks:A comparison of resident and nonresident evaluations[J].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2005,65(3):360-368.
[11] Kelly J M,Swindell D.The case for the inexperienced user:Rethinking filter questions in citizen satisfaction surveys[J].The American Review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2003,33(1):91-108.
[12] Brudney J L,England R E.Urban policy making and subjective service evaluations:Are they compatible?[J].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1982,42(2):127–135.
[13] Rossi P,Berk R.Local roots of black alienation[J].Social Science Quarterly,1974,54(1):741.
[14] Ostrom E,Parks R B.Suburban police department:Too many and too small?[J].The Urbanization of the Suburbs,1973(7):367-402.
[15] Lineberry R L.On the politics and economics of urban services[J].Urban Affairs Quarterly,1977,12(1):270.
[16] Williams B,Kellough E.Leadership with an eduring impact:The legacy of Chief Burtell jefferson of the Metropolitan Police Department of Washington,DC[J].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2006,66(6):813-822.
[17] Percy S L.In defense of citizen evaluation as performance measures[J].Urban Affairs Review,1986,22(1):66-81.
[18] Wang X H,Gianakis G A.Public officials′attitudes toward subjective performance measures[J].Public Productivity& Management Review,1999,22(4):537-553.
[19] 公共服务提供机制与方式研究课题组.公共服务绩效评价的指标体系建构与应用分析——基于厦门市的实证研究[J].理论探讨,2009(5):130-134.
[20] 王俊霞,王静.农村公共产服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与实证性检验[J].当代经济科学,2008(2):18-24.
[21] Schachter H L.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performance measures:A note on terminology[J].Administration &Society,2010,42(5):550-567.
[22] 樊丽明,石绍宾.当前中国农村公共品政府供给机制的运行及完善[J].税务研究,2008(12):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