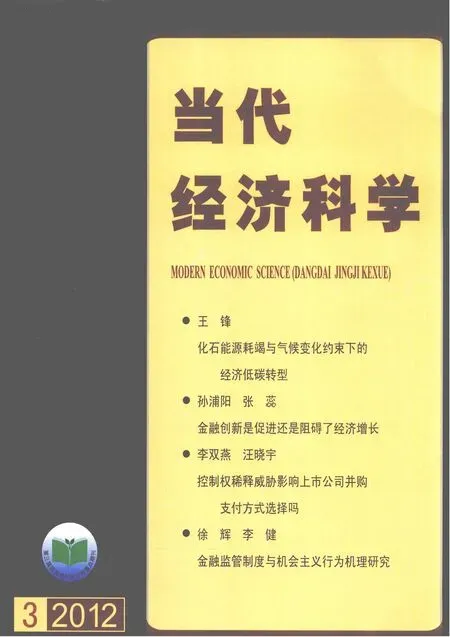中国外资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特征及其空间差异——基于2001-2007年省域面板数据的随机前沿分析
张建波,张 丽
(1.山东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山东济南250014;2.南开大学城市与区域经济研究所,天津300071)
一、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流向我国工业部门的大规模外商直接投资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和国民经济快速发展。例如,沈坤荣[1]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占GDP的比重每增加一个单位,地区全要素生产率(TFP)就可以提高 0.37 个单位;王红玲[2]基于工业分行业数据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工业生产TFP增长具有正向影响;王志鹏和李子奈[3]基于工业微观数据也发现外资对中国工业企业生产效率具有正的外溢效应,且指出提高外资参股比例有助于国内企业生产效率的进步。最近一段时期以来,随着我国资金积累的日益充裕,在工业领域大力引进外资的最主要动因已不再是解决国内资本稀缺的问题,而逐渐转向了发挥外资的正向外溢作用以带动国内企业生产技术的快速进步,要达到这一目的,必然要求外资工业企业在动态上保持TFP的快速增长,以使正向外溢作用能够持续地得以发挥。在此背景下,从实证角度研究中国外资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特征及其空间差异就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
二、文献综述
有关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早期的研究主要采用索洛增长核算法,但是这种方法假定所有生产者在技术上都是充分有效的,这明显不符合经济活动的实际情况。为此,Farrell[4]提出了生产前沿面的概念,并指出现实中往往只有部分生产者能处于生产前沿面上,其余大部分的生产者的效率往往与前沿面所示的最优生产效率存在一定的差距。目前,基于生产前沿面来测定生产效率的方法已得到了学术界比较广泛的认可,其具体的测定方法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非参数方法,在目前的应用中以数据包络分析法(DEA)最具代表性,国内基于DEA方法测算全要素生产率的代表性文献有:颜鹏飞和王兵[5]、郑京海和胡鞍钢[6]等,一类是参数方法,在目前的应用中以随机前沿分析法(SFA)最为流行,国内基于SFA方法测算全要素生产率的代表性文献有:涂正革和肖耿[7]、傅晓霞和吴利学[8]等。
考虑到两种方法的利弊以及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本文认为SFA方法较之DEA方法更具适用性,具体而言:第一,SFA方法既可以对模型中的参数进行检验,也可以对模型本身进行检验,而DEA方法则无法对前沿面的适用性进行判断。第二,SFA方法通过组合误差中的随机扰动项保留了环境影响因素的作用,这较之DEA方法更符合现实情况;同时,这也避免了DEA方法在影响因素分析上的逻辑困境。第三,傅晓霞和吴利学[8]对于中国经济TFP测定的研究表明SFA方法更适合于现阶段的中国经济增长核算。需要注意的是,目前采用SFA方法的诸多研究忽视了对随机前沿函数形式设定的检验,这就难以克服SFA作为参数方法的模型形式设定的随意性。采用SFA方法的新近文献已经开始注重对模型形式设定的反复试验和检验,以期获得最具适宜性的模型形式,如白俊红和江可申[9]等。本文亦采用这一模型形式设定及其检验的步骤进行外资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
三、模型设定、估计及检验
(一)数据选取及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是2001-2007年中国大陆29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外资工业企业投入和产出数据。海南和西藏两省区因个别年份数据缺失严重而难以补全,因而在实际测算样本中我们舍弃了这两个省区的数据。研究中所使用的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经济普查年鉴2004》和《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既有文献关于工业企业产出指标的选取并不一致,有些文献计算工业企业的技术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时采用的产出指标是工业总产值,而有些文献采用的则是工业增加值,两者之间的区别就在于前者的投入指标中包括了表现为价值转移形式的原材料等中间投入而后者则没有包括中间投入。鉴于生产性经济活动的意义更大程度上在于新价值、新财富的创造,而不是价值形式的转移,因而本文拟采用工业增加值(Y)作为产出指标。此外,考虑到研究的时间跨度较长,为了避免其间因价格波动较大而引致的测算偏误,本文选取2001年作为基期并根据各省份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对各省份外资工业增加值进行各年可比价格的换算①《中国经济普查年鉴2004》没有给出外资工业企业的工业增加值数据,因此本文根据收入法统计核算公式对其进行计算,具体的计算公式为:工业增加值=劳动者报酬+营业盈余+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由于通过《中国经济普查年鉴2004》无法获得“生产税净额”的情况,本文通过从营业收入中减去营业成本和补贴收入来获得生产税净额与营业盈余的合计值。那么,工业增加值=(本年应付工资总额+本年应付福利费总额)+(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补贴收入)+固定资产本年折旧。。
各省份外资工业企业的劳动投入(L)采用的是各省份外资工业企业的年末从业人员数这一代理变量,对于个别缺失值采用插值法予以补充。物质资本投入(K)选用各省份外资工业企业的年末固定资产净值并进行适当处理之后作为代理变量。由于统计年鉴中得到的外资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净值仅是账面价值,要对其以各省份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行折算,折算公式参考朱钟棣和李小平[10]的计算方法,如式(1)所示。其中,kit0为1990年各省份外资工业企业的年末固定资产净值;Δkit是各省份外资工业企业第年的固定资产净值增加量,本文以相邻两年固定资产净值原值的差值表示;pit表示各省份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

(二)模型形式的设定
现有的研究中,随机前沿模型较常用的函数形式有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函数和超越对数(Translog)函数,其中前者设定形式简单,但是假定技术中性和产出弹性固定;后者则放宽了这些假设,且在形式上更加灵活,能更好地避免由于函数形式的设定错误而带来的估计偏差。由于不能事先确定技术是否为中性、产出弹性是否固定、以及技术是否存在进步等,因此本文首先选用超越对数函数形式的随机前沿模型并对其进行检验。设定生产函数有劳动投入(L)和物质资本(K)等两项要素投入,那么本文的随机前沿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模型可以表示成公式(1),其中εit=vit-uit为组合误差项,且vit与uit相互独立;vit为第地区的随机误差项,服从正态分布,即vit~N(0);uit为第i地区的技术无效率项,表示个体冲击的影响,被假设服从uit=uiexp[- η(t- T)],uit服从非负截断正态分布,即uit~N+(μ),其中η表示技术无效率项的变化率。



(三)模型估计及检验
在不考虑外部影响因素的情况下,我们利用Frontier 4.1软件包分别对超越对数函数形式的随机前沿面板模型(模型Ⅰ)和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形式的随机前沿面板模型(模型Ⅱ)进行极大似然估计,以寻求适宜表达中国外资工业企业实际情况的生产函数形式。从表1中可以看出,模型Ⅰ和模型Ⅱ的方差参数均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1%的检验,表明效率的偏差主要来源于技术非效率效应,因而采用SFA技术进行模型的计量估计是合理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的设定形式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对中国外资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测算的有效性。表1的最末行显示,以模型Ⅱ为原假设、模型Ⅰ为备择假设的广义极大似然估计率小于自由度为3的混合卡方临界值,因此接受函数形式为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原假设,这表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更适合拟合本文的样本数据,更适宜表达中国这样一个快速发展国家的外资工业企业生产过程。基于此,我们在下文分析时均选取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Ⅱ)作为随机前沿模型的函数形式。模型Ⅱ的估计结果显示,劳动产出弹性和资本产出弹性之和为0.9252(略小于1),这表明在样本期间内中国外资工业企业的规模报酬呈缓慢下降的态势;时间变量的系数为0.1180,由此可得年均技术进步为12.52%,这反映出较之非外资企业而言中国外资工业在技术创新方面仍具有较大的优势;和的值均显著不等于0,这表明中国外资工业企业存在着明显的技术无效率;值表明外资工业企业的技术无效率值大部分分布于0.8826周围;值小于零,这表明在样本期间内中国外资工业企业的技术效率年均退步2.90%,亦即生产潜力的发挥未能适时赶上生产技术的快速进步,外资工业企业的部分技术进步未能转化成现实的生产力。
除了检验生产函数形式的设定正确与否之外,我们还设定了以下四个假设来检验随机前沿柯布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面板模型的适宜性:第一个零假设是认为模型不存在技术进步,即β3=0;第二个零假设是技术无效率值uit服从零点截断的半正态分布,即μ=0;第三个零假设是技术无效率uit对于时间不存在收敛的趋势,即η=0;第四个零假设是技术无效率服从零点截断的半正态分布且对于时间不存在收敛的趋势,即μ=η=0。以上四个假设均可使用广义似然比检验,其统计量的计算公式为LR= -2{ln[L(H0)/L(H1)]}。其中,L(H0)是一个受约束的零假设H0前沿模型的对数似然值,L(H1)是一个无约束的备择假设H1前沿模型的对数似然值。如果零假设成立,那么检验统计量λ服从混合卡方分布,自由度为受约束变量的数目。表2的模型假设检验结果显示,所有的零假设均被拒绝,这表明以随机前沿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进行估计的中国外资工业企业存在着伴随时间的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变化,且样本不存在广泛的、严重的技术无效率现象。因此,本文所采用的带有技术无效率项和技术进步的随机前沿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面板模型能够较好地拟合外资工业企业的样本数据,并且应该使用极大似然估计法进行模型估计。

表1 两种随机前沿面板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

表2 随机前沿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的假设检验结果
四、TFP增长的核算与分析
(一)TFP增长的计算方法
Kumbhakar and Lovell[12]研究发现,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变化可进一步分解为生产效率变化、技术进步变化、规模效率变化和资源配置效率变化,其中由于价格信息的可得性很差,因而资源配置效率往往不易计算,多数学者通常考察前三种细分变化。以往有些文献将投入要素产出弹性之和视为1,也就是将规模报酬不变的条件应用于生产函数模型之中,如 Wu[13]和张军[14]等,此时对于随机前沿生产函数而言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就等于生产效率变化率与技术进步变化率之和。考虑到外资工业企业的特性,不同于以往的这些研究,本文放宽了规模报酬不变的严格假定,采用Kumbhakar[15]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分解公式研究中国外资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变化趋势。假定不考虑随机误差项的随机前沿面板模型的一般对数形式为lnyit=lnf(xit,t)- uit,其中yit表示省份i在时期t的外资工业企业实际产出;f(·)表示柯布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式的确定前沿产出;表示外资工业企业的一组投入向量;t为时间趋势;uit为非负的技术非效率项。根据本文上一部分所采用的随机前沿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并采用简易形式的全要素生产率表示形式①需要说明的是,Kumbhakar[15]所提供的全要素生产率分解方法是以线性函数来表示的,其中技术进步为对数形式,这被称之为复合(compound)形式的TFP增长率形式,这种分解方式是对实际增长的一种近似表示,且技术进步越大时其近似效果就会越差。为了精确起见,本文将采用简易(simple)形式的TFP增长率形式,即以乘积表示的实际生产率值的形式。,xit那么中国外资工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率可分解为公式(4)。

(二)外资工业企业TFP的增长特征
表3列出了2001-2007年中国各省份外资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年度变化率及其样本期间平均变化率。需要说明的是,现有文献在计算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变化率时较多采用的是简单平均方法,这会导致增速波动大的样本的均值被相对高估,而增速变化平稳的样本的增速被相对低估;针对简单平均法的固有缺陷,本文采用几何均值的方法计算样本期间外资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变化率,这种方法的优点就在于可以消除各样本年度波动幅度不一致(即离散程度差异的影响)。从表3可以发现,2001-2007年期间全国层面外资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始终呈现出快速增长态势,其几何平均增长率达到7.77%;样本期间,其最快增速为8.83%,最慢增速为5.60%;进一步计算可知,全国层面外资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在各年度之间的变异系数为0.047,这表明中国外资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随时间的波动变化并不大,亦即其增长态势在样本期间相对较为稳定。从省域层面来看,除了甘肃和青海两省的TFP在部分年度出现下降之外,全国绝大多数省份的外资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均呈现出持续增长态势。其中,仅有青海省外资工业在样本期间内的平均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出下降状态,但是在2004年之后其年度全要素生产率表现出连续正增长的改善态势;吉林、天津、上海和北京等四省市外资工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在样本期间内的平均增速位列全国前四位,且平均增速均超过了10%。进一步计算可知,样本期间内全国各省域外资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之间的平均变异系数为0.365,这表明我国外资工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较为明显的区域非均衡性特征。

表3 2001-2007年中国各省份外资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率(单位:%)
(三)外资工业企业TFP增长的空间差异
外资工业企业的发展状况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而中国东部、中部、西部以及东北等四大经济板块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且各地区的外资企业管理体制和产业发展环境等各具特点,这些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对当地外资工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因此,有必要从区域的角度对中国外资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做深入比较分析①“十一五”规划中,中央政府建议用东、中、西和东北四大经济板块来代替“七五”以来沿用的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的区域划分方法。此后,国家统计局在统计操作上也变区域的传统“三分法”为现有“四分法”。与此相一致,本文亦采用“四大经济板块”的区域划分方法,其具体的划分方式为: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和海南等10个省份;中部地区包括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和山西等6个省份;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云南、贵州、广西、西藏、内蒙古、陕西、甘肃、青海和新疆等12个省份;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等3个省份。。图1显示了2001-2007年全国及四大经济板块外资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变化趋势,从中可以发现,全国及四大经济板块外资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总体上均呈现出跌宕起伏的波动变化趋势,其中2003-2004年度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相较其他年度有较为明显的回落。进一步分析可知,这是2003年“非典疫情”爆发对国内外资工业企业不利影响的预期延续;具体而言,“非典疫情”的爆发导致外资工业企业的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在当期均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同时也导致其对研发创新等一系列促进企业技术进步的当期投入的降低,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降低直接导致2003年外资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相较2002年出现一定幅度的回落,而研发创新等当期投入的降低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则存在一定的时滞性且这种创新投入不足的影响相对更大,这就导致2004年外资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相较2003年出现较大服务的回落。此外,图1还显示出,四大经济板块外资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长率从高到低依次为东部、东北、中部和西部,而这是与四大经济板块的经济发展水平高度正相关的,这表明我国各地区间外资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明显的“马太效应”特征。


为了进一步考察中国外资工业企业TFP增长率在区域分布上的空间差异,我们计算了全国范围以及四大经济板块内部的各省份之间外资工业企业TFP增长率的变异系数,如图2所示。计算结果显示,全国及四大经济板块内部的各省份之间外资工业企业TFP增长率的变异程度在总体上均呈现一向种“先大后小”的发展状态,亦即其波动性在逐渐趋稳定。其中,东部地区内部各省份之间的TFP增长率的变异水平和波动程度均最小,其平均变异系数仅为0.16;西部地区内部各省份之间的TFP增长率的变异水平和波动程度均最大,其平均变异系数高达0.58;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内部差异水平和波动程度居中,平均变异系数分别为0.25和0.28,低于全国层面的变异水平。这表明,除了西部地区之外,其他三大地区内部的外资工业企业TFP增长率变异程度均具有明显的区域性;换言之,在地理空间上毗邻、经济地理条件相近的省份之间,其外资工业企业TFP增长率也更为相近。西部地区呈现出与此相反的情况,原因主要体现为:一是与其空间范围十分广大、内部的地理条件更为复杂有关;二是很可能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密切有关。总体而言,东部与西部地区分别是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最高和最低的地区,其外资工业企业TFP增长率的变异程度恰与此相反;中部和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相近且均位居全国中游水平,其外资工业企业TFP增长率的变异程度同样差异不大并位居全国中游水平。由此可见,各区域内的外资工业企业TFP增长率的变异程度与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呈反向的关系;亦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区域,其内部的外资工业企业TFP增长率越趋一致,愈加呈现出相对收敛的趋势。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外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快速增长对于充分发挥外商直接投资的正向外溢效应具有非常重要的保障作用。本文基于随机前沿分析方法对中国省域外资工业企业在2001-2007年期间的面板数据进行了模型估计及假设检验,并据此对中国外资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进行了实证测算和具体分析。研究发现,样本期间内中国外资工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始终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其中技术进步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全国及四大经济板块外资工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总体上均呈现出跌宕起伏的波动变化趋势,且各区域间外资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明显的“马太效应”特征;全国及四大经济板块内部的各省份之间外资工业企业TFP增长率的变异程度在总体上均呈现一种“先大后小”的发展状态,亦即其波动性在逐渐趋向稳定,而且除了西部地区之外其他三大地区内部的外资工业企业TFP增长率的变异程度均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各经济板块内外资工业企业TFP增长率的变异程度与各经济板块的经济发展水平呈反向的关系。
鉴于外资工业企业在加快我国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具有重要而独特的积极作用,为了进一步促进我国外资工业企业更好更快地发展,本文基于以上研究发现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加快外资引进结构的转变优化。引进工业外资时,各地需要重点加强对汽车制造、重化工业、生化制药等资本密集程度和技术水平较高行业外资的政策吸引,以使我国外资工业企业的构成格局由以往的以家用电器制造、电子产品组装等技术水平较低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为主,逐步演变为以上述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为主,从而适应我国工业化进程不断推进和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的新形势。第二,促进投资持股形式的灵活发展。在外资持股比例已经较高的东部和东北地区,可以根据国家和地区发展战略的需要和行业自身的特点,灵活发展外商独资、控股和参股等多种投资持股形式;在外资持股比例相对较低的中部和西部地区,则可以考虑通过适当的渠道增加外资的持股比例,以带动该地区外资工业企业TFP的快速增长,促进外资工业企业在区域间的均衡发展。
[1] 沈坤荣.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J].管理世界,1999(5):22-34.
[2] 王红玲.中国工业所有制结构差异及其影响的实证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1(5):84-87.
[3] 王志鹏,李子奈.外资对中国工业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研究[J].管理世界,2003(4):17-25.
[4] Farrell M J.The measurement of production efficiency[J].Journal of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Series A,General,1957,20(3):253-281.
[5] 颜鹏飞,王兵.技术效率、技术进步与生产率增长[J].经济研究,2004(12):55-65.
[6] 郑京海,胡鞍钢.中国改革时期省际生产率增长变化的实证分析[J].经济学季刊,2005(2):263-295.
[7] 涂正革,肖耿.中国的工业生产力革命——用随机前沿生产模型对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分解及分析[J].经济研究,2005(3):4-15.
[8] 傅晓霞,吴利学.前沿分析方法在中国经济增长核算中的适用性[J].世界经济,2007(7):56-66.
[9] 白俊红,江可申,李婧.中国地区研发创新的相对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分解[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9(3):139-151.
[10] 朱钟棣,李小平.中国工业资本形成、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及其趋异化[J].世界经济,2005(9):51-62.
[11] Battese G E,Coelli T J.A model for technical inefficiency effects in a stochastic frontier production function for panel data [J].Empirical Economics,1995,20(3):325-332.
[12] Kumbhakar S C,Lovell C.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
[13] Wu Yanrui.Openness,productivity and growth in the APEC economies[J].Empirical Economics,2004,29(1):593-604.
[14] 张军.增长、资本形成与技术选择:中国经济增长下降的长期因素[J].经济学季刊,2002(2):301-338.
[15] Kumbhakar S C.Estimation and decomposition of productivity change when production is not efficient:A panel data approach [J].Econometric Reviews,2000,19(4):425-4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