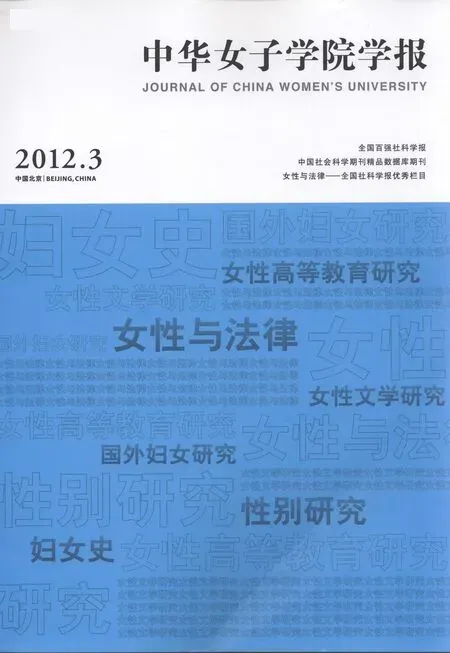社会资本的建构过程
——以皖北C村云南籍婚迁流入妇女为例
孙宇凡 李梦迪 田飞
社会资本的建构过程
——以皖北C村云南籍婚迁流入妇女为例
孙宇凡 李梦迪 田飞
通过对皖北C村云南籍婚迁流入妇女与家庭成员、乡村邻里等行动者之间的互动过程进行历时性考察,将该群体社会资本的建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因社会环境、家庭发展状况不同而特征不一,但各阶段的行动逻辑都是将经济资本、文化资本转换为社会资本,并同时以原有的社会资本为基础进行再生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布迪厄的资本转换理论。将三个阶段统合观之,该群体的社会资本形塑过程也呈现着内卷化的样态。
社会资本;内卷化;资本转换
一、引言
社会资本对移民的社会融合有重要的影响。雷开春通过研究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资本状况,认为社会资本有利于他们的总体社会融合。[1]悦中山、李树茁等人认为,嵌入于农民工——市民网络中的社会资本反映了该群体在迁入地的融入水平。[2]台湾学者唐文慧、王宏仁则通过对在台的越南籍跨国婚姻中受暴妇女的访谈,认为关系网络的拓展有利于这些女性走出父权家庭的阴影,更好地融入社会。[3]上述研究均是将社会资本作为自变量而展开的功能性分析,而将社会资本作为因变量的生成性分析相对较少。换言之,学术界集中讨论了“社会资本有什么用途”,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是什么样的过程与要素促成了社会资本的重要性格局”。林南指出,社会资本研究存在功能分析与生成研究两个方向,但后者未受到足够重视。[4]163-192鉴于事实的重要性与理论上的空缺,本文将探讨婚迁流入女性社会融合的一个重要课题:离开家乡到语言不通、水土不服的他乡,以媳妇、母亲、非本地人等身份生活二十多年后,这些婚迁流入妇女的社会资本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建构历程。
二、资本转换:理解社会资本生成的理论工具
首先,布迪厄对资本概念作了界定,他认为资本是一种嵌在主体或客体的结构之中的力量,并将资本分为三种形式: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布迪厄认为,经济资本可以直接换成金钱,而文化资本有所不同,它可以是一种长期的、身心化的惯习,也可以是物化的文化性质的物品与制度化、权威化的资格证明,如文凭。[5]46-58布迪厄在阐释文化资本生成的过程中,还强调了语言能力的重要作用。[6]48-49因为语言能力不仅是沟通的工具,也是一种身份合法性的象征,比如,个人的口音反映着行动者的社会背景与生活习性。同时,作为最早提出社会资本概念的学者,布迪厄认为,社会资本是行动者所拥有的潜在的或现存的资源丛,这些资源与拥有或多或少的制度化共同熟识和承认化关系网络有密切关系。
其次,布迪厄提出了社会资本的转换式生成机制。一方面,相对于文化资本、经济资本而言,社会资本具有特殊的关系型态,它的生产和再生产要求行动者对社交活动的持续性投入,而在这个过程中将会消耗一定的经济资本。另一方面,文化资本在转化以生成社会资本的过程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布迪厄通过研究文化资本的“排他”作用,指出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之间具有极强的亲缘性。[7]110因为文化资本往往被看成是区分社会阶层的重要标志,因而会接纳某些人而排斥另外一些人,从而限制了社会网络的拓展与社会资源的调用。当然,从解释学角度看,社会资本的再生产也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要依赖原有的社会资本存量,因而需要与朋友、亲戚等进行不断的交往,从而对关系网络进行确认与再确认。
总之,社会资本的生成与形塑是一种长期的转换与再转换的动态过程。但可惜的是,国内学者在研究人口迁移与社会融合的课题时,较少运用这一理论框架。鉴于资本转换理论的较强解释力,我们对婚迁流入妇女的生命历程进行阶段划分,以透视她们的社会资本建构与变迁的样态。
三、研究对象和方法
2010年7月至8月,我们在皖北C村进行了一项实地调查。C村是一个典型的皖北农村,与江苏省毗邻。C村耕地为3212.5亩,人口为1685人,以种植小麦、玉米、花生等农作物为主。C村人的生活方式受传统的皖北文化影响:村民家宅往往相距不远,每家门前都有非常大的院子可供种植蔬菜;村民之间交往频繁,妇女们喜欢说些“闲话”,即通过讨论“张家长李家短”的一些事情交换与澄清彼此的信息;保留着传统的赶集贸易模式,贸易较为频繁,且赶集地点离该村较近;结婚习俗仍保留了传统的“门当户对”的观念,通常而言,结婚费用由男方承担,主要用于盖新房、付彩礼以及“说媒钱”等,婚后女方与公婆同住并负责大部分家务劳动和一部分农活。
由于本研究组一名成员为该村居民,所以我们在C村居住有一个月左右,与研究对象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接触,顺利地对五位云南籍婚迁流入妇女进行了访谈。访谈对象的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五名受访女性的配偶中,四名为农民工。①此处使用“农民工”作为当前工作形态的归类,意在概括地表达此类群体的职业特征,即兼具务农与外出打工两种职业状态。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女性迁移者的社会资本建构历程,我们还对其中三名妇女的丈夫进行了访谈。

表1 访谈对象基本情况
四、社会资本的建构历程
虽然五位“云南女”②异地联姻现象情况非常复杂,由于研究者身份和研究侧重点不同,不同研究者对其有不同称谓,如“外来婚嫁女”、“远嫁妇女”。本文则以“云南女”作为对C村云南籍婚迁流入妇女的简称。在迁入时间、子女婚况等方面存在一定的相似性,但是由于个案已迁至C村二十多年,对一些往事只能记得大致的发生时间,因而我们借鉴生命历程研究的思路,对“云南女”的访谈资料进行梳理,形成了由事件、人物、时间等要素所构成的序列性资料。我们将她们居住在C村的时间划分为三个阶段,在各个阶段,她们的各种资本存量各有不同,因而转换至社会资本的水平也有所差异。
(一)第一阶段
1.资本的初步断链与重新获致
阿香告诉我们,她刚到C村的时候,周围没有人能听懂她讲话。她说:“那时候,俺只能天天跟自己讲话,他(阿香的丈夫)也听不懂俺讲话。俺只能给手势,打比方。”在饮食方面,阿香也不习惯皖北人吃的白米饭。除了差异较大的习性与语言、单一的社会关系,阿香还身无分文。因为“云南老家实在太穷了,俺跟他的时候身上就只有从堂姐那儿借来的十块钱”。在讲究“门当户对”的农村社会,男性一般在18岁前后就结婚了,而这些“云南女”的丈夫却因为多种原因延误了婚龄。一方面,阿香的丈夫表示,当时C村的“收成不好,有时候穷得都吃不上饭”,而且,农村的婚姻习俗是讲究彩礼的,所以不容易找媳妇,耽误了青春。阿香的丈夫说:“人家都管俺叫‘蹩脚男’,就因为俺年纪大,找不到媳妇。”另一方面,“云南女”的丈夫家族势力普遍较弱,当地姑娘看不上他们。阿芸的丈夫是个孤儿,自幼便寄居在舅舅家,等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舅舅托媒人找了几户人家都看不上他。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云南女”的丈夫往往自身的经济资本很薄弱,社会资本也很稀缺,并由此在文化上被贴上了“蹩脚男”的标签。这些原因导致“云南女”在原有资本初步断链后,由婚迁所重新获致的资本也具有经济资本薄弱、社会资本稀缺并被连带性歧视的特征。
2.生育子女与承担家务劳动和部分农活
刚到C村才三个月就怀孕的阿芸,需要独自承担所有的家务劳动和部分农活,因为家里就她和丈夫两个人。根据我们的访谈纪录,四名受访者回答“照顾孩子”是需要她们单独承担的工作。生育子女所带来的抚育义务、繁重的家务劳动和农活占据了“云南女”几乎全部的生活,使之不易走出家庭以建构自己的社会资本。
3.生育男孩/女孩的差异性与相似性影响
受传统生育文化的影响,丈夫与公婆很希望“云南女”能生个男孩。阿丽到C村一年后便生了男孩,公婆开心得“一下子包揽了所有的家务”,到处夸阿丽“中用”。究其原因,阿丽说:“家里人丁太少了,没有人家收成多,在村里说话‘不硬强’(没有话语权的意思),这下多了个男孩,怎么能不高兴呢?”在儿子上小学之前,阿丽只承担了部分的家务活,有一定的空闲时间带着孩子串门访亲,和邻里的妇女说说“闲话”。她的丈夫也在有了儿子之后,将家里的收入交由阿丽掌管。因此,有时候阿丽便趁赶集的时候,帮邻里捎一些杂货以促进彼此之间的交往与联系。相较而言,阿薇虽然在迁入的一年之后生了个女孩,但她并没有放弃努力建构自己的社会资本。阿薇说:“对门他家看俺生个女的,到处说俺不中用,劝阿亮(阿薇的丈夫)把我赶回去。但是俺就要争口气给他家看看。”因此,阿薇在生活之中便更加留心,尤其在赶集的时候认真学C村的方言,以努力改变邻里关系。阿薇的丈夫在访谈的时候说:“日子一长,也有感情,阿薇又这么好,俺也就没听对门的了,以后他家也就没再跟我提这个事。”有意思的是,传统的婆媳冲突在“云南女”的家庭中并不明显,其原因可能在于“云南女”解决了“蹩脚男”的婚姻问题,因而虽然生男生女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总的来说还是“中用”的。
在这个阶段,刚嫁到C村的“云南女”,因抚育孩子或承担农活等事务,其形象比较符合夫家与邻里的角色期待。换句话说,尽管生男孩或生女孩会有一定的差别,但贤惠的媳妇与妈妈的形象符合传统婚姻习俗与生育文化的期待。因此,“云南女”往往可以在原有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等断链,获致新资本有限的情况下,一方面通过生育子女促进自己社会资本的发展,另一方面通过有意识地重构,如帮邻里捎杂货,形成一套新的资本形式。叶文振指出,婚迁流动妇女在迁入地扮演着双重角色,即迁出地文化的传播者与迁入地文化的参与者。[8]本研究中的“云南女”在重人伦、讲关系的“乡土中国”中,将重构的文化资本(如学习方言)与经济资本积极转化为社会资本,以努力获得乡亲邻里的认可。
(二)第二阶段
1.原有资本的彻底断绝
我们发现,尽管刚迁入C村的时候,五个“云南女”面临着原有的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等初步断链的问题,但她们仍然对老家的亲戚抱有相互联系甚至今后探亲等想法。但是,由于联系的中断,在迁入C村三四年之后,便有三人不记得自己的具体籍贯,也不记得家里的亲戚长什么样了。此外,五名“云南女”中也只有一人的亲戚有过来信,但可惜的是,这封来信却不是出于关心,而是出于欺诈。阿丽告诉我们,她刚生过孩子的一两年一直惦记着老家,到了儿子三四岁的时候,弟弟来信说母亲生病了急要用钱,后来才知道这是弟弟欺负她在外面不了解家里真实情况想骗她钱的。自此,阿丽再也不和家里联系,也“不敢再问家里的事情了”。其他四名“云南女”也承认,从想家到不想家大约经历了三四年左右“慢慢的”历程。一方面因为交通不便,往返路费很高,这对“云南女”的夫家而言是一大困难,另一方面也担心因信息不对称而发生类似阿丽经历的情况。我们认为,这种欺诈事件在一定程度上象征着社会资本的崩解。因为信任作为一项社会资本,是基于理性证据较少产生的积极期待[9],而“云南女”因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恐惧正说明信任的消解、原有社会资本的消失。也正因为联系的中断,五名受访“云南女”都表示,老家也没有给她们提供过经济等方面的帮助。
2.“逆向强化”的社会资本积累
由于夫家自身条件较差,“云南女”的经济等资本建构受到影响,但她们没有放弃积累自己的社会资本。阿薇说:“有一回,俺和阿亮吵架,对门那伙看俺家笑话,一个劲让阿亮‘往死里踹’(狠狠地打的意思)。”事后,阿薇和阿亮达成一致:“要挣口气,一定要有出息。”从此,家庭关系变得更和谐,夫妻间相敬如宾。阿香等四人也表示,邻里有的人看不起她们,有的甚至破坏她们的庄稼,但她们反而“越挫越勇”。阿香说:“就是因为他们看不起俺,俺和他(阿香的丈夫)才出去打工,多挣点钱要让他们看得起。”阿香和她的丈夫是当地第一批农民工,后来挣了些钱回到C村盖了新房。阿香说:“看俺家盖了新屋,有的人还羡慕俺,要俺也带她出去打工。”阿香明白,自己想摆脱被歧视,就要帮助别人,“让人家记住对俺有人情”。
3.子女:作为“桥接型”社会资本
如上所述,生育子女给“云南女”社会资本的建构带来一定的影响。当子女上学之后,子女又成为“云南女”与其他父母之间建构联系的桥梁。阿芸的第二个儿子上初中的时候,阿芸鼓励他带朋友到家里玩,阿芸待别人家孩子也很好。因为子女教育的问题,阿芸找到了与其他父母聊天的共同话题。阿芸说:“Z庄的小李他妈,经常来俺这抱怨小李不听话,在学校调皮打架。俺总是安慰她,然后告诉她俺是怎么教育子女的。”我们了解到,阿芸的女儿在安徽省某大学就读,是该村第一个考取重点本科的女孩,阿芸以此为荣,乡亲则开玩笑夸阿芸是“大教育家”。但是,当我们问及当地很多孩子上完初中就出去打工了,为什么她这么坚持让女儿读书时,她却说:“俺怎么混都是云南人,俺不能再让小孩受这罪,得让她好好的,过好日子。”
其他四位“云南女”也表示,尽管她们在语言上、生活上慢慢适应了C村的生活,也因某些方面的成就博得了当地人的赞誉,但终究免不了“云南女”的心结。在参与观察时,我们随机问八名当地人“知不知道哪家有妇女是从云南过来的”,八名中有七名都可以指出具体位置,这说明在一定程度上,“云南女”作为一个标签持续存在于C村,也影响着“云南女”的心理。因此,伴随着子女的成长,“云南女”把更多的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子女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她们获取社会资本的桥梁。正如帕特南所说,桥接型社会资本具有向外需要的取向,可以通过弱链接获得社会资本的积累。但是,他也指出,与之相对应的黏合型社会资本具有内在取向的特征,通过排他而形成集体内部成员间的认同。[10]22-24在此,我们看到了作为乡村社会的、集体层次的黏合型社会资本与作为婚迁流入的、个人层次的桥接型社会资本之间的冲突。如上所述,尽管“云南女”通过子女与其他父母建立了沟通与联系,但乡村社会所具有的稳定性关系格局仍旧将其标签化,并没有彻底地接受她们。
4.“云南女”之间的关系互动
五个“云南女”虽然是陆续婚迁到C村的,但是相互之间从一开始便从亲戚邻里那里对彼此情况有所了解。在生活适应的初期,因为承担家务与孕育子女,她们不易走出家门。当子女上学之后,她们之间的关系互动便越来越频繁。阿薇是五个人中嫁到C村最晚的一个,她对当地的方言学习得较慢,为了防止在赶集时被欺诈,每次都和阿美一起去。阿薇说:“有的贩子就欺负俺这样的外地人,看俺口音不像C村的,就卖得比别人贵。后来被阿美发现了,骂了那小贩一顿。”除了赶集等生活上的联系,在关键时刻,五个人也都表示“还是得靠‘自己人’”。阿丽的丈夫曾得了一场大病,治疗需要七八千块钱。但是,阿丽的丈夫却过于老实,关系很好的朋友较少,而夫家的亲戚又都担心他“熬不过这一关了”,不愿意借钱给他们。这时,阿丽知道阿香家准备建新房,可能经济比较宽裕,便去找了她。阿香很爽快,把准备买水泥等材料的钱都借了阿丽。可以说,借钱是一个很能反映社会资本状况的事件,因为它考验着两个人关系的密切程度与资源的调动情况。孙立平认为,研究农民生活的时候往往不易发现结构的“隐秘”,因为从表面上看可能都是“叔侄”一类的关系,因而需要另辟蹊径,通过对诸多事件的考察,分析行动主体在事件过程中的互动情况,了解其中的“隐秘”。[11]6在上述借钱事件中,阿丽夫家亲戚与阿香的不同反应,体现了她们的社会资本建构状况。
通过对第二阶段的动态分析,我们看到,虽然“云南女”在初步适应C村生活后,面临着原有社会资本断绝、邻里的歧视等问题,但她们却凭借顽强的意志使得自身社会资本逆向上升。在这个积累的过程中,“云南女”与丈夫一起,通过不懈的奋斗与对子女的教育,赢得了一定的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也由此扩建了社会资本。但是,因为“云南女”的标签效应,“借钱”等事件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在社会资本“逆势”扩建的背景下,隐含着不稳定的要素。换句话说,这种“逆强化”、以子女为“桥梁”的间接型积累与建构具有一定的限度与脆弱性,难以摘除“顽固的”标签,也难以应对突发事件。
(三)第三阶段
1.“无主体熟人社会”的障碍作用
近年来,C村的青壮年陆续进城打工,他们一般流入到江、浙、沪等地。阿芸和丈夫每年只有过年前后或女儿放暑假的时候才回到C村,其余时间都在上海打工。而其他四名“云南女”中,有三名与丈夫常年在外地打工。阿丽之所以没有打工,是因为她的丈夫得了那场大病之后留下了后遗症,需要有人时常照顾。吴重庆认为,目前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常年的异地化生活,已导致乡村社会生活运作不具有“熟人社会”的特征。他认为这种“病态”的熟人社会可称之为“无主体熟人社会”。通过我们的访谈可以看出,C村从“农村”变成“农民工村”给“云南女”的社会资本拓展带来了在时间上与空间上的直接障碍。阿芸说:“过年回来的时候,看到村里人,有的一下子也喊不出来名字。可不是,一年就回来半个多月,哪来这么多工夫想那些‘东家长李家短’的事。”正如布迪厄所说,社会资本的生产需要消耗一定的时间予以经营。
当然,“无主体熟人社会”并非绝对意义上的“无主体”,而是指现在的农民如春去冬返的候鸟一般。当我们进一步考察从“冬返”到“春去”这段可以用来建构社会资本的时段时,却发现C村春节前后兴起了打扑克、玩麻将等娱乐活动,从而使得C村的集体空间聚拢于此。而五名“云南女”婚迁至C村之前,都不会麻将之类的活动,婚迁之后更苦于家庭人丁较少、繁重的家务劳动,没有闲暇时间、也不愿意学习这些娱乐活动。这样一来,她们便在公共空间中处于“缺场”状态,从而给自身的社会资本建构设置了障碍。阿美说:“有时候我也想学,要不感觉过年回来也就没意思了。但话说回来,哪来那时间呢?好不容易回来一次还不把该干的活都干了?”
2.“云南女”的子女联姻
按C村的婚姻习俗,男性与女性在学业(一般为初中)结束的两三年之后便可以择亲成婚。五名“云南女”的子女中,除了阿芸的小女儿在大学读书,其他人均在初中毕业后三到六年间成婚。阿美和阿丽都已经和阿香成为亲家。阿薇的女儿是和邻村的一个“云南女”的儿子结的婚,但已离婚。阿美认为,作为“云南女”,终究是外来人,自己在C村受到了很多歧视,所以不希望让子女嫁到当地人家里仍然被当成外来人。阿丽与阿香也表示,在给子女相亲的时候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阿薇则认为,要摆脱外来人的身份,不仅要找云南籍的人家,还要让子女嫁到其他地方。阿芸在访谈时表示:“小女儿上了大学,能嫁到城里最好了。城里人又不知道俺这情况,就不会介意俺闺女了。”阿美的三儿子初中毕业后就在上海打工,她不希望儿子找C村的媳妇。阿美说:“俺知道,俺儿子在上海买房子找那边的媳妇不可能,但要是回来找当地人的闺女,又担心堂堂男子汉结婚了还让人家看不起,多不好。”
由此我们发现,“无主体熟人社会”虽然制约着“云南女”的社会资本建构,但具有间接性、无直接伤害性,同时,这种力量的客观性使得“云南女”无力扭转以实现社会资本的“逆向强化”。曾经对她们的社会资本建构起到重要作用的子女,在婚姻选择方面受到“云南女”的引导,未能连接到异质性关系与资源,而是在“云南女”的“圈子”内徘徊,这也导致了她们的社会资本同质化、社会资源单一化。因此,我们认为,由于外部阻碍效力与内部同质化趋向,使得现阶段“云南女”的社会资本建构已经在一定阶段上呈现出固化甚至萎缩的可能。
五、结论
本研究所呈现的理论意义,一方面是对以婚迁女性为代表的移民社会融合的“追溯”研究。当前国内学者通过对移民的研究,发现了社会资本对社会融合的重要作用。但是,当我们进一步追问这些社会资本是如何生成的时候,却发现研究成果较少。国内学者一般通过定位法与提名法作为研究社会资本获取的方法,但这种定量方法侧重于从结构的角度静态化研究“点与点”之间的资本链,从而形成了社会资本是“一次性获取”的假象,折损了生成或建构概念的实质。我们认为,建构是一个动态的、历时性的过程,唯有将无数的“点”、“线”梳理清楚,才能真正地理解当前社会资本的“面”。梁玉成就社会资本同质性问题指出,测量的社会资本同质现状之背后,实际上有一个累积与筛选的动态过程。[12]本文依此研究取向,先追溯“云南女”社会融合之前的社会资本,再回顾她们从迁到C村到子女结婚这长达二十多年的生命历程,从而得到关于社会资本建构的完整的由点穿线、由线构面的历程。而将点、线、面相互勾连以体现其运作机制的便是布迪厄的资本转换理论。为此,我们将布迪厄的理论转化为以本研究为中心的生成模型,具体见图1。

图1 布迪厄资本转换模型在“云南女”研究中的应用
另一方面,我们通过三阶段的历时分析,发现在社会融合的不同阶段,“云南女”会运用不同的社会资本建构策略,也因而产出了不同程度与不同特点的社会资本。在第一阶段,“云南女”的社会资本的初步断链与重新获致并存,但获致的夫家社会资本并不理想。同时,她们的社会资本建构因受制于家务劳动、生育等因素而呈现出家庭内部化、速度相对缓慢、水平相对较低等特征。在第二阶段,伴随着子女成长与自身的生活适应,“云南女”社会资本建构的范围相对较广。她们通过子女这个桥接型社会资本,链接到家庭之外、“云南女”群体之外的异质性社会资本,同时,在与“外来人”与“当地人”的交往过程中,通过生活中的例行事件与突发事件,再确认已有的社会资本结构。在第三阶段,农民工流动所带的乡村变化给“云南女”社会资本的进一步拓展带来了障碍,同时,由于上述两阶段所带来的影响,她们对子女婚姻的选择使得其社会资本走向了同质化。
如果将上述三个阶段放在一起作连续性分析,我们认为,“云南女”的社会资本建构历程呈现着内卷化的特征。“内卷化”是美国人类学家戈登威泽提出的概念,后经格尔茨在《农业内卷化》一书中详细阐述而得以普遍化。格尔茨认为,内卷化是“一个分析概念,即一个既有的形态,由于内部细节过分的精细而使得形态本身获得了刚性”,并以此刻画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地区“由于农业无法向外延扩展,致使劳动力不断填充到有限的水稻生产中”的生产过程。[13]80-83尽管后来学者对这一概念的阐释与格尔茨等人对内卷化的理解有所差异,但内卷化有三项基本含义:(1)以系统的外部扩张为前提,即内卷的发生存有一定程度的积累。(2)内部与外部的限制为内卷发生的关键。外部条件可能是行政性障碍,使得系统的扩张历程遇到外部壁垒。内部限制可能是积累已久的传统文化之影响,使得系统的扩张受到内源性的拉扯。(3)自我指涉为内卷的趋向。由于遇到内外的屏障,系统只得进行内部的复制或精细化,使其效益水平呈现出一定的刚性。回顾“云南女”的社会资本建构过程,与上述的内卷化的过程性内涵相同,具体见图2。因此,虽然如上所述,“云南女”的社会资本建构存有阶段性特征,但其短期性发展又是嵌入在其整体内卷化的历程之中的。

图2 “云南女”社会资本建构的内卷化历程
此外,我们也看到,从生育子女到教育子女,再到子女联姻,都给“云南女”的社会资本建构带来重要的影响,这也印证了传统生育文化中女性角色的定位。与一般女性不同的是,作为“外来人”,子女本应当是“云南女”社会资本的自然延伸,但是“云南女”往往要有意识地以子女为“桥”进行社会资本建构,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其子女的婚姻选择上。
我们基于对C村云南籍婚迁流入妇女的回顾性访谈与现状分析,得出了内卷化的结论。当然,我们也承认,虽然在子女与环境的双重变化下,社会资本呈现着内卷化特征,但子女的婚姻或事业发展可能给“云南女”带来社会资本的新一轮拓展。因此,唯有继续对该群体进行追踪研究,才能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婚迁者社会资本的建构历程。
[1]雷开春.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资本的理性转换[J].社会,2011,(1).
[2]悦中山,李树茁,等.从“先赋”到“后致”:农民工的社会网络与社会融合[J].社会,2011,(6).
[3]唐文慧,王宏仁.结构限制下的能动性施展——台越跨国婚姻受暴妇女的动态父权协商[J].台湾社会研究季刊,2011,(2).
[4]Lin,N.,D.Ao&Lijun Song.Production and Return of Social Capital:Evidence from Urban China[A].R.Hsung,N. Lin&R.Breiger.Contexts of Social Capital:Social Networks in Markets,Communities and Families[C].New York:Routledge,2009.
[5]Bourdieu,Pierre.The Forms of Capital[A].A.H.Halsey,H. Lauder,etc.Education:Culture,Economy and Society[C].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
[6]Bourdieu,Pierre.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M]. Cambridge:Polity Press,1991.
[7]Bourdieu,Pierre.Distinction: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8]叶文振.流动妇女婚育研究的背景分析与展望[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9,(5).
[9]Jack Barbalet.A Characterization of Trust,and its Consequences[J].Theory and Society,2009,(4).
[10]Robert D.Putnam.Bowling Alone: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M].New York:Simon Schuster,2000.
[11]孙立平.“过程—事件分析”与当代中国国家——农民关系的实践形态[A].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清华社会学评论(特辑)[C].厦门:鹭江出版社,2000.
[12]梁玉成.社会资本和社会网无用吗?[J].社会学研究,2010,(5).
[13]Geertz,Clifford.Agricultural Involution:The Process of Ecological Change in Indonesia[M].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3.
责任编辑:董力婕
Examining the Social Capital Building Process:A Case Study of Yunnan Female Migrants in a North Anhui Village
SUN Yufan,LI Mengdi and TIAN Fei
This paper is based on a case study of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Yunnan women who migrated to Village C because of marriage,their family members and relationship with the community in Village C,in northern Anhui Province.The study has identified three phases i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the women’s social capital,each with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according to differences in the social environment and family conditions.However,all three phases share the same action processes conversion of economic and cultural capital into social capital and reproduction based on the original social capital.This supports,to some extent,Pierre Bourdieu’s capital transformation theory.In addition,when combining the three phases together,the social capital building process reflects a mode of involution.
social capital;involution;capital transformation
10.3969/j.issn.1007-3698.2012.03.011
2012-03-05
C913.68
A
1007-3698(2012)03-0060-07
孙宇凡,男,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2009级学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理论社会学;李梦迪,女,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2009级学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应用社会学;田飞,男,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人口社会学。230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