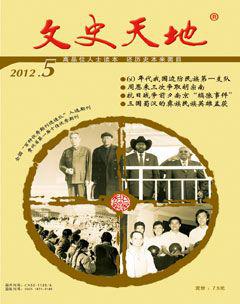科场上的姓名祸福
陈正贤
以姓名而决进退,如此用人,何能保证人尽其才?
姓名是人的一种外在身份符号,对他人来说,它的作用是方便指认、招呼以及文字记录;对自身来说,姓名文字的含义,往往多多少少寄托着祖、父辈对后代事业前程之类的企望,或者表达本人的某种人生志向。姓名的这两层“功用”,由于并不与他人发生利害冲突,因此不可能给人带来幸或不幸。但在中国古代,情形却并非如此,一些位高权重的官员乃至至高无上的皇帝,对一个人姓名的“误读”,常常给当事人带来意想不到的祸福。这种有意无意的“误读”,情况各有不同,较为多见的一种是,“误读”者在语言迷信观念的导引作用下,借助联想,强行在当事人姓名的音形义中读出另类“含义”,于是无形的利害关系便立即产生,而祸福也随之降临到当事人身上。
从史料笔记看,这类因姓名招致祸福的事,至迟在宋代就出现了。宋人庄绰《鸡肋编》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南宋时,会稽有一个叫钱唐休的人,在社会上很有声望,有人将他推荐给了当时的宰相赵鼎。赵鼎正准备考虑提拔任用之时,接到一个边境小警报,他在看边报时,无意中瞥见了钱唐休的名字,两者一加联系,心里忽然生出一种不祥之感,于是很不高兴地说:“难道这回钱唐就要完了吗?”钱唐即钱塘,是南宋都城杭州的别名,钱唐完了不就是南宋完了吗?就这样,这位钱唐休便被弃置不用。后来赵鼎起用折彦质为枢密都承旨,进而折再升为签书枢密院事并暂代参知政事。这样,两人就常常依次在奏牍上签名,有人见了,趁机将两人姓名前三个字连在一起,以“赵鼎折”(赵宋王朝完了)是一种不祥之兆来攻击他们。这真称得上是“现世报”,不知当时的赵鼎听了有什么样的感想。
宋人叶梦得《石林燕语》记载的一桩事也很有意思。宋神宗元丰五年,殿试结束,皇上召见新科进士,传唱官连叫三次一位叫暨陶的人,始终无人答应。神宗觉得奇怪,问身旁的苏颂。苏颂说,传唱官把他的姓念错了,这个“暨”应念入声。传唱官按入声一试,果真暨陶马上答应。神宗问苏颂,你怎么知道这个“暨”念入声。苏颂回答说,《三国志》上有一个叫暨艳的吴地人,这个人的姓念入声,我估计这位暨陶是暨艳的后人。一问暨陶,正是吴地崇安人。另据明人朱国祯《涌幢小品》记载,阅卷官原定暨陶为第一,只是因为连叫三次没有答应,便将第二名黄裳拔至第一。入声是古汉语四声之一,读时声音短而急促,这个声调南方方言较多,北方话则基本没有。这位暨陶仅仅因为传唱官的一“念”之差丢了状元,实在冤哉枉矣,但谁让暨陶摊上这么一个姓又遇上这么一位传唱官呢?朱国祯由此感叹说:“可见姓之平险亦能误人进身之高下矣。”
暨陶的事显得有些滑稽,但对姓名含义的迷信在古代却不少见,官场如此,民间也有这种情况。据宋人陈鹄《耆旧续闻》记载,书画家米芾好洁成癖。他为自己选择女婿时也希望对方是一个爱干净的人。一次,他见一位士子姓段名拂,字去尘,顿时非常高兴,说:“掸拂了以后还要再次去尘,这真是一位好女婿。”于是就将女儿嫁给了他。只循“名”而不责“实”,米芾的做法让人觉得十分滑稽可笑。
明代的皇帝也很相信姓名所预示的吉凶祸福。洪武乙丑科与永乐甲辰科状元均因为姓名上的问题而被临时换马。据陈鎏《皇明历科状元录》记载,洪武乙丑科状元,礼部上呈给皇上时为花纶。但在放榜前一日,朱元璋做了一梦,梦见大殿前一枚巨钉上挂着几缕白丝,在太阳下悠忽飘荡。第二天拆卷时,首卷考生的姓名叫花纶。朱皇帝见他年龄不大,就把他暂放一边。接下来看卷时,见一名考生的姓名叫丁显,觉得此人的姓名符合自己所做的梦,便把他拔至状元,花纶则因年少被置于二甲。丁显的姓与钉子的“钉”同音,显字的繁体字作“顯”,中有“丝”字,且在“日”字之下,正与皇帝的梦相合。当年二月会试结束时,试官们初拟花纶第一,练子宁次之,黄子澄又次之。不知是消息外露,还是凑巧,坊间曾一度流传“黄练花,花练黄”的童谣。一开始人们还不解其意,待会试结果出来后人们才恍然大悟。花纶被选第一,一时无人不知,因而同榜进士皆呼他为“花状元”。榜眼练子宁还曾作《送花状元诏许归娶》诗以示庆贺。想不到三月殿试后,太祖将原来的排名作了变更,皇上的一个梦便摘走了花纶头上的状元桂冠,这是花纶做梦也不会想到的。
太祖之子成祖朱棣,也曾因为姓名换了一位状元。据王世贞《皇明异典述》等书记载,甲辰科殿试后,读卷官初拟孙曰恭为第一,梁禋第二,邢宽第三。交皇上最终定夺时,成祖因为眼花看不清,将竖写的“曰恭”两字连在一起,看成了“暴”字。当看到第三名邢宽时,他对朝臣说:“本朝只许邢宽,岂宜孙暴。”就这样邢宽成了状元,孙曰恭只能屈居人后。据说邢宽在家乡时虽小有名气,但当地知府并不看好他,曾对人说:“邢宽像一瓶不酸的醋。”意思是此人没有多少真才实学。邢宽中状元后,觉得对知府的这句话应该有一个“交待”,于是写了一首诗送给知府:“邢宽只是旧邢宽,朝占龙头夕拜官。寄语黄堂贤太守, 如今却是螫牙酸。”这首诗倒确实够让这位知府牙酸的了,邢宽看来并不那么“宽”。
花纶与孙曰恭因为自己的姓名丢了状元,而景泰年间的孙贤却因姓名得了状元。据明人吕毖《明朝小史》载,甲戌科殿试,景泰帝遇到参加殿试的孙贤,就随口问了一声他的姓名。听到这位士子回答说叫孙贤,景泰帝马上联想到“不愿金玉富,但愿子孙贤”的古谚,并念了出来。在旁的大臣见皇上关注孙贤,念叨他的姓名,不敢问其中的原因,随即拟定孙贤为状元。
因姓名招致祸福的事,在清代也不少。欧阳昱的《见闻琐录》记载了两位。一位是咸丰朝湖北人范鸣和。范初入翰林时名鸣琼,散馆列一等第八名。按惯例,这样的名次,应该授以编修或检讨之职,继续留在庶常馆。名次在后的则分发各部为给事中、御史、主事,或出为州县官。但咸丰帝却只授给了范主事之职。据说这是因为他的姓名在北方人念的时候类似“万民穷”,咸丰帝听了这个名字很不高兴,以为不吉祥。知道这么回事后,范怕再次触及皇上的忌讳,就将自己的姓名改成了范鸣和。另一位是咸丰朝江西崇仁人刘颜瑞,他曾以同知的身份由吏部向皇帝引见。唱名的时候,咸丰帝一听他的姓名像是“流眼泪”。其时太平天国运动正如火如荼,东南许多州县相继为太平军占领,面对严峻的形势,咸丰帝一筹莫展。一听刘颜瑞的姓名,忽然触动了他那根敏感的神经,感到很是不吉利,似乎末日将临。于是这位刘颜瑞倒了大霉,不仅没有得到重用,连原来的官职也被咸丰帝借故削夺了。
徐珂的《清稗类钞》记录了三位。一位是明末清初著名画家王时敏的次子王揆。他中了顺治乙未科进士,选任馆职那天,某位参与其事的大臣想把他列为第一人,但唱名传呼时,由于“揆”与“魁”音近,顺治皇帝听到后顺口说了句:“是那位负心王魁吗?”一听皇上这话,那位原想将王揆举为第一的大臣没敢再说话。王魁是旧戏中的一个人物,原本是个穷秀才,与青楼女子敫桂英在海神庙相遇。敫见他饥寒交迫,倒于雪地,便救回院中。后敫慕其至诚好学,遂结百年之好,伴王读书三年,又送王赴京应试,临行前二人在海神庙结盟发誓,永不负心。王魁走后,敫桂英苦苦等待,不料王魁高中后入赘相府,负却前情,差人送来三百两银子和一纸休书。桂英悲愤欲绝,奔海神庙,求海神主持公道,海神终无灵验,桂英绝望,怒打神像,痛斥王魁,最后自缢而亡。死后敫桂英化为厉鬼,活捉了王魁,报了生前之仇。顺治皇帝虽然只是一句并不那么当真的问话,但谁也不敢对皇上问话的用意妄加猜测,为保险起见,自然只有让王揆受委屈,将他从第一名抑之第三甲。王揆因姓名与“王魁”音同,失去了状元资格,对此自然心中不快。康熙十七年,清廷为笼络汉族知识分子,开“博学鸿词”科,王揆受巡抚慕天颜举荐,但他找借口拒绝前去应征,也终生没有做官。王揆写得一手好诗,大诗人吴梅村把他列为“太仓十子”之一。也许正是这一点,《清史稿·文苑传》中才留下了他的姓名。
第二位是乾隆朝的胡长龄,他是乾隆己酉科进士。殿试时,他的卷子原排在进呈给皇帝的十本卷子的最末一名。乾隆帝其时已年近八旬,当看到胡的姓名后,笑着说:“看来胡人真的长命啊。”于是就将他拔置第一。胡长龄是一位颇重气节的人,当时和珅当国,胡长龄熟知和珅的种种贪污受贿不法情状,中状元后没有去拜见他,为此和珅心中十分不快。结果这位胡长龄当了十年穷翰林,以致生活拮据,家中值钱的东西典当一空。朋友们都十分同情他。为改变胡的这种窘境,他的一位朋友趁和珅寿辰之机,用乌贼鱼分泌的液汁仿胡体为和珅写了一副祝寿联,又请托一位侍郎向和珅说,胡又穷又病,连一件像样的衣服也没有,不能前来贺寿,只能以这副寿联表达一点心意,言下之意是请和珅多加关照。和珅笑着说:“想不到这位胡蛮子竟困穷到这步田地。”没过几天,胡就被任命为山东学政。接到任命后,这位好心的朋友又用原来的方法代胡写了一个帖子表示感谢。这些胡长龄都不知道。和珅事败抄家查检时,那些与和珅有私下书信交往的大小臣僚都受到牵连,胡长龄却逃过了这一劫。原来用乌贼液汁书写的东西,一年后字迹就自行消褪了。为此,嘉庆皇帝对胡长龄另眼相看,胡长龄由此受到重用,以后官至礼部尚书。
第三位是江苏人王国均,他是同治戊辰科进士。殿试后,阅卷官将他的卷子列入上呈给皇帝御览的十本卷子中。唱名传呼时,慈禧太后听到“王国均”三字,很不高兴,“王国均”不就是“亡国君”吗?于是将他抑置三甲,让他到安徽去当了一名知县。
看来,人的名字有时候真会带来祸福啊,尤其是在科举场上。
作者单位:浙江绍兴高教自考办
责任编辑:王封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