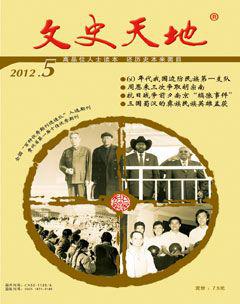蒋梦麟教育生涯中的三次风波
王学斌

在中国的教育史上,蒋梦麟永远是一颗闪耀的星。
民国之教育界,可谓人才辈出,群星闪耀,蒋梦麟自然是其中甚为璀璨的一颗。作为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专业的博士,蒋回国后先是出任《新教育》杂志主编,又先后担任浙江教育厅厅长和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坐到了教育界头把交椅的位置。当然,最值得蒋本人自豪同时也最为人称道的是他曾两度临危受命,执掌中国第一名校北京大学,作为校长任期前后长达24年之久,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也就是在蒋梦麟的手中,北大两度从衰败中走向复兴,成功捍卫了民国高校龙头老大的地位,蒋功不可没。然而,正是这样一位功勋卓著的北大校长,其教育生涯却颇为苦涩,中间多有波折,乃至最终不得不忍痛与其毕生追求的“教育救国梦”挥手作别。
从入主北大到逃离北京
1919年5月4日,为抗议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在丧权辱国的山东条款上签字,北京大学学生自发组织起来,举行游行示威。当天下午,北京各大专院校学生3000余人,在天安门集会示威,并火烧赵家楼,“五四运动”兴起。
面对汹涌的学生运动,北洋军阀政府自然不会善罢甘休。5月7日,北京政府提出解散北京大学、撤免蔡元培校长一职的动议。与此同时,为了保全刚有起色的北大,为了不让无辜学生受难,蔡元培决定离职出走,留下一纸写有“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的声明,悄然南下。
为了挽留这位德高望重的老校长,京城教育界人士纷纷活动起来,希望能够让蔡元培重回北大。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出人意料,各方人士努力的结果竟是最终促使“教育界新锐”蒋梦麟入主北大。此事的缘由当从时任北京医药专科学校校长的汤尔和南下“劝驾”说起。汤尔和来到杭州,极力劝说蔡元培回到北大。经过多日考虑,蔡元培有所动摇,认为可以收回辞职的初衷。但由于身体欠佳,蔡实不能立即返京处理繁重校务。在此情形下,汤尔和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替蔡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蔡元培首先答应继续担任校长一职,但不必马上回京,而采用委派的方式,让其得意弟子蒋梦麟代理校长事务。
值此非常时期,起用一个从未在北大甚至是国内任何高校担任过实际职务的年轻人出任代理北大校长,实在是一时间让众人摸不着头脑。学者李甲孚在《杂谈蒋梦麟》一文里曾分析道:其一,蒋梦麟是蔡元培的学生与同乡;其二,蒋回国后特别是在主编《新教育》时所表现出的才能与教育主张使蔡元培大为欣赏;其三,此时与蔡元培接触较多的国民党总理孙中山对蒋梦麟十分看重。以上三点使蒋成为入主北大的最佳人选。
得到接管北大的消息后,蒋梦麟很快便应允下来。多年来梦寐以求的教育实践机会终于来临,而且一开始便是执全国高等教育之牛耳的北京大学,这实在是一个再好不过的施展个人抱负的舞台,加之恩师蔡元培的举荐,岂有推辞不就之理?7月20日,蒋梦麟与汤尔和一道赴京任职,这一年,他才34岁。若在今日看来,任命如此年轻的干部出任北大校长,简直是不可思议。
初来乍到,蒋梦麟就发现“五四运动”之后的北大问题多多。首先需要安抚学生,把他们从示威运动中拉回课堂,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同时还需调和新旧势力之间的矛盾,使大家尽量和衷共济,为北大的发展贡献力量。故而,此时的蒋梦麟着实忙得不亦乐乎,在写给友人张东荪的信中,蒋不无感慨地写道:“我廿一日到北京以来,吃了不少的苦,好像一个人投在蛛网里面,动一动就有蛛子从那屋角里跳出来咬你。唉!若无破釜沉舟的决心,早被吓退了。人人说市中有虎,我说我任凭虎吞了我就罢了;没有吞我以前,我不妨做些做人应该做的事。我记得王守仁有句话:‘东家老翁防虎患,虎夜入室衔其头。西家儿童不识虎,执策驱虎如驱牛。我又记得《四书》里有句话:‘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我本了这个精神,向前奋斗。过了半月,诸事已有端倪。我对于校内校外帮我忙的人,终生感激他们——他们不是帮我的忙,是帮中华民国的忙。”正是凭着“执策驱虎如驱牛”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的精神,蒋梦麟逐渐使北大的一切事务走向正轨,而自己的教育救国梦想也一步步地得以实现。在学校管理方面,蒋梦麟秉持民主治校的原则,在北大初步建立起比较完整有效的行政管理系统,使北大走向了教授治校之路。同时,为了发展学术事业,蒋梦麟四处奔走,筹集款项,以用于办学条件的改善。为此蒋梦麟曾向胡适诉苦:“我现在忙得不亦乐乎,有几分厌倦。教育部无人负责,他校大都不死不活。京师教育事务,我首当其冲,简直是大学校长而兼教育总长。我现在买了一辆汽车,天天在街上跑,真是和gasoline(汽油)有仇。”
蒋梦麟苦在身上,却甜在心头。自己的辛勤努力终究没有白费,在其他高校几乎无米下炊的情形下,北大却能够保证软硬件设施不断更新,学生质量也日渐提高,一派蒸蒸日上的景象。
正当蒋梦麟在北大干得风风火火的时候,他教育生涯中的第一次波折却不期而至,迫使他离开了心爱的北大。
风波的导火索是发生于1926年3月18日的“三一八”惨案。在日渐高涨的南方革命形势的鼓舞下,北京的学生运动也随之活跃起来。3月18日,北京各界二万余人为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大沽口事件”举行集会示威活动,当人群行至段祺瑞的北京临时执政府所在地时,遭到军警的武力镇压,以致群众死47人、伤200人,其中北大学生张仲超、黄可仁、李家珍3人不幸罹难。
面对这一令人发指的罪行,连一向脾气温和、主张以和为贵的蒋梦麟也无法忍受了。在3月24日举行的追悼大会上,蒋梦麟公开谴责段祺瑞政府之暴行,沉痛地指出:“处此人权旁落,豺狼当道之时,民众与政府相搏,不啻如与虎狼相斗,终必为虎狼所噬。古人谓苛政猛于虎,有慨乎其言矣!”
正是由于对北洋政府的公开谴责,招致了奉系军阀头目的嫉恨,将蒋梦麟列入了逮捕处决的黑名单中。曾任北京政府国务总理的孙宝琦急忙告诉蒋梦麟详情,北京已不可久留。
迫于无奈,蒋梦麟在六国饭店避难3个月后逃出北京这块是非之地,暂回杭州蛰居。回顾这6年来北大的日日夜夜,蒋梦麟心中不禁思绪翻涌,悲喜交加,“留在记忆中的是一大堆乱糟糟的悲喜剧场面”。自己的教育救国梦刚刚在北大露出晨曦,却被迫离开这片充满希望的地方,不舍之情溢于言表。
然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被迫辞职,教育界派系斗争的牺牲品
回到南方之后,蒋梦麟受到了日益壮大的国民革命军领导人的重用,又翻开了人生新的一页。
蒋梦麟南归之时,也正是国民革命如火如荼地开展之时,北伐军势如破竹地向长江流域挺进。1927年初,北伐军进入浙江境内。不久,浙江省政府宣告成立,蒋梦麟被任命为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这也是他进入民国政坛的开端。上任伊始,蒋就致力于恢复长期以来因战乱停滞的浙江教育事业。首先在他的带领下,全省建立起职能明确、规范有序的教育行政体系。接着,蒋梦麟认识到师资队伍是地方教育事业能够长期发展的根本所在,于是他在考察陶行知所主办的晓庄师范的基础之上,主持创建了30年代闻名省内外的湘湖师范。此外,在他的不懈努力下,浙江大学也于此时拔地而起了。
短短1年多内,蒋为浙江教育事业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得到了国民政府的首肯。1928年10月,国民政府任命他为教育部部长,蒋梦麟再次步入了个人事业的高峰期。然而,正当蒋梦麟踌躇满志,欲图实现自己教育救国梦想的时候,他却遭受到国民党内部分元老的非难,乃至被迫辞去刚满两年的教育部部长一职,成为教育界派系斗争的牺牲品,这也是他教育生涯中的第二次波折。
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的民国教育界,内部实际上派系林立,按照教育背景,大致可划分为以李石曾、张乃燕(国民党元老张静江之侄)为代表的留法派,以蔡元培、蒋梦麟为代表的欧美派,以丁惟汾、经亨颐为代表的留日派,以及未出国门的本土派。四方之间由于利益不同和教育理念的差异时常发生摩擦,作为教育部的掌门人,蒋梦麟不幸也卷入到这场无止境的“暗战”当中。
1930年10月,中央大学学生因反对日本的无理行径,发动学潮。蒋梦麟得知后立即将详情转告蒋介石,听候其裁断。而蒋的这一举动却激起了以中央大学校长张乃燕为代表的留法派及留日、本土派人士的强烈不满。张乃燕甚至公开致函蒋梦麟,责难道:“小小学潮,何以电奉化报告,意果何据?……小事大报,动劳主席,教部岂非虚设?”两人矛盾趋于激化。11月25日,国民政府调任朱家骅出任中央大学校长。
这样一来,蒋梦麟触碰到了隐藏在教育界的那根敏感的派系神经,自己也因此坐在了火山口上。对于中央大学易长一事,元老们意见相左,互不买账,为了平息纷争,蒋梦麟唯一可做的便是引咎辞职。对于这段经历,蒋事后回忆道:“我当时年壮气盛,有所决策,必贯彻到底,不肯通融,在我自以为励精图治,在人则等于一意孤行。我本世居越中,耳濡目染,颇知绍兴师爷化大为小化小为无的诀窍。今背道而驰,自然碰壁。武力革命难,政治革命更难,思想革命尤难,这是我所受的教训。”
蒋梦麟辞职前夜,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突然来访,就中央大学易长之事痛斥蒋梦麟办事不力。临走前,吴稚晖指着蒋梦麟厉声而言:“你真是无大臣之风!”等到蒋梦麟再度回到北大的时候,刘半农曾赠给他图章一方,文曰:“无大臣之风。”
“无大臣之风”,用这五个字来评价蒋梦麟两年来在教育部长任上的作为,似有失公允。不过,这也点出了他在政治上不成熟的一面。在朝为官毕竟不同于一校之长,政坛波云诡谲,所以每推行一项政策,都需通盘反复斟酌考虑,力求照顾到方方面面。而只想做些实事的蒋梦麟未谙此道,于是碰了壁。不过,蒋梦麟也由此初窥政坛生存规则,长了见识。更为重要的是,他从此可以摆脱种种人事关系的纠缠,去再掌北大了。
倒蒋(梦麟)风波
“三一八”事件后,段祺瑞下台。北京政府落入奉系军阀张作霖之手,北大的处境变得愈加艰难。军阀政府决定取消北京大学,将北京的9所高校合并为“京师大学校”。经过这番折腾,曾经是新文化运动中心的北大已是奄奄一息了。好在北伐军不久后便进军北京,张作霖退回奉天,北大师生又看到了复兴北大的曙光。
1929年9月,国民政府任命蔡元培为北大校长,不过蔡并未就任,而是由陈大齐代理。但自1930年起,国民政府规定今后大学校长不准遥领。于是几经权衡,蔡元培决定让蒋梦麟再度出山,于该年12月赴任北大。
这个时期北京大学的情形,实在让人惨不忍睹,教授严重不足,学生质量下降,财政经费匮乏,图书资源流失……无法与蒋20年代任校长时同日而语。因此,蒋梦麟最需要做的事情便是接过烂摊子,尽快规划出一套切实可行的方案,重振北大。为此,蒋梦麟殚精竭虑,费尽心血。针对管理混乱的现状,他适时提出“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办学方针,使师生们得以各明其职,各尽其责。同时,蒋梦麟千方百计地引进人才,筹措款项,使北大教学质量和科研设施有了很大提高。自1930年底蒋梦麟赴任至“七七事变”爆发前这7年里,北大的发展虽然不能说是突飞猛进,但也彻底走出低谷,日益接近以往的水准。蒋梦麟不无自豪地说:“从民国十九年到二十六年的7年内,我一直把握着北大之舵,竭智尽能,希望把这学问之舟平稳渡过中日冲突中的惊涛骇浪。在许多朋友协助之下,尤其是胡适之、丁在君和傅孟真,北大幸能平稳前进,仅仅偶尔调整帆篷而已。科学教学和学术研究的水准提高了。对中国历史和文学的研究也在认真进行。教授们有充裕的时间从事研究,同时诱导学生集中精力追求学问,一度曾是革命活动和学生运动漩涡的北大,已经逐渐转变为学术中心了。”
然而,卢沟桥一声枪响,抗战全面爆发,打乱了蒋梦麟发展北大的规划,北方三校(清华、北大、南开)决定联合南下。颇耐人寻味的是,作为堂堂一校之长,蒋梦麟竟未能参与商讨南迁事宜,而是事后得知,“勉强同意了这个计划”。由此可知,蒋对此计划并非完全赞同,只是迫于形势,且木已成舟,无可挽回,方才没有再多作交涉。经过一番波折,三校将校址定在云南省会昆明,部分院系则去蒙自分校,组建了后来闻名于世的西南联合大学。蒋梦麟与南开校长张伯苓、清华校长梅贻琦组成校务委员会,共同管理日常事务。
由于是三校合并,故而西南联大内部人事关系错综复杂,利益冲突在所难免。蒋梦麟深知若是自己插手过问太多校务,势必会招致其他两校师生的猜测与反感,疑心蒋借管理联大校务之名而行谋北大一校私利之实。基于此种考虑,蒋梦麟干脆采取“无为而治”的策略,公开宣称“在联大,我不管就是管”,将繁重的校务交予清华校长梅贻琦处理,自己仅利用社会名望负责外务。应当说,从最终结果来看,蒋梦麟这种处事方式大体上维持了联大内部各集团的利益,大家相安无事,能够在大局上保持一致,团结合作,创造了战时高等教育的一大奇迹。而蒋梦麟在处理联大内部关系时所经受的内心苦涩与煎熬,恐非外人所能了解。
北大教授们的确没能完全体会到蒋梦麟那一片力撑大局的良苦用心。他们只看到蒋表面上整日无所事事,不是躲进防空洞里写写自传,就是与沈尹默切磋书法,如同赋闲之人一般,与昔日的北大同僚们似乎渐行渐远了。而且,自从合校以来,北大的情形就每况愈下,中文系教授罗常培指出:“政府太不同情我们了,过去几年,北大简直没办法发展,不单比不上清华,连浙大、武大都抵不住。”数学系教授许宝禄无奈地叹道:“过去五六年太黑了,个把好人侧身其中,连轮廓都看不见。”傅斯年更是直言不讳地说:“我们这些年与清华合作,清华得到安定,我们得到鄙视,……大家心中的心理是‘北大没有希望。”教授们对学校现状的不满最终要记在校长蒋梦麟的头上,大家对蒋的意见自然如滚雪球般越积越大,终有将蒋梦麟压翻在地的那一天。
而蒋梦麟的第二任夫人陶曾谷更给这本已紧张的气氛中平添了几分不愉快。陶原为北大教员高仁山之妻,高遇难后转嫁于蒋梦麟。而偏偏这位校长夫人同北大诸位教授都合不来。傅斯年曾在写给胡适的信中谈及此事,认为“蒋这几年与北大教授感情不算融洽,总是陶曾谷女士的贡献”。
于是,随着教授们不满情绪的积蓄,一场大的风波正在酝酿之中。
而恰恰在此时,蒋梦麟又做出了一个并不十分明智的选择:1945年6月,他接受新任行政院长宋子文的邀请,出任行政院秘书长一职。蒋梦麟接受宋之邀请,初衷不过是想体会一下政坛中枢之内的滋味如何,反正自己现在也属于半个“闲人”,但并无辞掉北大校长的打算。然而,在北大诸位教授眼中,蒋之举动无疑是“官迷心窍”,义无再忍。法学院院长周炳琳尤为愤慨,认为蒋梦麟要么踏踏实实地做校长,要么一心去追求自己的高官梦,绝不能三心二意,脚踏两只船。并指出:“蒋校长的兴趣不在大学教育,战时他对北大的事不问,但他每日忙着招待无关紧要的外国人和云南的显要,可见他的兴趣所在。”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蒋梦麟昔日挚友傅斯年、周炳琳、朱家骅等人,依据1929年蒋梦麟任教育部长时制定颁行的《大学教育法》中“大学校长不得兼为官吏”的条款,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推荐正在美国的胡适接替蒋梦麟校长之职。一场“倒蒋迎胡”的大戏正式开演。
眼见众人已向自己摊牌,蒋梦麟没有再作挽回的努力,也没有多替自己的言行辩解,而是不失风度地在8月份的昆明北大教师茶会上完成了权力交接,并勉励各位同仁为北大的未来再接再厉。就这样,蒋梦麟结束了执掌北大20年来的“谢幕演出”。一步走错,满盘皆输,令蒋梦麟始料未及的是,昆明一别竟也是他在教育事业上的“绝唱”,从此他再也无缘进入教育圈,他的教育救国梦想也便到此戛然而止。
也许是造化弄人,抑或是时势使然,蒋梦麟的教育梦一直是支离破碎的,两度执掌北大,其教育努力一次受到军阀破坏,一次因战争而中途被打断,在联大时期最终竟因昔日同仁好友的“倒蒋风波”而与教育事业彻底绝缘,想来晚年蒋梦麟的心中应是充满着酸楚与叹息。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
责任编辑:王封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