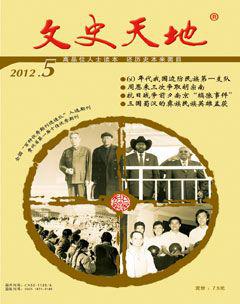难过的“粮食难关”
许荣华


“三年粮食困难时期”,曾宣传说是“天灾”所致。真的只是天灾吗?
(正安县)从1959年至1962年全县共死亡45751人,其中1960年死亡25309人,死亡率达5.4%。比正常年份死亡率高近4倍。
——摘自《正安县志》
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曾有人把它称作过难关。虽然已经过去了整整半个世纪,但对于在家乡亲身经历过这道难关的我来说,往事历历在目,记忆犹新。而今,我想把那些难忘的片断记录下来,也许对保存史料、吸取历史经验教训、教育后人,会有一定的益处。
饿饭:打破了我的美梦
我是贵州正安县新洲镇新洲乡正丰村长湾村民组人,贫农出身。1959年秋天,我初中毕业考取了高中,就读于正安县第四中学。那时,家庭非常贫困,进校后,学校给我全免学杂费,又给人民助学金,优厚待遇的方式跟初中三年完全一样。我感到非常欣慰,除星期天去搞搬运,每次挣几角钱来做零用外,其余时间发愤苦读,一心想到将来能跨进大学的校门。
光阴似箭,转眼就放寒假了。1959年农历腊月二十六日,我和同乡村的几个同学一道,冒着纷飞的雪花,徒步踏上了回家的路程。学校离家50余公里,多数是崎岖的山路,加之雪天路滑,第二天清晨才回到家中。当我走进家门的时候,眼前的情景十分凄惨:我13岁的弟弟老幺死后停放在屋中,17岁的妹妹埋头坐在火炉边,父亲和15岁的弟弟以及10岁的妹妹都躺倒在床,不时传来呻吟声。这是怎么回事呢?坐在火炉边的妹妹有气无力地告诉我:“现在到处都在饿饭,我们全家都饿倒了。老幺是前天死的,我们听说你昨天一定回家,就等你回来看一眼才埋。”面对死去的胞弟和唉声,我的眼泪不断往下流,心里充满了无限的悲伤。这一天,按照父亲的安排,要我做一些准备工作,晚上安埋老幺。但由于生产队的劳动力几乎饿倒了,找不到帮忙的人,我一人忙到天黑,准备工作还是没有做好,只好让老幺继续停在家中。
腊月二十八,是我们公社所在地新洲的赶场天。父亲起床后对我说:“今天我去赶场,到街上饭店吃点饭后,再带点回来明天过年。你在家锯几块木板,锤竹篙(照明用的干竹子),晚上一定把老幺埋了。”于是,全家吃了一顿白水煮的青菜后,父亲带着几斤我从学校退回来的粮票就硬撑着上路了。接着,我就借锯子,找木板和竹篙,不停地忙碌。谁知,当我锯好木板,正在锤竹篙时,有人来传话,说我父亲已在三岔河死了。这突如其来的噩耗,差点把我吓昏了。我强忍着悲痛,急忙赶到三岔河。原来我父亲还没有走到新洲街上,才走到三岔河边就倒在路上了。恰好我姐夫在附近听说后,赶过来将他扶起,看他落下了最后一口气,走完了他45岁的人生历程。家中幼弟未埋,坡上又饿死老人,一家人的命运实在太惨了。万般无奈,我只好找来竹席把父亲遗体盖上,摸黑回到家中。这一夜,家里虽然草草地把老幺埋了,可我父亲却在三岔河边的草地上整整露尸一个通宵。
1960年大年初一,阴沉沉的天空满是纷纷扬扬的雪花。几位忍饥挨饿的亲戚朋友相约,为我父亲送葬。眼看死人穿着旧衣,几块旧木板镶起当棺材,也没有敲锣打鼓、燃放鞭炮和披麻戴孝的场面,人人无不心酸。
父亲去世后,留下我们四兄妹,我是家中老大,家庭重担当然压到我的肩上。面对唉声连着唉声起,新坟跟着新坟埋的现状,我有苦难言。脑子里奔大学的梦想已荡然无存,唯一的打算就是求生,就是与弟妹们相依为命,尽力寻找出路,共同逃出这饥饿的深渊。
求生:天天采挖野生作物
没有粮食吃,饥饿越来越摧残人身,我家三个弟妹都不同程度地浮肿了。本来就很少的自留地上,所种的蔬菜根本就满足不了一家人每天煮食。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除了上山采挖野生植物充饥,已别无选择道路。认准了这个路子,在埋葬父亲的当天下午,我就冒雪上山,去离家不远的一道土坎上挖野麻根。经过几个小时的努力,挖回的野麻根有10多斤。晚上,我们几兄妹就把挖来的野麻根放在柴火中烧,烧熟了,剥掉皮就吃。吃后,大家都比较满意。从此,我天天上坡采挖野生植物,哪怕雨天雪天也从不中断。对于野生植物,我从小放牛时,在大人的指点下就认识很多,知道哪些东西可以吃,哪些东西最好吃。所以,每天上坡后,只要见到可吃的东西,哪怕钻刺蓬,爬岩壁,也要千方百计去采集,去挖掘,不放过任何机会。辛苦的劳动,或多或少都有收获,从而,使家里每天都有一些可以充饥的食物。
农村饿死人的情况终于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就在1960年春节后不久,国家仓库开始发救济粮了。初发时,每人每天二两毛粮(稻谷),后来增发到每人每天四两,最多时发到每人每天半斤。虽然发了粮食,但毕竟数量很少,所以,我仍然坚持天天上坡采挖野生植物。那时候的煮食方法是:把发的稻谷炒焦后磨成谷粉,野生植物分品种,有的洗净切细,有的磨成面粉,有的滤成淀粉,根据情况,掺合煮来吃。为了维持这样的生活,我不顾饥寒,历经两个多月的艰辛,跑遍了我家周围的山山岭岭、沟沟谷谷,采挖过蕨苔、葛根、野麻根、洋姜等二十多种,甚至把我家屋侧一根合抱大的枇杷树也砍来剥皮煮吃了。我真是怀念那时的自然资源,因为那各种各样的野生植物,确实为我们全家冲出绝境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
杀牛:倾力拯救灾民
农村大面积饿饭,到国家发放救济粮的时候,已经饿死了不少人,还有大量的人全身浮肿,濒临死亡的边缘。对此,公社采取紧急措施,开办“临时病院”,宰杀集体耕牛,不惜一切代价拯救灾民。具体做法是:划分片区,把相邻几个生产队浮肿严重的人,集中到较为居中的生产队集体食宿。我家所在的生产队很快就办起了“临时病院”。人员集中以后,立即宰杀集体耕牛,将牛肉和骨头一起煮。等牛肉煮得稀烂后,去掉骨头,再将磨好的粮食面粉放入大铁锅内搅成稀粥。吃的时候用木瓢分发,见人后在花名册上打勾,勾一个给一份,一瓢一瓢地平均分配,以免漏发和吃双份的情况。
我弟弟和最小的妹妹被列入“临时病院”的名单。虽然我家离“临时病院”食堂只有两百米左右,但他们无力行走,每天吃饭时,必须由我分别把他们背到食堂去露面,并对照花名册打勾后才能领到稀饭。有天傍晚,我背他们去领稀饭时,途中见到了一个死人。那人仰卧在路边,只见他口不合,眼不闭,衣着单薄,整个身躯只剩一具骨架。当时阴风惨惨,谁见了都会胆寒。但我为了弟妹们的生存,还是鼓足勇气,壮起胆子,连续往返四趟不绕道,终于为弟妹们领回了稀饭。
在开办“临时病院”的同时,大队还组织杀牛。先把牛肉集中在大队,然后由大队干部分头到生产队摸底,凡浮肿的人就给一张便条,由浮肿人到大队凭条领取两斤牛肉。
开办“临时病院”和供应牛肉,重点解决吃饭和吃肉问题,效果非常显著,使大量浮肿的人逐渐消肿,恢复健康,最终战胜死神,从而获得了新生。
在与死神的搏斗中,也有个别人擅自杀死集体耕牛,私自悄悄煮食的情况。如我们生产队的一个社员与外生产队的一个社员一道,在一天夜里,把一头自家喂的集体大黄牯牛,拉到一个偏僻的山沟里,用绳子把牛活活吊死,然后砍成块块,各自背回家中煮食。又如我们临近生产队的一个社员,也把自家喂的一头集体耕牛,拉到自家屋里,把牛鼻绳拴在火炉脚(木柱)上,再用绳子把牛的四脚缠住,牛倒地后还未断气,他就迫不及待地在牛的臀部割一块肉来煮食。接连发生这两件事,县公安局专门派人作了调查,当事人都对私杀耕牛、煮食牛肉的情况如实作了交待。本来,杀集体耕牛是违法的,但鉴于当时的历史背景,后来也就不了了之。
松绑:农民享受自由种植权
1960年5月,人民公社管理区决定让我当大队干部。当时有一个统一的宣传口径,就说前段时间到处饿死人,是上面有“死官僚主义分子”掌权,下面有“富裕农民”当道。这里说的上面,指的是公社、管理区;说的下面,指的是大队、生产队。所以,一时间层层撤换基层干部。我们的大队会计被定为“富裕农民当道”的对象,在“拉富裕农民下台”中被撤了职,我就是顶替他做了大队会计的工作。
随着各级干部的撤换、调整,上面的政策也开始放宽,允许社员家家户户种植部分集体丢荒的少量土地。如果生产队因耕牛少、劳动力弱而种不完的熟地,社员也可耕种。实行谁种谁收,社员自种自收自吃,上不缴国家公余粮,下不留大队干部提成。这样一来,群众普遍心情舒畅,劳动热情空前高涨。从1961年春天开始,尽管大量饿饭浮肿的人还正在逐渐康复过程中,但绝大多数的农户拖着瘦弱的身体,上坡开垦荒地。各家各户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想方设法在各自开垦的地上种植了包谷、高粱、荞麦、瓜豆等各种各样的农作物。这个时候,农家户的农家肥要先交集体,即使有一点,也没有劳动力挑上坡,耕作是比较粗放的。可是老天有眼,风调雨顺,秋收时节,收成不错,为解决饥饿问题增加了一分保障,群众无不舒了一口气。
群众从自由种植中得到了实惠,放宽政策收到了显著的效果。从1961年冬天到第二年春天,上面的政策进一步放宽了:一是行政体制的改变,将原来的公社改为区,管理区改为公社,有的原来较大的管理区、大队、生产队,一分为二,规模缩小了;二是撤销集体食堂,让社员自家开伙,同时将大队核算改为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三是进一步动员群众,大张旗鼓地提倡私人开荒种地。这些政策,群众普遍拍手称快。于是,掀起了一场声势更大的全民开荒的浪潮。无论走到哪里,放眼田野,到处都是紧张劳作的人们,银锄挥舞,一派生产自救的繁忙景象。这是一场向荒山要粮、向饥饿宣战的人民战争。经过放宽政策,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大家齐心合力,艰苦奋战。一年下来,果然五谷丰登,人畜兴旺,农村确实出现了新面貌,难关终于渡过了。
作者单位:贵州日报
责任编辑:翁泽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