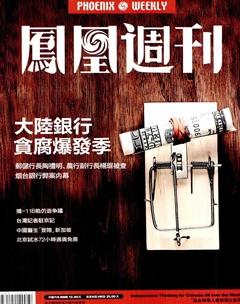晚年毛泽东重读古文内幕
周言
朱永嘉曾经受命担任毛泽东晚年所读古文的标点注释工作,而此书恰恰是他当年受命担任此事的记录。

朱永嘉先生可以算是上海复旦大学的“出土文物”。由于其在“文革”时期担任上海市革委会的常委和上海市写作组的组长,加上他在粉碎“四人帮”后那句惊天动地的言论,导致了其14年的牢狱生涯。出狱之后,仅靠那可怜的工资显然养活不了自己,朱先生回忆,刚出狱不久,当时章培恒先生负责复旦大学的古籍所,当时所里有编《全明诗》的任务,课题有少量经费,章先生那时便找朱先生看稿,每月给朱先生200元;后来又让朱先生做《明词汇刊》的整理和标点工作,让朱先生赚一点稿费,算是雪中送炭。
当然,《明词汇刊》出版的时候因为政治原因,不能署朱先生的名字。朱先生署名的书,只有后来在台湾出版的一些由他和萧木先生注释的古籍。《晚年毛泽东重读古文内幕》,是他被历史的尘土掩埋了30多年后重新出土的证明。我听他说,最近他的“文革”回忆录《从海瑞罢官到一月革命》也将出版,我有幸在老先生的家里翻看了其中的章节,私心以为,这两本书的出版,对于“文革”史研究而言,是一件破天荒的大事。
近年来“文革”人物的回忆录出了不少,比如林彪手下“四大金刚”,都在过世之后出版了回忆录,但是限于他们的知识水平,对于毛泽东在晚年的政治生活微妙的心理变化无从体会。朱永嘉曾经受命担任毛泽东晚年所读古文的标点注释工作,而此书恰恰是他当年受命担任此事的记录。朱先生认为,毛泽东晚年选择重读古文,实际上大有深意。
朱先生回忆,当时“林彪叛逃事件”爆发之后,“文革”开始走向没落。毛泽东当时挑选了《晋书》当中的《谢安传》《谢玄传》《桓尹传》《刘牢之传》,让朱永嘉负责标点注释。这四篇文章一以贯之的主题,乃是东晋如何在北方苻坚百万大兵压境的情况下以弱胜强。毛泽东曾经在政治局会议上推荐政治局委员读《谢安传》,当时苏联准备对中国动武,毛泽东意在以此文表达他对中央领导人和军队将领的期许,而让诸人读《桓尹传》,则是告诫周恩来这样的政策执行者,要学会向桓尹那样协调决策者和执行者之间的关系。
当时部队中的许多干部对张春桥等“文革派”有看法,经常不听指挥。“林彪叛逃事件”之后,在林彪的住所发现了四野之外的一些军队将领给林彪的信,这让毛泽东非常紧张。毛泽东当时让朱永嘉标点《史记》中的若干传记,同时表示不要注释。这些传记篇目中的人除了黥布是在刘邦临终前叛变,刘邦亲自将其消灭而外,其他的都是刘邦手下的功臣宿将。毛泽东当时便在考虑如何处理许××一类军队大员,进而让朱永嘉注释了柳宗元的《封建论》,接着便按照《封建論》中的告诫,将八大军区的司令员调防。毛泽东同时让王洪文读《刘盆子传》,意在训诫王洪文不要骄傲自满,要约束下属,否则下场和刘盆子一样。
当然毛泽东不仅仅是在“林彪叛逃事件”之后让政治局的委员们读古文。高华曾经指出,“文革”初期,当时毛泽东曾经让林彪读《三国志》中的《郭嘉传》和《宋书》中的《范晔传》,以此对林彪加以告诫。郭嘉乃是曹操的谋臣,协助曹操破袁绍立下大功,随曹操征战多年,英年早逝,年仅38岁;范晔是南朝宋国人,于元嘉二十二年以谋反罪名被满门抄斩,时年48岁。毛要林彪学郭嘉,一心事主,又用范晔最后参与谋反,被满门抄斩的历史来警告林彪,要谨慎从事。
当然毛泽东本人不仅仅以古文训诫他人,更以古文自遣。据朱永嘉回忆,毛泽东临终之前,曾经多次读庾信的《枯树赋》,此赋借由古树之所以枯萎摇落而衰变的物象,比喻故国和自己由于年迈而遭急流逆波冲荡,以及被人砍伐遭到摧残而逐渐衰弱的感慨。毛泽东在自己生命最后一程反复阅读《枯树赋》,联系到当时“文革”已经难以为继的现实,此中自然有着意味深长的内容,正如毛泽东自己诗词中所写的那样:“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
编辑 晓波 美编 黄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