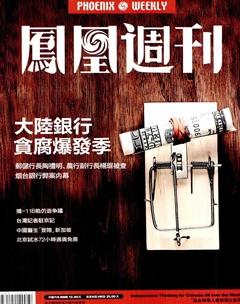费正清中心50年
周言
1 年初路克利来信,告知由其翻译的《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五十年史》已经由新星出版社出版。去年我在波士顿时,已经在书店中看到此书的英文本,没想到中文译者竟是路克利。路克利英文水平甚好,他本科在山东大学读书时,就曾经被誉为“小克利”。
 有“小克利”,自然也就有“老克利”,“老克利”自然就是在山东大学任教的著名翻译家冯克利。无独有偶,“老克利”也翻译了一本书,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便是那本去年在北美中国学界影响巨大的傅高义著《邓小平与中国的变革》。
有“小克利”,自然也就有“老克利”,“老克利”自然就是在山东大学任教的著名翻译家冯克利。无独有偶,“老克利”也翻译了一本书,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便是那本去年在北美中国学界影响巨大的傅高义著《邓小平与中国的变革》。
读路克利翻译的这本《五十年史》,当然想起了费正清以及费正清中心的许多故事。以前读朱政惠先生编著的《史华慈学谱》时,有条史料颇有意思,大致内容是1986年史华慈教授写信推荐麦克法夸尔担任费正清中心的主任,当时史华慈已经卸任中心的代理主任。麦克法夸尔先生的经历可谓丰富,他在上世纪50年代曾经是《中国季刊》的创刊编辑,《中国季刊》在麦克法夸尔手上很快成为当时研究当代中国最为著名的英文学术期刊。当时麦克法夸尔坚持最高学术标准,要求刊载的所有论文都要完整的标明引文和参考文献。
麦克法夸尔先生在大陆最引人瞩目的,当然是他的文革史研究,他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三部曲,在西方世界和中国党史学界影响极大。其中的第三卷《灾难的来临》,在大陆迟迟未能出版,此书曾经获得过1998年的列文森奖。列文森奖是美国亚洲研究协会为纪念中国近代史研究翘楚列文森而设立的,而列文森也正是费正清的高徒。该奖项从1987年开始颁发,奖励在美国出版的研究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学术著作,这些获奖的著作中最为中国学界所熟知的有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Jr.)的《洪业:十七世纪中国满人对帝国秩序的重建》,周锡瑞(Joseph W.Eserick)的《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杜赞奇(Prasenjit Duara)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的华北农村》等。曾经担任过费正清中心第四任主任的孔飞力(PhilipA.Kuhm)出版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便获得过1992年的列文森奖。
我和许多上过麦克法夸尔先生课的中国留学生一样,亲切地称呼麦克法夸尔教授为“麦先生”。麦先生在哈佛开设有文革史的课,与哈佛大学一墙之隔的麻省理工学院学生也可以选修。这门课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一直人满為患,当时曾经担任麦先生助教的丁学良后来回忆,远在80年代中期,哈佛校方就正式向麦先生提议,可否在该校《核心课程》大栏目下,新开一门专讲中国“文革”的课?如果开成了,这将是全世界主要大学里,首项以中国“文革”为主题的完整课目。当时麦先生非常为难,因为虽然麦先生本人对文革史很有研究,但是如何给学生讲述这一段历史,却成为了一个难题。但是麦先生最后还是答应下来,这也是他后来与沈迈克一起撰写《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一书的缘起。
丁学良还曾经谈到,首届“中国文化大革命”于1988年春开课时,哈佛本科生中主动要来上的达千名,哈佛本科生全部才6000多人。这么大规模的课,倒是给后勤部门出了道难题,因为没有这么大的常规教室。无奈,校方只好准许这门课在Sanders剧院里上;该栋古建筑物颇具文物价值,平时保管甚严,通常是在重大庆典时才动用。正式注册上首届文革课的学生是830名左右,仅助教就有22名,包括丁学良在内。丁学良回忆,那时没有现成的课本,麦先生就组织助教认真挑选中文数据译成英文,复印装订成册。让丁学良印象鲜明的是当时在讨论如何翻译“文革”特有术语遭遇的困难,常为一个译法争论半天。比如“走资派”,最后选定的是capitalist roaders;有学生在测验时望文生义,把它解释成:“非常富有的人开着豪华车在高速公路上奔驰”。
我有时见到麦先生时,想到费正清中心这50年的历史,不禁感慨万千,从费正清到麦克法夸尔,老一辈的中国研究者渐次凋零,麦先生去年80初度,按道理说他已经退休,但还是经常能在哈佛的校园里见到他,但是哈佛能够接任他教授“文革”史这门课的人,已经无从寻觅。
2 麦先生曾经和费正清一起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这本书同样对当代中国研究有着重要的影响,出版近20年来常常能见到相关的学术著作引用这本书。当年费正清80大寿时,麦先生还特意把丁学良叫去,当时真是羡煞旁人。费正清是西方研究中国学的开山鼻祖,四五十年代乃至其后在美国几乎家喻户晓。但是由于1949年之后中国大陆山河易手,美国的反共恐慌日渐增长,以前曾经和中国有着密切往来的费正清在这一时期遭受了严重的质疑,费正清索性躲在学院中专心学术,这反而促使了当时草创的费正清中心逐渐发展壮大。
当时费正清已经意识到活跃于美国学术界研究中国问题的中国人相对较少,所以他邀请了很多研究中国的中国学者来哈佛,这其中便有《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的作者周策纵。费正清还和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郭廷以关系甚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成立,费正清与当时同在美国的韦幕廷出力甚多。为了表彰郭廷以、费正清、韦幕廷三人之间的高谊,郭廷以的大弟子张朋园先生还特意以三人名字为题写了一本关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成立及发展的专书《郭廷以、费正清、韦慕庭——台湾与美国学术交流个案初探》。
朋园先生在这本书中,详细介绍了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草创时期所遇到的种种非难,譬如当时费正清来台湾准备联合台湾的学术界研究中国的近代化问题,当时还初步拟订了一个计划,准备召开一个小型的讨论会,但后来费正清做了详细的了解得知台湾的大学机构基本上都有繁重的教学任务,所以选择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合作。美国汉学家韦幕廷在研究孙中山和蒋介石,当时蒋介石还在世,于是郭廷以帮助其打通关节,顺利见到了蒋介石,蒋介石还很客气地回答了韦幕廷的提问。韦幕廷自然非常感谢郭廷以。也就是因为这些原因,当时许多海外的研究基金都是通过费正清和韦幕廷的支持才到近代史研究所中的,其他的台湾大学或者科研机构自然非常眼红,便联合起来抵制郭廷以,郭先生一怒之下竟远走美国。
费正清除却对台湾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助力甚大外,他对许多当时在美国的中国学者也是多加关注,譬如著名的历史学家余英时,余先生1962年在哈佛取得博士学位,后来去密歇根大学任教,1968年回到哈佛任教,他是当时东亚研究中心(费正清中心前身)的执委会成员。再如当時同样在学术界崭露头角的杜维明先生,便曾经在费正清中心修改他关于王阳明的论文。
有关于余英时先生后来在美国不同的高校任教的情况,我要粗略地补写几笔,《五十年史》中提到,余先生离开哈佛后,转到耶鲁大学任教,最后到了普林斯顿大学,直到退休。后来王泛森先生曾经回忆,他当时和余先生是同时到达普林斯顿,当时王先生还在中研院做助理研究员,来普林斯顿读博士,当时他已经听到各种传言说余先生要到普林斯顿。余先生有一次到普林斯顿演讲,好像写了—首诗,有人从中读出他有移居普林斯顿的意思,后来此事居然真的成为了现实。从耶鲁去普林斯顿的时候,余先生还写了一幅张继的《枫桥夜泊》的书法送给耶鲁的同事,这幅书法现在孙康宜女士的手中珍藏。
3 接任费正清的是傅高义,他因为研究日本问题和中国广州的改革开放广为人知,在傅高义的支持之下,中心还成立了日本研究所。傅高义后来与中国官方或是民间往来密切,曾经写过两本相关的专著,—本叫做《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另外一本叫做《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傅高义之后,在第四届费正清中心的主人、著名历史学家孔飞力的支持下,哈佛大学出版社发行了一套名为《哈佛当代中国书系》的丛书,参加这套丛书编辑工作的许多都是哈佛本校的教授,如麦克法夸尔、裴宜理、王德威等等。
麦先生在史华慈的支持下接任费正清中心的主任,中心发展由此到了新的高度,不仅仅中心的筹资达到新高,另外麦先生还为哈佛的当代中国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其中有一项便是收集和翻译毛泽东1949年之前作品的大型学术项目。麦先生邀请了西方最著名的毛泽东研究专家施拉姆承担这个项目,迄今为止,这个项目已经出版了近十卷本的《毛泽东的权力之路》,2003年,在麦先生的推动下,哈佛大学召开了主题为“重新认识毛泽东”的庆祝大会,世界各地的毛泽东研究专家齐聚哈佛,其中有逄先知、史景迁、白鲁恂等。
后来接替麦先生的是华琛教授,他的一项重要的工作是将1994年来哈佛任教的李欧梵引入哈佛当代中国的研究,麦先生对此举也表示赞同。而华琛对李欧梵表示友好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华琛是研究文化人类学的,李欧梵的研究在广义上是一种文化解释,与华琛的研究是相通的。许多哈佛大学教授参与、深受好评的《剑桥中国文学史》晚清到现代部分,便是由李欧梵所撰写的,后来李欧梵退休,接替他的便是王德威。

费慰梅、林徽因、费正清、梁思成合影。
华琛之后,傅高义开始了他在费正清中心的第二任期,这一任期他的一项重要举措是邀请当时访美的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这一事件推动了中美之间的学术交往。但是这一事件,并不能挽救当时费正清中心面临的筹资问题,这一时期,哈佛大学亚洲中心成立,这一中心的活动不仅限于学术界,它同时承担了哈佛大学筹款活动中亚洲计划的主力。这个中心与费正清中心名称相似,但是费正清中心的研究主题主要是中国。
傅高义之后是裴宜理接任中心主任,裴宜理新近的研究是在于建嵘的建议下研究安源工人运动,他还曾为于建嵘的著作《安源实录》写了序言。前段时间在美国时,曾经听说此书即将出版,但是一直没见到书,后来小骏兄告诉我是正在修改。我曾看到社科院近代史所的刘文楠女士谈及裴宜理的这项新研究,刘在美国读书时曾经仔细听过裴宜理关于这本书的报告,在刘文楠所写的札记中,他将裴的观点归结为如下几点:共产党的持久生命力在于其对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利用能力,而不是其运用苏俄模式的能力。李立三早期在安源发动罢工,用的是“文化置换”(Cultural Positioning)的策略,也就是把人们熟悉的文化资源重新整合,掺入新的思想,来为共产党的革命服务。建国以后,用的则是“文化操控”(Cultural Patronage)的策略,国家主动去操控文化,构建新的文化形象,并使之深入日常生活。因此,她认为目前共产党的持久活力在于能从更深的文化储备中汲取资源,而不是单纯的追求经济增长。
而现任的费正清中心主任,便是哈佛中国基金会的主席柯伟林。柯伟林执掌哈佛文理学院时,对哈佛的本科生教育进行了较大程度的改造,成果显著。《五十年史》中虽然没有写到新近柯伟林担任主任的时期,但是却记录了柯伟林的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在柯伟林的努力下,蒋廷黻的档案捐献给了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这其中包括了几箱子的个人文献和他在1944年至1965年的日记。柯伟林是费正清的弟子,费正清30年代和蒋廷黻关系密切,当时蒋廷黻担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费正清当时在蒋廷黻的帮助下在清华大学担任讲师。
费正清中心这50年的历史,所折射的正是中国曲折发展的历史,费正清在他的名作《美国与中国》等一系列的著作里,提到了一个著名的“冲击——反应论”。异曲同工的是,麦先生有一次曾经和丁学良谈到中国的现状,麦先生说,中国的文化过去太光荣了,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绝大部分都是以“文明中心”的地位来教导和开化周围的那些“番邦”。如今这样的一种文明中心忽然要弯下腰去向西方、向另外—种文明学习,肯定是一个很痛苦很屈辱当然也很困难的过程。他对丁学良说:“对于你这样的年轻一代来讲,在走向四个现代化的路上,不能脱离这样一个两千多年的大背景来看,遇到困难也要从这个大背景去理解。”我想麦先生的这番话,充满了一个研究中国、研究中国革命的老人对于革命之后的中国无尽的善意。
编辑 晓波 美编 黄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