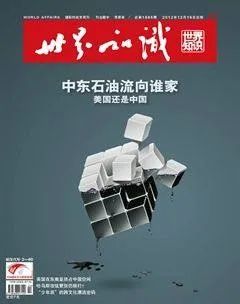穆尔西:终结民主的“新法老”?

2012年11月27日,埃及总统穆尔西颁布新宪法声明。这份寥寥数语的声明,赋予总统不受约束的最高权力,不仅有权任命总检察长,且其发布的所有总统令、宪法声明、法令及决定都将成为最终决定。此举一石激起千层浪,被广泛解读为穆尔西欲独揽大权,要做埃及的“新法老”,将时钟拨回到威权时代。当天,数万埃及民众涌向开罗解放广场,抗议埃及历史上首位民选总统——穆尔西。在接下来十几天里,这场危机愈演愈烈,“反穆”和“挺穆”的示威在埃及各地登场,被剥夺权力的法官集体罢工。埃及陷入剧变以来最严重的一场危机。
穆尔西意欲何为?
当选总统后,穆尔西没有按照军方的安排,成为一个“缩水版”的总统。与大多数人的预料相反,他表现得十分强势,连烧了“三把火”,而且一把比一把旺。甫一上台,他便废止了军方在交权前匆忙颁布的宪法修正案,收回了被剥夺的权力。8月,也就是伊斯兰教斋月期间,他以军方处理西奈半岛安全问题不利为由,发动“斋月行动”,将国防部长坦塔维和总参谋长安南双双拿下,换上年轻将领。在前两次扩权行动中,穆尔西均平稳过关。但他颁布宪法声明的“第三把火”却惹了众怒,不仅世俗民主派强烈反对,就连部分穆兄会支持者也不答应。穆尔西冒着背上民主终结者的骂名出此险招,究竟意欲何为?
其实,穆尔西欲通过此次扩权,达到两个目的。短期目标是确保制宪议会不被解散,新宪法草案获得通过;长期目标是约束司法系统的权力,扫清阻碍其全面施政的最后一块绊脚石。在废除军方宪法修正案、撤换军方领导层之后,穆尔西已与军方达成妥协,双方尊重彼此利益,互不干涉。然而,摆平军方后,穆尔西的日子还是不好过,因为他被司法系统束缚着手脚。埃及司法系统一贯具有“革命精神”,即使在威权时代也保持着很大程度的独立性。法官们自视为捍卫埃及政权世俗性的中流砥柱,誓与穆兄会决战到底。此前,法官们已多次与穆兄会和穆尔西本人正面交锋,如解散议会下议院、赋予前总理沙菲克总统候选人地位等。眼看宪法起草工作就要结束,穆尔西只得铤而走险,与法官们摊牌。
难产的宪法
此次危机的导火索是新宪法草案。制宪是关乎埃及前途命运的头等大事,各派政治力量自然寸步不让。以司法系统为代表的世俗派与以穆兄会为代表的伊斯兰阵营,围绕新宪法制订,产生了激烈的矛盾。自议会选举之后,制宪委员会组成方式成为世俗派和穆兄会斗争的焦点,穆兄会坚持制宪委员会应从被伊斯兰党派控制的议会产生,世俗派则认为这样组成的制宪委员会缺乏代表性,担心伊斯兰党派控制的制宪委员会将制订一部改变埃及世俗性质的宪法。埃及司法系统一直试图解散这个伊斯兰党派控制的委员会。3月24日,议会产生第一届制宪委员会,国家行政法院随即于4月10日裁定其不具合法性,令其停止工作。本届制宪委员会成立于6月12日。制宪工作正式启动以来,各派政治力量的争夺更加激烈,斗争在两条战线上展开。一方面,在制宪委员会内部,世俗派和伊斯兰主义者围绕宪法如何表述政教关系展开激烈争论。伊斯兰阵营内部意见也不统一,保守的萨拉菲派和温和的政治伊斯兰之间也有分歧。另一方面,司法系统认为制宪委员会缺乏代表性,法官们并不关心具体的宪法条文,而是想从根本上否定整个制宪进程,进而将制宪委员会和议会上院一并解散,打破伊斯兰阵营垄断政治过渡的局面。
数月来,这两条战线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息,制宪委员会未能按时在三个月内完成制宪工作,迟至11月30日才拿出新宪法草案。其间,国家行政法院仍在继续审理制宪委员会和议会上院合法性案,已三度推迟宣判。穆尔西正是在制宪委员会即将通过新宪法草案之时,宣布“扩权”,意在对司法系统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使其在制宪问题上不再拥有发言权。穆尔西的如意算盘是,将新宪法交由仍在运转的议会上院批准后交由全民公决,或者直接交由全民公决。在穆尔西看来,只要绕开司法系统,不仅新宪法获得穆兄会控制的议会上院批准毫无悬念,而且能够在全民公决中轻松过关。这不仅因为包括穆兄会在内的伊斯兰党派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还因为长期处于威权统治下的埃及民众,在全民公决中投赞成票已成为习惯。12月1日,穆尔西宣布12月15日就新宪法草案举行全民公投,这意味着制宪委员会完成了新宪法草案的起草工作,该委员会随后自动解散。受此影响,最高宪法法院12月2日宣布无限期推迟涉及解散制宪委员会和议会上院案件的判决。
教俗之争
这次危机表面上是宪法危机,深层次问题则是后威权时代埃及社会宗教与世俗两种意识形态的对立。埃及社会目前已被意识形态撕裂,极化特征显著,总统选举第二轮中穆尔西和莎菲克几乎持平的得票率很好地诠释了这一点。自议会选举结束后,特别是来自穆兄会的穆尔西当选总统后,“穆兄会恐惧症”和“威权恐惧症”在自由民主派和科普特人中间蔓延。前者是指自由民主派怀疑穆兄会并非真心实意“拥抱民主”,民主只是其为夺取政权而采取的权宜之计。他们担心穆兄会利用投票箱上台,目的是建立实行“沙里亚”的“伊斯兰国家”。后者是指威权政权倒台后,民众对民主的期望值升高,自由民主派担心穆兄会一家独大,控制议会、政府和总统职务,凭借其民意基础实行“多数人暴政”,催生出新的政治强人。因此,穆尔西宣布扩权,被世俗民主派解读为其欲窃取“革命”果实,独揽大权,将埃及带回威权时代。
伊斯兰阵营则认为,这个由民选议会产生的制宪委员会完全合法,而且伊斯兰主义者在委员会中所占的比例低于他们在议会中的比例。如果自由民主派不承认这个委员会的合法性,恰恰说明他们唱着民主的高调,却不接受民主的结果。因此,在伊斯兰党派看来,司法系统是打着捍卫民主的旗号,谋一己私利,置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于不顾。
伊斯兰劫持民主?
政治伊斯兰参政的真实目的,一直备受争议。根据历史经验,政治伊斯兰参政一般会导致两种结果。其一,无论政治伊斯兰参与民主进程的初衷如何,这一进程将促使有关国家的民主化,并使参与其中的伊斯兰主义者被塑造为民主主义者;其二,政治伊斯兰参与选举并非出于对民主的认同,一旦上台便会以“一人、一票、一次”的方式终结民主,建立“伊斯兰威权”。1992年6月,负责近东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爱德华·杰雷吉安在华盛顿子午线国际中心发表题为“变化世界中的美国、伊斯兰和中东”的讲话。在这个后来被称为“子午线讲话”的著名讲话中,杰雷吉安表达了美国对政治伊斯兰参加选举动机的疑虑。他指出,“我们怀疑那些利用民主程序上台的人,他们惟一目的是利用民主程序夺权和寻求政治控制。我们支持一人一票,反对一人、一票、一次。”
埃及剧变的悖论是群众抗议的主体——世俗政治力量未能上台执政,并未发挥核心作用的穆兄会等伊斯兰力量却通过选举上台,成为剧变的最大受益者,这是自由民主派难以接受的结果。穆尔西的所作所为似乎也印证了杰雷吉安的预言。然而,如果将穆尔西的做法放在埃及政治过渡的背景下观察,恐怕不会轻易得出伊斯兰“劫持”民主的结论。埃及刚刚摆脱数十年的威权统治,正在向民主艰难过渡。威权时代的终结,并不意味着埃及能够自动过渡到民主。埃及现在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无民主主义者的民主”的阶段,政治文化嬗变的缓慢,使过渡期的各派政治力量依旧按照威权时代的“老套路”行事。从法老到穆巴拉克的漫长历史中,埃及从来都是由政治强人实行人治。因此,穆尔西无法接受自己成为一个无权无势的“花瓶”,也不能适应权力分享与机制化这个民主的应有之义。他仰仗身后强大的穆兄会及其广泛的民意基础三度扩权,就很顺理成章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将当前埃及乱局归咎于穆兄会和穆尔西“劫持”民主,显然不公平,真正的病根是整个埃及社会的“民主不适应症”。即使是一位没有伊斯兰背景的总统,也会像穆尔西那样行事。因为,民主机制尚未建立,政治家还不适应民主的游戏规则。
世俗派的表现同样说明了这一点。司法系统的所作所为表面上是捍卫民主,其实是以意识形态挂帅,“逢穆(兄会)必反”。在其阻挠下,埃及在剧变20个月后还没有正常运作的议会和一部宪法。由于政治过渡进程停滞,政治解决机制缺失,民众只能通过“广场政治”甚至暴力手段表达诉求,使后威权时代的埃及乱象丛生。
动乱何时休?
穆尔西现已宣布于12月15日将新宪法草案交由全民公决,如果公投能够顺利进行,新宪法草案获得通过几乎没有什么悬念。届时,穆尔西便可用公投赋予新宪法的合法性,证明“倒穆”运动是无理取闹。目前惟一的变数是司法系统罢工,可能导致公投缺乏监督,使其合法性受到质疑。
这份对1971年宪法修修补补而成的新宪法,本身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埃及的政治图景。然而,它却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引发的轩然大波至今没有平息的迹象。这场宗教和世俗力量之间的斗争,已远远超出了新宪法本身,说明埃及社会已严重分裂和意识形态化。穆尔西上台后,在政治过渡方面无所作为,在经济、民生和治安等领域同样乏善可陈,他就职时承诺的“百日目标”仅完成了15%。民众对民主化和经济发展的期望落空,还将引发新的动荡,意识形态斗争导致的政治僵局和经济停滞将把埃及拖入更严重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