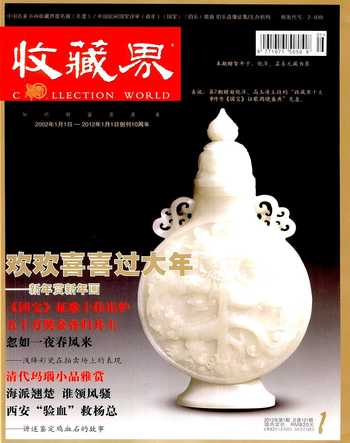浅绛彩瓷的文人画风:简淡化
棠樾



浅绛彩瓷的定位,首先应当定在文人画意上,定在浅绛彩瓷的创作蕴涵了丰富的超越画面的“象外之旨”上,这是毫无疑义的。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认为文人画意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概念,是一个能够囊括有关浅绛彩瓷定位的所有内容的概念。所以,我们试图做一些拓展性的工作,把文人画风、文人画趣、文人画品等概念从文人画意中剥离出来,多角度地把握浅绛彩瓷的文人画定位,多侧面地解析浅绛彩瓷的文人画形态。
过去,浅绛彩瓷的定位研究相对简单,把问题焦点完全集中在文人画意这个要害上,相关内容全都裹在一起讨论。紧紧抓住这个要害是对的,仅仅局限于这个要害就显得简单化了,比如文人画风,虽然与文人画意密切相关,却又不能混为一谈。说它们密切相关,是因为文人画意虽然超越了画面,却能够从画面呈现的艺术风格上获得启示和联想。说它们不能混为一谈,是因为文人画意属于内容的范畴,文人画风则属于形式的范畴。在艺术理论中,内容与形式之间是相互制约的关系,内容影响到形式,形式反过来也影响到内容。浅绛彩瓷的创作实践,非常生动地印证了这一观点。浅绛彩瓷的文人画意突出表现为淡泊名利、超然物外、寄形自然、卧游山水。正是这种超逸的思想境界,有力推动着文人画风朝着疏简平淡、虚静萧散的审美维度发展。反过来看,浅绛彩瓷创作中呈现出来的文人画风,更加延伸和张扬了作品所要表达的思想意义。具体说来,浅绛彩瓷的文人画风可从简约构图和淡雅设色两个方面加以阐明。至于线条皴法,属于文人画风问题,但是涉及到中国画的笔墨趣味,成为文人画中一个很特殊的问题,所以另辟文人画趣专节论述。
说到文人画的简约构图,我们很容易想起元人倪瓒的远山中水近坡树的图式,《渔庄秋霁图》《秋亭嘉树图》等都是典型作品。这种图式说是三段式,其实只有两段实景,即远景的连绵山脉和近景的坡树,中景的无边水面以及远景中万里无云的天色并非实景,乃是虚实相映的结果。整个画面空旷疏朗,简洁至极。浅绛彩瓷的山水画创作对这种构图钟情有加,颇多借鉴。罗旸谷创作过一件瓷板,题为《满城风雨近重阳》(图1,见徐锦范等编《中国近代名家彩绘瓷画图典》P5,学林出版社2005年版)。从画面内容看,画的是山雨欲来的秋景,似乎题作“满山风雨近重阳”更加贴切。从画面构图看,则是标准的三段图式,远处的山势层次分明,山下的树林和茅舍错落有致,用的是米家云山的横点皴法,含蓄地透露出迎接风雨洗刷的消息;近处坡石上绿树掩映,两株红树穿插其间,提示着入秋的季节;远处山峦与近处坡树之间,开阔的水面上飘浮着一叶扁舟,舟中人似乎并不在意风雨的到来,一边饮酒,一边流连于江岸的景致。整块瓷板的留白部分多于实景部分,极为简括空阔。徐照也画过一件山水瓷板,题为《溪山野寺》(图2,同上P4),索性把三段式并成了一段式,一抹远山,两间茅屋,三棵老树,集中在画面中部,上下都留出了大片的空白,一派天光水影共徘徊的旷远境界。不仅是山水画,浅绛彩瓷中的花鸟画和人物画在构图上也是异曲同工。任焕章画过一件琮瓶,其中一面是《鹦鹉红叶图》(图3,同上P44),画面上的折枝红叶从右上经左侧伸展到右下,画出优美的弧线,一只白毛红喙鹦鹉栖息在稍稍偏上的黄金分割点上,栖息的姿态与折枝的走向形成均衡。这种围绕折枝的留白,与三段式山水画的整块留白有所不同,细碎而疏落有致,穿插而生气盎然。至于人物画,笔者所藏许达生《芭蕉仕女图》文房承盘(图4)可以为例,画面中央是一位女子,那双纤纤玉手在琴弦上轻拨慢弹;右侧是一树芭蕉,延展开来的蕉叶营造了一处适合弹奏的宁静氛围。画面左侧的空白处没有视觉物象,却在听觉上弥漫着轻曼美妙的琴声,和弹琴女子与树间莺歌对话共鸣的心声。
浅绛彩瓷中多见的这种简约疏旷的构图方式,与宋元以来的文人画一脉相承,思想渊源则可追溯到中国传统艺术哲学中的两个基本关系,即少与多的关系和无与有的关系。老子《道德经》中就有“少则得,多则惑”和“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说法,意为“少了反而容易得到,多了反而容易疑惑”;“最大的乐声听起来反而声响很小,最大的形象反而看不见行迹”。任继愈先生认为,“贵无”是老子的重要思想:“老子‘无的概念有‘有所不具备的一种实际‘存在,它并不是一个‘零。‘无不是空无一物,它具有‘有的对立面的品格,老子称之为‘无状之状,无物之象,也就是没有形状的一种形状。”(任继愈《关于〈道德经〉》,国家图书馆编《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文化卷》P369,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老庄哲学中的这些思想,对于中国的艺术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催生了中国画历来强调的“笔简形具”、“逸笔草草”等美学价值观念。特别是文人画,面对大千世界,进行提炼和取舍,进行拔俗和升华,直逼至简至淡的事物本质,呈现出来的面貌就是不期简而自简了。文人画还善于通过大片留白创造无限的想象天地,创造包容一切的悠远意境,恰如苏轼《送参廖师》中所说的“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正是因为宁静,所以能明了各种动态,正是因为空寂,所以能容纳各种意境。清人笪重光说得更清楚:“空本难图,实景清而空景现;神无可绘,真境逼而神境生。位置相戾,有画处多属赘疣;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现在回味一下前面提到的那些浅绛彩瓷中的佳构,虽然实景不多,空白很多,但每一处空白都是那样的耐人寻味,给我们提供了极其广阔的联想空间。
再说淡雅设色,这是浅绛彩瓷最重要的外在标志。浅绛彩的说法来源于元人黄公望多用淡赭的设色特点,后来在沿用过程中内涵得到扩展,泛指山水画的淡彩设色。浅绛彩作为一种清代晚期以来的陶瓷绘画概念,无疑是内涵的大面积再度扩展:一是从纸绢画扩展到了瓷画,二是从山水画扩展到了人物画和花鸟画,三是从绘画设色概念扩展为绘画风格概念。前两点很好理解,第三点值得多说几句。传统瓷画发展到明清以来的御窑时期,为了渲染和烘托皇权统治至高无上的主题,设色上愈加浓妆艳抹和富丽堂皇。浅绛彩瓷在太平军放火焚烧御窑后问世,绘画设色的浓淡变化只是表象,绘画风格从宫廷化向文人化的转换才是这次中国陶瓷史分期的实质。所以,浅绛彩在命名了一个时代的陶瓷艺术样式时,这个词已经被符号化了,它所负载的意义已经大大突破了表层词义的局限。
现在,我们回到设色的意义上来讨论问题。浅绛彩瓷无论怎么设色,都归结到“淡”上,绿是淡绿,蓝是淡蓝,赭是淡赭,其他颜色概莫能外。正是因为“淡”的性质,所以产生“雅”的感觉,于是有了“淡雅”两字的概括性说法。通常以为浅绛彩瓷多用淡绿、淡蓝和淡赭,主要是针对山水画而言。主景山体的皴擦晕染用淡淡的水绿和苦绿,远山用淡蓝、淡赭或者淡淡的矾红,树木用的也是淡绿,茅舍寺庙以及塔、桥等建筑用的则是淡赭,如此清淡到底,虽然不够炫目刺眼,却有一份含蓄而浓烈的雅致情怀直达心底。相比山水画,人物画和花鸟画的色彩更加丰富一些,红色、黄色、紫色等都算常见,只是清淡到底的性质没有不同。任焕章画过一对花鸟帽筒《不知此鸟缘何事》(图5),在花卉描绘上运用了桔红和紫红,但都是清清的、淡淡的,能够感到一股清淡的芬芳沁人心脾。任焕章所画的另一只人物帽筒(图6)上,两位老者的服饰或为灰色,或为黄色,一概清淡,照应了人物的性情和人生态度。与构图的“简”一样,设色的“淡”也是老庄哲学思想影响到中国艺术发展的产物。老子《道德经》中有“恬淡为上,胜而不美”的说法,意为“恬静淡泊是最上乘的境界,刻意所为的繁琐修饰并不显得美观”;《庄子·天道》则有“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也”的说法,意为“虚静恬淡、寂寞无为,是天地的基准,是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后来,北宋的梅尧臣、欧阳修、苏轼等把“平淡”视为诗文创作的最为精熟老到的风格表现;明代董其昌又在文人画理论中引入苏轼的思想,认为“淡”的风格是自我身心修炼的产物,是艺术的最高境界:“诗文书画,少而工,老而淡,淡胜工,不工亦何能淡?东坡云:‘笔势峥嵘,文采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实非平淡,绚烂之极。”审视中国绘画艺术的发展历程,从黄公望的淡赭设色到山水画的淡彩设色,再到浅绛彩瓷的淡雅设色,都是对至淡至工的艺术境界的不懈追求和精彩诠释。
就审美取向而言,构图的“简”和设色的“淡”相辅相成,指引着完全一致的方向,那就是老子和庄子所提倡的天然为本、素朴无华之美。由构图的“简”和设色的“淡”结合而成的浅绛彩瓷画风,疏简平淡,虚静萧散,与文人画意构成了密切对应,是文人画家寄托自然追求淡泊的人生态度在绘画风格上的集中体现。(责编:雨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