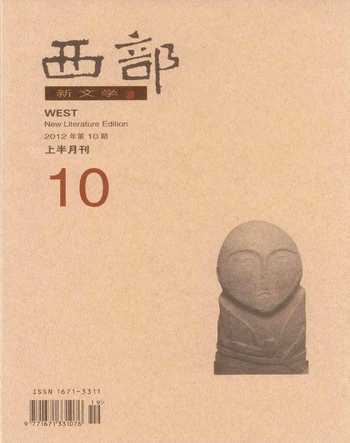《夹边沟记事》的生存哲学
刘瑞欣
自新时期文学以来,1950到1970年代的极左政治文化路线给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所造成的苦难生活,似乎一直是文学创作反复书写、永不厌倦的话题。既有亲历者的现身说法,如张贤亮、王蒙们的挥之不去的“噩梦”,也有当年蒙难者的后代,如韩东、方方的“隔代记忆”,自1993年以来更有无数纪实性作品纷纷出现,其中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以所写内容的真实、深刻,叙事风格的冷静为人称道。和其他“反右叙事”或者“饥饿叙事”、“苦难叙事”相似,《夹边沟记事》也是以极左路线下知识分子的“非人”生存状况为叙事对象,在这里论者要论述的就是这部作品所表达的独特的生存哲学。
一般情况下在小说中人物的生存哲学就是作者的生存哲学的体现,但《夹边沟记事》是一部“口述实录”性质的纪实性小说,故事中人物的生存哲学和故事的“记录者”的生存哲学事实上是不一致的,二者之间存在张力。
一
《夹边沟记事》记录的是1957年10月到1960年12月发生在甘肃省酒泉县夹边沟农场的“两千四百多名右派的苦难史”,在这里,上演了一幕又一幕为人生最卑微也是最基本的追求——活着而挣扎、而不择手段的悲剧。
俞兆远(《贼骨头》)的故事最能体现在这个“革命地狱”(钱理群:《地狱里的歌声——读和风鸣〈经历——我的1957年〉、杨显惠〈夹边沟记事〉》)中“为活着而活着”的生存哲学。他原本“满脑子都是士大夫‘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哲学”,“父亲还对他讲过‘曾子之廉,不饮盗泉和齐人不食嗟来之食的故事”。但是在不到三天的时间里,他眼睁睁看着同屋的两个右派饿死,“做一个正人君子的信条在他灵魂深处动摇了”。此后俞兆远和人合伙偷仓库的粮食;冒着中毒的危险偷拌了“六六”粉的麦种吃;为偷苞谷险些被狼吃掉,被打瘸了一条腿;粮食和草籽没了,捡荒野里 “或许是人骨、或许是兽骨”的骨头烤着吃。在被反复宣讲的长征故事中,类似的情节带给读者的是英雄主义的悲壮,而此时,在这场非天灾而是人祸的灾难中,知识分子身上的理性被生存的本能完全淹没了,人基本上成了一种动物性的存在。读来令人毛骨悚然。当有人为农场的牧羊人偷吃羊愤愤不平时,俞兆远还开导那人:“这事你生啥气呀,现在是啥时局嘛——饿死人的时局,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的时局——你有本事你也吃肥肠去,吃不上不要嫉妒人。”最让人动容的是,原本是为保命而偷,但到最后“偷”变成了俞兆远的心理疾病。在《贼骨头》的“后记”中,俞兆远回到家中已经不再挨饿,但本能地还去偷家里的粮食生吃。
《探望王景超》中写了一个细节:在一个小窑洞的土壁上有人用硬器刻下“生存”二字,历经三十年依然赫然在目。遥想当年,这些挣扎在饿死边沿的人们活下去的愿望是何等的强烈。除了《走进夹边沟》,其余诸篇几乎每篇都写到了出于求生的本能,这些右派们的“不堪行径”。出身诗书世家的王鹤鸣(《医生的回忆》)在回忆者赵医生眼中是彬彬君子,“从来不偷,别人把偷来的粮食给他,他也不吃”,但是到了1960年最后的三个月里,他却每晚去和马争食。为活命工程师牛天德吞食别人的排泄物(《饱食一顿》),为活命骆宏远冒死出逃,葬身狼腹(《逃亡》),为活命王朝夫恩将仇报(《许霞山放羊》),为活命豆维柯出卖肉体(《夹农》),为活命甚至“人相食”(《上海女人》、《在列车上》、《许霞山放羊》)……
二
关于《夹边沟记事》的文体有各种说法,论者在这里视其为口述体的纪实短篇小说系列。这十九篇作品(《夹边沟记事》,花城出版社2008年9月第一版)在叙事层面上形成套层结构,第一层次叙述者即故事的“记录者”——“我”时隐时现,但一直存在,而且从作品的口述纪实性质可以视之为同一个人。尽管叙事学的理论认为作为虚构性的文类,小说中的第一人称叙事者和作者不能划等号,但是在这里我们完全可以将文本中故事记录者的“我”和现实的作者等同。记录者“我”在文本中表达的价值取向、道德判断可视为作者的价值取向、道德判断。
和亲历者如张贤亮把苦难视作知识分子精神成长的必需从而粉饰这种不择手段不同,杨显惠借助“记录者”的身份,冷静而客观地用翔实的细节展示了不择手段的真实情况;和一些持道德至上主义者视这种不择手段为“知识分子的丑行”也不同,杨显惠在夹边沟这个“革命地狱”中将知识分子还原成一个个普通的个体,一个个生物学意义上的个体,一个个有着生的本能和死的恐惧的复杂个体,真实地展现了生死关头他们为活下去而进行的本能的挣扎,并对此持理解同情的态度。
《夹边沟记事》中“记录者”极少对故事中的人和事发表直接的评论,但在《许霞山放羊》中,当老实善良仁义的许霞山为保护自己的保命粮食一反常态和黄干事发生激烈冲突时,这个“记录者”控制不住地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人是有理性的,有思想的,但理性又是有限度的,也是脆弱的。当他受到强烈的刺激,当他的生存遭受威胁而无路可走之时,理性就退居其次了,那原始的不可理喻的本性就奔突而出了!”在这篇小说的结尾处,许霞山慷慨相助因食人肉而为他人所不齿的史万富,心痛曾忘恩负义出卖他的王朝夫的死,其实也是“记录者”即作者对人物的悲悯之情。
其次,在文本中记录者即作者通过人物之口多次渲染坚持节操者死相之悲惨(《一号病房》、《告别夹边沟》),反衬了为“活下去”而不择手段的合理性。但是,悲悯、同情人物的遭遇,理解、正视人物的生存哲学,并不意味着“记录者”即作者因而认同人物的一切言行。《夹边沟记事》的风格被称为“含蓄节制”(雷达语)。的确,十九篇小说大多是人物在时过境迁之后看似随意的追述和倾诉,基本上见不到直抒胸臆式的议论和抒情,作者也似乎在尽力扮演一个合格的故事倾听者和记录者的角色,但细读文本,你会发现其实不然。作为纪实体小说,杨显惠说这些文本“细节是真实的,但故事是虚构的”,“符合小说的一切要素”,换言之,看似口述实录的故事其实是作者精心剪裁、组织的结果。所以故事的“记录者”看似不动声色,实际上通过人物、情节的安排和取舍,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生存观。
《上海女人》中的李文汉出身大资本家家庭,1948年高中毕业参军,在朝鲜战场“三根肋骨被美国人的炸弹炸断”,回国后在公安系统工作,后遭受一系列不公正待遇。为了不被饿死,李文汉讨好孔队长,毫无气节,但是他对宁肯饿死也绝不放弃人的尊严的董建义尊重有加:“他的文雅书生的样子在我的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董建义的妻子,一个文弱的上海女人,千里迢迢探夫,夫死则不顾一切殓骨还乡。面对同伴们的惨死,李文汉似乎已经麻木,但面对这样一个现代的“孟姜女”,李文汉却被深深的震撼,对这种坚贞的夫妻情分三十年后仍念念不忘。高吉义(《饱食一顿》、《逃亡》)自顾不暇但尽力照顾年迈体弱的牛天德,和有着“知识分子的高贵品格”的骆宏远情同父子,冒死带骆宏远出逃,一生为骆的惨死自责不已。王鹤鸣(《医生的回忆》)偷食马饲料,临走之时,却真诚地向马大哥道歉,一派儒雅君子风度。魏长海(《在列车上》)被提及当年食死人心肝的往事时“脸色涨得通红,难为情极了”,自觉“恶心”。杨世华(《邹永泉》)眼中的邹永泉“躺在被窝里吃着刘政德拿来的白面馍馍,并不掰给我一口”,但是却让人钦佩,因为邹永泉有原则,“他不为了多换点粮食而去损害别人”。地狱之中仍有人仰望星空(王尔德语:“我们生活在阴沟,但依然有人仰望星空。”),这些 “绝境中的受苦人”自己凭动物般的本能活着,但对真善美,对情义,对高贵人格,仍怀着渴望和尊重。
杨显惠具有真正的悲悯情怀,他尊重生命,为一个个无辜生命的毁灭而痛心,所以他理解当年那些右派们被绝境扭曲了的变态行为,理解他们出于生的本能而罔顾道德准则,所以从不在道义上对这些 “道德沦丧的知识分子”进行谴责和抨击。同时杨显惠又是一个坚守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作家。他说:“我在1990年代经过思考,决定继续走启蒙的道路,接过五四的薪火走下去,且努力使自己的作品更‘沉重。” “我为什么二十一年不改初衷,旨在张扬人性和人道主义情怀。”
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夹边沟记事》的扉页上引用了大江健三郎的话:“文学应该从人类的暗部去发现光明的一面,给人以力量,让人更信赖人。”这也可以说是杨显惠的文学理念。所以当李文汉们的生命之舟在伸手不见五指、狂风暴雨肆虐、巨浪滔天的苦海中随时都有可能颠覆时,杨显惠让董建义夫妇身上高贵的人性成为指引李文汉们的指路明灯。他相信人心向善,所以他在文本中多次写骨肉亲情、夫妻情义带给这些“绝境中的受苦人”的温暖与慰藉。《一号病房》里的妻子们和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一样伟大。《告别夹边沟》里王永兴的父母和妻子倾尽家里所有粮食送到夹边沟,父母年迈,妻子生病,但都是第二天立马回家,怕多住吃完了送来的粮食,亲人挨饿。 在这“变态”和“常态”人性的相互映衬、对比下,杨显惠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生存哲学:生存权是人的基本权利,但理性的、人性的生活是人人渴望并且应该拥有的。
三
杨显惠直言《夹边沟记事》的写作“意在翻开这一页尘封了四十年的历史,希望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并告慰那些长眠在荒漠和戈壁滩上的灵魂:历史不会忘记夹边沟”。同样是写夹边沟的历史,高尔泰的《寻找家园》是“知识分子的心史”,直指重压之下知识分子的精神异化,杨显惠的写作则重在社会政治批判。故事中人物的生存哲学和“记录者”即作者的生存观之间的张力,使这种批判力度得到强化。《夹边沟记事》中的右派虽说都是知识分子,但作者并没有刻意强调他们的社会身份,和《定西孤儿院》中的孤儿们一样,把他们当作特定时期、特定环境、特殊遭遇的一个群体,都是“绝境中的受苦人”。这些“受苦人”无一天生的人性恶者,他们的诸多“恶行”都是被不合理的外界环境所逼。身世显赫、学贯中西的王鹤鸣也好,因中学时一时兴起给最高领袖照片画胡子而成了“右派”,自认“既无文化又无思想”的席宗祥也罢,杨显惠一概以平视的姿态对待之,设身处地与笔下的人物同歌哭。他无意为作品中的人物贴上人们惯常加在知识分子身上的道德、文化、人性等方面的预设的“标签”。
在这里可以和丛维熙的《走向混沌》三部曲中的一个情节做一个比较,更能说明问题。丛维熙在第二部《梦断桃花源》“挖湖造山的记忆”一节中,借助劳改干部董维森的口,对和《夹边沟记事》中的人物遭际相同的知识分子进行了这样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式的谴责:“你们是人,又是人中的知识分子。……如果这些话,出自那些流氓、扒窃者之口,我用不着这么认真——你来自石油学院,是有文化有知识的大学生,怎么能这么说话呢?你讲了这话,实际上就是自我堕落!就是自我轻蔑!……一场大饥荒,饿丢了许多知识分子的自尊。”(丛维熙:《走向混沌》三部曲)这是典型的视知识分子为道德、文化、人性英雄的心态,而相当多的当年那场灾难的幸存者拥有话语权后,也往往以道德、文化、人性英雄自居,自认应当对历史承担更多的责任,所以在创作心理上试图以个人经历来代替集体、民族、国家的经历,以个人的命运来复现一场运动,映衬一个时代,反思一段历史。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这种“代言”与“自期”在读者尤其是隔代读者的眼中,往往显得虚妄与失真。而杨显惠显然认为在夹边沟这样一个“革命地狱”中挣扎哀号的这样一群人“是知识分子,又是人”,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体,是人子,是人夫或人妻,是人父或人母,是被不可抗拒的外力抛掷于此间,如陷阱中的困兽。一个个作为“人”的各异的个体却共性十足的“非人”遭遇,反复被渲染叠加,最终达到了对病态时代的控诉,对良知、温情等美好人性的向往与歌颂,体现了“健康而高贵的文学精神”。
杨显惠在《〈夹边沟记事〉写作手记》的结尾说:“我们关注前人的历史就是关注我们自己。”他的创作对于读者、尤其是后来者来说,的确是振聋发聩的警醒:切记不要让悲剧重演!
栏目责编:舒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