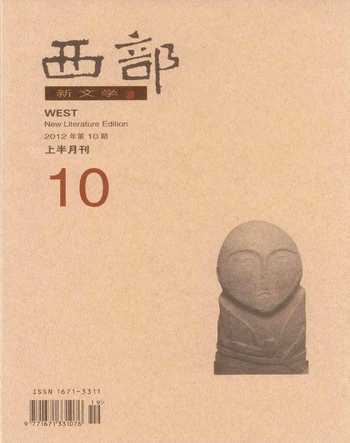裕子和李
李拿起自己的牛仔帽,捏了捏变软的边缘,把它立直后戴在硬扎扎的头发上。他垂下眼皮看了看自己脚上的破靴子,推测它还能支撑自己的身体走多久的路才不至于掉了底儿。正午的太阳直对着他,他的裤子被汗水浸透,皱巴巴地裹在腿上。离他曾经熟悉的小镇越来越近了,他甚至听到了稀疏的狗叫。李咽了一口唾液,他感到自己的喉头上下游移了一会儿,接着又安分下来。
李拖着皮外套走到小镇近处的大榆树下,旁边的木牌用手指的形状标识着镇子的方向,离他的目的地还有四点六公里。这是1932年的夏天,炎热而尘土飞扬的日子。李打量了一下四周,荒芜辽阔的平原上半个人影也没有,街旁一家供过路客人休憩的小酒馆门口站着几个妓女,皮肤晒成黑色,胸脯从长裙里大大地鼓突出来。她们默不作声地瞧着李,李却一眼也没看她们,他的眼睛因为极度的疲倦和渴望酒精而失去了流动的光彩。他推门进了小酒馆,迫不及待地想要得到片刻的休息。酒吧里被热气蒸腾出发霉的酸味,吧台上积着一层浮灰,圆凳全架在桌子上,看起来根本没有人经营。李把帽子在一根铁钉上挂牢,翻遍了整个酒橱才发现了半瓶威士忌。他双唇哆嗦着拧开瓶盖倒了满满一杯,用最快的速度把这发烫的液体灌进了食道,像马饮水那样急切。
李他妈的,到处罢工,斗争,搞得现在我什么也没有,穿着双破靴子,戴着一顶旧的发皱的帽子。我手里的这把枪,都他妈是贷了一大笔款子买的!我真是倒了大霉了!
李喝着威士忌骂骂咧咧,一条腿还跷在了柜台上。不过他的惬意持续了没有多久,酒吧老板撩开了挡板从后面走出来,他的身躯庞大魁梧,十个手指肥得像香肠一般,看得出来他对意图不付钱白喝酒的异乡之客们总是不客气地饱以老拳的。更糟糕的是他刚刚睡醒,胖脸呈现出发红的猪肝色。不过,李这样一个一无所有的流浪汉似乎根本没什么值得怕的。
老板嗨,谁允许你在我的地盘随便喝酒?你知不知道这和随地大小便一样,是违法的!
李宪法上哪条写了不许在小酒馆喝酒?只要你能找出我喝酒犯法的证据,我就把刚喝掉的全部吐出来还给你,保证量只多不少。
老板他妈的,你知道我是谁?
李他妈的,你知道我是谁?
老板 我他妈才不管你是谁,哪怕你是什么鼎鼎有名的史太格·李,喝酒也得经过我的允许。
永井裕子穿着厚厚的羊毛棉袜站在黑色的地板上,四周的墙壁把此处的空间同外界彻底隔绝开来,她头顶上方的剧场灯投下柔和而黯淡的黄色光,只有微尘在光柱里悄无声息地活动。这四下封闭的熟悉空间和黑色幕布给了裕子莫名的安全感,就像回到了母亲的子宫里。她微微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又缓缓呼出,她知道自己已从纷扰的感染中渐渐安静。
“现在开始吧!”从裕子的口里迸出生硬而咬字不清的汉语。
“真的有勇气去这么远的地方?”在动身的前一晚,裕子的丈夫从背后紧紧地抱住她,在她耳边问道。她躺在松软的被子里沉默着一言不发。她感到丈夫的手在轻轻地抚摸着自己小巧而精致的乳房,身体向她的背部慢慢贴紧,他的舌头和牙齿在若有若无地摩擦着她的脖颈,温热的气息水一样流淌过来。但她浑身上下的每一个毛孔里都充满了长途旅行前必有的疲惫和不安情绪,她把丈夫的手移到自己的腰上。
“对不起,今晚我需要休息。”裕子歉意地说。
丈夫的动作在黑夜里结结实实地停顿了几秒钟,接着就松开了她。裕子回过头去,看到他把一条已经长出苍老的褐色斑点的胳膊搭在额头上,遮住自己的眼睛。昏暗的月光从窗户缝隙里透过来,悄无声息地勾画出他身体在被子里凹凸的轮廓,像起伏的小丘陵。
裕子乘坐的航班飞离成田机场的时候,东京正在下雨,舷窗被雨滴划出一道道明亮的痕迹,她看着窗外撑着伞穿橙色工作服的机场工作人员招着手指挥配餐车停靠,心中便过早地生出了对这片土地的留恋情绪。离家远行的经历虽然并不是没有,但都是夏天时和丈夫一起开车去湖边度假,或者是应某个国际戏剧活动的邀约出游一个星期左右而已。她完全没有在一个陌生的国度独自生活整整三个月的任何经验。想到这儿,她感到一阵寒意突然袭上身,她把围巾重新在脖子上系得更紧一点,手深深地插进棉服下摆的口袋里。
航行还不到一个小时,裕子便吐了起来。她喝着飞机上配给的矿泉水,吃晕机药片,可是一点效果也没有。空乘人员把她安排在舒适的角落处,她这才感到自在一点。她极力忍受着胃部的不适昏昏沉沉地睡去,直到飞机着陆才醒来。裕子去拿托运的行李,在机场卫生间的镜子前端详自己的面庞,她几乎不认识那个虽然年轻但如此憔悴疲倦的女人究竟是谁。她抚摸着自己的脸颊,仔细地注视着自己的每一寸皮肤,直到身旁其他人开始对她投来奇怪的目光时方才罢休。
“一切都会好的,裕子。”她对自己说。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她被一个邀请方派来的女孩从机场接去饭店吃午餐,她的晕机症还没有完全好转,几乎什么也吃不下。紧接着,她又被带去咖啡厅见邀请她到这里来的剧团经理,咖啡的味道极其糟糕,而且是用冷水冲泡的。当裕子被告知当晚就要去剧场面试演员时,她感到自己的双腿开始微微发抖,她感到自己像一箱没有知觉和感情的货物,被各式各样的交通工具一刻不停地运送到各个地点。但除了听从安排,她似乎并没有其他的选择。
“真是个令人疲惫的开始。”裕子暗暗想,“这里的一切都和酒吧老板一样,没来由地令人厌恶。”
酒吧老板喜欢在喝得半醉时对厨房里的布置和老婆的针线活喋喋不休地大发评论,一旦遭到老婆半句顶嘴,他就会把她的肩膀揍到脱臼。对于站在他店门口的那些妓女们,他的态度也并没有变得温和一点。他似乎连同她们说一句话都感到厌恶,却总是盯着她们的大腿和胸脯,把她们推来搡去。他压根儿看不起女人。
说来也怪,李风雅的谈吐和多情的眼睛总是会轻易博得可怜女人们的喜欢。两年前夏日的傍晚,李同一个街头的雏妓相谈甚欢。他请她吃了顿便饭后,被她带到一间低矮潮湿的小阁楼里去,里面放着一条脏兮兮的床垫和两只绒毛靠枕。那女孩脱去自己的上衣,露出发育尚不完全的乳房和纤细的四肢,在李热切目光的注视下,她害羞而紧张地露出不自然的微笑来。
“我太瘦了。”她面带歉意地解释。
李像一个父亲那样吻了她,把她抱起来放在床垫上面,她轻得像一枚贝壳。在和她做爱的过程中,她不止一次地求李停一下,让她喘口气后再继续,李一言不发地顺从了她。第二天早晨李醒来的时候,发现她已经死了。李慌张地逃离了镇子,连告知妻子的机会都没有。两年后,突然掀起的罢工热潮让李丢了在外地好不容易谋来的工作,他只得回到他出生的这个小镇。他觉得自己是个杀人凶手,为了掩藏身份,他选择了牛仔的打扮。
老板听说史太格·李被老婆赶出家门,整整两年无处可归,现在不知道在哪里绝望地像条发情的母狗那样打转转呢!哈哈!
李(屏住怒气)只有愚蠢下作的人才喜欢拿别人的家事开玩笑。
老板他妈的,我说的可没有一句假话,你知不知道,有人还亲眼看到他跪下来乞求老婆放他进门呢!这样的傻瓜蛋方圆几十里也找不出第二个。
李讲话前先考虑一下,否则最好闭上你的嘴。
老板你这人他妈真古怪,难道史太格·李是你的小情人不成?
等裕子到了剧场门口时,她已经能听到里面传出的隐隐人声。她快速脱掉运动鞋,鞋垫因为长久的旅途跋涉已经变得潮湿。她把快要脱落的羊毛袜在踝部拉得更紧些,急急地推开门进去。剧场里顿时悄无声息,所有来面试的演员都把目光注视在裕子身上。但这难得的安静只有短短的一瞬而已,很快大家又开始了各自的交谈。裕子愣了愣,才意识到大家自然地把她的身份与他们自己的等同了。裕子反手掩上门,小心地选了一个角落站好,解下围巾折成三叠放在自己的包里。她环顾着四周,自在地松了口气。虽然踏上这片异邦之地已有十个小时,但令裕子感到舒适的时候却只有这一刻。
“我一定要挑选最有能量的演员。”裕子暗忖,此时她的嘴巴正轻微地发出几个单调的音节:“史太格·李,史太格·李…”她的目光在每一个人的面孔上浮动着,他们说话的方式,他们脸上变幻莫测的表情,在此刻都无一例外地触发着裕子心中那最敏感的部分。她试图把这个来自异乡的风尘仆仆的疲倦牛仔同在场的某个男性的脸庞产生某些关联,但是环顾下来却未能如愿。她闭上眼睛安静了几分钟,再看一遍后依然没有结果。裕子紧张兮兮地扯着毛袜子脱开的一条线,她的鼻尖上开始渗出汗来。
“是我把李想像得太过完美了吧。”她苦恼地摇摇头。
正当裕子绝望地准备开始臆想李的另一个形象时,一个男孩猛然推开了剧场的前门。他戴着一顶灰色的发皱的鸭舌帽子,蓝色的上衣领子软塌塌地吊着。他先是对里面的所有人投去不屑的挑衅一瞥,紧接着大摇大摆地走到舞台后场的角落,一屁股把自己掼到地上,起劲地嚼起口香糖来,看上去没多少绅士风度。裕子不动声色地注意着他的一举一动,一瞬间感到喉咙发紧。她一眼就看出了他的与众不同,他看起来似乎完全没有任何演出经验,像刚从河里捞出来新鲜活泼的野鱼,对裕子来说,他就像另一片不可接壤的土地那样陌生,但她从中感到了史太格·李所拥有的男性特有的粗粝、性感,和与之相关的一切品质。
李的突然出现是件和计划内完全不同的事情,这令她有些惊讶,也在最快的时间内消弭了她的疲惫感。她欣喜若狂,从人群里站起身。
“现在开始吧!”裕子高声喊道。
李竖起你的耳朵仔细听着吧,我他妈就是史太格·李!
老板啊哈!你不是在逗我开心吧!
李怎样,我知道你的脊背上正冒着冷汗呢。
老板恰巧相反,我为今天能见到你这头阉牛而欢喜不已。既然是你,就更没有在我的地盘喝酒的权利了。我这里只欢迎粗犷的野汉子,而不是像你这样扭扭捏捏的婊子。
李被一脚从椅子上踹了下来,事情来得太快,以至于他根本没有任何防备便跌坐在地上,地板发出一声沉重的闷响,细小的尘土飞舞起来。李抬眼看去,酒吧老板的肚子先挤进了他的视野,那人摇晃着硕大的脑袋,一绺黑色蜷曲的硬发挡在眼前,左肘放在吧台上,双腿交叉,脸色带着嘲讽,汗珠从他红鼻子的毛孔里渗出来,就像是河水源源不断地从冰上的小孔里涌出来那样,顿时,一股血液的冲击使得李的太阳穴隐隐作痛。他从地上爬起来,拍了拍被弄脏了的裤子。
李(语气沉静地)刚刚那杯威士忌值多少钱?
老板 五美分一杯,可是喝到你肚子里,这酒可就他妈的一分钱也不值啦。
李不管怎么说,我还是打算老老实实付账。
老板 哟,看来你还是个听话的婊子。
李钱在这儿,一分不多,一分不少。
老板 你不该让我认识你的,史太格·李!明天走在街上,小心你的屁股,会有人把它踢个开花的。
酒吧老板把硬币丢进上衣口袋里,伸手从柜台后面的某个隐蔽的角落里拿出一罐啤酒,咕嘟咕嘟一口气喝了个干净,伸出舌头舔了舔嘴唇上的白色泡沫,满意地打了个嗝儿。他的嘴里散发出浓烈的酒气和令人作呕的一股腌菜味。李屏住呼吸,伸手去拿那件冷冰冰硬邦邦的东西,他浑身的皮肤紧绷绷的,能感到筋脉的跳跃。
李恐怕你没有机会了,尝尝这个。
整条街道的商店大部分都打烊了,裕子在街的尽头转了一个弯就到了宾馆门口。从垃圾桶旁边走出一只猫,用眼睛瞄着裕子,它忽地蹿上屋顶,踩着铁皮发出一连串的声音,在寂静中显得十分突兀。裕子盯着猫消失的地方看了很久才开始慢慢地上楼梯。她掏出钥匙开门进去,顺便拉下日光灯的开关。房间被白光填满,裕子发现房间里单人桌的桌布被服务员换成了蓝白色的格子条纹。她坐在椅子上,开始想史太格·李的事情。
“以前我从来没有进过这样的地方。”鸭舌帽男孩说道,每一个字像是急急忙忙地从他的双唇之间冲出来似的,“只不过是偶然看到了剧团贴出的通知,就想来试一试,我可没有任何演出经验。”
男孩说话时,眼睛一直保持着垂下的姿势,裕子根本没有找到和它们对视的任何机会。裕子看到男孩的鼻梁旁边有一处很深的瘢痕,被剧场里的灯光照得发亮,所有人都会在第一时间内注意到他五官的不完美。
裕子突然发现自己对其他几个选定的演员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兴趣,她打了个哈欠,转身倒在松软洁白的床上,她盯着天花板,慢慢地,她好像也置身于那棵树的荫凉之下,小镇的天气热得令人真切地感到痛楚,她的耳朵和鼻子里全是尘土,就在她即将要陷入因暑热而带来的迟钝的那当儿,李扣响了扳机。
爆炸般的声音在小酒馆里响起时,树下站着的所有人都被结结实实吓了一跳。她们面面相觑着沉寂了片刻,便闭紧了嘴纷纷离开,向小镇的方向匆匆走去,只剩下一个还留在原地。这个穿着宽松的白色大睡衣的年轻妓女定了定神后走出树荫,她在刺目的阳光下把眼睛眯成一条线,乳头在衣服下微微凸起,就像两颗小豌豆。
妓女走到酒馆的门廊下面,窗户上的木框摇摇欲坠,她小心地把脸凑近,留神不让自己发出任何动静。她看到李的手指颤抖着,好不容易才把那柄枪再塞回自己的口袋。酒吧老板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发黑的血从他的脑袋里淌出来漫到地板缝里。她看着李拧开威士忌瓶盖,小口小口地喝酒来平稳情绪,便砰地一声推开了酒馆的门。
妓女 你就是史太格·李?
李没错,还有一个名字叫杀人犯。
妓女 你可知道我是谁?
李(看了看她)我当然晓得你是谁。只消掀起你的裙子,你的名字叫天堂。
妓女 凶杀和性爱是连体婴儿不可分割,瞧你方才怒火冲天,想来已经很久没有享受过男女之事了吧。
李你的洞察力还真是敏锐。
妓女 只有那最原始的释放才能使人的无名火真正消散的。
鸭舌帽男孩离李的形象似乎越来越远,他经常会在排练时因为裕子简单的一句请求一跃而起,在场地里大吼着转来转去,脚踏着地板啪啪作响。裕子从未见过一个人可以如此愤怒,这种阵势令她吃惊而不知所措,以至于经常连说第二句话的勇气都没有,只得老老实实地跪坐在地板上,双手叠放在膝头,满心希望他那不知从哪儿来的怒气快些消散。
戏的进度因为男孩的缘故变得越来越慢,剧团经理很明显地对此表达出不满,其他演员也开始对裕子颇有微词,排练时的气氛就更加僵得发硬。有一次,裕子试图用音乐来缓解些尴尬的情绪,没想到反而激起了男孩的怒气,他大步走上前按下停止键,夹杂在空气里软绵绵的日本歌声就此静寂了。
和男孩相处两个月后的一个下午,裕子给在日本的丈夫打了电话。
“他是我见过能量最强的演员,”裕子轻柔地告诉丈夫,“可是他不会把握自己波动太大的情绪,以至于我没办法掌控局面。”
“换掉就好了,”电话那头的声音不带一丝感情,“目前看来这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可是只有他才能胜任这个角色。”裕子不依不饶地说。
“你总是爱做有风险的事情,”丈夫冷冰冰地回答,他的声音从遥远的彼岸传来,显得愈发苍老,“如果你坚持这样,只能自己想办法处理。”
丈夫的话让裕子哑口无言,她恹恹地挂了线,在路上被晒得发烫的长椅上坐了半个小时,直到日落才起身回去。裕子感到自己完全沦入了孤独的深潭。
妓女 你刚才的那四枪不仅打在他头上,还打在了我的心上呢。
李(哈哈大笑)真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女人,我现在可是个杀人犯呢。你最好放聪明点,快些报警吧。
妓女 为什么不到我的小屋里去坐一坐呢?
李我他妈一分钱也没有。
妓女 今晚不要钱,就算我送你的一份礼。
“那些男人们有的在镇子上做官,地位高得怕人,有的是做房屋买卖的,有大笔大笔的款子,有的是学校里不苟言笑却受人尊敬的教师,他们无一例外地总会在夜色降临时一步步爬上我的阁楼,敲开我的门,像条炎炎夏日里的狗那样不停地喘粗气。他们表面上道貌岸然,一本正经,在我的床上却胆小得像只老鼠。曾经我还单纯地希望能够和他们这样的人多交谈些,可他们根本不懂得女人,他们在我的房间里大口地吃煮鸡蛋,在我的卫生间里一遍遍地洗澡,好像要把我沾染在他们身上的气味完全去除似的,他们在卧室的床上抽烟,烟灰掉在拖鞋里。我厌恶了这些恶劣的行径,厌恶了他们做爱后完全不顾我的感受酣然睡去,厌恶了他们到我这样一个女人的家里来还要冒充卫道士的虚伪。”妓女暗忖道。
在她的视线捕捉住李的那一刹那,便决定他才是自己的床榻真正欢迎的对象。
妓女 我最喜欢的,就是让一个双手还淌着热乎乎鲜血的杀人犯带着暴力掀开我的裙子。
在裕子打开门请男孩进屋的那一瞬间,她还在犹豫自己接下来决定要做的事情是否正确。她请男孩坐在桌子前,等她端着一杯水从内间走出来时,她看到男孩正默默地盯着她晾在窗户外的胸衣瞧。注意到她的目光时,男孩有些不自然地微微涨红了脸。此时的他突然收起了所有咄咄逼人的锋芒,像一个幼儿园孩子似的那样拘束起来。裕子搬了一把椅子坐在男孩对面,房间里的床单洁白干燥,氤氲着暖呼呼的奇异舒适气氛。
“想知道你对女人的看法。”裕子说。
“我?”男孩下意识地重复道,他看了她一眼,不自然地晃了晃身体,像被人打了一下似的。
“没错。”裕子肯定地微笑着。
男孩惊讶地把眼睛睁大了,他神经质地把食指和拇指搓来搓去,声音很小,像是在对自己说话似的:“没什么看法,我还没交过女朋友。”
“那么对我的看法呢?”裕子接着问,她的身体微微向男孩的方向前倾了一点。
“你是这出戏的导演啊。”男孩说。
“不仅仅如此。”裕子坐直了身体,“我今年三十六岁,十年前接触剧场,从那时开始我就成了永井导演。不久后,我嫁给一个医药产业的商人,他比我大整整两轮有余。我悉心地照顾他,算得上是个好妻子,自我介绍时便常把自己称为山崎太太。但更重要的是,我是永井裕子,是一个女人。”
男孩闭紧了嘴巴不再出声,制暖器在墙角发出咝咝的声响,时间好像悄悄地沉静下来。就在这时,裕子开始一声不响地拉开套裙的拉链。她把身上所有的衣物都脱下,整齐地叠好放在床边。在此过程中,男孩的视线一直凝聚在他们脚下磨得起了球的劣质地毯上。裕子站起身来,她用自己的腿轻柔地碰触男孩的膝盖骨,她看到男孩的喉咙动了动,他鼻腔里呼出的热气传到她的肚皮上。他抬起头,开始像赏鉴一件难得一见的艺术品那样上下端详起裕子来,裕子扶住他的肩膀,任由他的目光在自己赤裸的皮肤上移动,很快地,男孩就像通了电似的浑身发烫,颤抖起来,他笨拙地把唇吻在她的肚脐上。
“导演,你真美。”男孩说,他的声音在裕子听起来像是从遥远的水里传来那样含混不清。
妓女 你是否愿意随我回家?
李乐意之至。
妓女 (笑吟吟地)好呀,但是你动作要快些,比利·迪利快要回来了。
李(阴沉下脸)谁他妈是比利·迪利?你这不要脸的女人,竟然想要在两次嫖娼之间抽空与我欢愉?嗨,你弄得我完全丧失了想要和你同床的欲望。
妓女 不,亲爱的你别误解,鞋匠比利他是我丈夫。
李(惊讶)丈夫?你有丈夫?
比利·迪利是个严重的酒精和尼古丁依赖者,他的右脸上有一道长而深的疤痕,连带着整块肌肉都变形了,浮肿的皮肤下透着青色的毛细血管。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异乡人,到镇子来不到半年的时间就娶到了妻子。她告诉他自己在失业前在一家小酒馆做帮工。她漂亮温柔,而且出人意料地会用种种办法来安慰和取悦他,对他的种种劣习也总是宽容有加。比利爱极了这个娇小可爱的女人。不久比利在镇上开了家鞋店,生意兴隆。他戒了烟,醉酒的次数也开始减少,他把功劳都归结在伴随了自己几十年的好运气身上。
比利的好运气用光的那天,他穿着一件烫过的笔挺正装去出席朋友的婚礼。不知为何,他在饭桌上郁郁寡欢,连跳舞也提不起兴趣。他放弃了在朋友那里留宿的打算,连夜乘长途巴士,天黑之前就回到了家。透过客厅窗户,比利看到另一个男人在自己的妻子身上慢慢下沉,就像两滩发粘的蜜糖融入对方。比利捏紧了拳头,感到怒气从钥匙孔里源源不断地灌进去,几乎要点燃原本就灼热不堪的空气。他想把那人的头砸得粉碎,想把自己妻子的喉咙割断,直到她身体里最后一滴血流尽为止。
“可他没有这么做。”某个午后,妓女坐在凉爽的餐馆里对请她喝咖啡的银行家说,“等那人走后,他冲进门把我狠狠打了一顿,后来他知道了我两年前的真正行业,就逼迫我重新做起了这门生意。”
妓女抖抖烟灰,她并不愿意谈起此事,可是每个到她这里来的人似乎都要津津有味地听上一遍她和比利的故事才算罢休。
李哈,我倒想看看他女人在我身下呻吟的时候他脸上的表情呢。如果心情好的话,而且时机也算得上合适,我还能让他也结结实实地痛快一次。
每天排练完毕后,男孩都会到裕子的住处去,裕子深知他身体中的男性力量已被她用女性的阴柔气质调和,不过她仍然惊异于男孩迅速的变化。他讲话的速度开始变慢,声音变得稳重,他学会了沉默,耐心也与日俱增。她和男孩在排练场里也达到了惊人的默契,裕子的话他无一例外地全部顺从,有时,他甚至能够理解她的一个眼神所代表的全部含义。
“难以置信。”裕子在排练时总会这样不由自主地喃喃自语,她目不转睛地看着男孩安静地坐在剧场的一角休息。男孩抬起头顽皮地向她眨了眨眼。裕子温和地笑了,一种缓慢流淌的爱意夜幕一般笼罩了她的全身。
预演前一日的寒冷下午,裕子拥着男孩赤身裸体躺在宾馆的床上,她头顶上方是半开着的一扇小窗,贴着红黄色镂空图案的贴纸。窗外是这个城市最繁华的一条街道,街上源源不断的声音就从那缝隙里挤进来,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裕子抚摸着男孩的后背,伸了个懒腰,把自己的身体放平,她感到男孩俯身过来亲吻了她的耳朵。
“我爱你,裕子。”男孩在她的耳边低声说。裕子笑了笑,伸出手去抓挠着男孩的头发,有些心不在焉。她的所有思绪都被明天即将到来的演出填满了,从早上开始她便在脑海里一遍遍重放排练场的画面。裕子把手放到胸前合上眼睛,轻而长地吐了口气。
“你的丈夫对你好吗?”男孩拨弄着裕子脸颊上的头发问道。
裕子抬眼看着他,感到自己紧绷着的神经因为他的问题而放松了许多:“我的丈夫他很爱我,我们彼此的私生活并不互相干涉,所以相处得还算融洽。他工作很努力,每天有很多计划,早些时候他还会出国去,不过最近几年就常呆在家里……”
“你并不爱他。”男孩突然打断裕子。他的口吻是那样肯定,以至于连裕子都有些吃惊。她睁大了眼睛带着些真正的怒气瞪着男孩,男孩却只是静静地回望她,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裕子的脸有些泛红,她想说些什么话来反驳,但很快又垂下了头。裕子知道男孩说的话就像飞镖正中靶心那样准确,可是这么多年来,她似乎都没有勇气承认这一点。
比利 你他妈就是史太格·李?那个被女人扔出家门的史太格·李?
李啊哈,你就是比利·迪利?那个臭烘烘的鞋匠?
比利你要为你方才说过的一切付出代价。
妓女 比利,相信我,他并没有恶意……
比利 (把妓女推倒在地上)闭嘴!廉价的女人!
李谩骂女人时男人总自以为是,妄自尊大,殊不知那是蠢货才做的事情。
比利 你这条公狗,你有什么权利在我老婆面前讲这些话!
比利伸手给了李一记重拳,李轻松地躲过,李掏出枪把比利射倒。这一系列动作都是在很快的时间内完成的,就像是一首流畅的小诗歌那样完全看不出任何刻意之处,仿佛是在跳一曲天衣无缝的舞蹈。
李(对妓女)亲爱的,现在我们可以毫无障碍地进入极乐世界了。
舞台上的灯光暗了又亮,裕子屏住呼吸在黑暗里看向四周,所有的人都静静地发出呼吸声,她把冰冷的双手放在自己滚烫的面颊上。这里像是异度的空间,空旷,静谧,仿佛只有她一个人。舞台上的灯光像刀子那样令人难过,空气里除了热烘烘的味道以外什么也闻不到,气压低得惊人。裕子突然对这里产生了些微的恨意。似乎等了整整一个世纪那么久演员才谢幕完毕,剧场里爆发出一阵掌声,飓风刮过田野一般迅猛激烈,像一波巨大的海潮那样从裕子头上席卷而下,她感觉自己像一片羽毛那样轻地在这人群中浮了起来。有的人开始欢呼。裕子被男孩请上台去,舞台上白色的灯光直刺向她的眼睛,她看不清观众的表情。
“谢谢。”裕子用微弱的声音说,这声音被台下的掌声淹没了,她频频向观众席鞠着躬。等她终于直起腰来时,男孩便伸出手来搂住她的肩膀。她的小臂紧紧地贴着他的右侧身体。她抬起头,男孩饱满的微笑着的嘴唇就悬在她上方。
“结束了,”裕子在心里默默地对自己说,“我要回日本了。”想到这儿,她努力止住的抽噎突然失去控制,身体开始有节奏地颤抖起来。裕子把自己的脸埋在手里,她模糊地意识到自己的哭泣并不是任何欣喜的表示。
自那晚起,裕子就再没见过剧团经理,她辗转从他那里得到了一笔钱,数目少得可怜,但她丝毫不以为意地把信封塞进包里,礼貌地转达了谢意。裕子已经把自己的机票改签了两次。终于,她打电话给丈夫告诉他自己的返程日期,并礼貌地拒绝了他开车去接机的邀请。
“我想自己一个人回家去。”裕子淡淡地说。与此同时,男孩正温柔地拨开她的大衣领子,亲吻着裕子的后脖颈。
随着裕子离去时间的临近,男孩也越来越沉默寡言,他变得是那样了解裕子,连她表情的细微变化都能够捕捉得到。他尽量不在裕子面前表现出任何的悲伤。白天,他会兴致勃勃地和裕子谈起他们的成功演出,陪她去市场买东西,一刻不放松地挽着她的手臂,沐浴时帮她梳长而黑的头发,甚至帮她挑选衣服。可有时候裕子晚上醒来时,会发现他正用两只手把上半身支撑起来,在黑夜里直勾勾地盯着某个角落。
“你改变了我,裕子。”启程的前一晚,男孩和裕子并排躺在床上,他捉住她的手,“我本来以为自己会对这个世界无动于衷,是你让我发现生命中其他的可能,教我成为一个男人。”
裕子听着男孩的话,她微笑着点头,嘴唇却微微哆嗦着,一种说不清的失落渐渐袭卷她的全身。她彻夜未眠,两次去替男孩盖好被子。天刚亮时,裕子便动身离开宾馆,男孩脸朝下埋在枕头里还在熟睡,赤裸的身体随着鼻息一起一伏。
裕子把门关好,走上清晨寒冷的柏油马路。一股炽热的水蒸气似的东西冲到裕子的喉头,泪水使得她看不清楚东西,所有的物体都在她的眼前渐渐融入了白雾之中。从此以后,不会有任何一个人愿意主动和她谈论他的童年,也没有人会从窗户跳进屋子,从那与众不同的通道来访问她,逗她开心,也不会有人用那样长久的时间抚摸自己的脚,更不会有人在嘴里散发着淡淡的炸鸡味道时来深深地吻她了。在裕子的臆想中,倒在李枪下的那个人变成了自己的丈夫,他布满皱纹的面颊歪曲着,血从牙齿缝里流出来。她想知道李和妓女今后的命运,可那却不是剧本里的内容。
突然裕子身后传来运动鞋拍击地面的声音,她的手心瞬间被汗水浸湿了。她在原地站了几分钟,脚步声离她越来越近。她转过头去,一个穿着鲜艳颜色运动装的女孩从她身边跑过。裕子愣愣地目送她离开,接着又向身后街道的尽头望去。裕子盼望着李,就像是1932年夏天那个寂寞的小镇和树下的妓女们盼望着他的到来一样。在这一刻,裕子才意识到自己有多么爱他,爱这个比她小整整十五岁的男孩。可是整条街上除了几声狗的吠叫之外什么也没有,那里寂静无人,就像是一列空空荡荡的车厢,而裕子则是唯一的乘客。
刘天涯,女,1991年生于江苏徐州。现就读于南京大学文学院戏剧影视文学系,大四学生,部分作品在《山花》、《西部》杂志上发表,小说《一个女人的终结》被《中篇小说选刊》2011年第6期选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