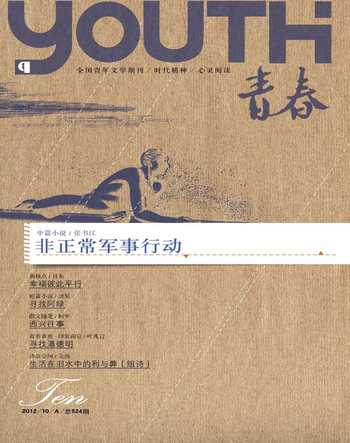亲密的陌生人
吴幸
97路的车厢里永远挤得满满的如腌制鱼肉般。
一个肉呼呼的脑袋贴在了思琪的脖颈上,令思琪感到心里凉嗖嗖的,她扭过头去,看到了一张中年男子的猥琐的脸,嚷道:“大叔,脑袋还能让一让啊?”
那人说:“只要能让我还不让?你来告诉我怎么个让法吧?”
那人也被另外的人挤得如卡着一般。
水生没说什么,伸出手使劲将那人推了推,然后将自己的身体隔在中年男子和思琪的背之间,这一来,他伸出去的左手便如同将思琪揽在怀里似的。他手心里的热量驱走了适才的凉意,又忽地涌进思琪的心。她白了水生一眼,水生面部没什么表情,眼睛里却有一股压抑不住的得意和兴奋,思琪心想,你倒会占便宜。但在水生的手臂有力的环护下,又分外有一种安全和踏实。思琪甚至有些想把脸贴过去,贴在他宽厚的胸膛上。
水生仿佛猜出了思琪的想法,低声问思琪:“想什么呀?”又不觉将思琪朝自己怀里紧了一紧。
思琪未挣扎,只是以极快的速度回答说:“在想当时你把阿梅搂在怀中时心里正想着什么。”思琪说时,心里忽地涌出一片片的烟花,那一夜的烟花开得分外灿烂,如云如霞,像一幅铺天盖地的工笔画,一丝一缕被刻在脑际间,永远也难以消散。
思琪的话刺痛了水生。因为公共汽车上这个偶然的环境给水生带去了亲近思琪的机会,又因为这个机会使水生内心一种潜在的欲望在急剧地膨胀,叫思琪的这根刺一扎,一切都在瞬间泄了个干净。水生的脸色立即变了,他苦笑了一下,然后黯然伤神地望着窗外。水生不再说什么。
思琪并不觉自己的言重,她见水生如此反应倒有几分快意。思琪想,难道你还想回过头来向我谈情说爱么?
公共汽车在嘈杂的轰隆声和车内的叫喊声中蹒跚地朝前开。思琪不喜欢她和水生之间的这种沉默局面,她觉得这样好造作、造作得像小说里写的那样。于是捅捅水生,继续说些有的没的。
车到了站。
在水生去取自行车时,思琪站在车站的遮阳棚下,看着烈日下水生的背影想,我难道真正不再爱水生了吗?那为什么我又是那样地爱和他在一起呢?为什么我对别的男人提不起兴趣呢?如果是爱他又为什么每当他想要亲近我时我就无端会生出一些恨意呢?那一刻我又何故对他一点兴趣都没有了呢?
思琪时常地觉得自己好像是个赶路的人,走走走,走到一个要紧的路口时,却突然地对赶路没有了兴趣。
思琪想,水生你那时候为什么那么轻易地将我忽略了呢?
先前,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骄傲的南京女孩,思琪,是那么地羡慕水生,羡慕他的聪明,羡慕他清新的泥土的气息。他来自乡村,却又异常的整洁和文雅。他的机警和幽默几乎就要掩盖掉他的原始的村落的痕迹了。水生在思琪心目中是一个很完美的形象。有别于其他所有的男生。
不太大的校园里,男女宿舍却相距二十分钟的路。每逢自习到很晚了,水生总是将思琪送回宿舍。那一路,思琪总是很活跃、很高兴。她同水生辩论、斗嘴,亦很真切地聊天,水生也是。两人一路,几乎不停嘴。只是分手时,思琪感到很怅惘。水生从来不肯走近16栋的楼下,他从不肯说为什么。其实思琪知道,他不愿撞见楼前一对对搂搂抱抱的男女们。水生和她谈了很多的话,议论了很多人事,却好像根本没谈到地方,仿佛还有最重要的内容迟迟未曾涉及。
但凡下雨的日子,思琪总是和水生共打一把伞。水生高高的个子如一棵树,思琪在他的树荫下感到十分的安全十分的温暖又十分的不是滋味。
他们从来没有碰一碰爱情这个话题,从来没有。甚至,两个人,思琪这么觉得,都在躲避着它。
现在想来,水生当时若痛痛快快地提出和思琪交往,思琪一定会满口答应,而且会感到快乐无比。因为思琪在心里是那样地喜欢水生。
但是水生什么也没说。
水生后来解释说他很自尊同时也很自卑。而思琪总是无所谓的样子。水生觉得像他这样农村家庭的人是配不上思琪的。思琪从没对水生的暗示作出应有的反应,水生想思琪自然是不同意这事,又不好明言挡着,免得失去一个朋友。水生说他便不再作此幻想,也不愿说明。水生也唯恐失去了思琪这个朋友。
思琪能怎么说呢?思琪有千条反驳理由,但思琪没说。思琪也觉得自己太矜持太自尊,非要等看水生明目张胆地追求才肯认账。思琪一直认为,既是暗示,便有可能是别的意思。思琪常常想,我不要你手捧玫瑰站在16栋下倾诉衷肠,一句“我爱你”总会说的吧。
然而思琪完全错了,错了的还有水生。
思琪想她是和水生在彼此能听到对方心跳的时候沉默不语的。于是两人只好擦肩而过。思琪每每想起这些,都忍不住一阵伤感。
和水生同乡的阿梅和思琪一个宿舍,把他当成亲人一样依赖。昨天某某买了多少多少钱的包包,今天某某的男友送了多贵多贵的礼物,这些百说不厌的八卦夹着土腥味的乡音,让水生想起一家人端着碗围在炕上“呼啦呼啦”地喝粥的情景,妈妈在一旁念叨着东家长西家短。想起那时昏黄的灯光,就让人心头一暖。每个周,总有那么几个下午,水生会陪她坐坐、聊聊,一天,他忽地觉出阿梅那双秀丽的眼睛充满了热烈和渴望。
半夜,水生走在校园的街道上,回味着那目光,心想,这是怎么回事?
后来,阿梅便常去水生那儿,并渐渐地帮水生干活儿。不是洗被单便是抹窗户。有一天阿梅洗被套时洗得满头大汗,便脱了春装,紧身的廉价T恤将她的身子裹得线条十分清晰。水生进来时,阿梅正立起身子用手背擦汗,她挺挺的乳房便呈现在水生面前。水生好一阵冲动又一阵感动,水生想这样一个女孩子对我好,我还有什么不满足呢?水生异样着叫一声“阿梅”,便冲了上去。
很自然地水生抱住了阿梅,而阿梅也抱住了水生,两人也很自然地说了些“我爱你”之类的话。那情话变成呓语时,水生便吻了阿梅,阿梅的嘴唇湿润饱满,吻了许久,两人便情不自禁地上了床。两人都是头一次吃禁果,紧张和急切中将水生床上的床单弄得一塌糊涂。
吃过晚饭,阿梅走了,水生一个人坐在床上,问:“这就是你要的吗?”
“不,是我比思琪差。我没什么权利挑思琪那样出色的女孩子。”
黑暗中,水生叹了一口气。
水生没将他和阿梅的事告诉思琪,虽然水生差不多还像以前那样同思琪交往。水生想就这么和思琪保持一种纯洁的友谊关系也不错。他没好意思开口告诉思琪这个朋友他已交了女朋友,他也没料到这件事将思琪伤害得那么深。水生想,我要晓得你对我有这份感情,我要晓得你不会看不起我,我又何苦把心思放在阿梅身上呢?水生好是懊悔了一阵。但那一阵过去后便平静了。对于自己,阿梅或许更合适些。阿梅能关照和体贴你而思琪则需要你随时地宠着她。
“水生,你自以为自己很聪明,但你却办了件最蠢不过的事。”小时候,母亲就这么教训过水生。
水生初始不以为然,觉得母亲是出自一种偏见,直到后来,水生才晓得母亲的判断是何等的正确。
一天正午时分,水生随便寻了家餐馆,点了一碗盖浇饭。水生在吃饭时,发现了一个女孩挽着一个小伙子从餐馆门前走过。水生的心忽地往上提了一下。他恍惚看出那女孩是思琪。水生不觉有些忙乱。他三口两口吞下了饭,顺着女孩和小伙子去的方向追上了前。水生满心不是滋味,他大步追时甚至不知道自己追上了又怎么样。实际上水生走近那两人后,才发现女孩根本不是思琪。只是穿了同思琪相同的裙子,个头又差不多而已。水生将自己嘲笑了一番,又回餐馆门前取自行车。
水生在用钥匙开车锁时,仿佛觉出他在突然间明白了思琪是怎样的痛苦。那种痛苦刚才在他大步追别人的三分钟内他尝到了。
终于在放弃了思琪之后的某一天,水生明白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东西被他放弃了。他力图寻回这失去的,可思琪却时刻警惕着。
思琪说:“你想叫阿梅日夜笑话我,说我捡了她不要的吗?”
水生被思琪的话扎得灰溜溜的。水生知道思琪这个骄傲的女孩子,为维护自己的自尊心,可以放弃一切。
那天思琪拉了阿梅在校园里散步,这个细声细语的乡下姑娘突然间强大起来了,说:“我看出来了,其实你爱水生。”然后又说了请思琪放过水生,不要再缠着水生,她和水生已经在一起了。思琪没弄清这意思,不由重复了“已经在一起了”这句话。阿梅便红着脸说:“就是我们已经一起睡过了,做爱,你懂么?”阿梅说出这话后自己有几分兴奋,便又忍不住详细地说了水生怎么和她相爱怎么拥抱她又怎么温柔地吻她。阿梅说他们吻了很久很久,后来她便不行了,水生就把她抱到床上脱光了她的衣服,水生自己也脱光了……阿梅絮絮叨叨,很精细地讲了水生和她怎么经历了人生第一次做爱。虽然电影电视上看了不少,但是思琪还是听得毛骨悚然。阿梅说完那一切时,她们已走到了16栋门口。思琪一回头,漆黑的夜空中,一大片的星星正亮得十分粲然。
思琪第二天没去上课。思琪不曾质问水生,思琪想她是没权作这种质问的。思琪只是觉得自己的心疼,疼得彻骨。三天之后,水生在思琪的眼里便是另一种色彩了。
思琪讲述完时,水生不再说什么。
水生羞愧满面。他低下了头。却看到了思琪涌满两眼的盈盈泪光。
水生踟躇了一下,还是说了:“我不介意你爱不爱我,你尽可以去爱别人,但是我请你允许我爱你。”
水生的话非常温柔,思琪的泪水便淌了下来。水生呆呆地望着思琪,心说我是这样的人吗?
水生像思琪忘不了那烟花一般忘不了思琪那一刻呈现在脸上的忧伤。
思琪好久没见到水生了。虽然思琪觉得此生此世都不会同水生结婚,但思琪却摆脱不了对水生的依恋。这份依恋是时光累积而成的。依恋越深时痛苦愈重,而表面上,思琪却永远摆出副满不在乎的架式。
思琪面对阿梅和水生的爱情,很长一段时间表现得镇定自若。在人前,谁也看不出她受了什么伤害。有人问她:“思琪你怎么同水生吹了?”思琪总是落落大方地答说:“什么呀,我从来没有跟水生在一起过,我们只是一般的朋友。你不信问水生。”水生便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对不住思琪的。水生想幸亏不曾贸然向思琪开口,要不然叫她挡回来就太难堪了。这是水生后来跟思琪说的。
但思琪在单独和水生在一起时,却掩不了自己内心的激愤,无法做到依然故我。思琪得费很大的劲才能压抑住随时会夺眶而出的眼泪。为此思琪极力地回避着水生。
思琪冷淡着水生,水生感觉到了。但水生却认为这是思琪因他有了女朋友,怕同她接触多了阿梅会不乐意之故。水生只是觉得思琪十分地善解人意。一直到几个月后的一个晚上,水生才明白不仅仅是这些。
那天水生和思琪又在自习室里遇到,又是很晚才离开。水生仍像过去一样送思琪回宿舍。思琪不再像过去一样喋喋不休地说话了。水生好奇怪,有意识地寻找话题。但是两人之间的沉默像一只贪吃的怪兽,怎么也喂不饱。
水生说:“你怎么啦,怎么啦?”
思琪说:“没什么。”
水生说:“是不是我不小心得罪了你?可我好像没干什么呀?”
思琪说:“你当然没有得罪我,再说就是得罪了我又算什么呢?”
水生说:“那你怎么对我这么冷淡?”
思琪说:“好笑,我们不过一般的朋友,有什么冷淡或者热乎的。”
水生说:“这可不像过去的你。”
思琪说:“你未必就还是过去的你么?”
水生说:“你的话好像句句都是冲我而来的,我不明白。”
思琪说:“是的,你是不明白!你天下这样聪明的人还会有不明白的事?你只是会装而已。你装得比谁都像。装得比谁都真。我恨你!恨你!”
思琪终于还是暴露了自己。她泪雨滂沱泣不成声。
而水生,却一下子沉默了。水生意识到他做错了一件事。思琪的眼泪告诉他这个女孩对他的爱心。
水生犹豫了好半天,说:“思琪,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我只是觉得我不配,我没有资格爱你这样的好女孩。”
思琪仍哭泣着,只是不断地冒出“我恨你”这三个字。
水生一路无语地将思琪送到16栋楼下。水生心里有些乱,但这乱劲很快就过去了。
思琪同样在第二天见到水生时如没事一般。但是他们的交往显得很不自然了。终于有一天,思琪同水生没有话说了。彼此路遇也至多相互一点头示意。有时,连这种示意都没有。只是这是水生和思琪之间的秘密,仿佛是一种默契,思琪和水生都不愿让旁人晓得他们之间的紧张关系,在人多时,大家混杂一起说笑,仍似往昔一般自如。
日子就淡淡地顺季节走了下去。思琪在拼命地掩饰自己心里的痛苦而作一副洒脱状时,渐渐越做越真了。仿佛习惯了眼前的事实。沤在心里的痛苦也逐渐麻木了。水生又算什么呢,思琪想,只不过这堆人中就他独特一点罢了,换上一群人,未必没有比水生强的。只不过我现在还没遇上而已。思琪反反复复作此一想,便活得轻松和从容多了。
但是思琪注意到了水生的沉郁。水生有好长一些日子落落寡欢,也没见他和阿梅双出双进了。人们纷纷传说阿梅和水生吹了,是阿梅提出的,思琪懒得听这些议论。思琪想这与我不相干就行了。
后来,大四快分别了,到处都弥漫着树倒猢孙散的伤感。那天,水生望望思琪,思琪装作不认识他。水生便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烟、撕下那烟盒,匆匆地写了几个字在上面。水生朝思琪走去,他将烟盒递给思琪,思琪迟疑了一下,还是接了过来。
思琪展开烟盒,看见了上面的八个字“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水生下笔很重,“何”字重重的一竖,叫他写破了纸。
思琪的泪水又忍不住往外涌。
水生很是自然地将思琪拥入自己怀里。用大手掌抚着她的头发她的面孔,说:“我在别人面前都说我认识的最聪明的女孩就是思琪,其实,我在自己心里总是说,思琪是天下头号傻瓜。”
思琪流着泪说:“为什么?”
水生说:“你最喜欢干的事就是狠劲地折磨自己,然后再折磨你最爱的也是最爱你的人。”
思琪把脸贴在水生的胸脯上,一任眼泪哗哗地流。思琪能听见水生“怦怦”的心跳。思琪感到很温暖很舒服。
水生的手臂使上了力,它们钳得思琪骨头都疼了。水生反反复复地吟着:“思琪,思琪,你是我的,是我的。”思琪在水生的声音中觉得一切都恍惚而迷醉。
思琪那天在水生那儿呆到很晚才走。水生送她回家时一直用手臂揽着她的肩,思琪将头靠在水生身上。思琪生平第一次和异性一起度过这么亲热的一个晚上。而实际上,水生几次用嘴唇去吻思琪的唇,都叫思琪避开了。
在回宿舍的中途,思琪和水生都同时看见了矗立在远处的楼群。那所有的房间都亮着灯,在暗夜里十分地醒目。水生和思琪的心几乎都缩了一下。水生的手臂上又加了一些力,而思琪却在那一刻惊恐地跳开了。一片很大很大的阴云迅速地覆盖了思琪的心,思琪仿佛看见,在那阴云之上,如火如荼地开放着无数艳丽的星。思琪嘶声喊出了一个字:“不——”
思琪那一声“不”字的悲哀,使水生觉得刚刚织成的一个梦幻又在瞬间里破碎了。
思琪开始朝16栋的方向奔跑了起来。水生愣了一下,追了上去。水生急切地喊道:“思琪,思琪,你等等,你听我说。”
思琪却叫着:“不,不。”一直往前跑。
几百米之后,水生追上了思琪。水生抱着她,想使她安静。思琪却不停地厮打着挣扎着,思琪说:“我恨你,我恨你。我永远不会嫁给你。”
直到走到16栋楼下,两人都没说一句话。思琪快要扭头进去时,水生拉住了她的手。水生想说点什么,却没说出口,只是捏了捏思琪的手,扭身走了。
思琪忍不住叫了声:“水生!”
水生回头朝她笑了笑.那笑容十分的惨然。
后来,思琪嫁为人妻了。
她的第一夜。
丈夫开始吻思琪,当他的嘴刚一触到思琪的嘴唇时,思琪有一种被火烫了一下的感觉。她下意识地将头向后仰了一下。但当她触到他热烈地充满情欲的目光时,思琪又软下了。她感受到了一种召唤,这种召唤超越了她的理智,直接从她的肉体深处得到了回应。思琪没了思维,她闭上了眼沉入这从未体验过的享受中。
他使劲地吻着她,思琪感到透不过气可同时又盼望这吻能永远下去。许久,他终于将手搁在了思琪的裙扣上。
思琪焦渴地答道:“我要你。”
当一切结束后,思琪躺在他的怀里,激动未已。思琪想,这是怎么回事?我怎么突然间就成为一个真正的妇人了?我怎么就这样轻率地将自己最珍贵的交给了这个年轻人?我怎么鬼迷心窍了?然而,那一切,又是多么的好,多么的不可思议,多么的快乐。
思琪想,事情实际上就这么简单,有时人为了这么简单的事竟作那样复杂的铺垫。男人女人最终直奔的目的只有一个,何故又去制造些中间环节呢?爱有多大意义呢?不爱又少了什么呢?无非如此。
思琪自觉自己有了一种彻悟。她觉得自己把一个并不要紧的东西严密看守了许多年,待有一天拿出来后,才发现也不值什么。
当他再一次凑近思琪时,思琪仍鼓涨起激情迎接他。思琪想这就是男人,这就是女人,这就是享受,这就是淫荡,这是人类最美丽而又最丑恶、最亲密而又最陌生的时刻;是每个人最公开也最秘密、最渴望也最鄙夷的事。
一天的清早,他摇醒思琪,不高兴地说:“你半夜里使劲地叫着水生,然后往我怀里钻。”
思琪骇了一大跳,说:“不会吧。”
他醋意十足,说:“你是不是幻想着那个叫水生的男人而和我做爱?”
思琪忙辩解道:“不不不。”
但是,一个人在房间里时,她觉出自己十分的孤独,孤独如荒野之游魂。她想,水生也是在跟别人睡觉时喊叫我的名字吧。
后来,思琪有了一个孩子,丈夫甜蜜地说,单名一个“幸”字吧,取“三生有幸”的意思。
三生有幸,三生有幸……
她抱了小婴儿到窗边,秋天的阳光照耀着她和那小小的生命。她拥在怀里,闭上了眼睛。她默想着。在她默思中的辽远之地,一片烟花开放成云霞,轻逸地起伏动荡。
她自问:这究竟是些什么?又有什么意义呢?
【评语】
题材并不新,似乎也不重大,但对于一个女子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样的事更重大呢?一般写这样种题材的,很容易会将人物的情感架在一个高位上以表现青春爱情的美,相反的做法是写这类事的庸常甚至不堪以实现立意上的“革命”,这都是失真的表现。你的处理非常得体,写出了“真”,做到这一点,其实很不容易。而且,因为你很细致地把握住了主人公种种微细的情感方面,并将容易写乱的内涵聚拢在一起,成为散而聚,乱而丰的样子。好的小说,往往是这个样子。
语言比你上一篇作业有了很大的进步,叙述轻巧流转,了无滞碍,仿佛信手而来、脱口而出,实则处处见出作者的基本的态度,语言本身便成为可靠的内容。当然,这只是大的感觉成立,这篇作品值得再斟酌调整的,也正在语言方面。
责任编辑⊙育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