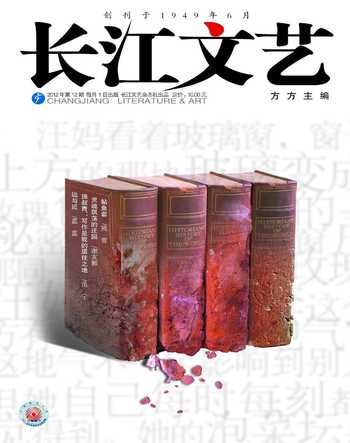施叔青:写作是我的居住之地
施叔青,女,1945年生,作家,台湾彰化人。17岁以处女作《壁虎》登上文坛。1978年移居香港,任香港艺术中心亚洲节目部主任,现任亚洲节目策划顾问。早期作品受超现实主义影响,后期风格发生重大变化,趋向现实主义。著有小说《约伯的末裔》、《牛铃声响》、《倒放的天梯》、“香港三部曲”等。
“漂移”是一个非常文艺的词。
身体的漂移,可观不同的风景;目光的漂移,折射灵魂的驿动;心灵的漂移,改变生活的轨迹。漂移让内在的精神世界总是处于不止不息的节奏当中。静,可积淀,可沉思;而动,可探索,可发见。漂移是一种随性的动,一种随心的动,让过去和未来产生缝隙,让原乡和他乡边界模糊。就在这缝隙之中,文学蓬勃生长;就在这混沌之中,思想澈然清晰。
2012年10月13日,武汉,一群“漂移者”在这里聚首。参加“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第12届双年会”的作家们,相对于这广袤的中国大陆,还有浩荡的中华文明而言,来自或旅居海外的她们,自然是一个个游离出去的分子。她们将精神血脉中固有的传统精髓,嫁接在新的生活和文化中,获得新的文学视角——这就是“漂移”的意义之一。
生于台湾、旅居香港、定居美国的施叔青也现身此次双年会,并接受了笔者专访。她自称为“岛民”,在不同的岛之间跋涉——现实中的岛,以及文艺领域中的“岛”——是漂移者的代表。漂移让她获得创作的活力,却不会有失去根的感觉,因为德国哲学家阿多诺曾说过:“对于一个不再有故乡的人来说,写作成为居住之地。”
一
1970年,施叔青赴美国修习戏剧,开始抵达出生地之外的第一个“岛”——曼哈顿。由此,她开始了自己充满喧哗和骚动、眺望与回眸、探索与凝思的文学之旅。尔后旅居港岛17年,看尽繁华。一朝忽然“入于禅定”,她找到了自己所依傍的“乡土”——不是地理意义上的原乡,而是灵魂的归宿,一种从驿动归于平静的状态。与施叔青交谈,这里那里,此处彼处,平静的叙述里铺展的是一段绵延而游移的旅程,可以知道,这位年近古稀的“岛民”,为何没有那种停留的感觉了。
范宁(以下简称“范”):居住在岛屿的人,总有一种眺望的姿态。望着面前茫茫的大海,会去想象海的彼端是什么世界。那些年的台湾,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眺望姿态?
施叔青(以下简称“施”):上世纪60年代的台湾大学生非常崇美。那时候的台湾还蛮落后的,所以一些来自美国的书籍和展览,对我们来说就是重要的精神食粮。很多人抱着崇洋的心理去美国。所以我也到纽约去学习戏剧。美国的生活,主要是学习如何做编剧导演,也自己编剧,在百老汇那些地方转来转去。那时候荒诞剧场大行其道。
范:为什么那一次没有留在美国?
施:当时有一个转折点。美国有一个频道叫Channel 13,专门放一些文化方面的电视节目。有天晚上我看到一个叫做《秋江》的纪录片,讲中国的昆曲。很老的一个纪录片,黑白的,只有两个人演出,演的就是《思凡》。
《思凡》讲的是一个叫做陈妙常的小尼姑,她不喜欢庵里的清苦,思念凡尘,所以要渡江离开。她在岸边,要求船夫把她带过江去。
这两个人在台上表演,唯一的道具就是船夫身上的船桨。但是他们在舞台上模拟出那种颠簸、移动和种种动作,非常美,服饰做工也很漂亮。中国的戏剧具有象征性,是超乎时间和空间的,这一点在西洋的戏剧中很少见。西洋戏剧从易卜森之后延续了写实传统,中国这种戏剧对他们来说很难想象,太过超前了。
我看了之后非常震撼。中国戏剧中居然有这么美的东西。我千里迢迢来美国学西洋戏剧,但我们有那么好的审美,那么好的艺术,都忽略了。所以我当时就起了文化回归的心思。读完书之后,我就策动我先生回亚洲(我先生是美国人),开始研究歌仔戏啊,台湾的乡土民间戏,还有研究京剧花旦的首饰做工什么的。我有一种很深刻的反省,觉得需要知道自己的文化。就这样,我从第二个岛回到了台湾岛。后来在台湾我一边教书,一边做研究。
范:后来又怎么去的香港呢?
施:人家以为我很喜欢旅游,所以去香港肯定是自动自发的。其实没有。我先生是哈佛大学的博士,他本来拿到学位后要去纽约大学教书,但是他不喜欢教书。跟我一起回亚洲后,他做了几年就决定离开学术界,到了美国开办在香港的银行,我也随他一起到了香港,我人生中的第三个岛。一去住就住了17年,我去的时候香港还是英国殖民地,我是1977年去的,一直住到了1994年才离开。
二
交谈中,施叔青认为,年轻人应该多出去走走看看,出去才有比较。“在一个地方久了会觉得什么都理所当然,所以我觉得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到外面去走,视野才会宽阔,这个很重要。”所以施叔青说自己是“岛民”,有不固定、漂移的含义在其中。她是风,漂洋过海的风,在海面掀起浪花的风,没有什么可以羁绊脚步。
范:您自称“岛民”,对这个概念应该怎么理解?
施:我觉得是“移动的、漂浮的、不定的”,我喜欢这种换环境的感觉。对一个作家来讲,你在一个固定的地方,思维也可能会固定——当然我们也可以争论,像美国作家福克纳,他终其一生就是在他小小的故乡,也写出了那么重要的作品。可是我本身,好吧,我基本上是个非常好奇的人。我就是粤语中那种所谓“叹世界”的人,很喜欢看一些不同的东西,总是带着一双很新鲜的眼睛,去看我居住过的不同的岛,开拓我的视野。我觉得很有意思。我很怕封闭的环境,会很拘束,我喜欢海阔天空,也比较有冒险精神。
范:岛屿是一个相对于大陆的概念。您对于庞大的陆地,难道就没有向往和憧憬吗?
施:我们现在很流行一种说法,大陆是中心,台湾是边缘。但也有这么一说:以小博大,从边缘打入中心。我是一个生长在海岛的岛民,这让我有更大的抱负,这是一种反弹,一种很吊诡的心理——我一定要做得更好,所以鞭策自己的心理。大陆这种稳定性对我来讲不是很重要,我可能就是一种动荡的、骚动的命运,就像风一样。我没有很向往那种稳定的东西。喜欢新鲜的人,不断探求的人,一定不想拘束在一个地方。
范:散文家蔡天新有篇作品叫做《神秘的岛屿》,他以英国这个大岛为例,讲述虽然在岛屿之上,但是这丝毫不妨碍英国成为一个文学的大国。岛屿对于眺望和想象的刺激,不知您是否也感觉到了?
施:当然有!我比较重要的作品之一就是在香港写的,完全是因为我以一个外来人的眼光,看到了他们觉得习以为常无甚稀奇的东西。对我来讲,我都会非常深刻地有感觉。这个变成了我的港式生涯的题材,非常重要。香港有些风俗习惯、人情世故,甚至是香港人的那种肢体语言,他们的价值判断、人际关系,都是我观察的对象。作家就是要观察。
因为学戏剧的原因,刚去的时候我就在香港艺术中心策划节目,是段很好玩的生活。那时候我们有艺术节,有一些很大型的,连港督都会出席的活动,上流社会又好玩又好看,我可以穿着漂亮的衣服,过着非常惬意的生活。那时台湾与香港完全不同。这种环境的变换对一个作家的刺激很大,看到了当地人所没有看到的,这都是我写作的保障。
范:我忽然想起一个“岛”的概念的延伸,比如很多人会认为,男性是大陆,而女性是岛屿……
施:不对!为什么女性不能做大陆?我们有那么多的人才呢!刚才我说“岛民”,但不意味着其中有贬低的意义。英国也是岛啊,但是人家建起了日不落帝国。所以,女人和男人,不是岛屿与大陆的关系。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一般来讲女人都是被打压的,你看那些世界各个领域的出色人才,科学界、医学界、文学界、艺术界,都是男人占主要。女作家要出头也是很难的,这是我要颠覆的。我要颠覆由男性掌控的历史。
三
在施叔青的作品中,女性都很强大,而且在写尽繁华云烟后,她开始书写更为宏大的历史,并将这种历史承载于一个个女性角色的肩膀上。大历史中的大女人,施叔青写到这里的时候,与男性作家有了明显的分野。
范:您笔下书写了五光十色的香港生活,也正是这些作品,奠定了您在文学界的一个重要基础。
施:其实去香港之前我已经出了两本书了,但是那时候我写港式生活,很多人感觉发现了一个新作家!
刚才我说过,我在香港艺术中心,生活过得很好,经常一晚上去五六个party,碰到一些我所尊重的世界级的指挥家、电影导演,好玩极了,学到许多东西,可是我觉得我不想为他人做嫁衣。我应该退回到作家的身份,而作家是寂寞的,在人群中写不出东西的。我毅然决然地辞掉了工作,背水一战。
那时我有两句名言,“自我的挑战,自我的完成”,我一定要做到。我自己觉得自己很悲壮,因为作家只能跟自己挑战,这需要很大的决心,但是我就这样做到了。很多奖项对我也有很大的鼓励。每到一个岛我都有一种重生的感觉,迁移,再活一次,我很喜欢这种感觉。
范:您笔下的女性很强大,她们往往会对接一些厚重的历史。
施:我这一系列香港故事中,女性角色是很强的。一开始我就有颠覆的决心,所以我笔下的女人都是很坚硬很坚强的。她们在职场里是女强人,办事能力强,思考细致且耐心,领导指挥能力绝对不逊于男人。
后来我又想到,我一定要把这种港式生活做更庞大的结合,于是我就想到了历史。因为光写这种五光十色的东西不满足,就像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对我香港这一段的评价:写的都是那些“吃尽穿绝”的生活。我就觉得,我应该要写一个比较庞大的东西,后来就写了一个长篇《维多利亚俱乐部》,这个俱乐部在中环那里,很高级的。我写的就是这个俱乐部所涉及的一桩贪污案。以这个来影射大英帝国在香港的统治,从日不落到日暮西山的感觉。
这是我的第一个长篇,我觉得我还要往回追溯,再往历史深处探索。大部头的中国大河小说,大多出自男作家之手,主角是光鲜亮丽的英雄和正面人物,历史的诠释权一直在男性手中。我就觉得是时候了!我作为一个女作家,我要把历史诠释权握在自己手里,为女性发声,我要站在女性的立场上,把过去的历史颠倒过来。
这个我很有信心,于是我就构思了“香港三部曲”,一个叫做“黄德云”的女孩子。她从东莞被人贩子卖到香港,要么去当女佣,要么去当妓女——香港被割占时不也只是一个“出身低微”的渔村吗?黄德云有双重压力,第一个就是性别,在男性社会中的压力;第二个就是被殖民的压力。我写她在这个恶劣的环境里,一步一步往上爬,靠着她自己的实力,离开了妓女屋,然后去当人家的陪读,然后又做房地产。这个女孩的命运,就是香港的命运。我就是要找回诠释历史的权力,要由女性来诠释历史,而不是你们男人讲了就算的,我们自己也要发声。
范:就是说一个女性作家,以一个女性为主人公,展示一段女性的命运,但是它同时也是可以创造历史的,是可以与男性所书写的历史比肩而立的。
施:是的,我很相信这一点。这也是我写到今天,写到头发都白了,觉得最有成就感的。
范:男性作家写女性心理的时候,经常有一种障碍,男性无法去解读女性心理的,但我看过有关对您的评论,“一个女性能够贯通男性和女性的两种视角”,您自己有没有这种感觉?
施:哪有!首先,男作家会写女人,比如对我帮助很大的白先勇。他把女人写得那么好,我都写不过他。而我呢,在写这些中篇小说的时候,别人都会把我和张爱玲比,我们都能写出那种细微的感觉。没有看过我本人的人,光看我的小说,看到里面的勾心斗角、小奸小坏,再看到现实中的我是这么大大咧咧的,还以为我人格分裂呢!
我名字里的“叔”以前是“淑”字,为了不那么女性化,我把三点水旁去掉了,后来有人看了我的作品,以为我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男性作家(笑)。
其实,文学就是一种发泄,一种治疗,我已经在纸上把我的伤痕,我的什么东西都已经发泄过了,我已经发泄完了,已经痊愈了,没必要在生活中再怎么样,我蛮与世无争的。
作为作家,我站在一个人性的观察和分析的角度上。人性中有很多不好的习性,贪嗔痴,不分男女,这都是人性。作家应该是比较中性的,女性作家的东西会被认为是比较纤巧、细腻、优柔、阴暗,比较属于月亮型的;男作家则显得比较阳刚。但一个好作家应该是两种兼得的,有观察入微细致的一面,但也有阳刚的气质。我也许是两种都有,我也希望如此。要我只是写那些短小轻薄的东西,我不OK。很多女性作家喜欢写一些茶杯里的风波,小东西,按举重来讲是“羽量级”的,像羽毛一样轻,我是要写重量级的,呵呵。算命的说我是女生男命。
四
施叔青参禅20年,学画十余年,最喜欢的是古典音乐,大部分的阅读时间给了经典作品,同时她还在追逐考古和文物,对楚文化赞不绝口。
范:参禅对您的写作有帮助吗?
施:之前我谈到了自己迁移的命运。迁移是很正面的,很好的,但也有无法摆脱的无奈感,因为你每到一个地方就必须要重新建立自己。我从台湾去美国,就要重新找寻自己的位置,这个过程不是那么好过的。1994年从香港回到台湾,我女儿去美国读大学,我在“空巢期”,回到的台湾也是人事全非,人脉什么都没有,我就要重新找寻、建立我自己,这是一个很大的功课。我感觉到严重的不安定感。后来我开始静坐,本来骚动不安的个性,变得可以沉淀下来,安静下来。
我一直有一个恐惧,就是创作的泉源枯竭。我身边一些作家,在创作初期能够写出非常优秀的作品,熠熠发光,但是他们把这些情绪发泄出来后就无法继续。我很怕创作会“早夭”,而静坐时,我的灵感源源不断。
参禅的时候我已经人到中年,浮光掠影之后,绚烂归于平淡。在香港的时候我可不敢想象,有一天我会不染头发,就这样以白发示人。
范:您接触了不少大陆的作家,印象如何?
施:我这一辈的台湾人,实际生活中,对大陆还是很向往的。我们从小就读地理书,说中华大地地大物博,江山如此多娇。我1979年就到大陆了,开始接触到大陆的伤痕文学。那时候,中国作家很有生活,又有苦难,写出来的东西都很震撼。我觉得有必要跟他们对谈,把他们的理念和思维方式写出来。
当时对谈的作家有很多,残雪,韩少功,坐在轮椅上的史铁生,汪曾祺——我跟他一起沿着沈从文的足迹走湘西。当然还有莫言,最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那时候他非常年轻,听说我喜欢传统文化,带我去他山东高密的老家,给我一大堆剪纸。现在这些剪纸作品还在我纽约的家里,我想它们现在可升值了,呵呵。
范:您提到过,特别喜欢楚文化的东西。
施:我第一次来湖北就为看编钟,楚文化太伟大了!我的个性属于浪漫的,现在又在画国画,湖北出土文物中那些线条图案真是太漂亮了!
我以前对《考古》和《文物》这两本杂志跟得很紧。我一直想当一个画家,梦想是画画。当年考大学没有考美术科,现在在学中国画,在纽约画中国山水。学了十几年的中国画。10月底我会到上海去看一个展览,上海博物馆有一个很大型的展览,美国的四大博物馆收藏的中国的古画一起展出。
范:可见您的兴趣真的是非常广泛。
施:我不愿意重复,所以不断出走。澳洲土人有一种利器,打出去可以弹回来,所以我不断出走,又不断回来,回到我中文写作的环境中。别人都在说无根、乡愁,但是我很能体会“处处无家处处家”的感觉,我就活在当下,“现在”就是我的家。就像阿多诺说的:“对于失去原乡的人,写作成为居住之地。”
范:那您现在的创作状态是怎样的?
施:以前有人跟我说过,以小说为香港的百年史作传,而作为台湾的女儿,我应该为台湾写点什么。台湾三部曲却是在美国写的,距离产生美嘛,这样可以更好地审视台湾的历史。我花了8年时间来写,深居简出,要写东西就不能一天到晚像花蝴蝶一样到处跑。我就在书斋里,呼唤过去那种历史的感觉。
范:您平常都读什么书?
施:我读的都是很经典的作品,《追忆逝水年华》、《百年孤独》等等,还有福克纳、伍尔夫的小说,还有杜拉斯的《情人》。内地的作家我印象深刻的还是当年对谈的那些,他们到今天仍然是中国最好的作家。
责任编辑 鄢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