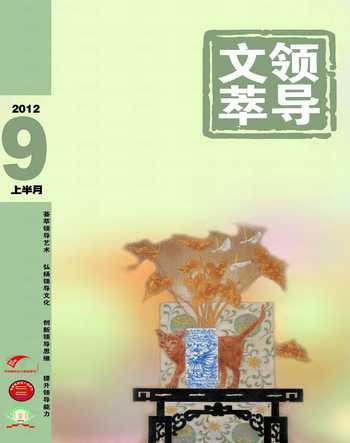龙应台:角色转换之间
李立
关于龙应台的新闻,总是能够吸引人们的眼球。今年2月,这位著名作家正式上任台湾“文建会主委”。5月20日,该部门改称“文化部”,她是“文化部”第一任负责人。
从文化人“变脸”成为政府文化官员,又还原为文化人,最近又再度为官,龙应台的角色转变让人充满想象空间。写《野火集》、《百年思索》的作家龙应台,当文化局局长、“文建会主委”的龙应台,究竟哪一个才是真正的龙应台呢?
驰骋文坛的“龙旋风”
对于大陆民众来说,龙应台最重要的身份是作家。以名作家与人文学者的身份游走两岸三地的龙应台并不乏争议。有人批评她总以“外省人式”的眼光看世界,甚至有些“缅怀威权时代”。龙应台自己说,她过去经常被台湾舆论政治性地解读为“独派”,现在又经常被解读为“统派”。喜欢她的人称她是“女鲁迅”,不喜欢她的人称她是“女希特勒”。褒贬任凭人说,龙应台还是龙应台。
1952年,龙应台出生于台湾高雄大寮。由于父亲是职业军人,小时候经常搬家,而在不断的搬迁中,也养成她站在心灵边缘冷眼观看世界的个性。
1969年,龙应台进入成功大学外文系,毕业后赴美攻读英美文学博士,毕业后任教于纽约市立大学。出国十年之后,由于想念“台湾夏日里四处漂漾的茉莉花香”,1983年8月,龙应台偕同德籍夫婿回台,任教于“中央大学”英文系。
龙应台以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与勇气,从《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开始,走上了以杂文批评社会的写作路线。她的文章犹如一把燎原的野火,烧痛台湾社会已久的陈疴,也为台湾社会提供一个反思的空间。1985年,龙应台写的系列文章集结成《野火集》出版,一个月内再版24次,在台湾掀起了一阵“龙旋风”。
1986年,龙应台离开台湾,与夫婿旅居瑞士,后到德国定居,此时她告别了《野火集》的写作方式,同时,也拓展了视野。这时候的作品有《人在欧洲》、《从东欧看台湾》、《写给台湾的信》等杂文集,与此同时,她也在为人妻、为人母的成长历程中,写出了一系列关心女性问题的书。
龙应台思索问题的深度与广度集中体现在《百年思索》一书中。这本书上下纵贯百年时序,论述涵盖东西文化,除了延续其锐利的观察之外,也蕴含了历史的沧桑与无奈。龙应台的文章也从犀利的批判转为同情的了解。
虽然旅居海外十多年,龙应台仍保持了对台湾的持续关注。1999年,龙应台出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长,提出“文化就是生活”、“文化就在巷子里”的观点。
“学而优则‘事”
龙应台曾经说过,她是儒家的信徒,总是想着“学而优则仕”。不过,她认为那个“仕”不是要谋官,而是要做事。
1999年11月,时任台北市长的马英九专程前往德国,邀请旅居法兰克福的龙应台回台北市当文化局长。
龙应台接到邀请后,她的思绪很多。龙应台说她之所以接受邀请担任此职,一个重要的考虑就是,台北市设立文化局是第一次,史无前例,她害怕这个部门会变成市长的宣传机构、御用单位或政治的附庸。她心里是带着这些恐惧“下海”的。“说实在话,当时我答应这件事时,没想到去做官,只想到去做事”,龙应台如是说。
的确,对龙应台来说,“偶然”当官只是带职下放,好像进行一次田野调查,只是跟读者暂别而已。
当有人问她当作家与做官有什么不同时,她回答说:“刚开始涉足官场时,我觉得作家是荒野里的一匹狼,没有羁绊,不需要与任何人相处。官员是猴子,猴子是族群社会,母猴要给小猴挠痒,小猴与小猴要打架,公猴之间要互相争夺地盘。从狼变成猴子容易吗?我觉得非常非常困难,困难得不得了,觉得身心俱疲。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产生了另一个比喻。我觉得作家是绵羊,官员是狼。绵羊纯洁、天真。官员在权力的运作里头,做成一件事往往要突破无数障碍,这就要有狼的战斗性,看准别的动物的喉咙就咬。从羊变成狼也是很困难的。最近,我觉得当作家和当官的区别是人变狼的过程。我现在属半人半狼,也是蛮难受的。有人说龙应台是否在抱怨?我认为不是的。因为什么都是咎由自取。讲得好一点,是知识分子的任重道远,是自己的性格取向而落了这么一个结合,这都是活该。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不后悔。台北市的马(英九)先生给了我这么个机会。我觉得自己从前的作品是在思索。现在是我在验证自己的思索对不对。所有的羊啊、狼啊都有痛苦,都在给自己上课,使自己变得更深刻、更成熟。因此,我还是要感谢社会的宠爱。”
从文化人“变脸”为政府官员,日后必然会再从官员回归为文化人,起初不少友人对龙应台角色变换的成功感到疑惑,朋友们都担心以龙应台的文化人性格去当台北市首任文化局长,怎么承受得了政治舞台上诸多不可承受之重?有人预测,文人性格如此强烈的她,不出三个月就会阵亡下台,李敖则比较“乐观”,预测她只能做六个月。
“刚开始的过程真的很苦,不足为外人道也。那时候,自己一个人回到房间里痛哭一场的机会是很多的。”她几乎已经忘了自己为公务哭了多少回,数都数不清。
政治人的思维和文化人到底不同。政治是不同利益群体的一种协调,要思考如何一碗水摆平,经常需要妥协,需要让步,不可能什么都坚持。
以工作成果去任人批判
龙应台刚入政坛时,几乎整个台湾都在看。情况也确实很艰难,台湾有一句话叫“官不聊生”,当官越大越痛苦,台湾现在民意高涨,官员实实在在是仆人,谁都可以指着鼻子骂。尤其是议会非常强大,每个议员都代表一大批选民,他们对官员简直是颐指气使。
龙应台这样描写她接受市议员质询时的情形:
就在这样的一个阴冷寒湿、焦灼不安、而且荒谬透顶的冬夜凌晨3点钟,我突然发现“龙应台局长”被唤上了质询台。一个议员,刚从外面进来,似乎喝了点酒,满脸红通通的,大声说,“局长,你说吧,什么叫做文化?”
对着空荡荡的议事大厅,台北市文化局长说:
文化?它是随便一个人迎面走来,他的举手投足,他的一颦一笑,他的整体气质。他走过一棵树,树枝低垂,他是随手把枝折断丢弃,还是弯身而过?一只满身是癣的流浪狗走近他,他是怜悯地避开,还是一脚踢过去?电梯门打开,他是谦抑地让人,还是霸道地把别人挤开?一个盲人和他并肩路口,绿灯亮了,他会搀那盲者一把吗?他与别人如何擦身而过?他如何低头系上自己松了的鞋带?他怎么从卖菜的小贩手里接过找来的零钱?
文化其实体现在一个人如何对待他人、对待自己、如何对待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在一个文化厚实深沉的社会里,人懂得尊重自己——他不苟且,因为不苟且所以有品位;人懂得尊重别人——他不霸道,因为不霸道所以有道德;人懂得尊重自然——他不掠夺,因为不掠夺所以有永续的智能。
品位、道德、智能,是文化积累的总和。
那微醺的议员事后告诉我,他以为我会谈音乐厅和美术馆,以为我会拿出艰深的学术定义。
我当然没有,因为我实在觉得,文化不过是代代累积沉淀的习惯和信念,渗透在生活的实践中。
这就是龙应台,当作家时,心里有什么想法乃至委屈,还可以找文友宣泄一番,但当上文化局长后,最令她感到痛苦的是,即使有满肚子的心里话,也找不着人倾诉。归根结底,许多话都是不能和别人讲的,痛苦和眼泪只能往肚里吞。
“真是非常苦。”提起这三年多来的酸甜苦辣,短短的五个字,道尽了龙应台内心错综复杂的思绪和感受。
做政务官三年多的时间里,龙应台封笔不作,停止评论。不是因为行程太忙,而是对权力另有思索。
三年笔不出“鞘”,是因为龙应台希望谨守民主的游戏规则。她认识到:权力越大,责任越大,所可能辜负的人越多。权力大,而又不知谦卑的必要,一不留心,就是一个“以万物为刍狗”的结局。
龙应台说,作为知识分子,像是裁判;做掌权者的时候,像是球员。知识分子可以是潇洒的,可以去批判,职责在于以文字影响思想、指出方向;当成为体制内握有实权的执行者,就完全不同了,必须是默默工作的人,而不是指点江山。一旦知识分子进到机制内做执行者,必须暂时放下知识分子的身份。如果想要用权力达到个人理想的话,必须变成一个忍辱负重、有耐心协调的
人。不能靠文章去宣扬自己,必须要以自己工作的成果去任人批判。这是必须的角色转换。如果想两者得兼,那就容易错乱。
探出头来的这个人
今年2月15日,一身黑衣点缀着橙色丝巾的龙应台,正式上任台湾“文建会主委”。龙应台说这是“失去自由的第一天”。
生肖属龙的龙应台说,这次接任新职务前,曾反省当年担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长时,没能和市议会、媒体搞好关系是最大的败笔。她反思自己曾经的“知识分子的傲慢”,自嘲“不食人间烟火,自视清高”。她说,此番重回江湖,一定会以最坚定的信念,用最温柔的态度来达成目标。“为了让文化建设回归文化本质,我可以弯腰、低头,甚至趴在地上。”
“做官,要达成一件事情,80%在于与人的协调上,这个基本道理我快到50岁才认识到。”龙应台感慨。这次重出江湖,她的身段变得柔软,她对“文建会”同仁说辛苦了,对历任主委说谢谢啦,对其他部会说请帮忙,她拜会好姐妹、新晋“立委”张晓风,惜别时不忘送去飞吻……
对于未来工作重点,龙应台说:“我最关心的是台湾最基层、最草根的民众,是否能和台北市民一样享有同样的文化权。未来将穿着脏球鞋,全台走透透。”
是的,龙应台又回来当官了。龙应台能否当好一个文化官员,有人乐观,有人悲观,就像龙应台的文章和言论,有人喜欢,有人厌恶。
当然,也许更多的人喜欢龙应台。龙应台说,每个时代都有思考和不思考的人。有些人追求时尚,不谈政治,只关心自己的事情。社会就像一个巨大的滚动着的车,总有人在里面自顾自地行乐。所幸的是,总有人探出头来看看这辆车究竟跑在哪里。
而龙应台,就是探出头来的这个人。
(摘自《世界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