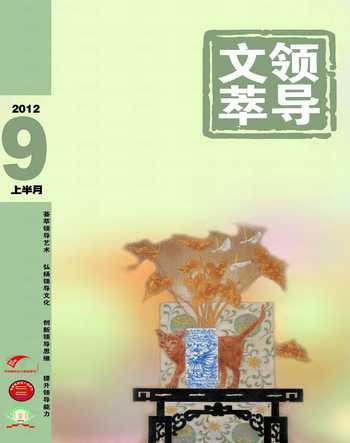资本国家化还是资本社会化:国企体制改革的选择
秦晓
国企体制是我们当前面对的各种经济问题中最需要突破而又最难突破的问题。说它最需要突破不是因为在国企经营层面上存在治理和管理、效益和效率方面的问题,而是因为国企在体制层面上造成“国进民退”、垄断、民间资本外流等社会问题,这个问题能否及时、妥善处理关系到党和政府的执政正当性。说它最难突破是因它涉及到对社会主义本质,宪法中关于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表述的认识和理解,同时,也触及到已形成的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
陈清泰文章(见《财经》2012年第13期“国企改革再清源”)最大的亮点是揭示了国有企业只是一个载体,它的本质是国有资本。所以国企的进、退实质上是国有资本的流动和重新配置。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将这个命题再推进一步,即什么是国有资本?我以为国企积累的国有资本应该是资产形态的财政盈余,因为财政只有现金流量的收支账,没有资产负债表,如果建立了“国家资产负债表”,这个问题就更加清晰了,它应列入“国家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方,同时国企的负债应列入负债方,其净资产即是国家作为股东的权益。国企资产形态的国有资本是计划经济体制的遗产,也是上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后发展积累形成的。无论是财政的盈余还是国家作为股东的权益,它都应被视为公共财政的资源。国企制度的改革,国有资本的流动和重新配置就是要还其属性,将其运用到与民生相关的公共产品上,如社保、医疗、教育、住房等。所以,这个转化的实质是国有资本的社会化和国企的民营化。当然,这一过程应是有序的、有效率的、公平的、通过市场运作的。
国有资本社会化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表现,它可以推动投资型的财政向公共财政的转变,加快社保体系的建立、改善公共产品短缺的状况。与此同时,它也有利于建立一个公平、有效、自由的市场体制。
目前要建立这样一个认识,实施这样一套改革在观念上、利益上存在较大的障碍。
一是所谓公有制和私有化的问题。列宁、斯大林在前苏联没有实现共产主义的情况下将这一制度付诸实践,形成了全民所有制,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也相应建立了全民、集体两种形态的公有制。实践证明这种体制约束了生产力的发展,剥夺了现代社会个人应有的权利和自由。前苏联的解体、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对这种体制的否定。在市场化转轨过程中,中国的国家体制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公有制;在微观层面上的国企不能被视为公有制企业,它的本质与西方国家的国有企业如新加坡航空公司及各种主权基金公司一样,都是政府财政投资的企业。将国企视为公有制企业,并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公有制为基础的概念和逻辑都是不成立的。
二是国企的属性和功能。即国企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商业机构,它除了要承担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外,还要承担政治、经济、社会的特殊功能,如“国企是共产党执政的基础”“国企应控制关系国家战略和国计民生的产业”等。
从政治上讲,权力来自人民,执政党的基础归根结底是取决于它们倡导的理念、建立的制度、推行的政策是否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和赞同,而不是对经济、资源的控制;从国家发展战略、国计民生的保障来讲是科学、民主决策和市场经济活动互动的过程,而不是政府通过控制企业、替代市场配置资源的过程;对具有自然垄断和公益特征的行业,前者如电网、铁路,后者如管制价格下的能源,水、电、气等大多数都可以通过颁发许可证、确定价格和收益、公开招标由私人部门承担。
政府的职责是制定规则和监管运行,而不是通过所有权来实施,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价格管制的行业不能一概被视为公益性行业。
什么是以公有制为基础?我认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它所追求的是社会的公平、正义。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制度所应保障的也是社会的公平和正义,这在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胡锦涛的“以人为本、和谐社会”中已有了充分的、与时俱进的体现。关于公有制的认识也是不断发展的,“股份制是公有制体现的主要形式”在上世纪90年代已写入了党的决议。
现在有些人在国企制度改革问题上重提姓资姓社,公有私有,这是对30年改革开放中形成的共识的颠覆和倒退,也是对市场化转轨取得的成就的否定。这不仅反映出观念的陈旧,更值得警惕的是特殊利益集团的掣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新一轮改革不仅需要观念的更新,还需要克服特殊利益集团的阻挠。(摘自《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