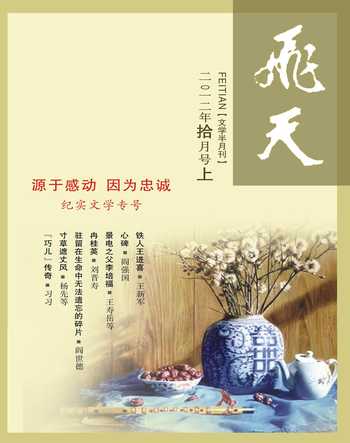精神铭石:镌刻于黄土大地上的艰辛与荣光
杨学文
去年秋天,我在甘肃省委宣传部参与几个文件的起草,记得有一个是关涉“甘肃精神”的。当时十七届六中全会刚刚结束,省十二次党代会还没有召开,甘肃宣传文化部门正紧急出台一系列配套文件。在几番热烈的讨论之后,大家对“甘肃精神”的内涵渐渐清晰,最后出炉的“甘肃精神”内容是:大力弘扬“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的优良传统,牢固树立“坚韧智慧、开明开放、求实创新、勇于争先”的新形象。
虽然这只是甘肃精神的提炼,不一定能诠释甘肃精神的全部。甘肃人的朴实厚道、吃苦耐劳的传统精神,其内涵过于博大丰富,不易概括。古《易》经里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等语,似乎就能代表这种精神。《易》经的起源据说就来源于甘肃天水一代,这使我们对甘肃精神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而“精神”这个词在我们这个时代总是言说不尽的话题,如果要用更少的词准确概括,感觉古人所称的“道”更合适一点:道德、道理、道义——“道”终是超越于私利之上、跨越于金钱甚至生命之上的。它的坚韧和珍贵之处在于不标榜、不作秀,像是民族骨髓里储存的光芒,越是在艰难的时刻越是有存在感,越在困境中越能闪耀。更重要的是,它不仅仅存在于某一小部分精英身上,而是广泛地蕴藏在民众之中,那些耕种在黄土地上的村妇民夫,小事讲道理,大事守道义,做人有道德,他们的善良、坚韧和理想,其内涵就是一种象征,一种向心力。如果把“精神”这个词再放大一些,例如在精神前加上“甘肃”这个地域,那就成了一种陇人的向心力,一种凝聚力,是不屈不挠、永不放弃、永不言败,是重新振作,是从头再来,是信仰,是陇人自古以来所具备的吃苦耐劳、勇于挑战困难的精气神……
总之,“甘肃精神”并不是伟大英雄主题的汇总,而多是平常的小事的聚合,是仔细思量后才能彰显出精神意义的东西。是从生活的点滴开始,从一些细枝末节凸显出来的一个人的品质。如果你就生活在甘肃,周围总会见到这样一群人,他们不计名利,不图报酬,脚踏实地,在困境中忍受磨难,坚持着“沙棘或柠条一样”的韧性,自始至终或许就是一锨土加一锨沙,甚至自己也不会言说,也讲不出许多大道理来,但有一天当掀开被黄土遮蔽的生活的真相,他的身后就留下中国传统文化中许多精气神的东西来。
有一种精神叫奉献
在外界人眼里,甘肃就是满目荒凉、干旱多灾的代名词,是骑着骆驼才能够行走和生活的地方。其实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甘肃的发展速度也相当之快,山水清明的地方多的是,许多地方和江南没有大的区别,遍地绿洲、千里粮仓。但话又说回来,如果你真要在这个地方生活,还得经受自然条件的考验,包括缺水、干旱、沙尘暴……
特别是干旱。甘肃大面积的毁林开荒早在宋代就开始。当时朝廷在今天的天水设有专门采伐森林的“采造务”机构,在现在的陇西和通渭一带“辟地数千里,建堡居要塞,戎座三百人,岁获大木万本,以给京师”。宋熙宁年间,又大力开垦天水到渭源的广大田地作为军需所用。从此,原来弃耕的土地和大片处女山地被大量开垦,原有的森林草地再也未能得到恢复。到明代,受“屯田普天下,而边境为多,凡流民均给土地”的召唤,从山西等地迁来大量移民,人口空前增加,开垦土地达到疯狂的地步,水土流失加剧,旱魔开始吞噬它的肌体。满清政权建立后,仅临洮一县的耕地较明朝就扩大了20万亩;乾隆年间,洮河流域的次生林被砍伐殆尽;到了同治五年(1866年),左宗棠出任陕甘总督时,他已经看不到渭河流域以北广大地区的天然林了。
甘肃有历史记载的干旱最早是在宋神宗九年:“陇上各处发生夏旱”,之后数百年间,频繁的战祸中无数的烧杀掠夺,大量的树木砍伐后林地被辟为农耕的营田,气候开始反常,干旱加剧,土地面目全非——甚至在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在听了当地的困难情况后,难过得流下了泪水,并派工作组来扶贫。半个多世纪以来,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几乎都来过这里:胡锦涛、江泽民、胡耀邦、李鹏、朱镕基、温家宝……来人之多,规格之高,堪称中国之最。
现在,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多数人还是农民,仍然过着艰辛劳作的日子——对艰苦生活的忍耐和顺从,对艰辛环境的改造和奋争,对他人无声无息的奉献。在无数次下乡或回家的路上,我都会看到这种在西部骄阳下颤抖的生活:在泥土中,在落满灰尘的大道上,女人们褴褛着草帽和衣衫,男人们赤裸着上身,在轻轻地唱着一种叫“花儿”的古老歌谣,在飞扬的尘土中扬起手中的农具,或者向我们微笑着点头。这里的农民,他们在夏日的中午一般没有时间回家去吃午饭,他们“丰盛的午餐”,就是在贫瘠的田野上只吃几颗煮熟的土豆,然后继续劳动。在近乎被窒息的劳动重负下,只要能够动弹,就去干活。这些地方的基层干部,其实也是和农民一样在受苦,他们中的很多人就是农民家庭出身,通过考学分配或者当兵转业而成了基层干部,所以他们和农民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他们还是一个农民家庭的长子或者丈夫。微薄的工资常常用在给摩托车加油、垫付电话费和零零碎碎的应酬上。就像渔民们到大西北来,当地人就会闻到一股鱼腥味,西藏的牧民到京城去,城里人就闻到一股牛羊的膻气味。他们胡子拉茬的身上还有黄土的味道——常常吃住在农民家中,帮农民干活,和农民同忧同乐,他们和农民的全部区别只是他们拿工资,在某种程度上讲他们就是拿工资的农民!学者范鹏先生曾说:甘肃的干部群众,看上去相貌平平,但很能体现“陇人品格”和时代精神——自然条件差,但老百姓很顽强,是为“天弱我强”;家中的土地很瘠薄,但人民很厚道,是为“地薄我厚”;人家付出一分,我们就要付出十分百分,是为“人一我十”。“天弱我强”、“地薄我厚”、“人一我十”,甘肃虽然有着令人吃惊的严酷条件,但这严酷并没有遏制住大家前进的步伐。相反,条件的严酷却让每一个甘肃人奋斗不已,严酷让每一个甘肃人获得了永久的动力,严酷甚至成了甘肃人发展的助推器。
《飞天》精心筹划的这个纪实文学专号,以饱含真情的文字叙写王进喜、冉桂英、韩正卿、李培福、石述柱、王万青、封芝琴等几个甘肃不同时期创业奉献的代表人物,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些亲切的面孔,他们丰富的精神世界,定然会打动我们日渐疲惫麻木的心灵。他们既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朴实无华的人,以美好品格影响感染我们的陇原骄子,也是给我们留下一个时代最美好印记的人——
有一种奉献叫担当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大地上发生了许多惊天动地的大事情,涌现出了一批可歌可泣的人物,其中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就是“铁人”王进喜。这个毛泽东、周恩来都亲自接见过的甘肃工人,在建国40周年之际,与雷锋、焦裕禄、史来贺、钱学森一起被中共中央组织部命名为“建国以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优秀代表”;世纪之交又同孙中山、毛泽东、邓稼先、焦裕禄、邓小平、袁隆平等一起被评为“百年中国十大人物”,写入中华民族的光辉史册。现实生活中的王进喜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
“铁人”王进喜出生于甘肃玉门县赤金堡巷口子村,即今天的玉门市赤金镇和平村,亦称“赤金堡王家屯庄”。1950年春,他成为新中国第一代钻井工人。“钻透祁连山,战胜戈壁滩,快马加鞭进军吐鲁番,玉门关上立标杆!”“宁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这是他曾经立过的壮志豪言。他拼命干工作的事例也多得不可枚举。例如有一次他的右腿被砸伤后昏死过去,醒来后他只叫工人从自己的衬衣上撕下一块布包住伤口,拉下裤腿后又去工作。会战指挥部领导强行把他送进医院治疗,他又偷偷跑来,拄着拐杖去井场上指挥打井。当井打到700多米时,突然发生了可怕的井喷。这时候就需要果断地压井,当时因为井上没有压井需要的重晶石粉,他和工人们研究,决定加水泥来提高泥浆比重。在没有搅拌机,水泥加进去与黄土不能有效融合的危急关头,他把拐杖一甩,纵身跳进泥浆池,带头用身体搅拌泥浆。伤口的剧痛使他每活动一步都很吃力,可他全然不顾,手脚并用,把自己当成了水泥搅拌机,用身体整整搅拌了三个多小时,手上、脸上,凡是露出皮肉的地方,都被火碱烧起了一个又一个大水泡。但井喷终于被压住了,大家把他从泥浆池里拽上来时,他的腿已经疼得不能动了,一下子跌倒在地上。大家都说,这口井是铁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不怕苦”、“不怕死”,“不为钱”、“不为名”是王铁人的做人准则。一起劳作的工人说,国家的东西就是铁人的命,谁把铁人的骨头砸碎了,也找不出半个“我”字。王进喜说:“我从小放过牛,知道牛的脾气,牛出力最大,享受最少,我要老老实实地为党和人民当一辈子老黄牛。”
1970年11月15日,被劳累拖垮的铁人在弥留之际,将组织给他的五百元钱补助款又交给组织,说:“这笔钱,请组织把它花到最需要的地方去,我不困难。”在场的人听了,无不为之动容,纷纷流下了感动的泪水。
其实,“铁人”在甘肃大地上也不止一个,王进喜不过是他们中的最优秀代表。自王进喜之后,“铁人精神”已经在甘肃的大地上薪火相传。
李培福就是另一个铁人。1912年出生于甘肃华池县悦乐镇的李培福,红军北上抗日时任华池县游击队队长。大生产运动时任华池县县长,毛主席曾亲笔题词“面向群众”,给予嘉奖。解放战争时期,他任陇东分区行署专员。新中国成立后,他任甘肃省委常委、省委农村部部长、主管农业的副省长。“文革”期间,他又任甘肃省革委会生产指挥部副主任,兼任“景电一期工程”总指挥。在那个动乱的年代,他避开政治的纷扰,痴心地造福一方,创建了以“高扬程、大流量、多梯级”著称的“中华之最”——景泰川电力提灌工程,被景泰川人民誉为“景电之父”。
早在1968年7月,身为省革委会生产指挥部副主任的李培福赋闲在家,身闲心不闲,想为老百姓干点事。当“文革”运动稍稍降温,省委讨论甘肃农业问题时,他毛遂自荐、主动请缨,正式提出建设景泰川电力提灌工程的意见,亲自担任工程的全面负责工作。他拖着老寒腿,拄着拐棍,于1971年9月30日完成了著名的“景泰川电力提灌工程”。1983年,这位“景电之父”却因劳累过度在兰州与世长辞。
现在,淳朴的景泰人像神灵一样祭奠着李培福。在某种程度上,王进喜、李培福们,已担当了一个时代对于“精神”或者“灵魂”二字的准确释义,诠释了一个时代的英雄含义,使我们知道了忠诚奉献,应如何定义。
有一种担当叫责任
韩正卿,这个从普通党员成长起来的领导干部,从领导到老百姓身口相传的“韩爷”,用琐碎的行动把自己的名字一点一滴地书写在甘肃这片黄土大地上,书写在老百姓的心中。
韩正卿的故事同样发生在这片多灾多难的黄土地上,不过他的身份不是一个普通的工人或者种地的农民,而是一个官员。书写官员的文章我们可见得多了,动不动就洋洋万言,成本成套,但内容却真假莫辨。书写韩正卿的大块头文章虽然不少,真正感人的大多还是流传在老百姓之间的“口头文学”。耐人寻味的是甘肃已故著名书法家赵正先生为韩正卿撰写的一副对联:“六十年代打洞七十年代打洞八十年代继续打洞;而立之年挖土不惑之年挖土天命之年继续挖土”,横批是“两把黄土”。
什么意思?
看韩正卿的简历并不复杂,原来多与“挖土”有关。1934年腊月初七日生的韩正卿是甘肃宕昌韩院乡人,年仅14周岁便当了好梯乡三个月的副乡长;后来调到省委组织部又下放锻炼。1965年到武都东江任公社书记。东江山大且陡,土地大都挂在陡坡上叫作“挂田”,冲着山沟口洪水制造的平掌子上的则叫“撞田”,撞上洪水侥幸能收点就收点,不能收就只能血本无归。来到东江的韩正卿年轻力壮,虽然是公社书记,却同社员一起平田整地,修渠垒堰,凿山开洞,硬生生夯起2000多米河堤,修了两条盘山渠道,搞出3000多亩水浇地,结束了东江没有旱涝保收地的历史。
1972年他到民乐任县委书记,这里地高天寒,不便灌溉,庄稼受到霜冻的危害,戈壁沙漠不断侵蚀着良田。韩正卿一身农民装束,靠万人会战,人海战术,让每个劳力每天拉0.7个压实方,所有干部包括自己上前线,他的指挥部就设在地上挖下去的“地窝子”里,终于修成了双树寺和瓦房城两个库容达4800万立方米的中型水库,保灌41万亩,有效灌溉46万亩,半山坡搞了20多万亩的水平梯田,引种了优质苹果树。
后来他调定西地区任专员、地委书记。头年到定西,第二年就到原所属定西地区靖远县兴堡子川搞电灌工程。这是一个高扬程电力提灌工程,总投资1.04亿元人民币,是甘肃省“两西”建设的重点项目,韩正卿以他吃苦耐劳敢打硬仗的顽强作风和领导才干,亲自指挥,精心施工,同工程技术人员和灌区群众艰苦奋战,于1984年完成总干渠并调试上水,相继在1985年、1987年北、东干渠通水。为了解决当地人缺少燃料的问题,他提着瓦刀推广“回风灶”,教七个县的县委书记、县长盘灶的技术,自己亲自跑到定西各乡镇去栽树。本着有水路的走水路,无水路的走旱路,水路旱路都没有另找出路(移民)的原则,使定西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趋势,从根本上得到了遏制。
1987年3月,他被任命为中共甘肃省委常委,两年后离开定西到了“引大”工程任指挥,兼任两西(定西、河西)农业建设指挥部指挥、甘肃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他搞得最惊心动魄的工程是引大入秦工程,这个总干渠、干渠和支渠共长868.17公里的工程,是中国目前最大的跨双流域调水自流灌溉工程。工程要穿过长110公里的隧洞群,比“红旗渠”上的180个隧洞还长79公里,其艰巨性世界罕见。他在工程失败后临危受命,始终本着为老百姓造福的决心,终于在1994年9月25日使引大入秦工程全线通水。老百姓送给他的大匾上写着:陇上大禹。
据说近年来,在韩正卿工作过的地方上,老百姓不忘他的功德,要给他立碑。
有一种责任叫坚守
我常常在工作之余,站到山顶上看周围的这片土地,看这片山岭相连的高原:它是平静的,也是起伏的。像在黄河里看风起云涌的波涛,满眼的黄褐色,到处是细碎的尘土。甚至在某些地方,连几棵正儿八经的大树都看不见,太阳的光晃在空中,把一条条土路和砂石路映得发白,柏油大道在夏日的阳光下如同一条黑色的巨蟒。高出村庄的是电线杆,金属的线反射出尖锐的光。空气中飘着许多发明的东西,像太阳下的碎片,干旱多灾的村庄就罩在一团黄白色的大雾中,所有的庄稼和包括一切耐旱的植物都是一种浅绿色的存在。憨厚老成、质朴无华的甘肃人,至今仍一代代保留着远古的淳朴民风,他们中的基层干部,也是坚持用奉献履行着责任,用忠诚诠释着爱民情怀。
全国劳模、民勤县宋和村党支部原书记石述柱,就是这片大地上这样一个典型。
石述柱生活的宋和村地处民勤县西沙窝,东、西、南三面被沙漠环绕。民勤地处河西走廊的东北部、巴丹吉林沙漠和腾格里沙漠之间,全县总面积90%以上被漫漫黄沙覆盖,被称为“无边沙海一叶舟”。就是这样一只小舟,还遭受着沙漠以每年八至十米的速度推进蚕食。1955年春天,19岁的石述柱担任村里的团支部书记,联络志同道合的年轻人,组建起一支30多人的青年治沙突击队,背着口粮,带上工具,开始治沙的第一次征战。从此几十年如一日,直到“把自己种进沙漠里”。他一生所有的工作就是当初入党申请书里写的那一句话:豁出一辈子,做好一件事!这件事情就是治沙。
石述柱在残酷的命运和困难面前从不低头、不服输、不怨天尤人。这种屡挫屡奋、不懈抗争的勇气,这种挑战风沙、造福乡亲、矢志不渝改造宋和的信念,使他成了宋和人的主心骨,也使他感觉到治沙对他来说已是一种担当,一种责任。在历任了大队团支部书记、民兵连长、副大队长、大队长、大队党支部副书记之后,1963年,27岁的石述柱被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他暗自发誓,脱皮掉肉也要根治沙患,把宋和建设好。并对乡亲们承诺:“我就是豁出命来,也要治住风沙,挖断穷根,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为了履行自己的诺言,石述柱带领宋和人,用胸膛挡风,用脚步盖沙,用指甲抠树坑,用汗水浇苗,用智慧护林,他用肩扛手刨的原始压沙方式,为宋和村筑起了一条长9公里、宽2.5公里的万亩林场,将沙漠牢牢挡在了风沙线以外。这道绿色屏障保护着全村3000多亩的耕地,每年还为宋和人创造着近300万元的经济效益。从上世纪90年代起,宋和村栽种的2000亩红枣也进入成果期,昔日的乞讨村变成了金疙瘩村。他的治沙模式,被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命名为“民勤模式”。他给宋和人带来的,不仅是几代人的幸福,而是一座精神的丰碑。
石述柱作为土生土长的宋和人,为当地老百姓创造了真真实实的幸福。而王万青则是从上海进入甘肃大地的青年,在“地图上圈定了自认为祖国最需要、最艰苦的地区”——甘南藏族自治州,度过了他人生最宝贵的时光,为那里的老百姓谋求福祉和安康。
王万青1944年12月出生于上海。1968年,24岁的他在当时卫生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上海医科大学完成了六年学业后,面临人生的第一个抉择。这个在上海出生从未离开过上海的孩子,在时代的召唤下来到偏远的阿万仓乡。在这个方圆1000平方公里,共有牧民3000多户的草原上,在远离家乡,长达40多年的行医生涯中,他多次在牧民帐篷中救死扶伤:在牛粪堆上为大出血休克的产妇实施胎盘剥离术;在夏窝子(夏季放牧点)中彻夜守候、人工呼吸抢救患肺炎心衰的新生儿;在牧民帐篷中为一个70岁的老人成功做了肛瘘手术,解除了困扰老人大半辈子的痼疾;成功地从死神手里夺回一名急性高原肺水肿牧民的生命……
在阿万仓工作的20年间,王万青为了藏族人民的健康幸福,与当地藏族姑娘结婚成家,夫妇骑马并肩,不离不弃,坚守高原大地,走遍了阿万仓草原的每一个帐篷,为生病的牧民群众送医送药,为每一个适龄儿童及时接种,为全乡3000多人建立了门诊病历,使全乡90%的牧民有了自己的健康档案,他本人也被评为感动中国2010年度人物,2010年获“第七届中国医师奖”,2011年被评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有一种坚守叫执著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几个在中国大地极具轰动效应的甘肃女农民,影响深远,其中有以修梯田闻名的冉桂英、有以妇女解放运动闻名的“刘巧儿”……
我曾遗憾地感到,在近40年的时间里,对她们几个的书写除了零零星星的通讯报道,没见到有影响力的纪实文学作品问世。直到2012年,《飞天》策划组织的纪实文学专号,似乎才填补了这一空白。灯下展卷,屏气读完,夜不能寐。直觉告诉我,一个纪录历史人物的时代来临了,人们心头将重新燃起一个时代的火炬。
主人公冉桂英从小就生活在山大沟深、土地瘠薄、苦甲天下的地方,过着这个世界上“像土豆一样的”最艰难的生活。滥垦、滥伐、滥牧、滥挖,使这个地方的老百姓,每人每年只打四五百斤粮食,却相当于每年向黄河输送430吨泥沙;每生产一吨粮食损失157吨土壤;即使挖一平方米草皮能得到五两草根,即使草场退化得20亩才能够养活一只羊,但人们还是使劲挖。定西人在好长的时间里“吃的回销粮,穿的黄衣裳”……
马一龙在《农说》中认为:人的合理作为可以弥补自然资源的不足,通过巧种实干,可以取得人力胜天的成绩。冉桂英作为当地出生的农民,带领大家通过修梯田的土办法,决心改变这里的山川。冉桂英忍受了生活的打击和磨练,一锨一锨铲地,一筐一筐背土,一株一株植树,执著地带领她的乡亲们,避开了风言风语,谱写出了一曲曲治山治水的动人篇章。在天寒地冻,大家都动摇了修梯田念头的时候,她却一面做鼓动工作,一面自己带头苦干。冻土震断了这个弱女子的镢头把,换一根她再挖。虎口震裂了,她用布条包一包继续干,直到厚实的冻土层被揭开。遇到没有月亮的夜晚,就打着灯笼去干活。等到收工时,每个人的衣服上都会结一层冰甲,走起路来喀嚓喀嚓直响。从1964年到1983年的近20年间,大坪村平均每年以130多亩的进度,兴修高质量梯田2700多亩,基本实现了梯田化,有效地控制了水土流失。山水在这里的确得到了改变!
就这样,冉桂英和她的乡亲们不仅改造了大坪的自然条件,大坪的梯田建设也带动了定西全地区的梯田建设。定西人前后投入了两千多万个劳动力,挖动土石方一亿立方米。如果把这些土石方筑成一米见方的土石墙,足足可绕地球两圈半!目前,定西已经修了接近600万亩梯田。用埃塞俄比亚救灾局局长赛纳西的话说:“过去我感到中国人的骄傲是长城,现今中国人的骄傲是将山坡修成平地,这项工程比长城更伟大,更有意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惹得”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几乎年年来定西,“目的就是看看这篇复兴黄土高原的大文章是怎样写的”。他生前多次提到,“必须为黄土高原恢复名誉”。他说:“黄色是绿色的底子,贫困可以征服。”2009年,经水利部组织专家组对定西市安定区(原定西县)梯田建设进行全面考评验收,并被命名为“全国梯田建设模范县”。昔日的跑水、跑土、跑肥的“三跑田”变成了保水、保土、保肥的“三保田”。几十年前,大家靠铲草皮做饭取暖,现在,他们依托水土保持生态建设,逐步形成了种草养畜和生态建设的良性循环。
现在看来,冉桂英在定西修的是生态意义上的梯田,也是心灵意义上的梯田,这里面包含的更多的是“精神的梯田”。我们从作品的细节描写里可以看出冉桂英当时的生活场景:
侧面的小房子里是各种劳动用的工具,有架子车的轮胎,轮胎上的花纹都磨平了。一根木头扁担立在那里,裂缝的地方钉了25颗钉子。它是冉桂英用过的,女儿李翠花也用它挑土修梯田。它挑过多少土,那是说不清的。
有一个马蹄表,绿色的铁壳,玻璃上有一层擦不去的尘垢,时间停在6:15,是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的六点一刻?没有人知道。翠花说,这表是什么时候买的,她也不清楚。但她说很早了,是她母亲冉桂英用过的。冉桂英也说到过这只座钟,起初修梯田时掌握不准时间。有了这只钟,就好办了,上了闹钟就会按时起床了。它的时间里储存着冉桂英最珍贵的一段人生。
拧几下,上了发条,它以为是主人回来了,又要修梯田了,赶紧嘀嘀嗒嗒地奔走起来。声音依旧清脆有力,充满刚性。钟一响,时间又复活了,又有了灵气,有了生机。它的声音是那么坚定不移,一刻也不松懈,一刻也不停留。
一个村庄的变迁就源于这个普通女人。在半个多世纪的历史长河里,虽然她和她的时代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都被时间悄悄地湮灭,就像一个秋天对一棵树的光临,不易觉察,曾经的辉煌也无声无息。冉桂英正在慢慢老去,她所创造的近似神话的劳动奇迹在这里留存了下来,沧桑的命运每每被人念及。
冉桂英现在仍然生活在定西,除去时代的光环后是一个勤劳、善良、本分的农民老太太。
另一个甘肃女性的生活轨迹,有别于在枯焦的命运中奋争了一辈子的冉桂英,她就是上世纪40年代在甘肃华池革命老区,为了真爱勇敢地反抗旧的婚姻制度,在四周铁板一样的封建环境中,执著地爱着自己所爱的人,终于好事多磨,好事成双的封芝琴。她离奇的抗婚故事被编成戏曲、说唱,并在1950年以《刘巧儿》的名字搬上银幕。
故事的背景还是这片土地,还是在甘肃偏僻寂静的荒野上。但“刘巧儿”大胆追求美满爱情后,大名就红遍大江南北,成为推进和实施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以及妇女解放运动中的楷模。“刘巧儿”像一组生活的画卷,不仅勾勒出了一个时代的背影,更描摹到人物内心,喷发出一个特殊时代灼人的情感热流,“刘巧儿”也成了甘肃人在苦难环境中勇敢追求人生幸福的时代符号。
就这样,我们看到《飞天》刊出的七篇纪实作品,有的虽情未尽抒,意未尽达,却皆蓄才酿势,厚积薄发,用事实说话,用细节写意,深刻凝聚和阐释了“甘肃精神”内涵,具有撼人心魄的力量。记得老作家孙犁曾说过:“作家,要忠诚于我们的时代,忠诚于我们的人民,这样求得作品的艺术性,反过来作用于人民。”在当前,我们已不能不注意到文学作品教化意义弱化甚至废弃的倾向。许多文学杂志特别是影视期刊,都不愿表现时代和英雄,拒斥政治和文学的联系,甚至那些境界阔大、思想深刻、气魄宏伟的作品数量也在减少,同时发表和上演也日见困难。这次《飞天》的组稿,将给我们提供一个新的例证:我们所处的社会和时代是能够产生这种汹涌澎湃、鼓荡不已的豪迈纪实作品的,而这种作品也将产生积极的影响,发挥出它的号角和鼓点作用,起到精神铭石和典型模范的作用。在重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今天,它强烈燃烧的情感、饱满贲张的情绪、昂奋亢进的时代激情、为他人谋福祉的道德标准,是应和了时代要求的,是和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律动合拍的,也是与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大背景相一致的。
本期责任编辑 子 矜 阎强国 郭晓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