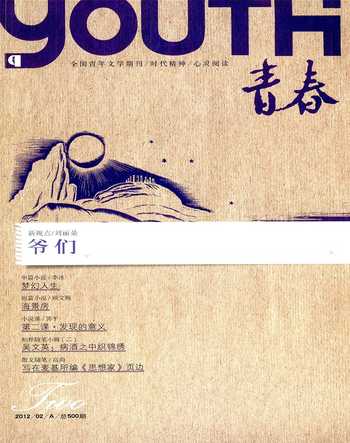卖刀的人下落不明
孙建国是我小学同学,现在他在哪里我不知道,是不是还叫孙建国我也不知道。十几年没见,他可能已经死了。
最后一次见他是在镇外的田埂上。田埂南北走向,东边是大片的水田,水田的尽头是被绿阴包裹着的村庄;田埂西边是一条河,名字叫做江宁河。我就读的中学在田埂西边往南。
当时我读初二,孙建国也应该读初二,但他没有。初一即将结束时,孙建国把学校看大门的老头打伤了,此类老头必然是校领导的亲戚,于是他被管教半年。出来后,孙建国就在镇上混。很快,他混得有点名堂了,据别人说,他已经身在本镇十大恶棍排行榜前列。但他具体怎么混,我们很模糊,偶尔听到他的消息就是打架、偷东西,跑到学校门口抢学生的钱。均战果辉煌。偶尔看到,他都是很沉默很镇定的样子。他对我们几个从幼儿园开始就一齐上学的人还算不错,经常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以为他要钱,但不是,他总是问我们有什么需要帮忙,然后在我们的惊恐中颓废地走开,带着失落。我们都不觉得他坏,甚至会突如其来地羡慕他。
我要从孙建国手里买两把刀,一把用于后天和周长林单挑,另外一把我准备单挑时藏在身上。我坐在田埂上等孙建国,自行车在我的背后,斜斜地撑在那边,一碰就倒的样子。我不会吸烟,但还是点了一根。不能让社会上的人看不起,我想。在想着要不要来第二根时,孙建国出现了,身子弯成弓形架在自行车上,两条腿一高一低的,向外突出去时,膝盖似乎要脱离他本人。孙建国在我面前停下来,双脚结实地踩在地上,两把刀被扔在地上。孙建国有两米高,而且还在长个子,坐在自行车上都比我高。两把刀在地上交叠在一起,看上去像是一把剪刀,如果再拨弄一下,就像一个十字架。我先递上香烟。红塔山,孙建国说,然后没经过我同意就熟练地把一包烟都拿走了。四十块钱吧,我问他。我把钱递给他。还有多少钱?孙建国问我。家里人给我买衣服的。不多了,我又说。再给我一百块钱,我帮你搞定那个人。我想了想,出于对单挑的恐惧,答应了。之前我没有单挑过,之后也不曾有,我真是一个害怕竞争的人。
我把刀塞进书包,然后我们并排骑车往回走。朝北,一会就下了田埂,上了马路。当时马路上还没有铺柏油,坑坑洼洼的。在我们往回走的时候,天突然变了,乌云压顶。一路上孙建国的膝盖好几次碰到了我的腿,我装作没有发生。我听着孙建国说他的事情,他的话让天都暗了下来,因为他总是说一些在我看来和黑暗有关的事情,总是说他在录像室里打架的事情。录像室我常去,看到的总是一个闪亮的屏幕和很多个漆黑的脑袋。因为要读书,我每次去都不会待太久,而很多人都非常愿意死在录像室里。
孙建国和小混混们不一样,班上我所熟悉陈付才、仇昌国、孙元宝那些人,说话都很快,大呼小叫,眉飞色舞,孙建国说话时总是有气无力。所以我觉得他很厉害,沉默的恶棍是最可怕的恶棍。我只是见缝插针地问他怎么对付周长林。他不说话,又突然冒出一句,我有办法。一路上,孙建国基本上是脱手骑车的,双手插在口袋里。在转弯时,他才伸出一只手扶一下车把,简直就是敲一下。很多和我们擦肩而过的人都认真地看看孙建国,不知道他们在羡慕,还是在诅咒他被撞死。
骑到万松时,我问了孙建国一个问题:那,现在你是不是还和王梅在一起。他说是的,然后又不说话了。过了一小会,他忽然掏出双手抓住车把,猛地骑起来,冲向前面的上坡。上坡的尽头是个天桥,不过天桥不是给人走路用的,而是灌溉用的,桥背部,也就是桥上面是个水渠。过了天桥,是一个很长的下坡,孙建国又把手放进口袋,任车子冲下去。下坡结束后我再下一个坡,就到家了。我刚到家,就下雪了,一会儿就变成了鹅毛大雪,眼前迷迷茫茫,什么都看不清楚。我放好自行车,把书包拎在手里走到家门口。我往对面的马路上看,路上没有人,平时就不多,现在大雪,似乎连树木都变少了。不过孙建国肯定在我看不见的那一段路上吱吱呀呀地骑着车。他的家在山脚下,要绕个大圈子才能到。照他的样子,他连大腿内侧都会积雪的。
第二天,我六点半出门骑车去学校,七点十分早读课,不能迟到。一般从家到学校要二十分钟。因为下雪,母亲让我提前二十分钟出发。路过江宁镇的时候,我看到了周渊红。她是我们班,甚至我们学校最漂亮的女生,几个刚刚毕业分配来的男老师被她搞得团团转。她正在往学校走,平时她也都是步行。我骑到周渊红旁边时,对她说:我带你。她同意了,赶紧几步,跳了上来。因为知道雪后路滑,她抱住了我的腰。她抱住我的腰,我逐渐觉得腰乃至全身都软弱无力,车子东倒西歪的。车子稍微倾斜,周渊红就会用力抱我,往左歪的时候我感到左边被抱紧了,往右边歪的时候我感到右边被抱紧了。她似乎很清楚她在用力抱着我,于是在倾斜时,她抱得更加用力。
我突然问周渊红,你喜欢杨键还是陈增才?她笑了笑,没有说什么。那周强呢?她叫着说,你问这个干什么啊。我说我们都看到你跟周强在办公室里不出来了。周渊红不说话了。我也没再问什么。从镇上到学校的路太短,只有几百米吧,我们说了几句话就已经到了学校门口了,一些学生正在下车,然后推着车子往校园里走。他们可能看到我和周渊红了,我不觉得不好意思,而是希望更多的人看到。可是周渊红对我没什么感觉,其他人如果骑车带她,那也可以。我想她现在对年纪大的人有兴趣,女孩都是这样的,于是在那个下雪的清晨我异常渴望自己能早点长大。
我和周渊红并排走着,没什么话讲。她忽然问我:你为什么要和周长林打架?你怎么知道的?她装腔作势地说,这个你就不要管了,我的信息很灵的。我告诉她,因为我把周长林的书本给撕了。当时,我们在期中考试和期末考试时,班级之间互相换教室防止作弊,我们坐到别的班级去考试。那天我们到三班去考试,我考完了之后在周长林的抽屉里看到一个蛮好看的本子,就拿出来看着玩,然后就把它撕了。为什么要把撕掉啊,看就看好了。周渊红笑着问我。因为上面写的全是情书,而且写得很流氓,说是要把一个女的脱光了,绑起来。那你也不要撕书啊,又不关你事,你就不应该看。周渊红开心地说。上面的情书全是写给你的,我说。周渊红看看我,然后低头,装作没发生什么事情。我接着说,然后周长林就来找我,我们先是骂,然后约好时间,在学校后面的田埂上单挑。周渊红突然不高兴,我后悔了。
到了车棚,我低头锁车,周渊红没有等我,自己先去了教室。我看看教室那边,忽然想到了周长林,他今天要倒霉了。或许是明天吧,因为今天大雪,孙建国可能不会在这种天气到处跑。教室里乱糟糟的,每个人的鞋底都有水,地面也是黑的,这让教室似乎矮了下来,整个空间感觉非常压抑。
后来,天气放晴了,我们在教室内外乱蹦乱跳,到了下午,我们去操场锻炼,练习中考要考的三项。在操场上我看到了周长林,他很神气,也很可爱,看上去简直像一个朋友。但他很快就要倒霉了。
再后来,周长林似乎一直都没什么事,孙建国也再也没有出现。我不知道这两者之间有没有联系。一转眼十多年,我再也没有见过孙建国,甚至连他的消息都没听说过。而孙建国如果出了什么事情,我应该知道的,我们两个人是一个村子的,村子就那么大,有什么大事谁都会知道。但我什么都不知道。
后来,在我等孙建国的那个田埂上,盖起了一座教堂,孤零零的。教堂的东边是大片的水田,水田的尽头是被绿阴包裹着的村庄;西边是一条河,名字叫做江宁河。我怀疑教堂的位置就是在我坐着的那个地方。那个教堂我没有进去过,很多次,我远远地看到很多老人以队伍的形式走进去,或者走出来。有一天,我看到一个明显不是老人的人,站在教堂门口。那是个神甫,个子很高,大概有两米。我立刻以为那是孙建国,马上又知道不是的。不过,我故意说那是孙建国。
我经常对不认识孙建国的人说起他的那些事,最后的结局,我是这样编的:
后来,在我等孙建国的那个田埂上,盖起了一座教堂,孤零零的。教堂的东边是大片的水田,水田的尽头是被绿阴包裹着的村庄;西边是一条河,名字叫做江宁河。我怀疑教堂的位置就是在我坐着的那个地方。孙建国呢,就进去当了神甫。他不打架了,也不偷东西了,也不到学校门口抢我们钱了。他也没有和王梅结婚。估计,他很清楚自己不当神甫也不能和王梅结婚,于是就去当神甫了。王梅的父母都高兴了,像是翻身解放了,从此摆脱了两米多高的孙建国。孙建国的父母也很高兴,因为村子里的人开导他们说,当神甫,除了不能结婚什么都好,要不然孙建国肯定是被抓起来坐牢,关好几年,出来以后还是干坏事,再抓起来,再坐牢。总有一天被枪毙掉。现在有吃有喝,又不用干活。孙建国当了神甫以后,脸慢慢红润起来。我经常去看他,其他几个从小长大的人也去找他玩。他每个星期回家一次,朝北骑一会就下了田埂,上了马路,二十分钟不要就到家了。
孙建国很有意思,总是表情严肃,总是把一只手按在胸口,对谁都做出很虔诚的样子。他胸口挂一个十字架,晃来晃去的,好像马上就要掉下来了。
责任编辑⊙育邦
作者简介:
李黎,1980年生于南京,1998年开始写作。现供职于凤凰传媒集团江苏美术出版社。在本刊发表过多篇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