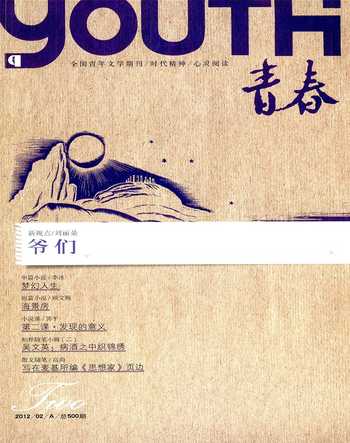吴文英:病酒之中织锦绣
柏桦
如果有人问我,最喜欢宋代哪位诗人,我会脱口而出:吴文英(按:我当然知道吴文英是词人,但我更乐意叫他诗人)。为什么?道理很单纯:根据心理的对立原理,人不想成为自己,想成为另一个人,用现代的术语说,即人想成为他者。文弱的李贺也才会叹唱:“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南园十三首(其五)》)以此类推:吴文英的长处正是我的短处,如是,我当然会喜欢他了。那么吴文英有哪些长处呢?吴癯庵在《词学通论》中说出了一段我不必亲口说出的话,他认为梦窗的诗词:“以绵丽为尚,运思深远,用笔幽邃,炼字炼句,迥不犹人;貌视之,雕缋满眼,而实有灵气行乎其间。”的确,他那“雕缋满眼”、潜气内转的浓丽字句,绮旖芬芳、镂金刻翠,我是运用不来的,但对其个中手腕却极为艳羡。因此,对于张叔夏说他的词“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折碎下来不成片段”却深不以为然。
梦窗的诗词组织之工细,布局之精妙,在其长调中最可见出,犹如下面将要引来的《莺啼序》,此诗词构造井然,不拖沓亦不板重,转身运气丝丝入理,且又法度谨严。那正是如近人吴学廉所说之模样:“肴馔百家有人在,楼台七宝自修成。”马志嘉、章心绰在《吴文英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06年版)中亦附和赞曰:“梦窗琢炼字辞,精于造句,固多警策,超逸处则仙骨珊珊,幽索处则孤怀耿耿,即分摘数语,亦闪闪有光,超凡入妙。‘不成片段之说,不知有何之本。”三人所说甚合我心,文英那“眩人眼目”的七宝楼台之绵丽诗句从来便是我的至爱;而对于有些人(如王国维,见后)说他“隔”或完整性不够或晦涩凝滞等,我不但不仅不以为然,也完全不能同意。这一意思,我曾在另一篇文章《论江南的诗歌风水及夜航七人》中说过,下面引来便是:
“比如喜欢赤裸裸的纯粹感情的王国维等人,就当然不会喜欢南宋的文人词,而作为其代表的吴梦窗等人,当然也就只能成为受批判的对象了。”(参阅村上哲见:《吴文英(梦窗)及其词》,《日本学者中国词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306页)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认为:“词人者,不失赤子之心者也。”他首推李煜,并批评南宋词,认为“隔”。他又说:“白石写景之作,……虽格韵高绝,然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梅溪(史达祖)、梦窗诸家写景之病,皆在一‘隔字。北宋风流,渡江遂绝。”(见《人间词话》)国维此说差异,犹如以上引文中被日本学者村上哲见所讽刺的那样,他只能喜欢那些“赤裸裸的纯粹感情”流露的诗,作为一代大家,这样的思路未免太狭窄简单了吧。须知诗乃“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的事业,它的本质是“尽可能多地包含技艺的快乐。”(罗兰·巴特的一个观点)我就在文英的诗词中享受了他那技艺的快乐,仅此一点,就足够了。而且南宋文人词,尤其是梦窗的词“在形式、修辞以及音乐性方面已达到高度洗炼。”(村上哲见)给予这烂熟至纯的诗词技艺以中国文化的精粹地位应是情理之中的事。再说,风流何绝?渡江之后,风流在江南大盛也!
的确,有宋一代,尤其是南宋,吴文英堪称是最能深隐秀丽地把玩汉字的诗人,他对诗艺的讲究,如他自己所说:“音律欲其协,否则成长短之诗。下字欲其雅,否则成缠令之体。用字不可太露,露则直突而无深长之味。发意不可太高,高则狂怪而失柔婉之心。”由此可见梦窗在形式上的别构一格,而且还可见他对刘勰《文心雕龙》的《情采》篇中“形式”的意味是玩味至深的:“虎豹无文,则鞹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为此,面对这位形式主义大师,《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才会将他比之为诗中的李商隐:“词家之有吴文英,亦如诗家之有李商隐。”
说了上面这几大段入话,下面让我们推开绣户来看另一片风景,即来共赏(并非细读)吴文英的《莺啼序》(一首宋词中最长的音乐),且看他是如何在病酒之中织成锦绣诗篇的:
残寒正欺病酒,掩沈香绣户。燕来晚、飞入西城,似说春事迟暮。画船载、清明过却,晴烟冉冉吴宫树。念羁情游荡,随风化为轻絮。十载西湖,傍柳系马,趁娇尘软雾。溯红渐、招入仙溪,锦儿偷寄幽素。倚银屏、春宽梦窄,断红湿、歌纨金缕。暝堤空,轻把斜阳,总还鸥鹭。幽兰旋老,杜若还生,水乡尚寄旅。别后访、六桥无信,事往花委,瘗玉埋香,几番风雨。长波妒盼,遥山羞黛,渔灯分影春江宿,记当时、短楫桃根渡。青楼仿佛,临分败壁题诗,泪墨惨淡尘土。危亭望极,草色天涯,叹鬓侵半苎。暗点检、离痕欢唾,尚染鲛绡。亸凤迷归,破鸾慵舞。殷勤待写,书中长恨,蓝霞辽海沉过雁,漫相思、弹入哀筝柱。伤心千里江南,怨曲重招,断魂在否?
话说《武林旧事》卷第五“湖山胜概”中“南山路”这一条目,其中便提到了当时南宋临安涌金门外的一座楼宇——丰乐楼,此楼据《淳祐临安志》载“据西湖之会,千峰连环,一碧万顷,柳汀花坞,历历栏槛间,而游桡画鷁,棹讴堤唱,往往会合于楼下,为游览最”。这可是一座了不得的楼,骚人、墨客、缙绅常聚于此行诗酒文会,吴梦窗在淳祐十一年春“尝大书所赋莺啼序于壁,一时为人传诵”。宇文所安曾用戏剧性的笔法在《绣户:回忆与艺术》(《追忆》)一文中描绘过这一幕:
让我们从十三世纪中叶杭州郊区的一座楼阁开始,时间是晚春。从这里的花园可以清楚地看到西湖,西湖边上的柳树冒出树叶,看上去像是有一层淡淡的绿雾。在花园里漫游的是这座大城市的艺术界中的精英——诗人和词人,富有的鉴赏家和业余爱好者,还有几名杭州城里最有名的妓女。
在这一天各种各样的游乐中,有一项特殊款待,即演唱吴文英新作的词,吴文英是当时最负盛名的词人,由于他精通音律、在风格上喜欢堆砌典故辞藻,以及他的词能够表现出细腻的感情变化,因而备受时人推崇。词评家们对这些特点在词的发展史上所起的影响是好还是坏或许会有争论,但是,对他的作品作为整体而具有的特点,则是持一致意见的。正如与他同时代、比他年轻的词评家张炎指出的,他的作品“炫人眼目”。今天,吴文英要向来客献出他最新的一首作品,一首寄调“莺啼序”的新词,“莺啼序”有四阕,是宋词中最长的一调。
接下来,宇文所安以新批评的细读手法,展现了他那一贯高超的阐释能力,从“回忆与艺术”这一关键点入手,他指出此诗的“写作使回忆转变为艺术,把回忆演化进一定的形式内。所有的回忆都会给人带来某种痛苦,这或者是因为被回忆的事件本身是令人痛苦的,或者是因为想到某些甜蜜的事已经一去不复返而感到痛苦。写作在把回忆转变为艺术的过程中,想要控制住这种痛苦,想要把握回忆中令人困惑、难以捉摸的东西和密度过大的东西;它使人们同回忆之间有了一定的距离,使它变得美丽。”作为读者,我们亦深有同感,一遍读过,我们看到的正是这样一幅画面:吴文英在室内“病酒”之中隔了一段距离,“春宽梦窄”地编织着一篇锦绣诗章,使其痛苦的回忆渐渐变得美丽。
那么吴文英有什么痛苦的回忆呢?说到这里须略略交待一下他的生平。文英早年居苏州,三十多岁后一直生活在杭州。他一生基本上都是以幕僚、清客身份在这两地消磨。因此他一生所吟诗词都以这两地为最。之外,他曾纳苏杭二妾,后一遣一死,这在他的诗词中有大量记载,如:《渡江云三犯》、《莺啼序》、《画堂春》、《绛都春》等均是吟二妾之事。夏承焘在《吴梦窗系年》中也为我们指点了此事:“集中怀人诸作,其时夏秋,其地苏州者,殆皆忆苏州遣妾;其时春,其地杭者,则悼杭州亡妾。”知道了这节情事,我们对此诗回忆的对象也就十分清楚了。
此诗词总分为四:第一段从暮春的一天写起,以“残寒正欺病酒”一句破题,“这种突兀的开头紧紧抓住了听者的注意力”(宇文所安),我们的脊柱神经似乎也灵动了起来(借自纳博科夫一个有关阅读的观点),“残寒”并非惜春,“伤春起,却藏过伤别。”(陈洵)如是,文英才要“掩沈香绣户”。虽然因“病酒”畏寒而掩上窗户与门户,但燕子还是传来了湖上春色浓烈的消息,诗人的词思也禁不住柳絮的轻漾而飞舞起来。此处跳接显得轻快,毫不着力,仅一转身,就变了过去。
从第二段起,回忆正始登场:诗人与情人初遇西湖上的情景可谓历历在目,点点滴滴都十分精细传神,“锦儿偷寄幽素”声音和词色均好,当让人轻轻玩味、品尝,不必作手术刀式的解读。另外,文英所回忆的“十载西湖”恰是他过去的爱情与欢乐,不免让人联想到杜牧《遣怀》中一句英俊颓唐之诗“十年一觉扬州梦”,晚唐与南宋在此跨越了时空完成了一次缱绻的对话,这又是高山流水遇知音,真可喜可贺矣!
第三段,一上来便是突接,似峰断而云连也。在此,诗人翻着一笔,往深一步续写寻访中对往日情事的追忆,并点出佳人已逝,真是几番风雨葬花,唯有“泪墨惨淡尘土”之中了,而离情别绪又恰似“此恨绵绵无绝期”。
末段更是对亡妾的深情凭吊,“离痕欢唾”最可触摸感人,也是前后照应,如陈洵说:“‘欢唾是第二段之欢会,‘离痕是第三段之临分。”从“欢唾”到“离痕”,又应了此诗词的主题:美丽的回忆尽在伤春与伤别。
以上对梦窗《莺啼序》所作的内容串讲,并非我在此的重点,因此有必要简略。细心的读者应注意我在每段中拈出的一二个词句,这才是我的用意所在,即通过这几个词句,逗引起我们去吴文英的诗词中捶幽凿险,探寻那无数色泽不一的丽字,那里可是有太多的悬崖上的花枝在向风试探呀,也在向我们之中一些警惕的迎风者试探。而稍稍分心,他那水光云影、摇荡绿风的词句就会“抚玩无极,追寻已远”(周介存);他那“举博丽之典,审音拈韵,习谙古偕”(朱疆村)之沈邃缜密、缱幽抉潜的意趣和妙处便不能透彻入骨、体会至深。
如此说来,吴文英似乎留给我们这样一副形象:他在“试灯夜初晴”之后,又若“五湖倦客,独钓醒醒”;他的文字精深微妙,只缘于他是一位“苦工通神”、锻炼词句的诗人,或按现在流行的说法,他仅是一位文字的炼金术士。这样说当然无碍,但有一点,我要特别提出,在这一切之上,吴文英的气格特别沉着致密,正是由于他这一非凡之特色,才使其能运用“锐感,即用敏锐直接的感受来修辞。”(叶嘉莹)而“锐感”也正是他发力完美之所在,天才之所在。又犹如《莺啼序》起首一句“残寒正欺病酒”,颓唐文人的缠绵形象一下子就被吴文英敏锐地感受到并呼之欲出了,当然吴文英炼字的神秘也在此被叶嘉莹的“锐感”当场捕捉了。顺便说一句,叶嘉莹还说过一句直抵我内心深处的话:“我个人以为吴词不是姜白石所能赶上的。”(见叶嘉莹:《唐宋词十七讲》,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401页)最后,我要以如下结语为本篇收尾:吴文英那“病酒”之中织成的锦绣(《莺啼序》),既有他炼字的神功,也有他天生的“锐感”在暗中相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