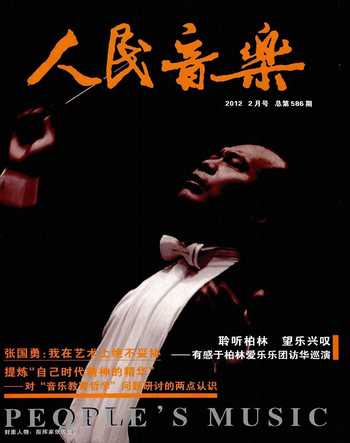关于现代音乐的重新思考
特瑞斯坦.米赫耶
译者按特瑞斯坦·米赫耶是一个蜚声国际的法国作曲家、频谱乐派创始人之一,1947出生在法国Le Havre,曾获得古典阿拉伯语学位、经济学学士学位和巴黎法政学院学位,现为法国里昂音乐学院作曲教授、上海音乐学院客席作曲教授。1967年他师从巴黎音乐学院梅西安(Olivier Messiaen),1971年获得第一作曲奖文凭,同年被授予罗马大奖。早期的创作风格包含一种持续的混合声波,声音含糊不清,或者是不让音乐有真正的发展。近期的音乐则把自然之声的频谱通过电脑分析、合成并使之完美融入到乐队之中,试图使音乐达到一个细分的、清晰的、充分发展的又不可预测的极端状态。
在频谱音乐大行其道的今天,上海音乐学院第三届当代音乐周于2010年11月2—5日,有幸邀请到这位伟大的作曲家作为驻节作曲大师,开设大师班、举行两场讲座,并安排法国时代乐团]奏一场他的《航海罗盘》室内乐系列作品音乐会。他的讲座与音乐让不少专程为他远道而来的听众获得了巨大的惊喜!
为了进一步研究他的创作思想,译者特邀他提供一篇具有代表性的短文《重新思考》,以飨中国读者。其严肃的创作态度、深邃的重新思考,对我国音乐界研究频谱音乐以及他个人的音乐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让人听首曲子要占用他的时间,因而要占用他的生命:作曲家等于窃取了每个听众的一点生命。这是否意味着现代音乐不如现代视觉艺术大众化、容易理解呢?是的,人们参观画展时可以自己把握时间,遇上不喜欢看的可以移步其它。相反,听音乐时人们的时间受到作曲家的控制,只能随着音乐的流淌而步步推进,这也使作曲家感受到一种强烈的责任感。
这种责任感使得音乐创作既不能只作纯粹的实验,也不能摈弃所有的探索,它应该提供有趣的、看似新鲜的(也是大胆的)、让听众可感知的、可接受的理念。即便作曲家试图创新或寻找极端复杂的创作方法时,以下的这个原则依然是正确的:即必须把作曲家与听众之间相同或相近的视角作为创作的共同基础。
这种要求使得作曲家不应停留在自我满足,任凭自己以一些音乐机构、管弦乐队或听众习惯的模式和廉价的赞美来进行音乐创作、来窃取他人的生命。不幸的是,这已经成为作曲界的一些发展趋势了:要么无视与听众交流,要么成为假学院派(强调概念不清的后现代和伪音乐学或伪哲学的一些观念)。
经常有人声称,“先锋派”立于“频谱音乐”身后,两者之间的距离与我们的前景只留给我们一种选择,那就是“后现代”。然而这种观点在我的日常作曲工作中没有任何效应。目前我在继续探索一些新观念和挖掘一些新材料。一部分探索基于技术层面,在新的信息技术工具或光谱分析方面寻求新的途径;另一部分探索则是每日在纯音乐与美学方面寻求创新、挖掘新的发声体或音乐发声体并有效利用这些新材料。何为“新”?当我听到某种我想说但尚未被我自己或别人说过的东西谓之为“新”。独特的新构想不能通过循环再生旧的材料来表达,新的观念应当提出新的材料。正是由于我们的世界观肩负着太厚重的历史负担,“先锋派”概念才让我们自动退回到50年代。如果我们继续停留在词源学上,老是通过定义把我们定性在“先锋派”里——那就大错特错!这是我们文明的倒退与死亡,它使我们真正地蒙羞受辱!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频谱运动”曾一度被认为是对“先锋派”的反叛。这在当时是针对一些作曲家把“先锋派”视作头等重要而发出一种抗议,尤其是反对他们拒绝对人类的听觉感受的现象作出一点点儿的让步。音乐探索并不是在乐谱上用一些抽象的组合制作而成,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与这种音乐姿态做斗争的原因。对当时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统治乐坛的“先锋”音乐持批评态度的并非仅仅是我们,前面我所描述的那些把持音乐界的伪学院派也指责“先锋派”是把听众赶出音乐厅,使听众神经错乱的操纵者。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批评还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们还有比责难更好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最初涉及频谱的音乐作品只不过是肤浅地使用频谱,不是有意识地运用频谱,当时缺乏一些必备的工具和必要技术和科学知识。在首批频谱音乐中,比如Gérard Grisey为18件乐器而作的《分部》(1975),频谱的运用还非常青涩,人们只找到一个长号的伪频谱。当时我们大多使用一些模拟电子系统:调制圈、反馈、延时和抽象泛音列组合的压缩。我的第一首被确认为具有个人风格的曲子是为圆号和室内乐而作的《忆—蚀》(1976),其主导模式是一个反馈系统。这首乐曲不是真正的频谱音乐,因为它没有建立在频谱的基础上,但是至少我着意尝试着把频谱和乐器的色彩置于乐曲的某些经过句的和声结构里(比如使用第三或第五泛音的强力度部分、十二和十七度音程、弦乐在码上]奏等等),以及尝试着发展一个在音色与和声之间的连续听觉。在这首早期作品里特别突出的是一种观念,是一个变化过程。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变化过程和连续转换的理念在频谱音乐诞生以前就已经出现。至于我,总是热衷于一些客体和创造性混合体的转化,这几乎是我与生俱来的。回顾以往,我认为,这些关于和声组合的观念,使得它能完全控制和服务于结构形式,这就是频谱音乐的基础。它确实是一种崭新的音乐写作方式,或许是音乐创作中最具冲击力的一部分了。在结构形式的层面上,这种音乐建立在与公共通用技术完全不同的原则基础之上,它通过繁殖扩散来发展音乐,如同相对论与辩证法使用体系的原理,在音乐结构中舍弃那些易于辨认的东西。这种方式比奇异的音响更令人吃惊,我甚至认为它是频谱音乐里最具创新的一面。不同于那些肤浅但被广为流传的观点,我所经常看到的则是,大部分听众被我的音乐所打动的不是通过细腻的和声或音色,而是通过乐曲形式所产生的冲击力,只有极少的听众才会真正欣赏到这种细腻的用心(我们应该现实一点)。尽管音色具有吸引人的自然外表,但不容易为听众所感知。我认为这些细腻的处理是必须的,其理由我已经陈述:我们希望以高质量的音乐回报给观众所付出的时间,即使那些东西没有即刻显示出来,我们也应该追求每个细节的完美(犹如日本庭院那种精心的设计和管理)。
在深入研究音色与和声时,我们最初的动机是希望开发一种控制音乐微妙变化的能力。但是,我们很快就开始觉得音乐可能会变得太具有定向性与可预见性,这就需要在音乐里重新引入一种可以出人意料、有对比和有终止的方式。与普遍的意见相反,其实这些因素从未在频谱音乐里真正地缺席,在第一批乐曲里(如《分部》)就包含了一些突变。在被视为这个时期具有象征意义的作品——我为管弦乐队而作的《Gondwana》?穴1980?雪里,其中就有连续性,也有许多终止和众多其他的转换类型:开始的经过句、移动意味的倒影、“灾难性”变化的爆发、压缩的变化过程、指定的变化过程等等,除了纯粹单一方向和持续]变之外,这些乐曲还包含一些其他的因素,我们也认为这种形式上的非连续性应该在频谱音乐中得到发展或]变,而不是遗弃。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毫不犹豫而又慎重地引进传统辩证法的思想,甚至包括旋律。我不得不花很长的时间重新在我的音乐里引入一些真正具有旋律意义的因素,以免回到过去的陈词滥调,陷入类似于“主题和变奏”的窠臼里。我想找到非常个性化的旋律轮廓,然而,对于极不需要旋律的今天而言,这是一件最棘手的事情。同样,在曲式结构上,我的目标既不是回到思辩性的浪漫派时期,也不是以发展动机片段的形式回归到五十年代的形式结构主张,而在他处寻找更好的解决方法,寻求一个富有逻辑性、连续性、明显强调的乐思片段。近年来我试图做的是服从于音乐逻辑之下,采用一种更灵活和更机动的(甚至更辩证的——如果人们坚持这一角度来看问题的话?雪、能够吸收对比的观念、紧张度的解决程式和其他众多布局的结构形式。要构建一种更复杂的结构,和声一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巨大因素。然而,明晰的音乐感知力在其发展形式中的作用仍然是无可置疑的。
区别于不断变化、而远离了原出发点的曲式结构, 频谱和声的发展在方兴未艾的科学和技术能力的协助下发展顺利。就和声来说,我接受一个非常特殊的概念:即我们所说的频率和声。我认为这一用语比“频谱和声”更恰当,因为它包括的和声组合远远超出纯粹的频谱组织。通过这种和声的办法,就有可能在整首乐曲里通过自然中的频谱类推,从而创造发明出一些新的和声?穴或音色?雪。我的大部分作品的构成实际上是建立在非直接的频谱构造上的,这就是我所说的频率和声。这些和声被设计成不相同的性格,甚至被调成了四分之一音或八分之一音,形成了无限的和声场空间而毗邻于色彩的空间。在这一领域里,对我们来说,和声与色彩是大致相同的东西。“频谱音乐”往往有一些惊人的音响被许多人认为这应归功于原来就有的深奥的管弦乐法艺术的制定。他们不了解其实这些音响出自于一些和声、一些音符以及它们所处的位置。或者宁可说,这些音高的结构和管弦乐法已经融为一体。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发现自己在发展与掌握和声这个领域中的意识与知识的努力比其他方面要多得多。尽管和声是多么地丰富与强大,但我很惊讶地发现,许多作曲家已经完全消失对和声这个范畴的关切。我清楚地记得80年代时,一些同事甚至讥讽我对和声如此地关注,他们认为和声根本就不存在。我的许多有缺陷的学生也都持有这种态度,他们对和声没有感觉。有时他们的音乐尽管具有很大的表现性,但最终站不住脚,因为其和声不支持他的音乐形式。和声通过自身与曲式结构的关系而强有力地影响着调性音乐。今天,人们往往过于缩减音乐中纯装饰的功能性。同时还有一些作曲家腻烦着音高。我认为,现在应该到了重新审视和声与色彩在音乐结构形式中所扮]的重要角色的时候了,这并非仅仅对“频谱音乐”风格而言。
直到今天,我才开始认为可以使用科学技术手段来实现儿时那些无法实现的、雄心勃勃的作品的梦想了。比如为室内乐队与电子音乐而作的《草原精灵》?穴1994年?雪,我认为自己成功地实现了当我20岁或甚至更早时的梦想。在这首乐曲里,复杂的组合声音的研究是在纯技术也同样在音乐的层面上进行的。它可能不会是即刻明显地体现出来,但这却无关紧要。其实,如果乐曲的“诗意”外貌所带来的影响可能更强于它的频谱内容的话,这种“诗意”完全取决于后者的精心构造。使得产生这种探索性的、创新性的和前卫性的精神都同时保留与统一在一种可以理解的音乐语言之中——这才是我真正的雄心壮志!
温德青 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副主任、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特约编辑于庆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