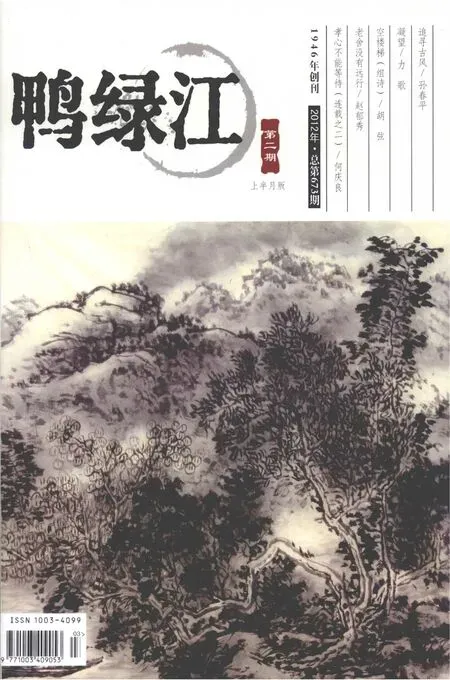春天的隐私
王新华,河南淮滨人,上个世纪60年代出生,农民,现打工于江苏吴江。近年习作散文若干,有文字见于《黄河文学》《天涯》《读者》《散文选刊》《散文海外版》等报刊,并入选年度选本。
陌生人
那天晚上下了班一身疲惫地回到家里,房东的女邻居(我们似乎还没有说过话)不里不外地站在我的门口,她说,我家的一拖拉机沙子倒在走道里了,你能不能帮忙给弄到院子里——我们给钱!我说,要说给钱,干了一天的活,现在不想挣钱了,要说帮个忙嘛,这没问题!听了我的话,那女人一脸的疑惑。最后,一声不响地走了。吃过饭我还是抹着嘴巴过去看了一下,两个男人已经在用箩筐往里头抬沙子了。看来,她已经拿钱找了别人。
默默地回到屋里,很有一点被人遗弃了的感觉。我也开始鄙视那个女人了:不相信别人会帮助自己的人,是一个可以帮助别人的人吗?
这个女人却又像是我身边的一汪水,通过她我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有一天,我们五个人要把一台近千斤的变压器装上拖拉机,试了两个回合,都没有成功。有的人还叫着说扭了腰。我们的不远处,有几个挖沟的汉子,我们几个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那里。可是,跟人家不熟悉,只是眼巴巴地看着他们,谁也没有上前。无奈之中,一个伙计只好到远处去叫他的一个老乡。老乡叫来了,扛着一把大扫帚,是一个扫马路的女人。也许是背水一战,也许真的是四两拨千斤,我们大吼一声,那个千斤的铁块子,终于上了车。
不知道是啥时候开始的,我这个乡下人,跟陌生人也有了交流上的障碍。这是因为别人,还是在于自己?
现在想一想,那几个挖沟的陌生汉子何曾拒绝过我们?也管说,是我们排斥了他们。正像那个女人对待我。
有一回,我正手持切割机切金属板,一把铁锨无声地伸了过来,我抬头一看,一个陌生的中年汉子站在面前。他还是没有说话。我明白了,他是这个工地上挖土的,这把铁锨的口卷得太厉害,敲不过来了,想让我帮他切一下。我当下停了自己的活,仔细地把那些坏损的地方给切除了。那汉子只是朝我笑了一下,一句话也没有说,扛着铁锨就走了。
汉子无声地离开了,我却有些感动。很显然,他把我这个陌生人看成了村子里的一个邻居。这是一个粗人,但我觉得,他对待世人的心态,比我自己,比另一种环境里一些富于修养的人还要健康,阳光。这是一个痛快的人。这样的人在今天显得很大气。比游览区里的一切构建,都更值得欣赏。你要用到一把铁锨时候,只管从他的手里拿。尽管你是一个陌生的人。
我的花衬衫
十几年前的那个初夏,在家乡的小镇上我花十五块钱买回了一件花衬衫。黑褐色的底子上满布着豌豆大小的圆点,洁白的,像鸽子明亮的眼睛,又似夏天夜晚野外的满天星斗。三十岁的男人穿在身上,人行走在四季里,血管里奔跑着春天的马蹄。种田的汉子,扁担是车轮,肩膀是大道,这件花衬衫只能一声不响地夹在中间。栽种烟叶、红薯和花生的季节,一个男人一天要从远处担上百挑子水。与别的衣裳不一样的是,不管它蒙上了多少灰土,汗渍,只要脱下来随便搓洗一把,花衬衫便又会干净得一黑二白,星辰满天。
几年前那个冷峭的初冬,我要远行了。妻子湿着眼角一声不响地给我收拾行囊,花衬衫被叠得整整齐齐的放进了蛇皮袋里。女人知道,她的男人离不了这件衣裳。
行走在异乡的土地上,这几年来我却没有再穿过它。不是它土气了,破旧了,而恰恰是因为好几回,别人对它的夸赞。别人打量我一番,问道,哪里买的?看那样子他也要弄一件穿穿。一件风里雨里穿了好几年的便宜货,还有啥样子呢?新买来的时候,村子里的人除了朝我多看一眼,也没有谁说个啥。我困惑了。后来,我便一下子转过神来:花衬衫还是那个样子,——是人“旧”了?旧,总是能映照出新。
想到这,便一阵惊心。虽然这是一个男人,一个不依靠青春吃饭的人。
离开村庄我便知道,四十岁边上的这个男人,已经老了。在家有人问我年龄的时候,我虽然也像李爱国那样回答过人家,可我并不相信自己已经老了。李爱国没比我大几岁,却经常说:土埋半截了。好像他一生下来就是等着土来埋的。我没有老。我一直还是爹娘的孩子,给庄稼拔草我总是耐不住性子一走完事,让爹娘在那里陪着太阳下山。我的身子正健壮得像村子里的一头■牛。我还没有被土埋去的这一半,村子里还找不到什么东西比它更长久:牛还会在我的手里死掉,门前那一片杨树我会把它砍倒栽上再砍倒,村子后面那条乌龙港没有人知道它流淌了多少年,这些年它却一年年地细下来,这样下去,这条细线同样会在我的眼睛里断掉。捱近四十,在村子里我的腰杆子才刚刚硬起来。我的麦子一亩地可以比年轻人的多打半袋子。有时我还会瞪着眼睛对他们说道:你还早呢!这句话一出口,小青年就低下头,不说话了。
外面的世界不是这样的。流水线上不承认、不需要经验。流水线上一分钟的事情就是这一天,一天的事情就是这一年。你在这个点上守了十年,也不能保证比一个新来的干得更好。今天的人遵守的是规则,个人经验无须到场。相反,经验常常会成为春天里的一件棉袄,碍手碍脚,无处存放。
一个女人——或者一个男人,三十岁一过,在一些求职的路口上就红灯闪烁了。年轻,或者看上去年轻,成了一个人最大的本钱,最有力的进攻武器。一个人老得如此匆忙,连一件衬衫都来不及穿旧。
花衬衫已经无处存放。在这个夏季来临的一天,我把它丢掉了。
这个年龄上,范进先生还没有中举。
劳动与光荣
炎夏的一天,老高打电话要我给他帮个忙。他说,现在的帮手还不大会干。
老高是我以前的同事,身粗力大的,拖电缆,搬重东西这些多人一起使劲的时候,老高总是带头喊着号子,卖力得很。不过,这都是管事的人在场的时候,管事人一离开,老高就要擦擦脸上的汗,打打身上的灰,摸出一根香烟点上。几年前有一次公司开掉了十来个人,就有老高。出来后的老高不想再让人管了,就自己带一两个帮手,找一些小活干干。
老高现在的这处活是私人装修,他只做水电。活是从一个装修公司手里转接的,装修公司的技术员是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他拿着一张图纸,安排着老高怎么做怎么做。老高一路点着头,还掏出香烟让,技术员不抽。
我们开始干活了。
一会儿,我就看到有个人在往楼上扛水泥。这个人穿着裤头,光着脊梁,黑黢黢的水泥和着汗珠子,从头到脚满身都是。看到这,我首先想到的还不是累,不是脏。我知道,水泥这东西对皮肤是有腐蚀性的,长时间糊在身上,人会脱皮。
我再一次注意这个扛水泥的人,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不是那个小伙子,技术员吗?
这时,老高的一个帮手也从楼上下来,悄悄地跟我们说:“那家伙怎么还扛水泥……”
“人家的事用不着你管!”老高不动声色。很显然,老高早就看出来了。
扛了一阵子,技术员拎着一把水壶,呼哧呼哧地喘着气,嗓子干哑着问我:“师傅,你们有没有插座……”
他壶里拎的是自来水,现在想把它烧开。三伏天干这样的活,一刻也离不开饮水。
老高的工具箱里不会没有拖线板,只是还没有拿出来接上电源,现在接一下,也就是几分钟的事,反正要用的。
还没有等我说话,老高就替我回答了:“我们上午不喝水!”
老高的话是我没有想到的。刚才他还在给人家让香烟。干了一个活,一个人就一分钱不值了。
技术员把烧水壶放到墙边,干咳出一口黑黑泥痰,一声不响,又接着扛了。
中午吃完客饭,我们几个在楼层的背阴处坐着,躺着休息。技术员在哪里吃过饭,也过来了。他靠着墙根坐下,离我们十几米远。
那垛子砖头跟前,有一个刚绑好的木架子。水泥扛完了,看来下午他要上砖头了。砖头的旁边,还有一堆沙子。
我若无其事的样子,来到他的跟前。他面无表情,不大答理我。通过询问,我还是知道了一点:他是徐州的,大专毕业,来苏南找了这个工作。我说:“你怎么还要干这个活?”他说,这个活是他个人的,为了多挣一点钱,上一吨水泥20块……
小伙子,大学生,可是,他挣的这个钱显然不是经营爱情的,也不是喝咖啡的。买一瓶饮用水,都是一个错误,因为那正是一斤大米的价钱。
我没有再问什么。我总感觉到在他遥远的家乡,有一个患病的爹娘,或者正在上学的弟妹……
跟老高说起这个人的时候,他就一句话:没出息的东西!
说这话的时候,老高正抡着大锤在墙上开槽……
吃过了
暑假,三个孩子千里奔波来跟爹娘团聚。那一天有了一点空闲,我就领着这些中原腹地的乡下孩子在这座江南的城市里转悠。转商场,转公园,也转农贸市场。
农贸市场里,一些鱼他们没有见过。像鸭子一样,伸着头看。有一种鱼脊背青灰,肚子黄白,嘴尖,身子细长。我告诉他们,这是鳗鱼,这种鱼吃着很肥,不过这家伙很肮脏,最爱吃腐臭的东西,沟河里要是漂有死羊死狗,它们就会围上去吃,有的还钻到死东西的肚子里。有一种鱼,身子跟鲤鱼差不多,鳞小,全身有黄褐色的斑纹,背上长着一排子刺。我对他们说,这是鲑鱼,据说这种鱼很霸道,大暴雨的时候,沟塘漫水了,它要是不走,别的鱼都不敢往外逃。
我这样一本正经地说着,女儿却疑惑了,她说,爸,你怎么知道?儿子说,咱爸爱看书!
我说,爸可没有看过这种书。这几样东西,咱们家里过去都有。鳗鱼咱们那里叫“白鳝”,你看它身子细长,是不是有些像黄鳝?鲑鱼,咱们那里叫“季花”,它身子就是花的嘛。
我的话他们好像不大相信。我自己也觉得,我像是在向孩子们叙述着一个传说。
现在在我们那里,别说是这两种鱼,就是黄鳝、鲇鱼、虾这些只要有水都会有的东西,也已经很难见到了。至于龟,鳖,可以肯定地说,已经绝种了。我上学的时候,在路上就按到过一只鳖,我从地里弄一点麻把它拴住,拎到教室里,系在桌腿上,上课的时候这东西一心想逃,爪子在地上扒得哧哧地响,结果引来了老师,把我训了一顿。我们抓到这些东西后都煮着吃了,没有人拿出去卖。那时候农家的房簿篱上,墙缝里,经常能看到插有一两块一面青一面白的龟鳖的甲板,这东西是中药材,等走乡串户的货郎来了,女人们可以拿出来换一点针头线脑。后来人们舍不得吃了,它们值钱了,它们就没有了。
这些东西现在都展示在盛着清水的容器里,还用吹着气泡的增氧器伺候着。孩子们好像本能地知道它们都很贵,谁都没有向爸爸提出来买一条拿回去吃,或是玩。我感到,我的孩子都不赖。最后,我们挪了个地方,买了一条两三块钱一斤的大白鲢。
现在,作为几十块钱一斤的食物,那些东西与我有着很大一段距离,让我无法伸手触摸。我不知道,它究竟是一个珠光宝气的贵夫人,还是我青梅竹马的妻子。
一件小事的结尾
那天晚上八点钟了,我穿着一身肮脏的工作服骑着电动车往回赶。公司里本来是五点半下班,带班的却把我们拖到这么晚。我相信,很多时候,想立功的人跟想作案的人,心电图是重合的。
走到一座桥上,我看到,那一边,一个男青年狠狠地打了一个女的几下子,跑到停在旁边的摩托车上,摩托车旁的另一个男青年又狂奔过来,在那女的脸上扇了几巴掌,又一下子把她按倒在地,踹了两脚,然后二人驾车扬长而去。
这中间没有恶毒的言语,也没有凄惨的喊叫。那女子从地上爬起来,双手捂着头,一步一步地离去了。
回到那个租来的家,加班的妻子已经回来了。很快,她就把饭菜弄好端到我面前。筷子握在手里,我却迟迟没有动。还不饿啊?妻子朝我嚷道。叹了一口气,我说,刚才在桥上,有两个男人打一个女人!哎哟,妻子的心也沉了下来,她站在我面前,像是还要听下去。我却没有讲下去。我说,从一点钟上班到现在,又饿又乏,一点劲都没有了,要不,我真想上去抓住那两个小子,也扇他们几巴掌!妻子一听,当下就变了颜色:你逞啥能,这不是在家里,人家两个人,他们把你打倒扔桥底下都没人知道!我没有和她争辩。她的话又让我看到了那一会儿桥栏杆上靠着的一个衣装整齐的男人,女子挨打的那一刻,他连欠一欠身子都没有。许久,我还是对妻子说,人家挨打,你不上前,轮到自己,就找不到人说话了。
就这样,这件事落在了我的心里。我忘不了,下了桥的这一半路,是像一条狗一样溜回家的。
没有想到,后来的几天里,想起这件事,我就为自己开脱了。说白一点,我是在寻找一种可能——那女子挨打是罪有应得的。
男女之间的恩怨,我首先想到的是情变,这也许是一场情仇。那个女子见异思迁,绝情寡义,深深地伤害了对方,一颗流血的心上长出了仇恨的野草。可是,这应该是一男一女的纠缠,或者进一步演变为两个男子的一场争斗,现在却是两个男子暴打一个女子。显然,这条思路已经导入了死胡同。我又改变一下女子的角色:她原来不是跟谁谈恋爱,或者说她是跟所有的男人谈恋爱的。她不单先后(或同时)花掉了那两个男子的钱财,而且还在生理上(以某种疾病)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麻烦,这两个男子在悔恨自己的同时,终于不可自制地找她出气了。我的感官记忆很快又否定了思维。那晚上虽然是在昏黄的路灯下,我还是看清楚了——那女子的装扮很朴素,一点都不像是吃那碗饭的。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她穿的是工作服,也许刚从某个公司的大门里走出来。
其他的可能性还有,可那就像一团揉乱了的丝线,我扯不出一个头了。
一天午间短暂休息的时候,我把这个事情说给了身边的一个同事。同事吸着两块钱一包的香烟,沉默不语。我们一起陷入了迷惑。这一段时间活抓得很紧,这个同事又刚被管事的骂过,我们都蔫蔫的。这个同事并没有丢下这个小事,我们起来干活的时候,他说道,那个女的肯定是公司的一个小头目,她这个人只顾老板,不管下面的人,压得那两个人都呆不下去了……
这是一张无边的大网,它几乎盖住了所有的人。我怎么没有想到这里呢?这时,我感到,一股气流透进了心里。我知道,以后我不会再想这个事了。
春天的隐私
江南的四月,不冷不热,穷富都好过的日子。可是那天晚上已经是连续第三天加班了。我们五个人的工作是车间里的照明安装,具体说来就是爬到车间彩钢板吊顶的上面,在吊顶的背面开灯位,钉盒子,排管子,走线路。另一个地方还有一班子人,干别的。
这五个人,两个山东小伙子进来得晚一点,也一年了,也算熟手,大家各揽一项,手脚麻利,嘴上不大说话,心里却都在想着:快点干,今晚看看能不能早一点下班。
十点钟上下有人便开始掏手机了。掏手机与打电话无关,都是瞅时间。我也刚刚瞅过。从时间上说,现在也可以下班了。下午五点多下班我们匆匆吃过盒饭,六点钟不到就爬上来了,到现在已经超过四个小时,一个加班一点都不缺斤短两。可是,现在一点下班的迹象都没有。施工队长还是一开始爬上来一回,看到我们井然有序,一声没响就下去了,再也没有过来。
他娘的,不干了!吆喝这一声的是老高。老高点上一支香烟,坐在那里抽着,不干了。老高不老,三十几岁,身材有那么一堆,换身衣服,就完全像个大老板了。老高的嘴像个破锣,什么话都往外说。老婆在老家,他在这边一个人租房子。有一天他咧着嘴得意地跟我们说,最近他把一个房客邻居搞到手了。妈的,还是个雏子,一连找了她一个礼拜。老高的嗓门很高,刚才那一声叫得却不够响亮。他的喉咙有些干哑。晚饭老高的一盒米饭才吃一半,就丢到垃圾堆里了。我也没有吃完,口干,东西嚼在嘴里不转圈儿。缺少水分,这几个小时里,我们几个人连一个下去撒尿的都没有。可是,老高的这一声,没有得到任何反应。掐灭烟头,老高只得重新抄起老虎钳,一段一段地穿线了。我们加班从来没有时间,头儿不说话,便要一直干下去。
时间在艰难中行走……
接近零点的时候,沉闷中,突然一声剧响。这一声是散客弄出来的。散客操起一根电线管狠狠地抽打了一下脚下的彩钢板,砰!散客来自边远的贵州,在这个城市他没有亲友和熟悉的老乡。于是我们叫他散客。散客不大说话,工资在最低的那一档上,一些苦重琐碎的活,不用点名就是他的。抽打过这一棍子,散客一屁股瘫坐下去,张着嘴,两眼僵直,像是用完了一生的力气。这一棍子的意义明明白白。况且是散客抽打的。我们几个立刻相互扫视一眼。他妈的,不干了!老高大叫一声。他们便收拾自己的工具包,准备下去。我也把手里的一个接线盒狠狠地摔在了地上。像大火中逃生一样,我们几个很快从洞口消失了。
没想到,我们几个人下来以后并没有嚷着去找施工队长要求下班,或者谁都不找而直奔外面的停车处,骑车走人。从上面下来没有走几步我们就慢了,直到停了下来。此刻,整个厂房一点声响都没有。那一档子人和施工队长也不见踪影,只能隐约听到一把电锤突突的冲击声。我们一下子被这种沉寂给震住了。
我们员工的日工资虽有差别,却都不高。公司把工资的一部分设为年终奖,年终结账,给你一万不多,给你一百也不少。就看你平时的表现。这个奖金就像一条腥鱼高高地挂在梁上,让一只只小猫时时刻刻想着它。对于我们这些人,它是一种希望,也是一块需要时时护卫着的软肋。
我们感到,权力不大也不小的施工队长,正朝这里走来……
山东小伙子首先缓过了神,他搬来旁边的一把梯子爬了上去,那里是一只昨天装好的日光灯,一只灯管不亮了,他现在要修理一下。另一个小伙子赶紧跑过去,帮他的老乡扶着梯子,安全第一。看到人家有了活,散客也急了,他操起旁边的一把扫帚,打扫着这一片没有来得及清理的场地。
我转脸看老高的时候,老高正在看着我。他的眼睛里是空茫和不安。几分钟前那一股大汉子的激情已经烟消云散。我们俩一起转过身,回到走过来的那个洞口,重新爬了上去。
他们三个也很快跟了上来。我们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拿出工具。这片场地上,一直到下班,也没有人再说一句话。
也许是因为比老高还大几岁,这件事我从来没有跟别人提起,包括我们五个之间。他们也没有。就连这个无话不说的老高也是。
责任编辑 牛健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