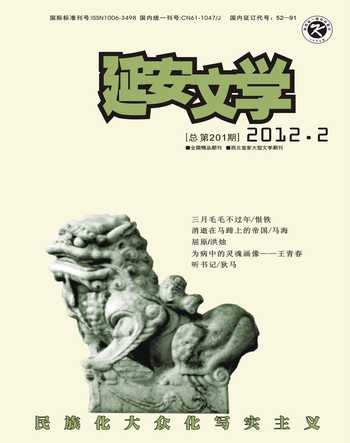屈原(节选)
洪烛
屈原的故乡未通火车,我在宜昌下,转乘汽车,越过一道道山。屈原离家出走的时候,连汽车还没有呢,要么骑马,要么乘船,去一趟首都不容易。当我向秭归走去,看见屈原正迎面走来。脸上充满梦想,根本不像一个会寻死的人。是啊,那时候的屈原,比我现在的年纪还年轻。我根本不该把他当老人。在跟屈原擦身而过的瞬间,我忽然想:如果他没有动身离开故乡,千百年后,就不会有这么多人,向他的故乡涌来?他的一部分梦想是破灭了,却实现了另一部分没有梦想过的梦想。
我每年端午节去湖北秭归,都能看见那位扮演屈原的人,在各种纪念活动上朗诵《天问》。他可能是县剧团的演员,但他在表演的时候,肯定忘了自己是谁,而认定自己就是屈原的化身。虽然我没见过屈原,仍觉得他跟屈原长得太像了,他穿着戏服,非常合身。不,我觉得那就是屈原穿过的衣服。他用浓重的湖北口音吟诗,那也是古楚国的方言。屈原当年就是这么抑扬顿挫地说话的。他站在舞台上,一遍又一遍地问天,我真希望他还能再提几个屈原没问完的问题。当他下台、卸妆、换上休闲服,我一边向他致敬,一边还希望他把屈原进行到底。至少在我眼里,他不是湖北人,他是楚人。他不是艺人,他是诗人。在这个诗人越来越少的年代,能有一个扮演诗人的人,也是值得庆祝的胜利。屈原,这个伟大的失败者,多么需要一点哪怕微乎其微的胜利。虽然他生前无法拥有,就让我们在他死后加倍补偿吧。也许屈原并不需要后人的补偿,我们却需要通过补偿获得慰藉。
他们说这里是屈原的故乡。真的吗?屈原还能认得出它吗?两千多年,变化太大了。我只知道老秭归已沉在江底了。你不如指一指三峡库区,看哪一块水面笼罩住屈原出生的地方。他们说这里有屈原的衣冠冢。真的吗?真的埋着屈原半路上被风吹掉的帽子,跳水前脱在岸上的衣裳?墓可以是假的,碑可以是假的,刻在碑上的名字却是真的。只要这两个字是真的,思念就是真的。这两个字写在纸上、水上、石头上,无论写在哪里,哪里就是屈原的碑。
龙舟上坐着的水手,我数过来,数过去,还是少了一个人。当然,坐在船上的人,觉得一个不少。按照他们报的人数,又数一遍,我发现多了一个人。恐怕我的脑海里有这么一个人,才把他的影子也数进去了?这个日子,怎么能少了他呢?这条船上,他坐在哪里?龙舟越划越远,越来越模糊。那个人的影子却越来越清晰。
谁说我的祖国没有荷马,屈原的湘夫人比海伦还美。奥林匹斯山的诸神太远,我有我的云中君。他心中的神山叫昆仑,“登昆仑兮食玉英……”郢都,玉碎宫倾的城市,和特洛伊一样蒙受耻辱。和荷马不一样的是,屈原自始至终都站在失败者一边。作为战败国的诗人,他身边没有一兵一卒,只剩下一柄佩剑:宁愿让它为自己陪葬,也不能留给敌人,当作炫耀的战利品。不,是他本人在殉葬啊,为了保住楚国最后的武器。谁说我的祖国没有史诗,《离骚》是用血写下的。虽然我的诗人不是胜利者,他投身于水国,也拒绝向强敌屈膝。一个人的抵抗,比一个国家的命运还要持久。如今已两千多年了,他还没有放下手中的剑。
中国的法定节日里,只有端午节,是专门纪念一个人的。是一个人的节日,由万众分享。分享他的美食,也分担他的忧伤。端午节和西方的圣诞节类似,都是一个圣人的纪念日,只不过不是纪念他的生,而是纪念他的死。因为他的死比生还要辉煌。他迈出了伟大的一步,使汨罗江在这一天里,与长江、黄河并驾齐驱。一个人的行走,成为一个人的节日,多多少少还是有些孤独的,在这个日子里,我们重温他的孤独,为了使他不孤独。千万条河流里的千万条龙舟,忙得不可开交,都是为了像海底捞针一样,把他的那点孤独打捞上岸。“找到了没有?”“哎,没找到——”“那么明年接着找……”在寻找他的孤独过程中,我们忘掉了自己的孤独。这个日子,他用孤独,把这么多人团结了起来。
住得离三峡最近的诗人,神女峰是他的梦中情人。在他投江之后,两千多年之后,他的故乡也沉入江底了,成为三峡库区的一部分。哦,水国,他水中的祖国……他是被命运打倒的,可梦想还站着。“神女在等人?”“她在等谁呢?”我想告诉他们:“她在等那个青梅竹马的诗人。”是的,梦中情人在等梦见自己的人。游船驶过昔日秭归城的上空。我说:那个梦见神女峰的诗人,就在水底,继续做梦。此刻,他也正梦见我们,梦见一艘大船,就像从头顶飘过的一只风筝。
在西陵峡与巫峡之间,是诗人的故乡。它的名字叫秭归。在诗人与巫师之间,是亦诗亦巫的屈原。他的姐姐叫女媭,一位以爱呼风唤雨的女巫。屈原,每天都面对巫峡写诗,不知不觉,把诗炼成了一门完美的巫术。诗就是巫啊,巫就是诗啊。诗人的姐姐是女巫,女巫的弟弟是诗人。诗与巫的关系,是血缘关系。可如果没有爱,诗人会江郎才尽,巫师会破绽百出。我从云里雾里的巫峡,顺流而下,去秭归,向屈原和他的姐姐,学习怎样爱,怎样让爱变成神话。在爱与神话之间,江水滔滔,巫就是诗啊,诗就是巫啊。
你是祖国最大的一个盲流,逆打工潮而走,逆政治路线而走,逆时尚而走,逆江水而走……你比盲流还盲目。你也不知道要走向哪里。偌大的楚国,找不到一块落脚的地方。只能机械地走啊走,离出生地更远了,离首都更远了,离亲戚朋友更远了,离国王更远了。当你走到国境线上,没人拦你,你站住了,再也不愿挪动半步。你是最盲目的一个盲流,不知道前途在哪里,只知道自己的底限:“祖国可以不要我,我却不能不要祖国。”你把汨罗江当成边境线,再也不肯越过雷池半步。祖国把你拒之门外,可你不愿意去外国,只能在那几乎看不见的边界,来回徘徊。你画地为牢的亡灵再孤单,依然是楚国的鬼哟。
他的纯净水是朝露,他的美食是落英。这个爱干净的人,这个干净得不能再干净的人。沾在衣襟上的灰尘可以掸掉,无处不在的谣言却是掸不掉的:“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这个爱干净偏偏又被弄脏的人,这个弄脏了心里还想着干净的人,他的难受非你我所能理解。他一边先在江边洗了脏衣服,然后才跳进水里,把自己洗一洗。洗得清吗?他恐怕不知道:自己即使被弄脏了,也还是比江水要干净。晾在岸上的衣服干了,穿衣服的人呢?还是湿漉漉的。
你的诗里有许多我不认识的字,不知道怎么念的字,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的字。我不认识它们,但是我认识你。即使你诗里所有的字都不认识,我也能读懂。只要认识两个字就够了。这两个字就是你的名字。即使我读不懂你的诗我也可以读懂你。我知道那是古诗,却常常忘掉:你是古人。我无法流畅地背诵楚辞,却总是念叨着你的名字。这两个字就是最美的诗啊。因为你的名字的缘故,你诗里那些我不认识的字,也变得很美,梦一样般神秘。我像解梦一样解那些字,我像猜谜一样猜你的心情。那些我不认识的字不是常用字,似乎只对你有效。你的梦,却经常被无数像我一样的人想起。你其实不只有一个名字,离骚、天问、招魂、怀沙……都是你的名字啊,哪怕我仅仅记住那些诗的标题,就等于记住了你。你是诗人,又是一个大于诗的人。更加无边无际的是你的梦啊,甚至大于你。你的梦里面装着太多大于个人的东西。有时候还大于你的祖国。你写诗的时候,心里可能还住着一个外星人?
我相信那在竹简上刻下楚辞的,一定是热爱屈原的楚人。我相信那古墓里的竹简,一定是用湘妃竹制成的,留有湘夫人的泪痕。我相信泪迹斑斑的湘妃竹,一定是在洞庭湖边生长的。我相信屈原行吟泽畔,一定看见过竹子,看见竹子就想起湘夫人。我相信屈原的泪,流得一定不比湘夫人少。在别人的故事里流着自己的泪,边哭边唱,心里一定很疼。我相信诗句无论刻在竹简上、石头上,还是抄写在纸上,都是屈原的伤痕。作为楚人的后裔,作为诗人的后裔,我会把楚辞在心里刻得更深。
汨罗江是倒着流的,向着苏东坡流过去,向着李白流过去,向着司马迁流过去,最后又流回屈原的脚下。在屈原之前,还有谁呢?我不知道。在屈原之前汨罗江无名。即使它已有了名字,也没多少人知道。我眼睁睁地看着它,由新诗流成了古诗。在一座山的那边,流成宋词。在又一座山的那边,流成唐诗。雾大了,它可能在《史记》里迷路了。拐了很大一个弯,才重新流进了楚辞。江水越来越清。可以洗我帽子上的红缨。我明明是迎着汨罗江走过去,可江水不断倒退着,领我往战国去呢。那里有它的老熟人。站在最上游的诗人,离我越来越近。我看见他的帽子上,系着一枝和我一样的红缨。刚刚洗干净的。在楚方言区,汨罗江倒着流的。越来越难懂。
我做的梦,比云梦泽更大,浊浪滔天。我做梦的时候,整个楚国都在做梦,梦见一条船在沉没。梦游,就是在迷宫里怎么走也走不出来。和那些即将倾倒的宫殿相比,只有迷宫是不朽的。为了找到那迷路的王,我陷得更深,不能自拔。我必须往梦里装进云梦泽,装进整个楚国,才能放心地醒来。我想告诉他,告诉他们:在我的梦里面,你们很安全。别人都说云梦泽是一片苦海,只有我知道:它会一点点地变甜。我已忘掉我是谁了,却无法卸下那越来越沉重的思念。
忧伤的时候,你就看一眼彩虹吧。可惜,那救生的浮桥不是每时每刻都有。没有彩虹的时候,你就看一眼太阳吧。虽然天上的火焰到了晚上就没有了。没有太阳的时候,还有月亮可看。如果月亮也没有了,就看一眼星星吧。如果星星全没有了,你再不要放弃空空荡荡的天空。天空里什么都没有,又什么都有。屈原把你叫作云中君,当你看着更高的天,他在看你。他在水下看着你的一举一动,水中什么都有,又什么都没有。他看见你的忧伤,就忘掉了自己的忧伤。云中君啊,你能告诉他吗: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人,该怎么高兴起来呢?他把你当成自己的影子看,其实他本身就是你的倒影。
你不想成为雕像,无论是青铜的,还是汉白玉的。你不想失去体温,不想变得麻木,宁愿忍受谣言像一千根针在扎你,伤口能渗出血来。即使变成铁打的,你还是会喊疼,你的心还是肉长的。“诗人的眼里有一片苦海啊,他愿意与之共沉浮,不想成为它的岸。”走了那么远,终于在湖畔站住了,就像一大块天外飞来的陨石,经历了雷鸣电闪,你的五官、体形,都是火雕刻出来的。你不想停住脚步,还准备再一次走向苦海,正做着徒劳的挣扎。你不是普通的石头,你是一颗敢死的星星,在流浪途中把自己烧干净了。“它失去了光,失去了热,变冷了?”“不,摸上去好像还有一些烫……”
屈原的孤独来自于没有知音。他不知道自己的诗写给谁看。他的旅行没有对话,只有独白,远游彻底变成了梦游。他也曾尝试着把苍天当成交流的对象,可老天爷从来不回答他提出的问题。他只能自问自答了。在别人眼中就是自言自语,与疯子无异。可惜啊,走了那么远的路,居然没遇见另一个疯子。他多么希望发现一个跟自己一样忧伤的人。可所有的人都那么开心,那么没心没肺,根本不在乎天就要塌下来了。后来,天确实塌下来,却只压垮了他一个人。唉,有什么办法呢,骨头越硬的人越容易被压垮。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大诗人,是一位“垮掉的诗人”。仅仅因为他总想替天人扛起冥冥之中的压力。他是由于超载而垮掉的。
一个是战国的诗人,一个是大汉的美女,屈原和王昭君是邻居。九畹溪和香溪是邻居。可惜他们没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否则一个是竹马,一个是青梅,在三峡之间结伴游戏。诗人比美女还要爱美,还要爱照镜子,在井水里照镜子,在溪水里照镜子,最后,又到江水里照镜子去了。他住到镜子里去了,因为镜子最干净。镜子里面比镜子外面要干净。美女比诗人走得还远,走到山的外面,山的外面是水。走到水的外面,水的外面是长城。走到长城的外面,长城的外面是草原。她离屈原照过的那面镜子越来越远。那面镜子叫故乡。她抬起头,能远远地看见一面悬挂在夜空的镜子,月亮是故乡的投影。月亮里有山的影子,水的影子,还有在山水之间徘徊的诗人的影子。她知道,自己不久也会变成影子的。变成给诗人的影子做伴的影子。诗人是赤子啊,像骑着竹马一样骑着波浪,绕着故乡转一圈,又一圈,一年,又一年……远走的美女却回不来了。想家的时候只能看一眼月亮。月亮似乎比故乡离她更近一些呢。很多时候她连月亮都不敢看啊。刚刚抬头看一眼,心里已像青梅一样酸涩。
在首都,他是多余的,到了外省,还是多余的。在满朝文武中间,在楚王眼里,他是多余的。混迹于人群,与樵夫与渔父擦肩而过,还是多余的。给他一座洞庭湖,也钓不到一条鱼:有什么办法呢,他只对垂钓虚无有耐心。虚无是多余的,对虚无感兴趣的他,也就是多余的。诗人都是多余的人,而诗并不多余。诗比洞庭湖里的鱼更有活力,更难捕捉。当路遇的渔翁向他炫耀满载的鱼篓,他不好意思地拿出刚写好的《九歌》,却不敢让别人相信:这九条鱼真的会游进祖国的文学史里。是的,真正的诗都会用鳃呼吸。因为在那瞬间,诗人总是感动得要窒息。对于他来说,只要有感动,花香是多余的,空气是多余的,甚至连把诗写出来的过程,都是多余的。“他对这个世界的要求确实不算多,只想每天醒来能呼吸到一点诗意……”对于万物来说,诗人是多余的,是多余的一个零头。对于诗人来说,万物是多余的。他只热爱万物之间的空虚……
你是汨罗江的一条鱼,你是鱼身上的一根刺,在刺穿江水之前,已刺穿了自己。在激流中一扭身,用力过猛,你制造的伤口至今没有愈合。你在汨罗江里游着,汨罗江在楚国的版图上游着,楚国在大地上游着,游着游着就游不动了。只有你还在使劲啊,你的名字是汨罗江的一根刺,使每个站在岸上的人,心里都有一点疼。当祖国搁浅的时候,你的那点小刺激,纵然无足轻重,却胜过许多无关痛痒的诗歌。“瞧,这才是真正的诗人:他的名字本身,就是一首最短而又最锋利的诗。”你用伤口来包裹刺,又用江水来包裹伤口,为什么你的歌声格外忧伤?那是用伤口唱出来的。“他诅咒了一切,却从来不曾诅咒自己的祖国……”你不仅是一位有骨头的诗人,你的骨头是一根刺。你是汨罗江的一条鱼,你是祖国心头永远的痛。
第一个诗人比第一个人还要孤独,比上帝还要孤独。他发现了自己与周围的人不一样的地方:头上没有长角,心里却有刺,无处不在的刺啊。无处不在的疼痛,使他成为人的异类。第一个诗人是第一个异类,异类中最孤独的一个。他甚至找不到另一个与自己相似的人。在人群里找不到,他只能到镜子里找了。在城市找不到,他只能到江水里找了。原本想打捞一个影子,给自己做伴儿,却被那个影子拉下水了,拉进更深的深渊。第一个诗人是第一个生了怪病的人,也是最后一个自暴自弃的神。在人与神之间,他孤独得要命。他的想法比国王还要多,他的快乐比渔夫还要少。第一个诗人,总是弄不懂自己为什么活成了这样?总是弄不懂别人为什么可以没心没肺?第一个诗人并不知道自己是第一个。第一个诗人并不知道什么叫诗人。第一个诗人,一出手就超凡脱俗,至今仍是顶峰。
你永远是我眼中的首席诗人,再没有谁能佩戴你腰间那么长的剑,即使他们能把诗句写得更长,却再没有那种划破混沌的锋芒。再没有谁能走过你那么曲折的路,即使他们能把爱情搞得更为曲折,却再没有那种致命的痛苦。没有痛苦,就没有锋芒啊。我要向你的痛苦致敬!正是它,而不是别人仰望的目光,使你的梦想至今没有生锈。再没有谁,能像你一样,把梦想千锤百炼,打制成一件怎么也无法冷却的青铜器。经历了两千年的埋葬,它明明是刚刚出土的,却更像是刚刚出炉,摸上去很烫,很烫。
最远的诗人离我最近。此刻,我在燕国眺望楚国,我在什刹海想像云梦泽。那个坐在酒吧门口弹琴的流浪歌手,会是他吗?是否在等一位来不了的知音?最古老的诗人在我眼中最年轻,哪怕他的胡子好久未刮了,蓬乱的头发制造出古怪的发型,甚至衣领也没洗干净……即使这样我还是不大敢看他的眼晴,那里面的忧伤是多么熟悉。唉,他有着我弄丢了的东西。最真实的诗人才能给人带来幻觉。哦,也许还包括幻听:他明明弹唱着今年最流行的《春天里》,却被我当成了快要失传的《离骚》。春天里满街飘着柳絮,哪来那么多的牢骚呢?莫非他的抑郁,也是从另一个人那里遗传的?最多情的诗人才会最孤独,最孤独的诗人才能看得清命运的无情:今天晚上他能去哪里?只能在别人的屋檐下,唱歌给自己听。他明天还得跟太阳一起无奈地活着,哪怕灯火阑珊的什刹海,已不知淹死过他多少个影子。
我来到你的地盘,没有看见你。我看见柔肠寸断的湘妃竹,没有看见你的身影。我看见泪水和江水一起流,没有看见你的眼睛。你知道远远来的这个人是谁吧?你知道谁是我吗?夫人,我没有看见你,却看见一个变得忧伤的自己。忽而模糊,忽而清晰,水里浮现的那张脸,哭的时候像我,笑的时候像你。看见我哭,你就冲着我笑。看我见强作笑颜,你忍不住又哭了。
我早晨吃了只粽子,那是向你致敬。我上午去江边看了龙舟赛,那是向你致敬。我下午在电脑上搜索你的名字,那么多的人都在向你致敬啊。看来我也得写篇什么了,用我的名字向你的名字致敬。晚上,入睡前又翻一下《离骚》,虽然还是看不懂,也是向你致敬啊。我用醒向看得懂的你致敬,用梦向看不懂的你致敬。也许你并不需要别人的致敬,是我在找一个致敬的对象。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啊,心里没有敬意的人,对不起这个节日。我算了一下:都是两千多年前的事情了,为什么这么多没见过你的人却无法忘记你?再过两千年可能还是如此。我们被忘记了,你却不会被忘记。如果说我的祖国真有长生不老的人,那就是你啊。向你致敬的人一代代老去,你还是怀着一颗粽子那么大小的童心。
你是一条蚕,前半生吐的丝叫《离骚》,后半生吐的丝是汨罗江。诗句晶莹透亮,江水晶莹透亮,你才是源头啊。前半生,楚国是一片桑叶,你从湖北流浪到湖南,一边行走,一边吐丝。后半生,云梦泽是一片桑叶,你忽而浮出水面,忽而沉入水底,把缠绵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唉,你被自己吐出的丝给捆住了。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一个人被脚下的路给绊倒了。
郢都病了,楚国的心脏病了,一个时代弱不禁风。这怎能怪你呢?千里之外的你,病得更重。连返回的力气都没有了。你却在怪自己:不该在祖国生病的时候离开,不该在离开的时候发那么多牢骚,不该在发牢骚的时候辜负了养育你的青山绿水……牢骚也是一种病啊,诗人也是病人啊。这怎能怪你呢?你没辜负国王,是国王辜负了你。并不是你要离开的,是他不想看见你呀。今天大雾弥漫,听说他患了不治之症,你一下子就忘掉了怨恨。“傻诗人啊,你救不了他,还是救救自己吧!”可只要一想起祖国的病,你就忘掉自己了。你病倒在路上,病倒在一个怎么够也够不着祖国的地方。“唉,我怎么敢告诉你呢?告诉你残酷的事实:你没忘掉国王,可国王早就忘掉了你……”
对美的爱养成了他的洁癖:他只觉得美的东西是干净的。其余的一切都不得不忍受。改不掉的洁癖,被当作宠物来喂养:早上用朝露,晚间用落英……人间烟火总会使他感到有点晕。他搞不赢政治,反而被政治搞了,被驱逐出境,带着一颗受伤的心。“政治是肮脏的,与美相对立……惹不起总躲得起吧?”他心里住着的是一只食草动物,原本就不该参与那血腥的角力。现在怎么办呢?只能拿楚辞的舌头,一遍又一遍舔舐伤口。“还疼吗?”“疼。不舔的话只会更疼。”你们该知道《离骚》怎么写出来的吧?可诗里面如果没有疼的话,也就没有美。他是用伤口咀嚼着美、反刍着美啊。他的记忆有相当一部分是虚构的。虚构的那部分才是从心里长出来的。
下雨了,我想送一顶斗笠给你戴。没有淋雨的我,都知道你被雨淋着。被雨淋着的你,却不知道自己正淋着雨。在想什么啊?连避雨都不会的傻诗人。衣服淋湿了却毫无感觉。看见你面无表情在雨中走着,披头散发在江边走着,我真不知道能帮上什么忙。找一件蓑衣给你披上?或者把你行吟的模样画下来,留作纪念?我能画得出你,却画不出雨。若隐若现的雨啊,早就把你从里到外打湿了。渔父苦劝你好半天都不管用,难道我画出的线条,能够改变你的命运?笔直的雨丝,怎么拦也拦不住你扭曲的身影。只能说你心里有一场更大的雨,有一种不可抗的力……
顾影自怜,云梦泽是一扇大得没边的铁窗啊,你够不着水里面的天空。有鱼游过,有鸟飞过,都在向你炫耀自由,可你不是它们的同类,你是楚囚。这个春天,一点也高兴不起来。你被春天关在外面了,你把自己关在牢房里面了。这颗心,受伤受够了,变得像核桃一样硬,怎么敲也敲不开呀。绕着云梦泽走了一圈又一圈,四处敲门,发出的都是墙壁的声音。花都开了,门还是不开啊。更郁闷的是,找不到门在哪里。每天看山,山无言,像是在面壁。每天看水,水无语,像是在面壁。抬头低头,总有一堵高墙迎面而立。如果连云梦泽这扇窗户都关上了,就真的死定了。“最大的孤独,莫过于连影子都背叛了自己……”投水的那一刻,分明想用头颅把铁窗给撞开啊。“看一看谁更硬!”
想知道他为什么走得那么慢?想知道他的步履为什么那么重?想知道他为什么边走边喘息,边走边叹气?他只是一个人啊,却把整个家、整个国都扛在肩上,走到哪就带到哪。想放也放不下啊。就像一只流浪的蜗牛,一路走,一路留下闪光的泪痕。他能不被压垮吗?干嘛要给自己制造那么重的负担?可怎么办呢?如果没有他,楚国真的就是一只空壳了。别人觉得他被祖国流放,他却觉得自己扛着祖国搬家。祖国在哪,自己就到哪。自己到哪,祖国就在哪。即使祖国变成一个泡影了,他也舍不得放下。
你抱着的那块大石头,已经被磨成鹅卵石了,可你身上的棱角还没有被磨平。河水断流,河床上的鹅卵石全露了出来,你还是你。跟任何人都不一样。两千年过去,水冲刷了一切,却拿你没办法。连楚国的版图都变形了,你却没有变,还是有棱有角的样子。汨罗江为什么不平静?因为水底有一个抱着石头行走的人。鹅卵石孵化不出梦想,可他保存着跳水时溅起的那朵浪花。仍在头发上斜插着。
把我当成你的岸吧,至少会相信:水不是无边的,苦日子总算到了头。把我捧着的书当成你的岸吧,那首《离骚》正在翻开的书页上晒太阳,只要还有人读,你的诗就不会淹死。把节日当成岸吧,每年一次,浮出水面,喘一口气,比汨罗江更深的是你的深呼吸。把龙舟当成岸吧,将粽子系紧又解开的,是一根你想抓却没抓住的救命稻草。把影子当成岸吧,或者,把岸当成影子。
秭归屈原祠的屈原铜像,让我想起战国。群雄追逐的九鼎,不知去向。吴王金戈越王剑,不知去向。楚国的编钟,不知去向。荆轲投出的匕首,不知去向。楚国的编钟,不知去向。荆轲投出的匕首,不知去向。秦始皇收缴六国兵器熔铸的十二个铜人,不知去向……春秋战国,血与火冶炼的青铜时代,分了又合,合了又分,不知去向。只剩下这一块沉甸甸的青铜,在火里烤过,在水里淬过,在风里雨里等待着,等待着自己变成一个人。等待着自己睁开眼睛,露出笑容。等待着自己,慢慢地长出一颗诗人的心。青铜时代的诗人啊,只有你没有生锈。长江从你脚下流过,银河从你头顶流过,泪水从你脸上流过,没完没了。你仿佛已站立了两千年,还是无法迈出一步。不,你一直在原地行走,一刻也没有停下。青铜时代的诗人啊,只有你还在站着,还在走着。当你沿着长江走去,江水停止了流动。
在他活着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传说。当他成为死者,又因为传说而活着。传说他是在那条河流里淹死的,我们至今仍为他保留着散步的地方,保留着走也走不完的岸。也许死者比生者更喜欢怀旧?也许生者比死者更需要聆听传说——更需要一种另外的生活?唉,我们不能代替他再死一次,却愿意代替他继续生活,直到传说变成了真的。死者的传说,恰恰也是送给生者的礼物。他送出的礼物越多,自己拥有的也就越多。“有人说你的一生是一曲哀歌,我却从哀歌里听出了你偷偷藏起来的快乐。”“你走进了传说,可你命名的河流,仍然在现实中不紧不慢地流着……”“你是因为传说才变得不朽的,还是因为不朽才变成了传说?”
栏目责编:张天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