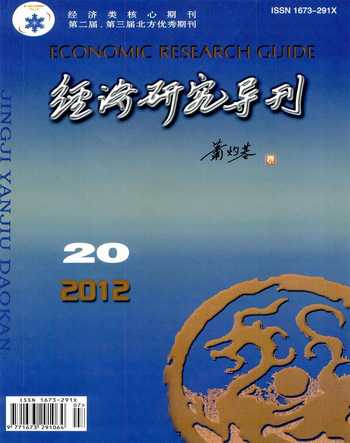论西欧国家福利转型
王强
摘要: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和全球化市场竞争的加剧,西欧各国所自我标榜的福利国家和社会保护制度发生了新的变化。一方面,所谓“福利国家紧缩”成为全球的风潮;另一方面,推进社会保护、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的责任推给市场、社会甚至家庭,这种责任在国家、市场、社会和家庭之间发生了程度与种类不同的转移,从而出现了把“福利国家”推给“福利社会”,而国家承担的社会福利减少的趋势。社会福利作为国家提供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逐渐成为多元社会主体合作的平台。鉴于此,主要从政府—社会定位的角度分析福利制度在西欧国家的衰减。
关键词:福利国家;公共经济学;福利紧缩;福利社会
中图分类号:D00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0-0018-02
福利国家作为一种制度供给,是一种由国家通过立法来承担维护和增进全体国民的基本福利的政府形式。福利国家制度的关键是政府保证所有公民享有最低的收入、营养、健康、住房、教育和就业机会,这些保障表现为公民的政治权利而不是以慈善的形式出现。福利国家理念从经济领域出发,诉求通过国家干预方式增加国民的幸福,运用差别原则实现社会再分配和财富的转移。但是,这一美好理想却也隐含着政府运作成本扩大以及政府合法性的危机,尤其这一制度供给在公共财政上的困境,使得这一制度逐渐被福利社会所取代。
一、福利国家的兴起——理论与背景的结合
作为现代国家的一种制度供给,福利国家的兴起是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庇古的福利经济学的产物。吉登斯认为,福利国家的建立是像法国社会学家杜克海姆所说的两股社会主义思想的具有张力的结合。一股思潮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关心的是对经济生活的指令性控制,另一股思潮以福利经济学为代表,关心的是对经济社会下层的保护。在自由竞争市场经济模式遇到困境时,人类毫不犹豫地转向建立在社会契约之上的公共权力,希望借此消除自由竞争带来的经济萧条;同时,社会正义的概念通过“无知之幕”也使得福利国家呼之欲出,对弱势群体的关怀成为福利国家诞生的价值基础。
在庇古看来,福利是人们需要的满足。针对经济自由主义通过个人福利增大来提高社会福利总量的观点,庇古指出,在社会福利总量一定的情况下,通过社会再分配,可以进一步提高社会福利总量。庇古关于“福利经济”的理论包含了两个基本观点:一是国民收入总量越大,福利就越大(把蛋糕做大);二是国民收入越平均,福利也就越大(分配公平)。而后者正是福利国家的宗旨,通过“最大最小值”实现社会制度的美德。
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更多的是站在传统自由经济的对立面主张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而不是以建立福利国家为宗旨。凯恩斯主义从再生产的角度,依据“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和“流动偏好”三个原理,指出资本主义“非自愿失业”的存在和经济的动荡是源于社会“有效需求”的不足,进而提出了充分就业和“需求管理”的理论主张。
二、福利国家的理论困境——新自由主义的发难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多元主义逐渐占据思想领域,对福利国家的批判也逐渐展开。费舍指出,“在二战以后的西欧,从来没有把创造经济财富作为目标本身,而是使它首先服务于社会团结,通过对雇佣就业者群众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实现一体化。”
对福利国家理论批判最强烈的是新自由主义,在新自由主义者看来,福利国家是一切罪恶的根源。一位新自由主义学者这样写道:“我们将带着轻蔑的嘲笑来回顾福利国家,正像我们现在会开玩笑式地说奴隶制是组织有效率、有活力的生产活动的手段一样。”福利国家给它所设想的受益者——被它界定为弱者、贫穷者和不幸者的人——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它削弱了个人的进取和自立精神,并且在我们这个自由社会的基础之下酝酿出某种一触即发的怨恨。西德“社会市场经济”之父艾哈德认为,有效的福利支出必须以不断增长的国民收入为前提,而“竞争是获致繁荣和保证繁荣最有效的手段。只有竞争才能使作为消费的人们从经济发展中受到实惠。它保证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而俱来的种种利益,终于归于人们享受。”因此,“在一个以自由社会制度为基础的国家里,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是保证自由竞争。”对“机会平等”的推崇和对“结果平等”的排斥促使他们抵制“最大最小值”,排斥“只有在不平等随着时间的流逝有助于社会中最贫困的人享有的收入和财富最大化的情况下,这些在收入和财富分配中的不平等才被认为是正当的。”
三、福利国家的现实困境——“德国的社会福利变得愈来愈昂贵了”
20世纪70年代初期,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陷入了“滞胀”(高通胀、高失业、低经济增长)的困境。进入20世纪80、90年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新自由主义者到处宣称,社会福利国家“已经过时,在世界范围比较,它的代价过份昂贵”,已经成为“未来的威胁”,社会不平等的扩大将是不可避免的”,“转折是不可避免的,每个人都必须作出牺牲”;“德国的社会福利国家变得愈来愈昂贵了”。新自由主义从传统福利国家制度中找出了六大弊病:(1)当公民不再有能力和意愿缴纳如此之高的税额的时候,国家是无法维持如此高额的开支的,过高的税收只能导致大量逃税和黑工。(2)当国家的利息负担大于来自经济增长的新增收入的时候,单单支付利息这一点就要造成国家新的债务,并最终导致国家财政破产。(3)过度膨胀的国家机关和过分臃肿的管理机构,使国家已成为庞大的、不透明的官僚主义怪物。(4)在全球激烈竞争的时代,不带来经济效益的工作岗位已经失去了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必须迅速减少,以便降低劳动开支。(5)惩勤奖懒的平均主义分配做法在全球化时代绝不是体制的结构改革方向,从伦理上说,工作者的收入就应明显地多于不工作的人。(6)国家对公民较高的社会支出本身并不能长久保证较高生活水准和社会和平,只有经济有相应增长,才能做到就业岗位的增多和實际收入的提高。赫波特·马尔库斯认为,福利国家使得劳动者丧失了自由,变成“发达的工业文明中的奴隶”,是“升华了的奴隶”,其地位仅仅是工具而不是自我发展的自由人,所以和奴隶无异。换句话说,人为了福利而丧失了自由,福利的发展以牺牲人的自由和发展为代价。西欧福利国家的困境主要体现在财政上:一是社会福利的扩张快于经济增长,福利开支寅吃卯粮。1960—1975年,英、德、法三国的GDP年增长率分别为2.6%、3.8%、5.0%,而同期的社会保障开支年均增长率则分别达到了5.6%、6.7%和7.4%,社会福利的增长速度比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快了一倍左右,这种扩张方式为福利国家的财政危机埋下了祸根。二是社会保障支出日趋庞大,给政府造成沉重的财政负担。养老金、失业津贴以及医疗费用的扩大促使西欧国家的福利开支逐年递增,1965—1970年西欧各国的社会福利支出增长了11.6%,1970—1975年间增长了15.3%,社会福利开支占GDP的比重也从60年代的20%上升到了70年代的30%。
四、福利社会——新的走向
福利国家向福利社会的转型是政府与社会分离的体现,公民社会的成熟以及公共物品技术上的进步使得政府逐渐退出公共物品的提供,专注于公共政策的提供,政府不再凌驾社会之上,也不再是公民生活的核心,而是社会多元主体中的一员,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更加融洽。福利社会主张社会福利的私有化、市场化和多样化的理论,即福利计划应当建立在“个人自由、自主和自助”的基础上,每个人都应首先尽可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生活保障问题,国家、社会机构只有在他的收入和财富不足时才进行干预;利用市场的竞争机制和加强私人机构的作用,减少国家的社会福利责任和财政负担;在社会福利的项目和公共服务的提供方面,适应社会生活和福利需求多样化的趋势,坚持多元化和多层次性,增加人们享受不同种类和不同层次社会福利的选择性。正如托尼·布莱尔所说,“总之,一个积极改革的福利国家——积极福利社会中的社会投资国家——应当是什么样的呢?被理解为‘积极福利的福利开支将不再是完全由政府来创造和分配,而是由政府与其他机构(包括企业)一起通过合作来提供。这里的福利社会不仅是国家,它还延伸到国家之上和国家之下。比如,对污染的控制从来都不是中央政府一家的事,但这件事无疑是与福利直接相关的。在积极的福利社会中,个人与政府之间的契约发生了转变,因为自主与自我发展——这些都是扩大个人责任范围的中介——将成为重中之重。这种基本意义上的福利不仅关注富人,而且也关注穷人。积极福利的思想将把贝弗里奇所提出的每一个消极的概念都置换为积极的:变匮乏为自主,变疾病为积极的健康,变无知为一生中不断持续的教育,变悲惨为幸福,变懒惰为创造。”从新自由主义学者对福利国家制度的批判,到20世纪80年代初西方学者提出“福利社会”概念,从20世纪80年代撒切尔夫人对“福利社会”的初步践行,到90年代以来西欧社会民主党人以积极“福利社会”为目标的第三条道路改革,“福利社会”逐渐成为替代传统福利国家制度的现实方案和明智选择。
结语
福利制度作为一种制度供给经历了由国家主导转向多元合作发展的道路,体现了国家与社会的分离。这种转型是公民社会成熟的结果,也是政府理性的体现。这种转型是国家与社会定位的有益尝试,是政府走向善治的必然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