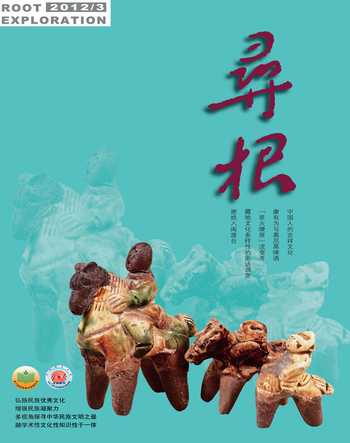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文化的命运
徐志伟
我童年所接触到的乡村文化生活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二人转”、东北大鼓等为主的演艺文化活动;一类是以祭祀、祈祷为主并和信仰混杂在一起的“封建迷信”活动。
“二人转”是流行于我家乡的主要戏曲形式。每当农闲季节来临的时候,村里就会有人出面去联系、预约“二人转”剧团。这种剧团是纯粹民间自发的,由某个较有组织能力的人发起,然后邀请十里八村的有这方面特长的人加入,组合到一起,走村串巷地演出。当然这种演出是以营利为主要目的的,这也是维系这类剧团存在的重要因素之一。每演出一场,剧团的团长都要挨家挨户地向当地的村民收取劳务费。如果哪个村民碰上手头没钱,也可以用玉米、大豆等粮食来顶替(现在想来,这种以粮食换取文艺的做法的确很有意味)。由于“二人转”的语言、形式等能够迎合村民们的文化趣味,所以深受他们的喜爱。演出的剧目通常以传统剧目为主,新戏很少,村民们也大都喜欢传统剧目,对新剧目则不大感兴趣。无论传统剧目还是新戏,都明显地经过了文人的加工与再创作,所以,很难确认它与普通村民的精神联系到底有多大。当时,对于我们一群小孩子而言,乐趣自然不在于看戏,而在于现场热烈的气氛,小朋友们在人群中窜来窜去,交换着食品,这已经是极大满足了,管他唱什么关公或秦琼。
或许是我那个村子里的人不够浪漫,他们通常对这些民间艺人是看低一等的。旧社会的“戏子”观念在他们的头脑里留有很深的印记。这些看似有一技之长的“戏子”在乡村强大的传统观念下,生存状况其实是极为不妙的。如果有哪个村子的青年因爱好戏曲而随剧团离家出走,其家人就会遭到当地人非议,认为是因为其家族“祖上无德”,才会培育出如此没出息的子女。他们的身份在乡村也是无法明确的。按当地习俗,这些艺人死后甚至是不能入“祖坟”的。他们在年轻时可以随便挥霍自己的年华,歌舞升平,死后却只能被埋葬在荒山野岭,在另一个世界忍受孤独。这不免有些凄凉。当然,他们也可能有另外的命运,他们中一些极其出色的人会被选入县里的正式剧团,并有机会成为正式的“国家干部”。尽管他们的工作内容没有任何改变,但身份却变了,成为国家文化机构中的一员,获得了“吃官饭”的机会。村民们对这样的人还是很钦佩的。当然,这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事情了。如今,由于受整个国家控制机制变化的影响,“二人转”剧团已经纷纷市场化了。艺人们的收入与社会地位都有了巨大的改变,村民们不能不对这些“每天吃喝玩乐也能赚钱”的艺人们充满了羡慕。由于电视的普及,村民们足不出户就可以在荧屏上看到艺人们的身影,能在电视上露面,一度成为村民们价值判断的一个标准。同样是面对这些来自民间的艺人,由于新的媒介的介入才改变了村民们的认同观念,这再次印证了“形式是重要的”这句话。虽然电视里的戏曲的味道已经越来越不对了,但毕竟真正懂戏的村民并不多,“外行看热闹”,他们也没有觉得这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细想起来,政治或市场的介入其实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们破坏了戏曲原有的民间形态,但另一方面它们也给戏曲提供了生存的空间。尽管这种空间有些暧昧,会令很多有识之士不舒服,但它毕竟激发出了戏曲存在的种种新可能。
我家乡的另一项重要的文化生活是以祭祀、祈祷等为主的“迷信”活动。而这些“迷信”活动是与个人的功利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无非是保佑家人安康、五谷丰登、肥猪满圈之类。但对于在一个偏远乡村世代生息的农民而言,这些似乎也就足够了,除此之外,他们也的确别无所求。我童年时代生活的那个村子的“信仰”以佛、道为主,村民或供奉观音菩萨,或供奉狐、黄二仙。乡间关于狐、黄二仙的传说不胜枚举。很多故事都带有自叙传奇色彩,讲述这类故事一度是当地村民茶余饭后的重要消遣(当然又不仅仅是消遣)。其讲述绘声绘色,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有时甚至会让人毛骨悚然,不敢出门。这些平日里老实巴交的农民讲起这类故事来却各个神采飞扬。我记得比较清楚一些的是这样一个故事:说某个村子的某个人因救过一只受伤的“黄仙”(我这样称呼是因为我至今仍对其心存畏惧),得到了报答。秋收的季节“黄仙”托梦于他,让他选择某个夜晚在屋里烧香祈祷,不准出门,“黄仙”会帮他运粮入库。此人将信将疑,但还是照做了。在选定的夜晚,此人不停地烧香、祈祷。天快亮的时候,他偷偷开门看了一眼,场面让他顿时惊呆了:满院的“黄仙”正排着长队不停地往仓库里背粮食。他赶紧关门,但为时已晚,“黄仙”们顷刻不见踪影。待他到仓库观看时,不由得大喜:好家伙,粮食已经堆得像小山一样了。第二天一大早,一个经常上山打“黄仙”的人便满村大叫,他家仓库的粮食昨夜被偷盗一空。在乡村,正是这些真真假假的故事的存在,才使得贫穷与破落之上又多了一道灵光。村民们也因此学会了对各种生灵心存敬畏,不敢轻易伤害他们。
村民懂得在任何时候都保持一颗敬畏之心,这似乎应该获得我们的赞许。但这种“敬畏”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其实是浮动的,找不到根基的。从表面上看,乡村有着它自身的逻辑,它保持着对城市生活的一种质疑能力,任何东西如果想要介入乡村都不得不改变它的自身,这是乡村独立、固执的一面。然而从更深层面上看,这种独立、固执又是相对的,各种各样的文化幽灵有时候恰恰就是利用它的这种独立、固执,创造出它的新的存在形态,从而获得自身。
在今天,农民成了被现代化甩得最远的一群人。在高昂的教育、医疗等费用面前,鲜有社会保障的他们苦不堪言。纵使那个传说中万能的“黄仙”在今天也是无力回天。“黄仙”这个财富与信仰的结合体失落了,那么新的寄托该在什么地方呢?城市人可以把现代化和赚钱当成信仰和寄托,但农村人对此却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可信仰而无法寄托。这时,天主教出场了。作为农民眼中的一种“科学”“文明”与“进步”的复杂混合体,它迅速迎合了中国乡村的巨大精神虚空。聪明的传教士们在传播天主教时重点强调的是它有病治病、无病防病的一面。这对于生病时进不起医院的村民来说,无疑是最大的诱惑。这种信仰形式既受到了官方的认可,也满足了村民对于现代生活方式的诉求,所以,后来者居上,迅速获取了当地人“信仰”的中心地位。2004年夏天我回乡祭祖的时候,我的一位伯父对我认真地说:“以前的信仰是封建迷信,现在的信仰是科学的,受法律保护。”有趣的是,村里依然保持原来信仰的人并不甘心处于边缘地位,他们经常和天主教的信仰者发生争论、冲突,相互诋毁。最严重的时候甚至发生武力争斗,最后由于公安机关的介入才得以平息。结局是原来的民间信仰被宣布为“迷信”,而天主教的正统地位因此得以确立。天主教因为与“科学”、法制力量的结合而具有了震慑力,而原来的民间信仰因为失去“科学”、法制的支持而不得不处于弱势。当然,对天主教的信仰并不表明村民的心理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他们只是从一种“迷信”形式过渡到另一种“迷信”形式。他们看到了比“黄仙”更让他们折服的力量—科学。天主教在今天要承担的功能也就是过去“黄仙”等所承担的功能。在这种转换中,我们再次感受到了意识形态强大的整合能力:飘荡在“信仰”深处的,是现代化的猎猎风旗。
这是浮动的乡村,失去了根基的乡村。在这个普遍信奉现代化的时代,我们似乎已经无法在它身上看到什么质疑的可能。相反,农民已经成为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最重要的力量,他们对现代化的渴望甚至已经超过了中国社会的任何一个其他阶层。现代化能够许给贫瘠了几千年的乡村一个富裕的未来,这是其他任何方式都难以做到的。村民们当年的那些祭祀和祈祷难道不正是为了这一点吗?
作者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