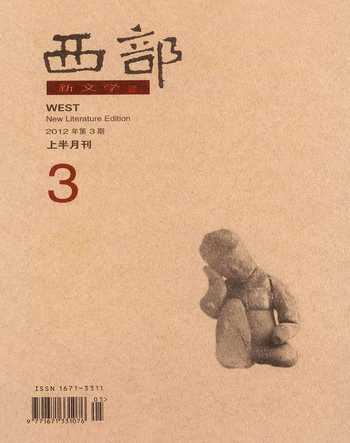生育报告
冯秋子
2003年秋,第三次来巴黎演出舞蹈剧场作品。第一次是1999年应邀在巴黎的法国国家舞蹈中心演出现代舞蹈剧场作品;2001年、2003年和2009年再来,是参加以当代艺术为展演主题的巴黎秋季艺术节。
2003年11月10日晚上,是我们的第三场演出,也是《生育报告》的首场演出。此次我们受邀参加巴黎秋季艺术节的有两部作品。前面两场,我们演出的是另一个舞蹈剧场作品《身体报告》,观众反映比较热烈,来的人不少,媒体报道也比较多。令生活舞蹈工作室全体人员欣喜的是除专业人士以外,来了很多普通观众,这些购票观看演出的普通观众,在我们看来是真正意义上的舞蹈剧场这种艺术形式具有的观众。
我的状态保持着,一如既往下午彩排,来了不少巴黎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媒体记者。通常,记者拍摄安排在彩排时间进行,他们可以自由走动,想拍什么位置差不多都能够实现。
我事先问艺术总监吴文光(也是演员和影像制作),他可不可以抽空拍一些图片。他先说可能顾不上,后又有点犹豫,说:“给我吧。你的机子可以挂在脖子上吗?”我说可以。他说:“拿来吧。”不管怎么样,他拍了几张,效果还好吧。我们又留下了一点演出过程的资料。我没能拍摄演出过程。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我喜欢拍摄现场,很想我的镜头如眼睛那样,能够看到现场,记录现场。对舞蹈剧场而言,是在作品进行中截取图片,但苦于自己那个时间在演出过程中,做不了这件事(倒是拍过一些别的艺术团队的演出现场),以前是没有好一些的机器,现在有了机器,是人在场上,我没有、也不能分心去拍片。
《身体报告》彩排时,我曾跳出情境,赶着拍下一些图片。
《生育报告》完全没有可能,我不能有离开现场的感觉。严格维护演出的状态,我才能全力以赴,不受任何影响地发挥我的作用。前面两场演出我非常认真、投入,内心安宁,心底有持续的力量和激情,冷静、节制,从始至终,有节奏地往前、往深处走。我沉浸在舞台的时空里,没有想别的,只把握着这个时间里我的心灵朝向、我的伙伴们的位置,还有时间……我在内心的波动中,扭转我的身体,让身体随同我的呼吸而呼吸,随同我的每一个来自里面的感觉而动作,并且表达出此时此地它们在所面临的真实可触的情境中的生活。直接的东西,在人的内里面过滤以后,变成真实的另一种存在,它仍然是直接的,但厚实而有力量,它是人的生命流程里最没有个人杂念的一些瞬间,但是,又因为“个人”,而使生命具有了不同的质感。作为舞蹈员,作为艺术工作者,我体会到节制,体会到细微的动静与人内心的消耗,体会到生命被唤醒时朴素慢慢还原如初的道理,体会到有声、无声,体会到活着,死去。
我有生以来表演的第一个作品就是《生育报告》。是文慧和我从1998年起,一点点进入探索、磨砺的现代舞蹈剧场作品。到1999年下半年,另三位优秀的专业舞蹈员陆续加入进来。历经三个多月紧张艰苦的排练。
作为非专业演员,我与大家一起努力,尝试着做我们想要的舞蹈剧场作品。
这部作品,在国内、国外的舞台上,我们演出了上百场。首演是1999年12月在北京人艺小剧场。我盘坐在一张一米多高、铺着棉絮的大床上,奔跑着,越跑越快,但声音平缓地讲述丢失孩子那场戏,我流出了眼泪。我寻找孩子的影像打在舞台悬挂起的用四张大被的棉絮拼接成的屏幕上。演出结束后,金星说,冯,不哭出来就好了。我们在人艺小剧场演出三场,她连看了三场。她说在三场演出中,她变换不同角度观看。
她的话在理。我体会到艺术的节制分寸。以后的演出中,我再没有哭过。眼泪团在眼窝里,我没让它流出来,也没有过哭泣的姿势。
我学习着在舞台上找到人活着的形态。从日常生活中学习到的,和从舞台上学习到的一样多,一样不同寻常。
排练和演出是艰苦的。它磨练我,让我有耐心回到出发的地方。我愿意守候在如家一样的原地。很多时候,我在一个地方呆着,心动的时候,想着出发。十二三年间,发生了许多变故,但我仍能感知到原初,仍然能够起身上路,即使是在心里面走路。
在路上走,知道为什么行走。我活着,扛着生活,向前赶路。然后回来原处,思想众生万物之源渊。
2003年11月10日晚上在巴黎演出。我流落出去一些时间。
人在死亡的边缘行走,在绝望中朝着渴望的图景冲刺,求生的念头几乎是看不见的。因为疼痛之剧烈,因为疼痛而淹没了自己,因为裂变中死亡的气息笼罩在头顶上,因为空气中没有可以抓住的、能够驮驾自己到达彼岸的战车,没有一只能够依靠的胳膊,或者是一只手,一个胸怀,一个安慰,一种声音,所以,全部的内容回旋、汇集在一个词上:活着。
曾听我母亲说,女人生孩子,就像在水缸沿上跑马,说掉进去就掉进去了。
我在《生育报告》中,其中一段独立进行的舞蹈,是人倒立在一把椅子上,一边叙述生育那一天经历的事,一边起舞。每一次演出,做出来的动作和前面表演的有很多不同。从椅子那一片土地上生长出来,枝叶往哪里伸屈,枝叶如何伸屈,每一根枝不同,每一枝的每一轮的生还不一样。土地和阳光,给予枝条融解、再生,枝条给予土地和阳光以补充。
不过,在舞台上,想不了别的。
实在没有理由想别的东西。此时此地,我还没有见到孩子。他踢了我好几个月,和我朝夕相处好几个月,我与他同在一个物质世界,却抓不住他的手,抓不住他的胳膊,抓不住他生命的根,不能把他顺利地带到这个世界上来。我在这一刻,没有了力气。那一时节,瞬息万变,他能够出来吗?他的生命能不能成全我的生命,我的生命能不能成全他的生命,全是未知数。他就在我的身体里,而我不能够帮助他。我是唯一能够感觉到他全部动静的人,却使不出我的力气去帮助他,我真没用。我什么也做不了。绝望差点儿埋没了我的心跳。我赶紧恢复理智,让自己保持清醒。除了尽自己的全力,我几乎想不出还能做什么,所以,我没有想到哭泣,没有想到自己想哭泣,没有过多地指望谁能帮助我,只想自己能够帮助孩子,帮助他顺利地出来。那些时间里,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自己已经无足轻重,只是为了孩子而存在其间。只有孩子,孩子真实地存在着,他在我的肚子里。我有些绝望。焦虑追赶着我,可是我跑不动。我帮不上他的忙的想法,又一次冒出来。事实上,只有我能够帮助他,不能放弃努力。我的力气还没有全使出来。给我一点儿时间,只需要一些时间,让我努力,让我尽我的全力。
我进产房前,住在病房。对面病房住的女孩,没有结婚。那个生下来已经死亡的男孩八个月大了,因为他的母亲还没有结婚,不得不做引产,被医生注射的一针管药液熄灭在他母亲的肚子里。他生下来前就已死亡,他在他妈妈的肚子里被停止了生命。他不知道一根细小的管子挤进来,是为结束他的生命。他以为那是他的妈妈递给他的粮草运输线。他一定是吃惊的,因为没有几个孩子在这种时间里能被脐带以外的另一根细线连接起来,他是一个例外,他被这根细线连带起来的瞬间,就停止了呼吸。
不知他是不是用脚或手拍打过他妈妈的肚皮。
他妈妈当时正被她的父母包围着。他们说不能生下来,我们不能养一个私生子,我们家不能做这样的事情出来叫人家说三道四,我们的脸没地方搁。我们不能让这个孩子毁了名声,你爹妈两个家系,条条缕缕沿袭至今,没出现过这种伤风败俗的事情。你不能让我们老了老了,没脸出门。我们死了那可以,我们活着,抬不起腿脚,抬不起头啊。往后,我们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你怎么能忍心,让我们的老脸丢得没处掖藏,嗯?你想一想你的爹妈,我们怎么得罪你了,一把屎一把尿拉扯你成了人,我们有罪了?你让我们怎么活下去呢……求你啦,孩子的事,有什么呢,你以后好好地找个人,成个家,还能生,想生什么样的,生他,现在千万不要,生什么生。你对自己也得负起责任对不对?你做了对不起我们的事,你以后也没法好好地活啊,你自己也会被人的手指头戳疼喽。你现在小,不懂得,想不到以后的日子怎么过法,我们好歹是过来人,我们得为你着想。爹妈这一辈子该你的,不为你想,为谁想呢……话说回来,你也得为自己想一想,为我们想一想。一个孩子,没生下来,就不算个人儿。女人一辈子想生孩子,时间有的是,这个时候咱们不要他,是因为条件不成熟,等条件成熟了,再要不迟嘛,咱们什么都没有少……那多好,啊,你说这样子好不好?只要一点时间,绕过去,往前头走,跨过去这一段,咱们的路面就宽敞了,展悠悠的了。现在的情况是,这么走,越走越是钻进了死胡同啊。孩子,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咱们不要这么走法,啊?爹妈给你跪下了……
于是,那个被他们称作孩子的青年女子,坚持到不能再坚持,同意引产,把她的孩子解脱出去。婴儿生下来是个死胎。但是那个女孩一直昏睡,不醒过来。她住我对门,身体一直往外出血。她中间醒过来一次,跟大夫说,你给我也打一针,让我一块儿死吧。女孩的父母说,那不行,你得好好活着,你是我们的,你不能这么想,你死了,我们怎么办,我们还活不活啦?净说阴雨天撮泥堆儿的话。爸爸妈妈在,你见天价好好的,啊?好好地活着。
我不用想我的身体怎么动,只管我怎么想,只管我的感受是什么。我在自己的回顾里,在自己对于身体和生育的感受中。我的身体完全不受规范的限制,它是自由的,柔韧的,沉重的,魔幻的,毁灭的,艰难困苦,而后再生。那种自身与新的生命一体的、经受考验与磨练的过程,把过去的自己和新的历史阶段的自己,以及生育以后的自己,骤然间锻造成一个完整的、诚实可信的人。
这是谁的权利呢,生或者是死?大人无法决定,孩子自己也无法决定,他是那么可怜地待在一个角落,等着谁来决定他能不能够生,或者是不是非得死。只是不知道他自己愿意不愿意生,或者愿意不愿意死。他还没有能力、没有机会表达他的愿望。
我一面跟随着孩子一起深呼吸,一面想办法看见他,感觉着他的意见。我觉得他想生。因为我深呼吸的时候,他让我感觉到了一个完整的生命的存在,他配合着我一起呼吸,他骤然减轻了我的疼痛,他传递给我面对活着的方法:让我感觉到生理的疼痛不算什么,我们可以超度过去,这是我们的必经路途,我们要走的路的其中一段。这段路,我们能够度过去,能往前面走。我们两个一起走。我们的力气是因为我们绑在一起而聚集出来的。他支持我,我感觉到了他的支持、他的爱护。他把自己缩成一个小团,等着穿越那个黑暗窄小的隧道。他是从容的,他准备着启程,他准备着艰难地爬雪山过草地。他以所占份额最小的团体,等待着上路去长征。他的道路幽深、危险,但他做好了准备。天哪,这个孩子对这个世界,对我,是这样的态度。
那一时刻,我体验到了世事存在中的大和小、多和少。
我清醒过来,我是唯一能够引领他穿越沙漠冰川的人。我不是死亡之谷,我不是魔鬼,我是他的血亲。我领着他一步一步地迈过血肉模糊的隧道,去看见阴沉沉的天空。
外面在下雪。窗户开着。有雪花往房子里飘。
他们把孩子带走了。产房里只有我一个人了。右胳膊上仍插着吊针,催产素继续滴答着注进我的身体。身上没有遮盖的东西。两个多小时以后,我感觉到清冷。肚子瘪进去了,人空前瘦小。溅到身上的血汁干了不少。身体仍停泊在血水里。血把我和床单粘连在一起。我试着从血水里把身体分出来,没有完成。伤口疼痛得动弹不了。我想拉出床单覆盖身体,最后拉出了床单的一个角,盖在够着的地方。很久以后,进来一个打扫卫生的女子。我说,请帮我找点东西盖吧!有点儿冷。她说产房没有能盖的。看见风中飘动的窗帘,她说盖不盖窗帘?盖吧。她一把扯下窗帘,抖一抖,给我搭在身上。一块黑红黑红的绒布。
再次见到孩子,他饿得“啊啊”地叫,张大嘴,身体往一个方向斜着找,眼睛紧闭住。没有吃的东西给他,他又往另一个方向找,“啊啊”地将头朝向那个方向,身体跟着头的方向。我还是没有奶水给他。我跑出病房喊护士,护士说不用喂,吃不了什么。我急得满头大汗,我给不了孩子什么帮助。
他的小胳膊上戴着一个小牌,写着他的名字,写着我的名字。这确是我的孩子。
我给他起名叫巴顿。
我不知道他喜不喜欢自己叫这个名字。
我曾经给我的侄女起名叫“冯蓁蓁”,她长到十三四岁的时候反抗我,说她要叫“冯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