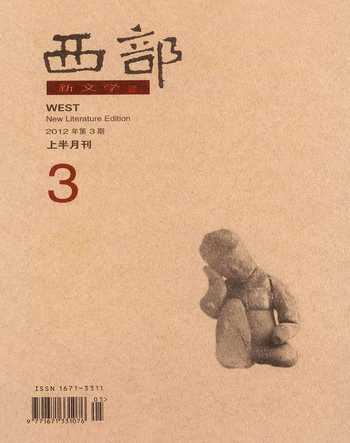上访记
李康美
如果不是白月月那张“糜面嘴”,余美焕那一天是绝对不会走出家门的。
早上起来,余美焕的眼皮就一个劲地跳。开始她还觉得很高兴,反复和丈夫论证说,恩川呀,我的眼皮跳得厉害,你说是不是有什么好事情来了呢?王恩川刚刚送孩子上学回来,也就顺话答话说,现在孩子上学这么远,中午不回家,还得再交午餐费,兴许你出门栽一跤,面前就蹦出一捆百元大钞了!余美焕没好气地说,人家和你说正事,可你总是做梦娶媳妇。王恩川说,你自己听听,到底谁在说正事,怎么反而倒打一耙呢?余美焕不再理睬王恩川,嘴里却自言自语地念叨说,左眼皮跳财,右眼皮跳崖……突然又大呼小叫地喊,喂喂,那句话是怎么说的?王恩川厌烦老婆神神叨叨的样子,但又惧怕老婆的身坯子和坏脾气,侧目瞅了瞅老婆,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
余美焕是可以称作五大三粗的那种女人,肤色也黑,年轻时在娘家那边,还曾经有过“黑牡丹”的美誉,可是到了现在三十八岁的年纪,除了身材越来越壮实,面盆似的脸孔上,在那种黑色依然中,也再看不出鲜亮的光彩了。
哎,问你话哩!余美焕的手掌不由得捂着砰砰乱跳的右眼皮追问说,那句老话究竟是怎么说的?王恩川这才认真地打量着老婆,看见老婆已经有点儿心慌意乱,只得如实相告说,你自己刚才已经说对了,左眼皮跳财,右眼皮跳灾嘛。余美焕愤怒地说,怎么又变成跳灾了?王恩川说,不管是跳崖还是跳灾,也就是说法有点儿不同,道理其实都是一样的。余美焕的情绪越发受到影响,三个手指也使劲地把右眼皮扯长了,似乎只有消除了右眼皮的跳动,才能把冥冥之中的灾难提前祛除了。王恩川看着老婆那样的怪相,哈哈笑了一阵儿,又连忙劝解说,别信别信,都什么年代了,眼皮跳一跳,还真能跳出什么事儿了?余美焕对此也不是很认真,但却以此要挟说,那你今天可就别惹我,把我惹毛了,可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王恩川巴不得离家出走,刚才在路上,有几个哥儿们就吆喝着打麻将,现在马上有了正当的理由说,不敢惹,就赶紧躲,中午吃饭你都不要等我了。他说着话就立即往出走,半道儿又想起身上需要带钱的,而他们家的所有积蓄全由老婆收藏着,即使送孩子吃早点,老婆也会把账算得很精细。哎哎,能不能再给一点儿钱?王恩川返回身涎着脸说。
要钱干啥呢?余美焕几乎是吼叫着问。在她的右眼皮上,已经贴着一片菜叶。王恩川知道这也是一种压惊的民间偏方,过去都是把麦秆破开,掐下细细的一段粘在眼皮上,如今村里没有了土地,还能从哪里找麦秆?看着老婆的怪样子,王恩川再次笑弯了腰。这就越发激怒了老婆,老婆更加严厉地问,你说,要钱干啥呢?!王恩川不敢说打牌,只能编谎说,一个大男人,总不能闲得学驴叫唤。他想进城转一转,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挣钱的门路。余美焕很干脆地说,还没挣钱就要花钱呢?不给!王恩川仍然耐着性子说,进城也要坐公交,找不到活儿还要吃饭吧?余美焕一激动,眼皮就跳得更加厉害,她再次怒吼了一声说,这几步路就走着去,找到了活儿也就有人管饭呢!
唉,我怎么就摊上了你这个婆娘哩!王恩川嘴里嘟囔说。
你说啥?!余美焕大步冲过来说,刚才的话你忘了?你是不是真想看看我右眼皮跳的效果呢?
王恩川赶紧再转身,跑出门彻底不敢回头了。
白月月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走到余美焕身旁的。其实余美焕的出走也有丈夫王恩川的责任。按常情,当王恩川在楼下遇到白月月时,就应该制止白月月说,今天什么事情都别找余美焕,她一直喊着右眼皮跳灾呢,和疑神疑鬼的人在一起,没有乱子也惹出乱子了。可是王恩川只想着打牌,要打牌就需要带些钱,如果白月月把老婆领走了,他就可以从家里偷出一点儿钱出来。所以,王恩川也不问白月月找老婆有什么事,只是很干脆地说,在家呢在家呢,她也是等着你一块耍耍呢!白月月看着王恩川可可怜怜的样子,甚至还多余地问了一句说,是不是又受那个黑货的欺侮了?王恩川这句话倒是很真实地说,唉,饭饱生余事,闲闲地呆在家里,每天都是磕碟子绊碗哩。白月月不再多说话,撇下王恩川就直接上楼了。
你个黑货在家干啥呢?白月月踏进门就说。在村里的女人之间,许多人都把余美焕叫“黑货”,余美焕也从来不计较。当然其他人也都有别的外号,走路快的人叫拧得欢,长得又粗又短的人叫麻袋,再比如说眼前的白月月,由于她有着三寸不烂之舌,大家又把她叫做糜面嘴。糜子面吃到嘴里带有甜味,熬成浆糊像胶一样粘,每一个外号,说起来都既形象又生动。
平时都是好姐妹,余美焕看见白月月进来,情绪很快就好转起来,说,哎呀,糜面嘴来了,我正憋得难受呢,也就是盼着你这个糜面嘴能给我解解闷。
闷啥呢?呆在屋里就不闷了?白月月做任何事情都是察言观色,循序渐进。
余美焕这才松开捂着右眼皮的手掌说,你瞧你瞧,我的右眼皮咋就砰砰地乱跳呢?
白月月也嘻嘻地笑了说,叫你个黑货还好听,再叫你个烂菜叶,可就和破货差不多了。
余美焕嗔怪地说,我正心急火燎着,你就不能说点儿好话嘛。
白月月说,你赶紧把那眼皮上的烂菜叶取掉!黑脸上贴着一片绿,就像是夜色中的荧火虫,看着都让人瘆得难受,我能有一句好话嘛。
余美焕终于取下眼皮上的菜叶说,现在你有什么好话呢?
白月月问,你觉得眼皮还跳吗?
余美焕眨了眨眼睛,然后又使劲把眼睛睁开,静了稍许,忽然就搂住白月月说,好像不跳了,你这个糜面嘴真成了治病的良药。
白月月顺势拉着余美焕往出走,一起出门后甚至还把屋门“哐”地带紧了。余美焕这才问白月月到底有什么事?白月月说,病都是呆在屋里憋出来的,跟着大伙在外边逛一圈,如果有机会再大声喊一喊,就什么毛病都没有了。说话间已经到了楼下,远处的院子那边聚集着许多女人。余美焕不知实情,只觉得她们根本不像是扭秧歌,也不像是闲逛的神情,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要找人闹事的激愤。余美焕禁不住后退了一步,明显地觉得右眼皮又“突突突”地跳了起来。白月月的手早就松开了余美焕,只是在嘴里催促说,快走快走,没有你这个黑货弄不成事!
余美焕一下子明白了说,又是找政府闹事呀?
白月月说,知道了就不要再啰嗦。
余美焕平时也总是打头阵,可是今天她真是不想走出门,就还是拿出老话说,月月,今天你们就把我饶了吧!不管是迷信不迷信,这右眼皮跳毕竟容易让我分心,分了心也就没有劲儿,没有劲儿也……也就不是主力军。当不了主力军,有我没我有什么要紧。
那边的女人们已经喊开了,“黑货、黑货”地叫着,似乎余美焕不过去,就成了队伍中的逃兵。白月月趁势又激将说,你想回就回去吧!你如果觉得这样的阵势还能溜,以后也就真成了烂菜叶!
余美焕本来就是在家里坐不住的人,现在看见大家都已经集合了,就更是觉得迟到了一会儿都是丢人,嘴里说“有我没我有什么要紧”,可是脚底下早就向那边移动着。后来又几乎是跑进了队列,冲向前边后,还习惯性地挺直了黝黑的脸庞。六月的热风一吹,余美焕也不再觉得眼皮跳动,似乎是把全部的激情都转移到即将发生的战斗中去了。
王禾村早就不成为村子,原来的乡政府在三年前就改成办事处,村委会的大门上也挂成了“王禾社区”的招牌。尽管一下子都变为城里人,但是彻底失去土地还是今年春天的事情。一条高速铁路从村北经过,剩下的最后一块农田也要修建高铁的火车站了。开始,大家还都高兴地想,这以后再不用面朝黄土背朝天地种庄稼了。去年,散落的村庄已经全部拆迁,两千多号人呼啦啦地就拥进了“王禾社区”的高楼里。没有了土地,也没有了各家各户的小院,猪呀羊呀狗呀鸡呀的家畜和家禽也就养不成了。
当城里人舒服是舒服,问题是以后再没有来钱的路,分得的那点儿卖地的家底儿,迟早也就会坐吃山空了。这样的后患谁想着都煎熬,有的女人睡梦中还喊着“唠唠唠”,醒来后才知道高楼上是不能养猪了。有的女人还带着几只鸡上了楼,几天后阳台上的臭味儿,就招来了上下左右的抗议声。余美焕右眼皮的跳动,实际上也是晚上没睡好。昨天下午,她的娘家哥哥又来了,说是她的侄子上了大学,每年五六千元的学费可怎么办?余美焕支吾说,她也没有钱,哥哥气呼呼地甩门离去说,你们城里人怎么都是这么个眉眼?!
农村人把他们当城里人看,可是城里人又把他们看成农村人。余美焕和几个妇女,前几天还缝了些鞋垫在街道边上卖,那些城管队员一边驱赶一边训斥她们说,都是哪儿的无业游民,把街道当成你们农村的院子了!她们说她们也是城市居民,可是人家不和她们讲理,甚至还引起了一片讥笑声。王禾村的人越想越窝火,就多次去市政府上访闹事。这样的上访闹事也没有个立即可以解决的主题,接待上访的人也只能讲些大局势,再就是说些自力更生、路在脚下之类的客套话。尤其可气的还有村上的男人们,开始他们也参与,慢慢都打了退堂鼓,以为每家都有些存款,走一步先算一步吧。
女人们想得远也想得细,再加上现在六月天的太阳一晒,她们又记起了收庄稼的季节,似乎今天再去市政府,就成了真正的找饭碗,讨饭吃!
余美焕完全不知道,今天的上访闹事,几乎不需要跑多少路。她刚刚加入了队伍一会儿,白月月就悄声告诉她,一大群领导马上就会出现在咱们的面前,听说还有一个市长带队,这不是碰在枪眼上了吗?余美焕连忙问,从哪儿得到的这种消息?白月月说,全中国的人都是亲套亲,市政府里就有人通风报信呢。
说话间就快走到正修着高铁火车站的那个工地了。白月月忽然冲着大家喊,都注意了,不能这样一堆一伙地等待,这样就远远地把他们吓跑了。散开,先散开,等到他们停下车,咱们就堵到车队的前头,不给个说法不散伙!余美焕从来都是不甘寂寞,也随声大叫说,咱们也才二三十个人,他们的人可能比咱们的人还要多,打头的车实际也是马前卒,可别抓住芝麻丢了西瓜。要我说,只要把带队的市长团团包围,其他人跑了也没啥!有人说市政府的市长好多个,你余美焕认识哪一个?余美焕说,可是市长坐的车肯定最豪华,瞅不准人难道认不准车吗?白月月就骄傲地说,看看看,还是我想得周全吧?别看这个黑货黑,肚子里却有许多门门道道呢。有人立即也附和说,对对对,没吃过猪肉也听过猪哼哼,好车都能看出来。
余美焕受到了赞赏,就更加意气风发地布置大家说,散开,都散得远远的,或者抠野菜或者拣破烂,总之要像个干活的样子,不要让他们一眼就识破了咱们的阴谋诡计!这句话大家又不愿意听了,纷纷指责余美焕说,正大光明地要工作要饭吃,怎么咱们反而是阴谋诡计呢?余美焕只得赶紧解释说,打个比方么,生哪门子气。白月月也提醒余美焕说,到时候你要管好自己的嘴,市长可不是王恩川,由着你的性子又撕又骂又训斥。余美焕愠怒地说,快滚得远远的,我家那东西如果是市长,还用得我这样着急上火吗?再说了,我这张臭嘴只是在家里使性子,出了门哪,也知道个文明礼貌呢!
六月的天气早上还罢了,眼看着太阳渐渐升高,晒在阳光下面的每一张脸,个个都挂着细密的汗珠了。似乎大家都很听话,还没走到车站广场的工地旁,眨眼之间就都走散了,只是把余美焕留在了原地。余美焕真正成了领头人,成了身处中心地位的指挥官。因为要修现代化的火车站,周围的树木几乎砍伐得光光净净了,余美焕在光天化日之下站了一会儿,才突然感到了一种作弄,他妈的都怕热,站岗放哨的就应该是我一个吗?上访闹事凭的就是人多势众,从市区过来的这个路口,剩下余美焕一个人,她的心里就莫名的紧张。心里发紧,右眼皮好像又开始跳了。
人呢?人都跑到哪儿去了?余美焕不由得又大声呼唤着。
没人应声。
除了通往市区的那条宽阔的大道两旁刚刚栽下的花木和冬青,在这方圆二三里的地面上,有阴凉的地方,也就是那高速铁路的桩墩下。余美焕远远地往市区方向望了一眼,视察的车队仍然是无踪无影,这就匆匆地跑到北边去寻找她们。结果这么一看,余美焕的火气又上来了,原来她们一群人,根本没有佯装拣破烂或者抠野菜,而是三个一堆四个一伙地靠在铁路桥墩的背阴处歇凉哩。
哎,你们都是属猴的,就我一个是属猪的?还没有上阵,都知道偷奸耍滑了。余美焕说。还是白月月这个“糜面嘴”接话说,人常说能者多劳嘛,这一点点亏你也吃不起?余美焕问,我哪儿就是个能者了?白月月本来想说她刚才的逞能就是本事,见余美焕的黑皮肤经太阳一晒,不但黑得透亮,而且还泛着殷殷的红色,立即又改口开着玩笑说,说到底还是黑货好,你们看黑牡丹的模样不是又回来了吗?
这句话把大家都惹笑了。
余美焕越发扫兴地说,你这是说的什么屁话呀!算啦算啦,指望你们找市长闹事,还不如呆在家里睡觉哩。
有人说,让大家先散开还不是你刚才布置的?
余美焕说,那也不能把我一个扔在干滩上!
有人说,干什么事情总得有个带头人,我们自觉自愿地佩服你还不好?
余美焕倒吸了一口冷气说,我多说了几句话怎么就变成头儿了?噢,多亏现在还不敢随便抓人,如果放在前几年,稍微追查下来,你们也会把我出卖了。行了行了,我家王恩川不聪明,可是还知道要进城找个活儿干呢!你们如果还是这样躲躲藏藏的,那我也马上回家去!
白月月这才重新走向那边的大道说,还是大家都过去,一想起以后没有饭吃的日子,睡在席梦思床上也睡不着。
大家一下子又跟着白月月走了。
余美焕见不得自己被孤立,又多了一句话说,也没有必要太着急,市上领导过来视察,这里肯定有人提前等候,迎来送往也是官场的规矩。可是你们看看,现在这里的工地上,除了推土机、挖掘机,有没有迎接的车和人过来?
由于大家还在生着余美焕的气,再没有人赞赏她的经验和见解了。
这群妇女开始还是义愤填膺地站在大道旁,渐渐地就受不了滚滚的热流了。为了表示她们的勇气,来时谁都没有戴草帽或者伞具什么的。问题是左等右等还不见视察的车队过来。余美焕有了刚才的教训,紧咬着嘴唇不说话,只是用冷冷的目光看着白月月,意思是说,你不是说市政府潜伏着王禾村的内线吗?怎么现在装哑巴?其他人也都是白月月吆喝出来的,白月月又成了被几十双目光抽着的陀螺。
白月月支支吾吾说,看我干啥呢?全村人的利益,难道是我故意捣乱哩?
余美焕忍不住又抢先问,别的不用你解释,你只说视察的领导在哪里?
白月月说,反正有人打电话了。
余美焕就追问是谁打的。可是白月月总是不说出那个人。这时候,白月月又成了众矢之的,她越是搞得很神秘,大家就越是追问得紧,甚至,有人还骂她是骗子,如果把大家热出了病,也就是白月月变着法子给自己家赚钱呢。因为白月月的丈夫一直开着小诊所,过去在门前还挂着招牌,只是全村拆迁后被分配住到了五楼上,去看病的人就少了许多。
白月月无奈地掏出了手机,当着大家的面拨通了电话说,喂,郭主任吗?我是月月呀,那个……那个市长带队视察的事情怎么还不见过来呢?对方不知道说了些什么,白月月又娇里娇气地嗔怪说,那你也该再和妹子通气啊,这不,害得妹子里外不是人,还以为是我说了谎话。最后,她还捂着手机轻轻地吱咂了一下嘴唇,显然是回应对方的调情。
余美焕吃惊地看着白月月,半天才说,这个糜面嘴啥时候又变成狐狸精了?竟然和哪个郭主任经常亲嘴咬舌头!
白月月涨红了脸解释说,别乱说!人家是我……我娘家那边的亲戚,论辈分我把他叫哥呢。
余美焕说,骗鬼去吧!如果是亲戚如果是哥,哪就用得着喊他“郭主任”?
刚才站得远的人真是没有看出什么、听出什么,即使听出名堂的其他人,也不想在大热的太阳下对此事纠缠不休,但是呼呼的斗志已经松劲,扯住余美焕要白月月把电话里的事情说清楚。白月月这才脱出身来说,黄市长带队视察一点儿没有错,但是由于安排的视察点太多,现在已经回到酒店准备吃饭呢。至于什么时候才来这儿的车站工地,吃过中午饭后才能确定下来。
余美焕说,这不是和上当受骗差不多吗?
白月月不再理睬余美焕,索性把背后那个高人的高招告诉大家说,赶紧回去吃完饭再过来,现在任何事情都讲究个超前意识,如果市长询问我们的具体要求是什么,我们就明确回答说,将来车站修好后,不是有许多商业网点吗?那些网点可不能再让承包商卖出去,王禾村的人,可就是要靠开门店摆摊位过日子呢!人常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王禾村的人再没有其他指望了,能依靠的也就是这个火车站。
按理说,白月月说出来的主意真不错,可是余美焕的心里却一个劲地想着白月月和那个什么郭主任的隐私了。凡是女人,大概都会时常忘记了自己的长相,何况余美焕还曾经有过黑牡丹的骄人资本,这样,嫉妒之心就再次折磨着她的神经系统。白月月的丈夫个头很高,生相也是细皮嫩肉的,和余美焕的丈夫王恩川比起来,实在是骏马和小毛驴的关系,尤其还身为看病的医生。如此的差别,白月月怎么在外边还有男人呢?而且还是端着公家的饭碗,不知在哪个部门当着主任,竟然经常知道市长的行踪,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啊?
临上楼回家时,余美焕又朝散伙的那群女人望了一眼,她们仍然相随着白月月说说笑笑地嘀咕着什么,这更加让余美焕不是滋味了。刚才大家还嚷嚷着她是带头人,现在看来纯粹是哄她玩,把她当枪使,真正的中心好像永远是让白月月占据着。
胡思乱想着往上走,余美焕突然一脚踏空,滚下楼梯后,整个人就不能动弹了。剧烈的疼痛感是从右脚踝那儿扩散开来的,从瞬间的昏厥中清醒后,余美焕才意识到,肯定是右脚踝那儿的骨头坏了。这时候,她已经忘记了这和右眼皮跳动的必然联想,只是断断续续地呻吟着,快……快来人啊,我的腿断了啊!来人啊……
楼下的门洞里终于伸出一颗头,但是那颗苍老的头颅却只能往上瞧了瞧,大声地询问余美焕说,这好端端的怎么就腿坏了?
余美焕知道那是七爷的喊声,七爷不只是年纪老,而且早就腿脚不灵便,别说上楼来救她,喊那么一声也要费出吃奶的劲儿呢。余美焕也朝七爷喊,七爷呀,赶紧叫人哪!七爷说,我能出去也就不是半残废的老东西了。余美焕说,打电话……你帮我打个电话啊!七爷说,你平时身上不是装着手机嘛!最可靠最得劲的还是赶紧让你家恩川回来嘛!余美焕刚才是急糊涂了,有了七爷的提醒,她才忍着疼痛把身子坐正,掏出手机呼唤着丈夫王恩川。王恩川仍然谎称他正在城里的人市上找零工,听余美焕哭爹喊娘的说她的腿断了,这才连声说他马上回来马上回来。可是话筒里,却发出了麻将的一片哗啦声。余美焕质问丈夫死到哪儿去了?话筒里却成了挂断电话的嘀嘀声。
一会儿,王恩川又打回电话说他已经拨打了120,还责怪余美焕怎么就把最快捷的办法也忘了。余美焕心里想着自己的可笑,嘴里却骂着丈夫,你狗日的,回来再和你算账!
救护车是鸣着响笛开进王禾社区的院子的。这又检验了农村人和城里人的区别,包括白月月,在屋里还以为是谁把警车叫来了,心里说,这还没有等到市长闹事,怎么就惊动了公安局呢?可还是恐惧得不敢出门。一直到有人看清是救护车,才又都跑下楼来看热闹。
谁呀谁呀?是不是七爷又犯病了?有人议论说。
白月月一遇见病人就立即联想到她家的门庭冷落,尤其是看见还要把病人往外拉,就没有好气地脱口说,平时把钱也看得太紧了,怎么就不知道提前预防呀?
王恩川正好抬着余美焕出了楼门,火气更大地冲着白月月骂道,谁他娘的爱钱谁知道!我一再说我家美焕今天不对劲儿,为啥还要把她拉到太阳底下晒半天呢?
白月月这才弄清是余美焕出了事,却还是嘴不饶人地狡辩说,腿在自己的屁股下面长着,你家黑货也不是穿开裆裤的毛孩子,怎么崴了脚就怪罪别人了?
王恩川还想说什么,躺在担架上的余美焕狠狠地拧了他一把,他才尖叫了一声,匆匆地走近救护车。
余美焕被抬进了救护车。
拍片子,打石膏,余美焕待在医院里不能动弹了。
检查的结果确实是骨折,虽然渐渐止住了疼痛,但是余美焕还要忍受着继续赊财的心理折磨。住在医院里,就得按照医院的规矩办事,CT、心电图、抽血化验,还要尿液和粪便,不只是王恩川的脸上挂上了阴云,余美焕自己也心疼地埋怨医生说,腿坏了看腿,怎么就把我当成大病号了?可是医生有医生的道理,好端端地上着楼,怎么就一脚踏空了?诸如突然的脑梗心梗都会发生短暂昏迷。总之是需要排除各种病因,才是对你以后的生活负责。有些话甚至和白月月说的话如出一辙,现在你们把钱都看得这么紧,在平时的防治上肯定也是粗心大意,既来之则安之,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比什么都重要!
三天工夫,就把五千块钱送给了医院,余美焕就睡不着坐不住了。王恩川同样心疼钱,又不敢在余美焕面前露出忧郁的神色,只是转弯抹角地念叨着孩子说,儿子暂时住在他大伯那儿倒也放心,但是时间长了恐怕就没有人能管得了啊。其实余美焕比丈夫更着急,她的腿打上了石膏后,就闹着要出院。尽管能检查的全检查过了,可是医生还是吓唬她说,这么严重的伤情,起码需要打一个疗程的针、吃一个疗程的药,不然,很可能还会发炎,你们农村人对小病总是不在心,比如说,发炎问题不及时解决,发展下去就会化脓,后患无穷呀!“农村人”那么几个字,一下子把余美焕逗火了,她愤怒而又坚决地说,出院出院,农村人难道都是猪脑子吗?王恩川也觉得那样的话伤了自尊,随即插话说,同志,那我就明确告诉你……
出院出院!余美焕不由分说地打断丈夫的话说,吃屎的还把屙屎的缠住不放了。医生也发了脾气说,瞧你这人怎么连一点儿道理都不懂,嘴里也不干不净了!余美焕只是拍打着床铺喊,出院出院,我要出院!医生说,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出院和住院的问题,先把你刚才骂人的事情说清楚!余美焕弱了声说,我是吃屎的行不行?你们让我出院,就像是把一堆狗屎扔出去!
回到家里,余美焕的心情好转了一些。村里也时常有人看望,或者是一篮子鸡蛋,或者是一箱饼干和奶粉,这好赖也算是堤内损失堤外补吧。但是很快余美焕心里的气又大了,她又想起那天右眼皮跳动的前因和后果,白月月是自己受伤的罪魁祸首,怎么她倒躲得远远地不敢见她了?!
那个糜面嘴真不是个好东西!余美焕禁不住又骂出声来。
谁是糜面嘴?王恩川疑惑地问。女人堆里的事情男人不知道。
你把白月月给我叫过来,看我不撕烂她的嘴!
啊!王恩川这才明白糜面嘴就是白月月,赶紧劝解说,白月月的老头子可是医生呢,以后看病再不能舍近求远了,得罪了别人也不敢得罪她。
那天都是她缠着我出了门,也许就是在太阳底下把我晒得迷三倒四的,现在她倒作聋装哑了?余美焕的眼睛里噙上了泪水。
王恩川不知道那天女人们在车站工地寻找市长闹事的场景,也就无话可说了。
白月月!余美焕打通白月月的电话喊道,你眼睛瞎了耳朵也聋了吗?女人之间的外号都是亲昵的称呼,余美焕就不再叫白月月为“糜面嘴”了。
白月月接着电话,也没有叫余美焕“你个黑货”,只是用哼腔哼调的声音说,有事说事,没有事我挂了!
余美焕早已经想好了要说的话,立即接着话茬说,我只是想问问,这几天你和那个郭主任又睡了几觉?别折腾地生了病,那样的病你家老头子也看不好!
白月月稍有为难地说,你先操心自己的腿吧,小心把心也劳病了。
余美焕见仍然震慑不住她,干脆就敲明叫响说,我当然管不了你,可是总有管住你的人吧?我不信你家老头子就喜欢绿帽子。
这句话倒把白月月惹笑了。
一会儿,白月月果然就走进余美焕的门,不等余美焕冷脸相讥,白月月的丈夫也随即进门。这倒让余美焕提心吊胆,现在这世事,即使是发现了别人的私情,也没有多少人做出傻事,如果做出告发的傻事,甚至是告发者比私情者还要遭人唾弃。人家的身子人家用,与你有屁关系啊?余美焕在电话里的要挟,说到底也就是拿她出出气。
我把我家老头子给你带来了,有什么事情你直接对他说。白月月咄咄逼人。
余美焕赶紧说,我这腿伤现在还不需要换药,可是以后麻烦崔大夫的时候多着呢。
白月月说,你问他郭主任!
余美焕只得装糊涂说,哪个郭主任?糜面嘴你今天是怎么了?
白月月的丈夫以职业的习惯先看了看余美焕的脸色,这才嘻嘻一笑说,你们两个好姐妹,没有必要再打肚皮官司吧。人常说,人有旦夕之祸福,既然出了事,就不要再埋怨天埋怨地,舒畅的心情比吃药打针都要紧。
白月月仍然不饶人地说,这个黑货要说的是郭主任!
她丈夫仍然是嘻嘻笑着说,你们女人的事情你们自己说,我没有那份耐心,也一直不喜欢虚荣。说完,就好像完成了他的任务,平平静静地走出门去了。
白月月继续追问说,你个黑货怎么又不敢说了?
余美焕看着门外的背影低声嘟囔说,你怎么就把他哄骗得这么乖顺?还是要学会糜面嘴,水也能让你说得点着灯。在外哄别人,在家哄丈夫。
白月月这才正经地说,那我就实话告诉你,政府办那个郭主任,其实是我家老头的朋友,他用一个民间偏方治好了郭主任母亲的病,郭主任也就时常联系了。我倒是盼着找一个当官的情人呢,可这命里也没有那样的福气。一场误会一下子又把余美焕推到尴尬的境地,她只能没话找话地问白月月,那天她出事后,下午还见没见到市长过来视察?以后承包车站门面房的事情给没给个准确的话?白月月这才坐下来说,把你个黑货腿都弄断了,大家谁还有那个心思再去上访?为此事郭主任还打电话埋怨呢,说是所有的工程都是建筑商承包,如果不把市上的领导逼急,恐怕连一间门面房都不会包给王禾人。
工地上还是大坑坑、土堆堆,事情也没有那么急。余美焕说。
你个黑货就傻到底了,城里人的事情怎么还不明白?比如咱们这片小区的楼房,刚刚画在图纸上,就要先拿出分配方案呢。现在那些开发商,个个都是空手套白狼,只要把工程搞到手,马上就张罗着卖房子了。再拖下去,黄瓜菜都凉了!
余美焕单腿一伸就准备下床,要不是白月月拦挡得快,说不定又会旧伤变新伤。白月月受惊地骂着说,你个黑货是想找死啊!那天把腿栽坏了,偏偏就一个劲地埋怨我。今天再栽在我面前,别人又会说我是杀人灭口吧?
余美焕说,少啰嗦,赶紧组织大家上访闹事呀!
白月月说,像你这样子还能进城去?
余美焕说,我让恩川用架子车拉着我,队伍前边拉着一个大伤号,谁看见都害怕呢!
白月月故意往出退着说,不敢不敢,我可不敢再拖你,我还怕唾沫星子把我淹死了呢。
余美焕自己却急切地拨通王恩川的手机喊,你个死鬼又在外边溜达啥呢?马上往回走,顺便再借一辆架子车。多余的话先别问,回来你就知道了!
吃过中午饭,王禾社区的院子里又聚集起越来越多的人群,今天的阵容格外强大,凡是能走得动路的人都加入了。可是最显眼的人无疑是余美焕,她没有让王恩川拉着她往前走,而是让他推着车辕往前行。她觉得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体现自己的带头人地位和号召力。
浩浩荡荡的队伍,跟随着余美焕的打头车,步入了通往城区的大道……
责编:柴燕